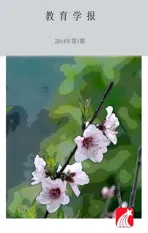文化的视角:美国课程史的转向及其意义
2014-04-17何珊云
何珊云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杭州 310028)
一、社会危机与美国课程史研究的形成
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1960年,美国联邦科学与教育机构、军方、科学家、卡耐基公司等联手推出布鲁纳(J. S. Bruner)研制的宣言《教育过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旨在提高美国科学水平的以学科知识结构为中心的课程改革。[1]课程研究由此陷入生存危机。此前30年,在美国,课程学者曾是“八年研究”、“生活适应”等著名教育改革运动的核心力量,但到20世纪60年代,课程学者的位置被学科专家、教育管理学者和教育心理学者取代了,课程研究的社会影响力瞬间锐减,甚至课程学者的学院处境也岌岌可危,因为选修课程研究的学生日益减少。总之,各方面的变化都表明,课程研究确实如施瓦布(J. Schwab)所言陷入了“垂死”状态,“已无法对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2]
为了拯救“垂死”的课程研究,课程学者纷纷开始理论革新。施瓦布提出课程学者应转向课程“实践”研究,致力于在“实践”一线建构各方民主参与的“课程共同体”(curriculum community)。[3]后来被课程理论界视为“概念重建之父”的麦克唐纳(J. Macdonald)则强调必须跳出“学科结构”,尽可能以“不同的想象力”来架构课程研究。[4]哥伦比亚大学课程与教学系更是组织两百多位课程学者,共同探讨如何寻找“具体的概念”,使处于“十字路口”的课程研究获得新生。结果阿普尔(M. Apple)的导师休伯纳(D. Huebner)提出的方案获得广泛认同,即通过采纳“意识形态、控制、权力”等“政治学概念”来革新课程研究。[5]
以上的这些努力使美国的课程研究焕发出蓬勃的理论新生。到20世纪70年代,局面更是大有改观。这一方面是因为学科结构运动陷入失败危机,另一方面更由于日益紧张、分裂的社会现实为课程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挑战与使命。为了回应社会危机带来的挑战,推动社会进步,课程研究迎来“概念重建”时代,学者们纷纷寻求不同的更贴合美国社会危机的理论工具。在六七十年代生机盎然的理论革新氛围中,课程学者除了到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寻找新理论外,还形成了强烈的历史视野,并因此促成了课程史研究。
古德莱德(J. Goodlad)、巴拉克(A. Bellack)作为资深课程学者,可谓是课程史研究最著名的提倡者。他们分别于1966年、1969年发表文章,提醒课程学者必须重视课程思想史和实践史,以防重犯过去的理论与实践错误。[6]进入20世纪70年代,巴拉克的弟子克利伯德,以及坦纳(D. Tanner)、哈兹雷特(J. S. Hazlett)、富兰克林(B. M. Franklin)等人成为开创课程史研究的主力。这些课程学者不仅于1977年成立了课程史研究协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urriculum History),而且以一系列的论文与著作,彰显了一种获得广泛认同,旨在应对现实社会危机、寻求社会进步的美国课程史研究范式。[7]
从克利伯德完成的首部美国课程史专著《美国课程斗争,1893—1958》(The Struggle for American Curriculum,1893—1958)来看,和阿普尔的课程政治学一样,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美国课程史研究也是为了证明,课程决不是简单的课程开发或评价问题,也不仅仅是“学科结构”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只不过,与阿普尔依靠政治学概念分析美国课程背后的紧张政治社会关系不同,克利伯德等人的课程史研究则是从课程理论史和学校改革史等角度,揭示复杂的“利益团体”(interest groups)及其“斗争”关系在美国课程演变中的表现与影响。[8]而他们为克服社会危机所开出的“药方”则是在课程实践领域恢复杜威进步主义教育传统的主导影响力。[9]
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美国课程史研究明显受到了当时史学领域的“社会”转向的影响。无论是史学界的社会史研究,还是社会学取向的课程史研究,都是为了回应美国社会现实危机。然而,课程学者没有考察也无法预料的事实是:自70年代,美国经济政治体系自身也一直在寻求新生,到80年代,便重新恢复稳定,整个社会尤其是最具社会变革精神的年轻一代逐渐接受了高科技、互联网、新自由主义等新力量布置的发展轨道。在此主流政治经济势力逐渐控制社会及教育运行秩序的变革进程中,课程史研究无疑需要适时调整理论视角,从而革新、深化当初的课程社会史传统。
二、文化转向与美国课程文化史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依靠在高科技、互联网、金融、服务产业等领域积累的优势,美国不仅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而且制造了令人无比向往的“新经济神话”。而以里根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家也通过提出保护自由市场、推崇个人创新等顺应时代潮流的“新自由主义”施政方针,成功赢得了入主白宫所必须的多数民意。与此经济政治变动相对应,美国社会主流也不再看好结构性的社会批判或革命,而更愿意将美国社会及个人希望寄托于成为具有“创新能力”的个体,进入“新经济神话”制造的成功世界。
阿普尔、吉鲁(H. Giroux)等政治社会批判取向的课程学者都曾因为不能赢得主流社会认可遭遇“严重创伤”:著作被大学当局认为是“狗屎”,不得不流离失所,[10]甚至“被禁止发言”。[11]相比之下,美国联邦政府为巩固美国新经济地位及创新能力,推出的“课程质量标准化改革”计划则轻松地赢得了社会主流的广泛支持,从而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20世纪80年代仍健在的课程理论泰斗泰勒(R. W. Tyler)则因为大力发展更科学的学习评价机制,继续在联邦课程改革中保持其“课程评价之父”的权威地位与影响。这些情况表明,课程理论革新运动在经历70年代的繁荣之后,又一次站在了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
面对美国联邦政府及主流社会发起的质量标准化课程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日益逼仄的课程理论发展空间,阿普尔、吉鲁等人仍坚持自己的批判立场,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经济政治新变化并不能掩盖这一真相:即20世纪70年代的紧张社会关系仍是教育领域及整个社会的基本事实。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引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视野,使社会制度层面的教育紧张关系,深入到了文化或教师、学生的日常生活体验及文化表达层面。[12]那么,课程史研究又将如何优化以往的课程社会史呢?就此而言,首先需要注意,80年代以来,不光课程史研究需要适时更新,整个美国史学界都在探索如何突破此前作为史学主流的社会史研究。而正是史学界的革新探索为课程文化史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激励。
就史学研究视角而言,美国史学界的革新动向大体可以概括为从“社会”转向“文化”。1989 年,新一代历史学家林·亨特(L. Hunt)领衔推出《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该书首次提出,可以将史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走向界定为“社会理论的衰退”和“新文化史的崛起”。[13]“文化”转向由此在原本受“社会理论”支配的史学界占据一席之地。2002年林·亨特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则清楚宣告,“文化”取代“社会”成为史学界的最新主流视角,已是广为认可的事实。
从理论范式来看,林·亨特等人推崇英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因其致力于理解“工人阶级”如何根据自身的日常生活与道德经验创造自己认可的“文化”,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史学家夏蒂埃(R. Chartier)贡献的文化史分析路径:即不再把各类社会群体(微观历史主体)看作是宏大政治经济结构的被动受众,而是考察各类微观历史主体如何通过自己的“话语”(discourse)活动或“文化表达”(cultural representation)实践,建构自己的社会行动、日常生活和意义。夏蒂埃的文化史研究明显受到法国后现代思想大师福柯(M. Foucault)的启发,所以林·亨特等人也十分推崇福柯的理论范式,因为正是福柯率先在认识论上打破文化(话语)与政治经济的两分模式,以及文化之于政治经济的从属地位,并依靠《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著作,充分论证了文化本身就是权力实践或其他社会实践的直接表达。
林·亨特20世纪80年代末在史学界发起的“文化”转向及其推崇的文化理论为美国课程史研究实现新生提供了启示,90年代的美国课程史研究也因为与林·亨特等人的“新文化史”展开互动,出现了相似的“文化转向”理论革新运动。不仅如此,90年代的美国课程史研究还高度认可“新文化史”之所以从“社会”转向“文化”的现实考虑。和林·亨特及其推崇的福柯一样,美国课程文化史发起者也拒绝承认,所有人都只需生活在8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主流势力建成的“新世界”,他们认为,即使60年代以来的社会危机以及由此危机造成的激烈社会变革运动在新时期已经基本消失或不再那么明显了,也不能证明这个“新世界”就是“历史的终点”,毋宁说它是一个机械单调、意义贫乏的霸权文化结构,并且已经给非主流社会、女性群体、地方社会以及非西方世界等等施加了许多文化扭曲与压抑。
可以说,正是为了应对新时期美国主流文化结构造成的文化矛盾与紧张,寻求更有意义的文化实践与生活方式,美国课程史研究所以才像“新文化史”那样转向“文化”,并致力于发展课程文化史。在这一理论革新进程中,首先要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史学家科亨(S. Cohen)的不懈努力。作为20世纪60年代末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和教育史学双料博士,科亨不仅继承了其导师、美国教育史权威克雷明的进步主义追求,而且一直在探索如何根据现实变动革新美国教育史与课程史研究。林·亨特一发起“新文化史”运动,科亨便给予热情关注。1994年,海登·怀特(H. White)提出“后现代叙事史学”,将“文学”引入“新文化史”时,科亨自己的课程文化史研究也大致勾勒成形。
1996年,科亨发表《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电影:教育反抗影像》(Postmodernism,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Film: Resisting Images of Education)。[14]其中显示,尽管科亨没有刻意将自己的研究定义为课程文化史,他更愿意称自己是在做“新文化史”研究,但他不仅是在研究“学校教学”这一美国课程史的经典主题,而且采取了林·亨特、海登·怀特的文化史研究方法,也就是将电影文学作品《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作为“核心史料”,分析20世纪80年代的导演及主角教师如何认识、颠覆令人窒息的学校教学结构。这便是科亨最初贡献的课程文化史范式,它通过引入文学、电影等叙事文本,尝试对主流社会的学校教学及其文化结构展开后现代风格的研究与批评,为学校教学结构中被压抑的情感与美好体验寻求表达途径。
1999年,科亨推出专著《挑战正统:迈向新教育文化史》(Challenging Orthodoxies: Toward A New Cultural History of Education)。此书不仅继续强调电影可以作为考察美国教学变革的新史料,而且阐述了福柯、海登·怀特、格尔兹(C. Geertz)等人的文学评论、话语分析和文化人类学对于重新理解美国学校教学实践的文化(话语)结构及其历史变迁的重要意义,[15]堪称全面总结了科亨本人为美国课程文化史研究贡献的理论主题与分析工具。21世纪以来,为回应外界诸多批评——指责他将“记忆”、“叙事”、电影等大量非“档案”记录的文化文本视为可靠的历史文本,年迈的科亨又发表了《天真的目光》《历史、记忆与共同体》等文章,[16]继续传播他的文化史理论。
如果说科亨代表了史学及教育史学界的课程文化史建构努力,那么课程理论界最引人注目的课程文化史开拓者则当属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课程与教学系的波普克维茨(T. Popkewitz)。2001年,波普克维茨联合富兰克林、佩雷拉(M. Pereyra)等15位课程学者推出《文化史与教育:知识与教学的批判性论文集》,20世纪90年代以来课程理论界零散的文化史实验因此得以汇集成理论格调一致的学术运动。和科亨的课程文化史一样,此次运动也主张引入照片(photographs)一类的非文字材料,因为它们同样能反映某一主体的课程实践,即“如何理解和建构(课程)现实”。[17]当然,就理论革新而言,课程理论界的这场课程文化史运动最值得关注的贡献还不是新材料使用,而是引入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即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并因此成功推出了福柯式(Foucaultian)的课程文化史研究。
作为这场运动的理论领袖,波普克维茨无疑发挥了榜样作用。1998年,波氏便通过专著《为灵魂而战》(Struggling for the Soul)为课程文化史研究贡献了相当成熟的福柯式的理论范式,即分析“教育知识作为权力”(knowledge of pedagogy as power),会使教师对“儿童”做出怎样的“区分”与“建构”,又会对现实中的儿童造成何种“歧视”。[18]《文化史与教育》延续了福柯式的追问,并将它扩展到更多的课程与教学微观领域。[19]2007年,波氏又完成一部福柯式的课程文化史专著,深入分析了过去一百年美国各类教育改革主体如何依靠启蒙时期的所谓“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建立并不断完善一套可以抹平一切历史文化差异的“合理推论体系”(system of reasoning),来界定何为“需要拯救的危机重重的社会(society at risk)”,何为“需要拯救的落后学生(backward student)”,从而可以不断发起学校改革,并增强对于学校教育的“治理权”(governmentality)。[20]近两年,年逾七旬的波氏仍在继续揭示在学校教育中发挥“权力”作用的知识或文化,并将视野扩大到19世纪以来整个西方教育。[21]可以说,正是由于波氏及科亨等人的持续开拓,课程文化史不仅得以兴起,而且定调于对左右美国学校教育的文化结构,展开福柯式的历史揭示。
三、作为“文化批评”的课程理论的意义分析
关于科亨、波普克维茨等人在课程研究的文化转向上的努力有何意义,在这一点上,美国课程及教育学界已有许多学者做过立场不同的分析。反对观点主要来自支持美国联邦政府的主流学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有趣的是,反对观点并未产生遏制效果,反而额外加速了课程文化史的传播。如一位年轻学者所言,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课程文化史能够赢得听众,听众很容易被其文化叙事与分析吸引,乃至像顿悟一般突然明白为什么自己只能接受机械乏味的学校教育。这位学者还对“西方三大教育史期刊”即美国的《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英国的《教育史》(History of Education)和加拿大的《教育史学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in Education),专门做了一次研究。他这样做,就是为了看看福柯式的文化史分析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 结果发现,从1999年到2008年,三大期刊一共刊发专题论文563篇,有29篇都是研究福柯式的主题,如不同时空的学校知识权力如何“规训”学生的“身体”,学生的言行举止被什么样的“观察文化”(visuality)加以检视与评估等等。言外之意,过去十年,超过5%的重要论文作者都在从事福柯式的课程文化史。[22]
这一量化研究也表明,科亨、波普克维茨等人推动的文化史赢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可,也因此近些年又衍生出许多更微观的课程文化史研究。然而这一切究竟有何意义呢?何况课程文化史的影响即使再大,也可能如反对者所言,并不能变成任何具体的教育改革政策。在几乎不可能对学校教育产生实质改革影响的情况下,科亨、波普克维茨等人及新一代追随者何苦从事课程文化史研究呢?
有学者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切课程研究革新都是为了摆脱一个沉重的“历史负担”,即传统课程理论“没有学术努力”(without scholarly engagement),一味以“实践”、“设计”代替“学术”。[23]这一分析框架的确适合用来理解课程文化史的意义,因为课程文化史不仅提高了课程研究的学术品质,而且可以赢得教育史乃至新史学界的学术认可。但仅聚焦于“学术”追求,还不足以解释美国课程文化史的意义,而是需要采取“长镜头”的考察视野,置身美国课程文化史所属的“历史语境”,才可以更透彻地看出其意义。
置身这一“历史语境”后,首先会看到,课程学者原本可以大显其“实践”身手的美国公立学校体系早已换了新主人,即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学区,以及各种“专业”的学科标准、学习心理与课程评价专家,其中并不需要课程文化史学者或其他任何课程理论革新者的“学术”创造。在学校实践空间丧失的情况下,课程学者如果不转变成联邦政府欢迎的“专家”,而是继续以理论自由的学术性课程研究追求教育与社会进步,就得重构自己的实践观。
正是在这一点上,福柯提供了启示。福柯认为,“理论并非外在于实践,或只是在表达、服务实践,它本身就是实践。”[24]波普克维茨及其他文化史学者吸收了福柯的实践观,并因此将课程理论直接视为实践。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作为理论活动的课程文化史能够成为什么样的实践。这需要考察“历史语境”中的第二大动向,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本土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除之前提到的“新文化史”外,对课程文化史影响甚大的莫过于美国人类学。事实上,就“市场”或实践空间而言,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的处境比课程研究或教育学还要糟糕。但在格尔兹、萨林斯等人的开拓下,几近沉沦的美国人类学还是成功实现了转型,这便是通过对“异文化”展开“深度描述”,藉此对美国本土及西方“文化”展开批评,使人类学重新成为美国社会文化领域活跃的进步力量之一。
马尔库斯曾以“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que)来界定美国人类学的转型秘诀。[25]这一概念同样适合用来概括美国课程文化史贡献的实践模式,课程文化史甚至和美国新人类学一样,都属于新时期美国学术界“文化批评”运动的分支。只不过,课程文化史的“文化批评”实践集中指向在美国基础教育领域中起支配作用的知识或文化,还未做到像人类学那样为美国社会提供精彩的“异文化”文本与价值观教育。虽然有此不足,但却不能否定课程文化史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推进了美国课程研究的学术化进程,而且以福柯式的教育文化史研究证明,课程理论也可以成为有意义的“文化批评”实践,因此能为学校实践空间日益萎缩的美国课程学者到更广域的文化社会领域开辟新的实践方式与空间,提供有益参照。
参考文献:
[1] Tanner, D. et a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2nd Edition[M]. New York: Macmillan, 1980: 523.
[2] Schwab, J. The Practical: A Language for Curriculum[M]. Washingto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70: 1.
[3] Helebowitsh, P.S. Generational Ideas in Curriculum: A Historical Triangulation[M]. Curriculum Inquiry, 2005, 35(2):76.
[4] Macdonald, J. et al. Strategies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M]. Columbus: Charles E. Merrill, 1965: 70.
[5] Huebner, D. Politics and Curriculum, in A. Passow. ed. Curriculum Crossroad[M].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Press. 1962: 95.
[6] Bellack, A.A. History of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ractice[M].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69, 39 (3): 283-292.
[7] Hazlett, J.S. Conceptions of Curriculum History[J]. Curriculum Inquiry, 1979, 9(2): 129-135.
[8] Kliebard, H.M. The Struggle for American Curriculum, 1893—1958[M]. New York:Routledge,1987: xii-xiii.
[9] Labaree, Does the Subject Matter? Dewey, Democracy and the History of Curriculum[J].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31(4): 513-521.
[10] Torres, C. A. Education, Power, and Personal Biography[M].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31.
[11] Apple, M.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viii.
[12] Giroux, H. Between Boarders: Pedagogies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tudie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29.
[13] Hunt, L. ed. New Cultural Histor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10.
[14] Cohen, S. Postmodernism,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Film: Resisting Images of Education[J]. Paedagogica Histo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1996, 32(2): 395-420.
[15] Cohen, S. Challenging Orthodoxies: Toward a New Cultural History of Education[M]. New York: Peter Lang.1999.
[16] Cohen, S. An Innocent Eye: The "Pictorial Turn," Film Studies, and History[J].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2003, 43(2): 250-261. History, Memory, Community, in Historical Studies in Education, 2004, 16(2): 353-361.
[17] Popkewitz, T.S. et al. eds. Cultural History and Education: 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Schooling[M].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2001: 75.
[18] Popkewitz, T. S. Struggling for the Soul: The Politics of School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er[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8: 18.
[19] Popkewitz, T.S. et al. eds. Cultural History and Education: 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Schooling[M].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2001: 125-150.
[20] Popkewitz, T.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Age of School Reform[M].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21] Tröhler, D., Popkewitz, T., Labaree D. eds. Schooling and the Making of Citizens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Comparative Vision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22] Coloma, R.S. Who’s Afraid of Foucault?[J].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2011, 51(2):184-210.
[23] Hlebowitsh, P. The Burdens of the New Curricularist[J]. Curriculum Inquiry, 1999,29(3): 343-354.
[24] Bouchard, D.F. ed.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of Michel Foucault[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208.
[25] Marcus, G. E. et al. eds.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