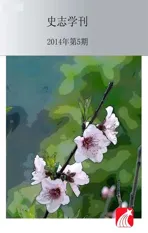《列女传》对息妫形象的重构
2014-04-11王利明
王利明
《列女传》对息妫形象的重构
王利明
息妫在《左传》中是最早以明确的语言表述贞节观的女性,她美丽知礼,对感情执著、自尊自强不肯苟且,她的贞节意识是出于对自我情感的维护和尊重。而在《列女传》中,刘向夸大了息妫的贞节观,息妫成了“终不以身更贰醮”并以身殉夫的贞妇。
《列女传》 息妫 重构
《列女传》是西汉刘向编撰的一部妇女专史,文中载录了从上古尧舜至秦汉时期一百余位古代女性的言行事迹,刘向将这些女性分为七个类型,即“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每类一卷,共七卷。息妫是《列女传》中“贞顺”篇中描述的女子,她貌美、忠义、贞节、对爱情至死不渝。息妫较早出现在《左传》《吕氏春秋》《史记》中,《左传》中息妫美丽知礼,对感情执著,是首次提出贞节观的女性。通过比较发现,《列女传》对息妫形象进行了重构,本文意从《左传》《列女传》息妫形象入手,探讨刘向重构息妫形象的原因。
一
息妫,妫姓,陈国国君陈宣公之女。息妫在《左传》中共出场三次,分别为:
(庄公十年)“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1](P184)
(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1](P198)
(庄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文王)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古时寡妇自称)之侧,不亦异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妇人不忘袭,我反忘之!’”[1](P241)
《左传》作为一部传《春秋》的史书,作者并不刻意去刻画女性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往往是由于叙述某个人或某个事件而涉及牵连到的,是由于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中对这些女性人物的不可回避[2]。因此,息妫在《左传》中的形象是客观的,真实的。《左传》中的息妫是绝美的,她的美受到了他人的窥觊,蔡候“止而见之”,“杜注:不礼敬也。据十四年《传》,息妫甚美,则此所谓弗宾,盖有轻佻之行。”[1](P184)美貌没错,但因美而给自己带来了亡国破家的命运,是让人可叹的。春秋时期,男尊女卑,“女子无婚姻自主权,出嫁由父兄做主,再嫁则由父兄或夫家的宗子做主。”[3](P97)亡国后的息妫被迫嫁于楚文王,昔日王侯女、国君妇,且与息君伉俪情深,今日成为仇人的妻子,心头郁闷,而又无法将心中的怨恨发泄,只能沉默以对。“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言”是息妫对抗命运的一种方法,是悲苦异常的息妫在长时的寂默中对故国的眷恋,和对前夫息侯的深切怀念。而“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则是对不能自主婚姻不满的强烈呐喊,是捍卫尊严的方式。面对强权,一个小女子虽不甘,亦只能靠“未言”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以“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的愤慨来捍卫自己的情感。如果说上面所述,展示在人前的息妫形象是美丽、隐忍的、对强加的婚姻不满的、渴望贞节的。那么在婚姻无法改变,准备捍卫自己的这段不得不要的婚姻时,息妫是坚决的、毫不迟疑的。当受到尹子元的骚扰诱惑时,严叱道:“先君(文王)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古时寡妇自称)之侧,不亦异乎!”“未亡人”,朱熹释为“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则当与之同生,与之同死。故夫死曰未亡人,亦言待死而已,不当复有他适之志”[4](P34)。“春秋时期,社会流行的是与贞节观迥然对立的观念——‘人尽夫’”[3](P108),这样的环境,寡妇自己要求守贞很罕见,息妫以“未亡人”自居,说明她是要“从一而终”的,其贞节观凸显。“未亡人”的坚守,是春秋时期女性贞节观的萌芽,是“女性对爱情的执著,对那种缺乏尊重女性情感及意识的社会和不能主宰自己命运而被随意嫁娶的现实的不满和反抗。”[3](P112)
二
《列女传》[5]中,息妫被列入“贞顺”篇,其传曰:息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虏其君,使守门。将妻其夫人,而纳之于宫。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见息君,谓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以身更贰醮。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哉。”乃作诗曰:“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曒日。”息君止之,夫人不听,遂自杀。息君亦自杀,同日俱死。楚王贤其夫人守节有义,乃以诸侯之礼合而葬之。君子谓夫人说于行善,故叙之于诗。夫义动君子,利动小人。息君夫人不为利动矣。诗云:“德音莫违,及尔同死。”此之谓也。
在刘向笔下,息妫是烈节贞妇的典范。为了塑造这一形象,《列女传》通过忽略息妫改嫁的事实突出“终不以身更贰醮”的思想,设计息妫息君“同日俱死”的情节塑造“守节有义”的贞妇形象。
《列女传》中,列入“贞顺”篇的女子必须符合“避嫌远别,为必可信,终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洁行,精专谨慎”[5]。这样的标准。“贞顺”是已婚女子必须遵守的事夫重要准则。息妫在《左传》中,“将归,过蔡”时,蔡侯“止而见之”,明显不能“避嫌远别”,尽管是逼迫的被动的。其后,嫁于楚文王,并生二子,虽“未言”,可行为上总是背叛了昔日的夫君,不能遵守“为必可信”的信条。加之再嫁,不能符合“终不更二”的标准。刘向为了让息妫符合“贞顺”的标准,有意忽略了息妫初嫁息君时,曾遭蔡侯的骚扰,也忽略了因息妫,蔡侯遭灭、息国被亡的史实,只是提取息妫被楚文王纳入宫的事,简单言之“将妻其夫人,而纳之于宫”,忽略息妫是再嫁的,然后通过息妫的语言来强调“终不以身更贰醮”的思想。“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生动地再现了一名为了尊严不畏死的女子形象,也间接为下面的故事做了铺垫。“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以身更贰醮。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哉!”如果说第一句意在表达自己为了尊严不畏生死的思想,那么这句就是息妫不忘旧情,不愿“事二夫”,宁愿生死同穴。为表心迹,作诗为证“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曒日”。诗中强烈地表达了一个女子对一个男子忠贞不渝的爱情。为突出息妫的“贞烈”,刘向安排了息妫息君“同日俱死”的故事情节。在刘向笔下,息妫是“贤其夫人守节有义”之人,是值得尊敬的,故“以诸侯之礼合而葬之”。并借君子口,称赞息君夫人的贞节观。无疑,《列女传》中的息妫是贞节观强烈的女子,是从内心里维护“从一而终”的,是严守贞顺标准的贞烈女子。这一形象的塑造,完全颠覆了《左传》中给人们展现的那位美丽、隐忍、对婚姻不能自主的现状不满的女性形象。
三
从《左传》到《列女传》,息妫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刘向为何要把息妫编入《列女传》中的“贞顺”篇?联系刘向编撰《列女传》目的,不难探其原因。
刘向是西汉皇族后裔,是宣、元、成三朝的老臣,其时,西汉皇朝正由盛转衰,当时宦官、外戚交替专权,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刘向亲眼目睹西汉后期后妃逾礼、外戚专权的社会现状,就利用领校皇朝中室秘籍和民间收藏的图书已达十年之久的有利时机,依靠丰富的古籍资料,特意编撰《列女传》。《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向睹欲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使。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6]可见,刘向编撰《列女传》,本不是为了作史来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而是“以诫天子”,树立符合儒家理念的女性道德榜样,以此教化百姓,提倡妇女守节,提出一套合乎儒家伦理道德的妇女规范,实现君权的最高威严。正如《汉代婚姻形态》一书所言:“(刘向)试图用封建道德观念和等级意识的集中体现‘礼’,来更严格、更广泛、更深入地规范婚姻关系,以达到‘布教化’‘正世风’的目的。”[7]“为了说明妇德贤否与国家兴亡紧密相关的道理,作者必然会对这些人物形象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一定的加工塑造,甚至一定程度的虚构,以增强说服力,达到劝诫的目的。”[2]息妫选入“贞顺”篇,主要是息妫曾说过“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的话,而话中流露出了一定的贞节意识,这种意识,正是刘向需要倡导妇女德规之一。为了强化这种“贞节观”,在故事情节上设计了与息君同日而死的结局,并设计了楚文王感其“贤”,给予息妫与息君同葬的殊荣。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4,198,241.
[2]曾瑾,王芳.从《左传》到《列女传》中女性形象的变化[J].新余高专学报,2008,(6).
[3]陈筱芳.春秋婚姻礼俗与社会伦理[M].成都:巴蜀书社,2000.97,108,112.
[4](宋)朱熹注,王华宝校点.诗集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1989.34.
[5]刘向.列女传[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彭卫.汉代婚姻形态[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王利明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助理研究员
(责编 樊 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