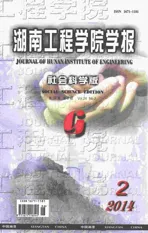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初论——以审判案例指导为参照
2014-04-09黄涧秋
黄涧秋
(苏州市政府 法制办公室,江苏 苏州215004)
自从2011年起开始正式推行案例指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分批公布了五批共22个指导性案例,其对审判业务的实际影响不容小觑,无论在司法实务界还是在学界均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热评。与行政诉讼相类似,行政复议也是一种针对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其基本活动同样是适用法律于案件事实并最终得出处理结论的逻辑过程。那么,为了更好地促进行政复议制度功能的发挥,我国是否需要建立与司法系统相似的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在行政复议法面临修改之际,对于这一论题,国内学界还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拟以建立指导制度的依据为起点,揭示其必要性,并初步勾勒出该制度框架的雏形。
一 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的依据
由于行政复议案例指导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尚付阙如,正在成长中的审判案例指导制度可以为它提供一个制度性参照和分析框架。当然,在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行政复议案例指导进行理论建构和制度设计,不能脱离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机关内部运作系统的监督救济制度这一本质属性。
首先,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什么是审判案例指导制度。审判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指导纲要》中指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方面的作用。”二是201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廓清了此前各地实践中对于指导性案例界定的诸多争议,将指导性案例的范围限于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统一发布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例,其外延涵盖社会广泛关注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等五种类型。在此前提下,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表现为: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如果简单地移植《规定》确立的指导制度,我们可以把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初步界定为:由一定级别的行政复议机关或行政复议机构从各地各部门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中按照一定标准遴选产生的典型性案例,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该种案例。申言之,行政复议指导性案例来源于各个行政复议机关已经作出并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该行政复议决定所涵摄的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指导意义,该指导性案例经过正式程序发布并生效以后,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参照该案例的处理要点和精神进行行政复议受理和审理活动,以保证同案同处、异案异处。指导性案例效力的根源正是基于案例发布机关对于作为其下级的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活动上的指导、监督性权力。一般来说,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机关应当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上级复议机关对于下级复议机关的指导、监督性权力在《行政复议法》中主要体现在第20条和第28条,即行政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由上级行政机关责令其受理,或者直接受理。行政复议机构发现有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或者不按照期限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应当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建议。为强化上级复议机关的指导监督作用,2007年《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专设“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一章,其第54条对于上级复议机关的指导监督作用作出了概括性规定:“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监督”,但是,该条例对于上级政府工作部门对下级工作部门的监督却没有规定,个中缘由不得而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条例第59条还建立了下级复议机关重大行政复议决定的报备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质是上级复议机关对于下级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活动中的个案事后监督。
上级复议机关对下级复议机关的指导监督是一种单向的、不对等的监督行政关系。在《行政复议法》实施以后,各地实践中涌现出林林总总的指导监督方式,例如业务培训、工作评查、复议稽查、文书评比、不予受理审查、复议决定的备案、重大决定的再审查、典型案例研讨会等制度和做法。[1]在个案指导方面,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和各省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定期出版《行政复议典型案例选编》等书籍。国务院法制办行政复议司编写的《行政复议典型案例选编》中将该书的编写目的定位为:“总结行政复议工作经验,加强对全国行政复议工作的指导,促进行政复议工作规范化建设,提高行政复议人员的办案能力和水平。”相比较各地已有的实践做法而言,拟议中的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依据同样来自于《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所确立的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制度。但是,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特点:第一是制度化;第二是较强的拘束力;第三是事前指导性;第四是功能的普适性。在现行行政复议法律所确立的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制度体系中,行政复议案例指导是最为刚性、最强有力的一种制度。
在制度依据上,行政复议案例指导与《规定》确定的指导制度存在两点区别:第一,司法系统的案例指导制度在组织法上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级监督上的依据,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并无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在组织法上的依据来自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各级地方政府都服从于国务院,各级地方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的工作,各级政府工作部门受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领导。第二,司法系统案例指导制度功能发挥的后盾在于上级人民法院的改判权,借鉴指导性案例,可以降低上级法院撤销、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可能性;[2]除了责令受理以外,由于我国没有二级行政复议的一般制度,行政复议案件的改判权在上下级行政复议机关之间并不存在。从这一点看,行政复议案例指导的效力更需要专门的法律制度给其武装上“牙齿”。
二 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
初步看来,行政复议案例指导的法律依据在于上级复议机关对下级复议机关的指导监督职权,通过自上而下的案件受理审理协调机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案件办理尺度,保证各级复议机关准确适用法律,提高行政复议办案质量,最终提升行政复议制度的公信力。这些无疑都是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来说,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功能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避免同案不同处,实现法制统一
毋庸讳言,同案不同处现象在我国各地的行政复议实践中大量地存在,既侵蚀了行政复议制度本身的公信力,又破坏了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对于行为后果的合理预期。行政复议中同案不同处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一般性原因,如法律规则的原则性和模糊性、行政复议人员认知能力的局限;也有特殊性原因,例如行政复议案件条块管辖的双轨制。而后者更为严重地导致行政复议案件法律适用的“碎片化”。虽然按照既判力原理,同一案件不能同时在两个复议机关先后受理或者同时受理,但是假设同一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被不同的相对人分别在该行政机关的同级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这两种复议机关均没有理由以对方已经受理甚至已经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而拒绝受理或者予以终止。更进一步,设若这两种复议机关分别作出截然相反的决定,那么,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机关将何去何从?当然,这种双轨制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行政复议管辖体制的彻底修正。在当下的情况下,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弭这一固有弊端。
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在其指导性案例覆盖的范围内实现“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消除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对于相同或类似案件事实的裁断的不一致性。案例指导制度与业已确立的司法解释制度均为立法上承认的规范制度,它们都以形式正义的进路推动指导性规则普遍化的进程。[3]行政复议案例指导的机理也然,同案同处的内在机理是一种从个别到个别的类比思维,通过待处理的案件事实与指导性案例一一比对,最终确定是否按照指导性案例的要点作出相同的判断。通过这样的运作机理,可以保证同样的案件事实或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在不同的复议机关都能得到相同的评价。
(二)廓清法律解释,弥补法律漏洞
成文法的局限性在行政法律规范中也大量存在,此不赘述。例如,《行政许可法》第15条和第16条分别规定了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对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和规定权,该两条条文表面上看起来明明白白,但是在实际适用中又是变数百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年发布的第5号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要点指出:地方政府规章只能在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不能设定新的行政许可。由此可以反推,在《行政许可法》通过后的八年内,关于其行政许可设定权与规定权相互关系的理解始终是众说纷纭,难定一尊。同样地,由于我国缺乏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相互冲突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正好可以担当起廓清法律解释、弥补法律漏洞的时代重任。
必须注意到,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不是行政机关造法,而是一种法律解释的过程。行政复议程序中也应当遵循“不得拒绝裁判”的原理,指导性案例在法律无明确规定或者法律规则存在滞后性等情况下,根据立法精神和法律原则,对成文法的漏洞进行必要的补充,为类似案件的解决提供参照。不仅如此,指导性案例还能为复议工作提供法律观点、审理技巧、法律论证方面的指引,提升行政复议人员的办案水平。[4]行政复议指导性案例以生动的法律解释来弥补立法的抽象性缺陷,沟通立法意图与行政机关执法之间的乖离,最终推动行政法律规范的自我更新。
(三)限缩行政自由裁量,规范行政权力
行政机关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自由选择行为方式、程序和时间,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行为中大量存在,是行政权力运行的常态。同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运用又可能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行政裁量权的控制成为各国行政法上的共识。虽然,各级行政机关主管部门大都在行政处罚领域制定了本系统的裁量基准,但是,行政违法行为的实际情况纷繁复杂,很难用一个最恰当的、一以贯之的基准来对处罚幅度进行划分。
相对于行政诉讼来讲,行政复议不仅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还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对于不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机关可以进行变更。行政案例指导制度有助于监督行政权的行使,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相比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其他控制手段(例如立法控制和行政机关的自我设定的裁量基准),司法审查是一种外在的、个案的控制,由于其地位的中立和裁判的技术经验丰富,确实是较优的行政裁量治理方式。[5]行政复议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也然。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通过对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的约束,间接地约束了作为被申请人的各级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或者说通过指导性案例为各级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提供统一尺度或者合理性标准。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不仅仅是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的一种外在约束,它同时也有利于消除行政执法人员对于法律适用的茫然和提高行政效能。毋庸讳言,实践中许多行政执法人员在面临新型、疑难案件时常常会因为法律认识水平的拘囿而感到无所适从,如果行政执法案件因为行政执法人员非故意性违法而被频繁地撤销或者确认违法,这种动辄得咎的客观现实反而会导致行政执法人员遇到疑难案件时索性予以回避,结果造成了大量的行政不作为现象。行政复议指导性案例对于成千上万的同类执法案件具有“速记”的功能,对于行政执法人员来说,案例指导是一种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进路。藉此,其“同案同处”的制度功能可以为行政执法人员处理同类执法案件提供快速通道,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行政判例通过行政法不成文法源所蕴含的原则和规则,应对行政裁量的日益扩展的挑战。在美国,发挥先例的指导作用是防止专横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种措施。[6]不仅如此,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程序中也有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例如,按照《行政复议法》,对于是否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属于复议机关的酌定范围。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行政机关在可能做出对他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时,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这同样适用于行政复议活动。该《公报》案例的刊登,它非常典型地限缩了行政复议机关的裁量权,是对法律规则的补充和深化,受到了学界的广泛推崇。自此,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在类似案件上都会非常谨慎地处理听取第三人意见的问题。
三 行政复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
指导性案例的法律效力是其运作的核心,也即一旦某行政复议案例被有权机关确定为指导性案例,该指导性案例的处理结论或者处理要点是否对各级复议机关具有拘束力。
《规定》第7条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本条规定的关键词是“类似案例”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指出,指导性案例不具有造法的效力,只是一种法律解释的形式。从《行政诉讼法》第53条关于“参照政府规章”的规范体系来看,“参照”不等于“适用”,政府规章不是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依据。因此,从“参照”本身的文义来判断,可以肯定的是,指导性案例不具有法律适用意义上的拘束力。
我国学者湛中乐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参照考察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他认为,目前指导性案例是否可以等同于司法解释的效力是不确定的,其效力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实证研究。[7]指导性案例具有事实上拘束力的表现主要在于:如果各级法院不按照它进行裁决的话,那么其将面临着在嗣后的上诉和再审程序中被上级法院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可能。如果在审判中不按照《规定》参照类似的指导性案例,该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但是,这种事实上拘束力之说似乎不能清晰地表明《规定》专门赋予指导性案例的特别意义。上面所述的改判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当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现实考虑,或者说是一种激励、倒逼机制层面上的拘束力,各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仍然有可能基于本身的内心确信而拒绝参照指导性案例。再退一步讲,如果说指导性案例的事实上拘束力仅仅停留在激励、倒逼机制层面的话,那么除了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事实上也具有相同的实际影响。再从《规定》制定的本意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案例指导制度应当是对各级法院审判工作的一种事前控制,鉴此,用事实上拘束力来定位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的进路似乎与《规定》本身的宗旨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瑞士、西班牙和我国台湾地区设有行政复议再审的规定,我国学者建议予以吸收,以协调法的安定性与具体正义之间的矛盾。[8]但是,在现行行政复议法律上,行政复议不存在类似法院二审、再审程序的二级复议,因此,上述审判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激励、倒逼机制不能在行政复议层级监督中发挥作用。考虑到快速解决行政争议的需要,拟议中的行政复议法修正案也没有纳入行政复议再审制度。因此,从行政复议层级监督的制度架构来说,我们不可能依赖指导性案例事实上的拘束力来对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受理、审理活动进行约束。正是因为如此,行政复议案例指导的效力需要采取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规定》不同的路径,易言之,案例指导的效力问题以及其他规则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正式确立。对此,有学者建议,通过行政复议法的修改,由新法律授权相应的机构创制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和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例,并对案例创制程序、形式和内容进行规范。[9]目前,国务院法制办正在就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征求意见,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应当充分利用此次修法的契机,适当地嵌入于行政复议制度的整体重构的框架之内。
在将来通过修法确立的案例指导制度中,指导性案例效力问题的条文设计可以模仿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国务院法制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在受理、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该“参照”运行的机理是:在待处理复议案件的案件事实、争议焦点、法律关系等方面是否与指导性案例相互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该不一致部分是否足以推翻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效果,如果不足以推翻,就必须遵照指导性案例的处理尺度和处理标准。如果行政复议机关在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时而未参照的,应当说明例外性理由。
案例指导制度确立以后,正式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为各级复议机关和复议人员在政府系统内部管理的层面施加了强制性的注意义务,各级复议机关和复议人员予以遵循应当是工作常态。那么,如果行政复议机关在案件处理中违反案例指导制度,它们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反过来看,案例指导制度的监督部门(例如国务院法制办)或者上级机关可以通过什么手段予以制裁?这一问题又要归结到上文所述的事实上拘束力问题。由于我国现行乃至将来的行政复议层级监督制度都不可能纳入再审程序,对于违反案例指导制度的复议机关,监督部门或者该种复议机关的上级机关不能通过类似与行政诉讼的改判程序予以修正。鉴此,行政复议机关违反案例指导制度的责任机制只能通过行政管理层面的监督途经予以确立,具体来说,监督部门可以通过案件评查、备案审查、考核评比以及对行政复议人员追究责任等方式为案例指导制度的实施确立有形的拘束力。当然,对于各级行政复议机关是否遵循案例指导制度的检查和核实,可以与今后即将推行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对外公开、行政复议办理流程网上运行相互结合起来。
四 结 语
自1999年《行政复议法》正式实施以来的十余年中,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主渠道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当下行政复议法面临大修大补之际,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对于贯通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层级监督的通道、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功能来说无疑是一剂良方。本文试图以业已建立的审判案例指导制度为参照,就行政复议案例指导的制度构建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该制度中的具体规则,例如案例创制主体、创制程序、遴选标准、执行评估等内容还有待学界进行进一步探索。
[1] 钱焰青.上下级行政复议机构业务指导关系探讨[J].法治论丛,2007(2):84.
[2] 李 傲,孔庆欣.行政诉讼案例指导制度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4):70.
[3] 陆 洲,李华围.论实质正义的普遍化——以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为样本[J].甘肃理论学刊,2012(5):148.
[4] 胡国均,王建平.指导性案例的司法运用机制[J].法治论丛,2012(4):122.
[5] 文 婧.论区分规制下的行政案例指导制度[J].时代法学,2009(5):82-83.
[6] 章志远.经由行政案例指导迈向行政判例法[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9(1):15.
[7] 湛中乐.论行政诉讼案例指导制度[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1):27.
[8] 樊华辉.行政复议制度新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92.
[9] 王思健,王昱懿.行政复议案例指导制度的探索[J].行政与法制,2013(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