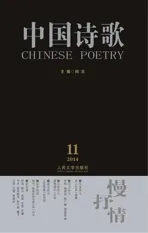我们在森林迷路〔组诗〕
2014-01-25WENXI文西
WEN XI 文西
我们在森林迷路〔组诗〕
WEN XI 文西

本名陈春花,土家族,1994年2月生,湖南湘西人。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作品散见于《散文选刊》、《延河》、《文学界》、《安徽文学》等。出版作品集《冬日田野上的青草》。
走进墓园
墓园里没有我死去的熟人
但我买了一束花去墓园,一到这儿
就丢失了选择权,我不确定这一块石碑
是不是比另一块更好
所以我把花放在了指示牌上
路面干净得让我想起一场雪
那些脚印都流走了,整个山谷
只剩下我和麻雀发出的威胁性警告
经过A区1排后我就往回走
后来只记得一对夫妻
那是个漂亮的女人,肌肤饱满
男人一副短命相,他们在
2002年4月1日死去,照片下的
字迹湿润,仿佛刚沾过水
蝙蝠在城市里飞
走在烈日下的街道上
看见一只蝙蝠在头顶闪烁
它的翅尖颤抖,消失在人群大海般的
呼吸里。你觉得这是一个秘密
也许它在寻找一个洞穴,用来安身立命
舔舐还未愈合的伤口
阳光把建筑照得雪白
没有阴影可以藏身,没有一个角落可靠
迎面走来的人,个个千疮百孔
你觉得他们跟你一样——
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那些不可告人的爱情
攥紧衣袖,掩藏受过的伤
害怕一放松,面孔就会将内心暴露无遗
你在城市里游荡,像鬼魂
碰上一个酒鬼或乞丐,两人就同时潦倒
在彼此身上撕开缝隙,把泪水与
骨血放进去,它们就成了历史
如今我们仍留在原地,而蝙蝠已飞远
爱你的方式
你刚从另一个城市归来
很快就被寂寞淹没,恐惧中你只能
想起一张脸
外祖母曾说,七夕那天,只要站在一株
葡萄树下,说出对方的名字
就能听见他的低语
而我站在葡萄树边
却害怕说出你的名字
害怕一场盛宴后各奔东西
围 栏
武昌火车站候车室二楼的
围栏还在,两年前,你也在
围栏闪烁着光泽,比两年前的泪水更清澈
那时我们靠着围栏
脸庞相互摩擦,渴望在各自身上留下痕迹
但我的身体干净如初,只有记忆
在时间里漂浮。你的胡茬又粗又硬
每次亲吻时,我都提醒你小心点
你嘴巴贴在我乳房,我就成了你母亲
夜里,我们惶恐,仿佛一对
苟活的虫蚁,为了夹缝中的爱情
也可以活得没有尊严
你给我买牛奶,木梳,反复阅读我的散文
你把自己分身成一个秘密父亲
只有去黄河,淮河,鄱阳湖边散步
我们才平等,手挽着手,讲述
出生前与死后的故事,像一对患难知己
我们见异思迁,难以避免伤害
我们残忍地暴露彼此的缺陷
如今围栏还在,而情人与眼泪不在
那些疼惜,谎言,误解都烟消云散
封 存
每当走过那段上坡路
我就想起她捧着玻璃瓶去给父母送水
穿着陈旧的凉鞋,在太阳下走得小心翼翼
摔倒时,她没有觉察到
一块玻璃碴划进瘦弱的脚踝
她把一块玻璃碴带走了
带着玻璃碴在远方结婚
生下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得到她的更多消息
曾经遗留下来的血迹逐渐风干
而记忆不会流失,它将保存完整
在时间停止之前
伤疤与密码
她是个洁白的女人
因为洁白,人们原谅了她被抛弃的事实
但觉得她洗澡过于随便
洗澡时她从不抹沐浴露,只用清水
女人们纷纷效仿,这让香囊在夏天里跌价
夜里,她才会把头发扎起来
露出身上惟一的缺点——
耳根处一块拇指宽的疤痕
看起来像个锁孔
她喜欢转动脖子
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咔嗒一声响
伤疤就会打开,我们都会听到它的精确密码
我将不做任何事情
善与恶是两具尸体
都将腐烂,如果我不被误解
或者理解死亡
如果黎明来偷盗我的家园
我还不苏醒
如果我赞美欢乐与奢侈
我将看不到广场上的难民
正举着黑浆果做脑袋
无辜的刽子手站在墙根发抖
如果我在婚礼上说尽奉承话
我将被夸西莫多的钟声敲醒
第一个沉睡的婴儿成为聋子
没错,我将不做任何事情
我反复跟踪一个人
在街上我反复跟踪一个人
他长得像我死去的亲戚,手背
青筋暴突,月国窝的疤痕在阴影下闪烁
他尽量避开光线,把眼睛藏进衣领
隔着一层布料传出他的喘息声
我感到痰卡在喉咙里
回忆从软骨的缝隙滤出,又脆又薄
我怀疑它们在坛子里腌过后拿出
来晾干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死去的亲戚把脸转过来
面容十分新鲜。我开始失望
并对以后的跟踪失去兴趣
屋顶醉语
从屋顶往上扔酒瓶
然后竖起耳朵听它在冰冷
的地面粉身碎骨
这是属于欧洲的一个节日
干旱季节里的第一场雪
掩盖了我的初恋
仓库里的粮食在梦呓
野草与石头都吃足了水
夜里我会搜寻大熊星座
它有两双利爪藏在皮毛下
去吧,你们这狡猾的盗墓者
把我穿旧的那件大衣扒开来看看
里面究竟还包裹着什么
这个冬天,我爬到屋顶上
站在睡眠的上面
喝酒,唱歌,把昨天高高抛起
不知道我是勾引野兽
还是勾引古代的书生
我看见了神灵,而你们一无所知
空鸟巢
你脱掉衣服,四肢得到舒展
你把头发从窗口甩出去
晾在树梢上,那里
一个干净的鸟巢空着
邻居的面容铺成玻璃
那天下雨,她从草地上捡起发白的衬衫
把它挂在阳台上 还写了
一张纸条,塞在门缝下——
幸好你从来不锁门,举手之劳嘛
你看到她在追蝴蝶,想与她拥抱
然后说再见
这是你一瞬间的想法,还有心跳
舞 会
让风将圣殿拖到广场
星辰挣脱锁链
芦笙吹醒了白骨
女人的裙摆搅翻了夜色
年轻的哥哥不要躲藏
少女的心在发慌
一面面墙在肩头行走
兔子坐在墙头 豹子坐在墙头
羽毛是野性的旗帜
高擎松油火把
将我们的仰望烧得闪闪发亮
我们围绕着四季转圈圈
肢体生长摇摆
英武的哥哥拉住我的手
我就想私奔
朋友,与我喝完杯中的残酒
请不要让我看到你作为人的样子
这一刻我们是野兽或者神灵
流浪的皮鞋
他漫无目的地走在旷野
只有旷野将他收容
云在树梢绿得发亮
下雨的征兆
被侵蚀的石块逐渐清醒
棱角依然掩映在草根下
一只皮鞋将脸打开
蹲了一个冬天的监狱
他会穿着皮鞋敲打
街坊邻居的大门
像位贵客
整个家族被他称为毒瘤
现在只有我与他轻声说话
害怕膨胀的风发出回声
水晶房子
晨风从一个方向吹来
建筑的颜色在慢慢脱落
简陋的床,污黑的沙发,生活杂志
烟灰缸里的烟头还未熄灭
脸都没有了还要衣服干吗,乔说
他和女邻居
走进狭窄的卫生间,擦身子,做爱
这一切如此熟悉,仿佛
曾经历过生死灾难
他想起在青岛海边,妻子与孩子们
堆的堡垒被浪潮冲垮
后来从砖缝中长出来的蝴蝶
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乔在公路边招手
看到一辆汽车就说,我们私奔吧
他本可以过得安好,如今他只剩一截粉笔头
在围墙上画了一个立方体的水晶房子
他居然还记得它的样子
久远的父亲
我记得一张二十五年前的照片
你没有留下遗产,嘴唇和话语也没有留下
停在纸上的肖像是惟一完整的东西
写诗,画画,弹吉他,算命,玩魔术,打架和
贩卖妇女,这些通过一个女人的回忆而变得真实
但我只看到你的黄头发,像树根,根向上伸
而不是地里
一直戳破边框,面庞比叶子年轻
高高的颧骨在灰尘里呼吸
你的牙齿洁白,柔软,咀嚼牛奶
他们都说我不像汉族女孩,因为你的鼻子尖而挺
眼睛纯褐色
不过从我身上看,你比一阵风更透明
纪念太原之行
这里的季节反应迟钝,嘴唇不会轻易发芽
只有杨花存留下来以便抢占未知的空间
我们坐下来闲谈,就像认识好长一段时间了
到处都是酒精分子飘荡,在街道和古董之类的
破玩意儿中间,我们看见统治者,但他看不见我们
一下雨这儿就冷得要命,文化与历史不断从
冻得发抖的嘴唇蹦出,不过
从我面前滑过的是一张张做梦的脸
而不是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省份都相似
我们不敢打开窗户,害怕头顶的白色
然后我们以蚂蚁的姿势拥抱成一堆
在玻璃上投下一个模糊的点
现在车厢空荡荡的,昨天
那几个男孩他们的面庞与手都不知去向
现在每个角落都缺少填塞物
所以我才会离开太原,离开你
离开曾经热爱的多余的部分
雨
冬天患上重感冒,一场雨来得意外
连现实也慢慢地偏转角度
对面的塔顶,避雷针,晾在铁丝上的
婴儿尿布也跟着转动
被冲刷得洁净的路面
那儿有一帮工人在抗议工资少了
他们不完整的抱怨火花
扩散出去,又被雨水熄灭
我的长发粘在了脸上
很快冲出了雨林,但仍被迷茫包围
在一个凉亭里我想到瑞典已经在航行
那里有我的亲戚,但它到达
大西洋的边缘时会被一枚鱼籽弹回来
我要去哪里?常常半途而废
灾 难
暴风雪铺天盖地,想压倒人间的体制
城市广播 道路 房屋 火车站
都被雪白的大口吞没了
我想起小学一年级思想品德课
至理名言:珍爱生命
所以我决定脱下衣服 裤子 鞋子
将头发剃光,扔掉身份证和三个情人
送给我的檀木梳 晕车药 黑白丝巾
并且要把歌德 福克纳锁在
抽屉里。然而灾难只是一个警句
我们无处逃跑,只有把自己交给神灵
等待,那逐渐康复的阳光的空间
冬 天
水银柱持续上升
表明今天不需要增加羽绒服
那么策划一定是昨夜
完成的 就在我沉睡的时候
暴风雪也许来造访过你们
以他的巨掌将花园连根拔起
将天空囚禁
偷吃带盐味的空气
并且对所有的指针下了慢性咒语
以此拖延我们的睡眠
让我们成了假象的牺牲品
虫与人的花园
冬日的阳光绞杀窗帘上的螨虫
在地板上投下平静的阴影
其实在这幅躺着的图像里
正在上演着一场时间的战争
出嫁时我也许会想起这幅场景
并成为家乡的异乡人
她今天给我打了电话
口气悲凉,她在贵州
但不打算逃跑
流产后,她把孩子种在了花园里
这只我紧握的面包
这是一个下雨的晚上
房间里的电饭煲在沸腾
飘出香味,里头蒸着一只面包——
我最后的食物。所有东西都被我吃光,消化
面包烫手,我还是将它捏在掌心
之前它是冰冷,坚硬的
现在柔软得手指一掐就凹陷
那么是我让它发生了改变
我舍不得塞进嘴里,想起上帝怎样
照着他自身形象与愿望创造物体
他创造时也许想到了和面包类似的属性——
柔软,温暖,所以他一直没有毁灭它们
我捏着这只面包,握住它
在潮湿的夜里与它相依为命
我们在同一个房间,但我无法与它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