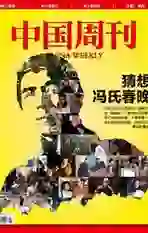“走不通”的小贷之路
2014-01-15闫小青
闫小青

二十年前,杜晓山把尤努斯的格莱珉“乡村银行”模式搬到了中国。在当时,中国银行业界普遍怀疑穷人的还款能力,杜晓山及其团队却在社科院开展实验项目——扶贫社,贷款给农民,而且不需要农民提供任何财产抵押。此后二十年,杜晓山一直工作在小额贷款领域,扶贫社累计发放贷款超过一亿元,惠及农民数以万计,而他也被业内誉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
在这位“中国小额贷款之父”的眼中,中国小微贷目前的发展如何?能否破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沉疴?
大银行做小微,还是政策的需要居多
中国周刊:现在小微贷款的途径很多,为何却无法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杜晓山:广义的小额信贷有三类:福利主义的、公益性制度主义的和商业性的。在中国,对小企业而言主要融资途径是第三类,现在全国有7000多家小贷机构,贷款余额有近三千亿元。贷款规模比较大,途径也确实很多,但是却都有各自的问题和陷阱。对小企业而言,几乎没有一条路是完全走得通的。
中国周刊:商业性贷款机构里银行利率最低,对小企业来说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杜晓山:如果说银行能够做得好,那企业肯定会去银行借,风险小、利率低。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从银行借钱太难了,所以“最好的选择”目前恐怕还谈不上。在过去的说法里,小企业是在“金融排除”行业的榜单之中的,这虽然是银行业里的玩笑话,但可见小企业并不受银行的亲睐。
中国周刊:现在银行都在开展小微业务,情况会有所好转吗?
杜晓山:确实,五大国有银行自称在做小微贷款,十二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也自称在做,几乎这些银行都成立了小微部,还有一些单独成立村镇银行。但是,它们到底做得怎么样呢?现在最新的数据是这些银行2011年公布的,从中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银行所谓的小微贷款业务的平均额度超过了500万。500万对很多小企业来不是小数额,申请难度先不说,即便是申请到钱也很难消化掉,我倒是认为可能性更大的是,从银行贷走这些钱的更多是中型或者大型企业。
中国周刊:为什么说银行是“自称”做小微业务?
杜晓山:小微这块儿业务,对大型银行来说是全新的,难度比较大,成本和风险都很高,这些都是可以想见的。一方面,大型银行涉及到小微业务的机构网点相对少、人力不足,但实际上它是劳动密集型的业务。
另一方面,征信需要大数据支撑,银行的条件也不完备。其实,银行做小微贷款业务是国家政策倾斜小企业的一种体现,换句话说,不是银行要做,而是国家要求银行去做。现实点儿来说,大行的机构形态、业务能力等等,已经决定了它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和服务方法,比较多的银行贷款还是在房地产领域、大企业、大项目,还有政府融资平台。
中国周刊:也就是说,“大银行做小微”是有它的政策目标的?
杜晓山:对。我们来看目前国家金融的结构要进行调整的方向,一个是小微、一个是“三农”、还有一个是新兴产业。总的来说,政策意图就是希望各种金融服务都能够为小微服务。你能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很多“工农中建交”开展小微贷款的信息,“大银行做小微”就是国家对小企业发展的大力扶植的最佳体现之一。银行家们说小微业务是银行自身内在的发展,但我认为更多还是政策的需要居多,因为从利润角度,大型银行根本不会有动力去做这样的尝试。
经不起推敲的P2P
中国周刊:相比之下P2P便捷了许多,会不会是一种好的选择?
杜晓山:对小企业而言,是不是好的选择要用事实来说话。江苏的一家P2P网贷,客户需要付出的总成本是15%,这是就我观察的目前成本最小的一家,但是成本不超过20%的,在这个行业里少之又少,一般都在20%到30%左右。动辄20%以上的贷款利率,这根本就是高利贷,说P2P贷款是好的选择简直谈不上。也不能说它没有优点,网贷胜在便捷。
实际上,你刚才问的是它对于企业的利弊,但对于P2P而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是在整个行业的生存问题。如果一个行业自己还都不能生存,如何来为他人提供好的选择?
中国周刊:您是指年底的P2P倒闭潮?
杜晓山:不仅仅是倒闭潮。其实单纯从目前倒闭的数量和规模来评估,还算是正常的。有人说这是行业自然的洗牌过程,我认同这一点,贴着无门槛、无标准、无监管的“三无”标签发展了很多年,必然会有一些机构违规,甚至违法。也因为“三无”的标签,让很多没有足够风险能力的企业入行,最终无力支撑而倒闭。可以说,P2P的发展一直是野蛮生长,仅仅认为这是一场是洗牌也过于乐观,我看洗牌之后整体的趋势也并不会光明。
如果从源头讲,P2P的本质是信息平台,这一点大家很清楚。但如今中国的P2P网贷公司并非独立的第三方平台模式,而是线上和线下结合,并且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或资金兜底保障的模式,但是很多行业里的人选择忽略这一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让P2P变成一颗颗“定时炸弹”。
中国周刊:这是怎样的“炸弹”?
杜晓山:我的一个基本观点,P2P行业有两个底线:第一不能是非法集资,第二不能是高利贷。虽然P2P网贷是合法经营,但很多地方经不起细究。
譬如,国家对个人借贷的规模有限制,不能超过200人,否则就不是正常民间借贷而是非法集资了。可是现在我们哪个部门在监管P2P?怎么去监管某一笔网贷有多少债权人?这是行业的灰色地带。根据我的判断,越过这两条底线的P2P比例超过50%。你说的倒闭潮就是“炸弹爆炸”,那些洗钱、卷款逃跑、涉嫌非法集资的机构不仅仅损害投资人的利益,而且是对整个行业的伤害。
中国周刊:目前我们国家对于P2P的监管是何种状态?
杜晓山:从国外的经验看,涉及P2P行业的监管有的国家是银监部门在管,有的国家是证券部门在管。而我们国家谁在管?没有人在管。基本都是行业自律,但自律并不是强制的,并不能防止“炸弹”的爆炸。endprint
中国周刊: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的自律公约(全称:《个人对个人(P2P)小额信贷信息咨询服务机构行业自律公约》)的约束力如何?
杜晓山:我们是要求加入公约的机构透明审计,但是坦白地说,目前不少机构交上来的审计数据并不是我们要求的项目,这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规范。即便是有足够的约束力,毕竟加入公约的目前只有六十多家机构,和茫茫七千家相比,杯水车薪。
恶法不如无法
中国周刊:中央对民间借贷的重视,是不是一种政策方向的信号?
杜晓山:政府一直在做调研,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政策、法规什么时候出台。我们的建议是:还是不要急于盲目立法,先搞政策性的指导意见,不成熟的立法性政策其实是一种伤害。恶法不如无法,这样的说法虽然极端,但是中国在金融政策上并不是没有吃过这样的亏。
客观地说,对于P2P这样刚刚起步的、尚不明朗的行业需要政策监管,但不是遏制增长。有一些舆论导向、甚至是官方的舆论导向在丑化民间借贷、丑化P2P,最终又是引向一场陷入国进民退的困局。
中国周刊:这是政策引导的偏差?
杜晓山:这倒不是,我觉得是屁股指挥脑袋的问题。我们国家往往是中央的政策方向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就会有偏差。你比如我一直在做的农村小额贷款,商业性的金融机构本性是追逐利润,对于农业的扶持,它只会说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或者是给媒体、公众好一点形象分;对地方政府来说,如果我们的项目不能直接跟政绩、GDP挂上钩也很难拿到那些政策扶植。这基本上都算是一般性规律了,老生常谈没意思了。
我想说的是,不排除有一些很好的干部,有一些很好的有远见的金融机构的领航人,会自觉地为小企业、农业提供便利,甚至包括有一些国有大行也想尝试。我接触到的这些人,他们的处境往往很尴尬,成为孤立者。
中国周刊:他们被谁孤立?
杜晓山:我就举个例子,农行原来的董事长项俊波,他曾经提出要联合各家银行建立普惠基金支持小微。小贷机构组织不能吸储自身融资难,那么银行发贷给小贷机构再由小贷机构借给农民。这样,银行有钱,小贷机构又知道该借钱给谁,两全其美。我觉得这个基金的概念很好,但是不会有人响应。他们不是被哪些人孤立,而是触动到既得利益的事儿谁也不会主动去做,要银行拿出钱来去做利润不高的事情是需要中央政府下决心、下命令的。说到底,一家国有银行的董事长也只不过是个职业经理人,还没有这个权力。
中国周刊:小额信贷的探索中,政府应该处在何种位置?
杜晓山:营造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不要一味肯定一种模式,也不要盲目反对另一种模式,更不能全盘否定任何一种模式,尤其是民间的、非政府的,可以加强监管,不能因为监管难度大、成本高就全盘否定彻底取消。另外,我们国家目前比较缺乏的是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倾斜,无论是资金规模还是政策支持,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机构的力量有限、动力不足。就我了解,农业还有一些机构,比如中合农信,但对于小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一类的机构在运作,但从国外的成功经验看这一类小贷机构发挥的作用非常可观。
中国周刊:每年都会有关于小额贷款的中央一号文件,似乎从没提及过关于公益性机构的内容?
杜晓山:主要是因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太统一,大家还没有评估清楚风险。如果只是基层对这些问题看法不一致还好说,但关键是监管部门都有不同见解。管理者担心不正规的机构危害社会稳定,无法决定该不该鼓励,或者该鼓励谁。公益性小贷机构在中国基本上没有明确的管理办法,如果地方政府比较开明,就会容忍它存在,但如果支持它的官员调走了,一个机构可能就此消失了。
中国周刊:也就是说,要等到决策者完全想明白之后,才会有“善法”出台?
杜晓山:完全想明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