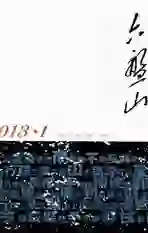天眼
2013-04-10殷高
殷高
……怕,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没有它,天晓得我们会怎么样。
——【法】埃米尔·阿雅尔:《如此人生》
李富贵说得有些急、有些纠缠。贾旺鼓劲点着头。他企图用额头控制住李富贵说话的节奏。可是不奏效,对方的嘴巴像脱缰的马——呱嗒嗒——呱嗒嗒……
李富贵说,当时自己正在睡午觉,媳妇在院子里不知鼓捣什么,迷迷糊糊就听见她惊叫了几声。声音很急,很恐怖,蛇钻进了裤腿里一样。他赤脚跑出了房子。一院子闪烁的阳光,媳妇白花花地披了一身。
媳妇拿指头直往晾衣绳上指。
晾衣绳上,搭着一条洗过了的牛仔裤,裤子的一只裤管正慢慢地、悄无声息地往短里收缩,似乎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不动声色地蹂躏着。李富贵吃惊地问怎么回事。媳妇让酸杏倒了牙那样地摇着头。就在这时候,牛仔裤丝丝缕缕地冒起青烟。他说,哈,快看,着了!着了!惊愕的同时,并不掩饰幸灾乐祸。为牛仔裤,他们拌过嘴的。他对穿牛仔裤的女人存有很大的偏见,甚至说那玩意儿是女人不想穿裤子的一个借口。他那爱俏的媳妇,执意地穿了这条牛仔裤,不知忍受了李富贵多少奚落,她看见自己心爱的牛仔裤着了火,想也不想上去扑救了。
说到这里,李富贵叹息起来,说要是晓得媳妇魔怔,他一准儿会拽住她,不让她去摸那条神秘起火的牛仔裤的。
可那时他只是懵懂地、无措地看着。
他说,她的手刚挨上裤子,又触电似地缩了回来,块头不小的身躯砸向地面。眼看媳妇跌倒了,他才奔了过去,差一胳臂没有能够得上媳妇的身体。伏天里的太阳是个烧得很旺的火盆子,烤得地面坚硬如铁,她的后脑勺就乒地磕在地上,一下子昏死了过去。他害怕起来,腿肚子抽筋,衣领口往外窜热气,单膝跪地掐住她的人中,摇晃着她的脑袋,直着嗓子喊她的名字。
拨弄醒了媳妇,他再一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舌苔干燥发苦、烤焦的烟叶子一样沙沙在嘴里响。一个大男人,屁大功夫吓倒了两次,说起来他娘的也怪丢人。李富贵说。
——苏醒了的媳妇眼睛直勾勾,眉眼是自己的,表情不是自己的,仿佛看着这个世界,又仿佛看着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嘴里也胡乱说起来了,居然拉着他的手说,我的儿呀,娘渴死了,快熬醪糟汤来喝。甚至特别叮嘱汤里不要搁枸杞,搁上红枣。李富贵说,他母亲生前的确喜欢喝煮了大枣的醪糟汤,可母亲去世后媳妇才嫁过来的,压根儿就不知道婆婆这个嗜好。
李富贵说,这八成就是民间传说的鬼魅附体了。他活了三十几岁,没见过也不相信这种事,现在发生在从来不装神弄鬼的媳妇身上,不知怎么办了。
去找村医。村医说这种病医学没办法,得请贾旺。贾旺是个半拉子阴阳,会治这种邪病。
李富贵就风风火火来寻贾旺了。
李富贵说贾会长,你看咋办哩,家里净出怪事么。恐怕得要麻烦庙上。
贾旺是村庙上管事的。在当地,庙上管事的不叫管事的,叫会长。可是乡村小庙香火不盛,哪里作兴开庙会,顶多,九月初九庙前戏楼上唱大戏了,庙里给戏班子出点钱凑凑热闹。无会而长,抬举的意思了。不过,被村支书李富贵抬举,贾旺还是挺受用的。素常,就是没有芥蒂,庙里的会长与村上的支书之间也存着一点微妙的敌意,互相很少来往。
礼尚往来,贾旺也叫了一声李支书,给对方戴上官帽,才神秘地问:家里这几天半夜响动吗?比如说伙房的灶台啊什么的。
李富贵想了想,肯定地说没有。
贾旺的声音很特别,像捏着鼻子,也像从电话——黑白电影里的有摇柄的那种老式电话——里传来的,遥远而清晰。说话时还喜欢拿食指神秘兮兮地捅别人的肋骨,说一句捅一下,像给自己的话断句、加注标点符号。被捅的人如果穿得单薄,也就够受的。今天,他和李富贵隔了一张桌子,所谓骆驼脖子长吃不了隔山草,指头没着落了,遂弯曲了敲击桌面。可是,笃笃地敲击声没有制造出神秘的氛围,相反,成了一种消弭和破坏。为了补救,他尽量地低下额头,拿眼睛直朝李富贵看了去,下眼睑露出更多的眼白,做足了神秘的表情,才用电话里的声音说,这回的火烧得蹊跷,与去年的不大一样呢。
去年,李富贵家就被火烧过一次。那一次,李富贵的一辆停在院门口的旧桑塔纳,半夜里起了火,烧成了一堆废铁。那次火灾有多种可能,但有一种可能除外,就是自燃。李富贵用鼻孔哼了一声,撂下了一句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请来工匠修宽了大门楼子。竣工那天,贺客正站在门口云山雾罩放鞭炮,李富贵开着锃亮的新小轿车进了村子,车头上搭着红被面,一路摁响喇叭,风风光光把车子直接开到院子里去。他用这种方式,给那场火灾泼上了自认为最有效的一盆冷水。如今,火却烧到院子里来了,而且烧得莫名其妙。他打了个比方。去年的火灾好比人丛里挨了一拳,只是不知谁打的;今天这事算得上一起火灾的话,就像头上被谁弹一个嘎嘣儿,摸头四顾,却是阒无一人。
李富贵说,两个娃娃上学了,院子里只有自己和媳妇。若再赖上一个,还有个日头。可是再毒的日头,能把衣裳晒着了?
能的。贾旺老伴说话了。
才说了一句,锅里的馍煳了,她急地抓住电炒锅的双耳,一簸,一张大圆饼倏地从锅里跳起来,空中翻了身,又稳稳落回锅里。在电炒锅上烙馍,不好拿捏火候,她显然还不习惯。
有外人,贾旺不能去捅老伴的肋骨,急的指头乱捣空气。奈何老伴没看见,或者说假装没看见。他就又有意味地清嗓子。老伴拒绝接受贾旺的暗示,翻过了馍,用下巴指了指贾旺,继续说道:他的一顶帽子就这样烧了的。
李富贵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她向门外看了看,压低声音说这事怪双星媳妇!
双星是他们的儿子。
贾旺说不要怪她,会怪了怪自己,不会怪了才怪别人。
他老伴的嘴又弯又扁:好好,你们都不怪,怪就怪那根晾衣裳的铁丝,行了么?
贾旺说当然怪那根铁丝。于是他在空中比划起那根看不见的铁丝,说,它不是松了嘛,两头高,中间有个弧度,夹帽子的夹子能活动,撑裤头的衣架也能活动,风一吹,就挨到了一起。
贾旺老伴说,看你能说出花儿来,铁丝上晾着公公的帽子,儿媳妇就不该把自己的裤头再搭上去。老辈子的人,骑过月经的血裤衩太阳底下也不敢洗也不敢晒,怕遭天谴呢。
贾旺说双星媳妇是近视眼,你又不是不知道。
老伴挖苦他说,老天爷没有近视么,他老人家勾头一看贾旺家的晾衣绳,哦哟,不得了了,贾旺这个老糊涂鬼,一个伺候神的人,帽子竟然黏糊在儿媳妇的裤衩上!老天爷脸上也挂不住了,心想吹一阵风吧,八成就是风的缘故,落一阵雨吧,没准会贴得更紧。没奈何了,才打发火神下来烧了公公的帽子,给老的给个脸儿,小的呢也提个醒儿。
李富贵说真的烧了吗?
贾旺眼白又多了,像一只肥鸟那样转动短项上的脑袋,机敏地盯了每个人一眼,又盯了盯房门。门外,一只母鸡若有所思地蹒跚过去。末了,他才点了点头:烧得只剩下帽檐儿!
帽子起火的原因,贾旺后来费心思弄明白了,不过他对谁也没说。他估摸,烧了李富贵媳妇牛仔裤的也是这种火。心里有了底,他四平八稳端起茶盅:喝茶,喝茶。
李富贵胡乱对付了一口茶水,小心地说,火烧财门开,兴许是好事?
贾旺老伴说快别胡说了,帽子着了没过几天,双星的小儿子跳房台阶玩儿时就跌断了腿。并说,多亏贾旺是半吊子阴阳,院子里压了五色石;请来庙里的神在家里折腾了一通,总算太平了。
李富贵听了,二话不说从衣袋里掏出钱来。
贾旺说现在不行,香火钱须到庙里给。
李富贵说还不是一样。
贾旺说刀豆一行茄子一行,不能混淆,这里是给我给,庙里是给神给。神为人治病,我是给神跑腿的。唉,我们这路人,鬼使神差嘛。
双星的小儿子神保拽着黑狗尾巴玩儿,看见贾旺隔门泼洗脸盆里的水,丢开黑狗跑了过来:爷爷,神保要净手!神保要净手!神保知道,来了人爷爷就要洗手,洗了才能手上香、写符。这时候爷爷把洗手叫净手,神保也就跟着叫净手。他去年夏天跌伤的腿,现在已经痊愈了。
贾旺只得重新给洗脸盆倒上清水。神保手伸进盆子里拍打几下,溅起的水花几欲迷了眼睛,急忙扯下脸盆架上的毛巾胡乱擦了两把手,趴地上煞有介事地朝中堂下的方桌磕了三个颇有质量的响头。镰刀把高的人儿,给神磕头一点也不含糊,很仪式化,一本正经。李富贵忍不住咕地笑出声。敬神的人儿不答应了,板起脸子训他:不敢笑!敬神呢!磕了头,也不管不顾小巴掌沾了许多灰尘,忙忙抓起一块圆镜,镶进自己的脸蛋去。镜子里的神保撅着嘴,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大妥帖,非得返工重来才可以的样子。
贾旺的老伴伏在一口瓷盆上和面,她向李富贵挤挤眼,小声说,每回都这样,和爷爷比赛,磕头时看谁额头沾的灰尘多。今儿地上干净,没有弄脏额头,你看他不太满意呢。她说着话,没有防备,神保冷丁把头塞进面盆里来,给额头、鼻尖涂满面粉。作奶奶的吓一跳,举起拳头作势要打地推开他:小祖宗,额头没沾土不打紧的,关键要心诚。
神保不理睬奶奶,庄严地从贾旺手里接过三炷冒烟的土香,给方桌上的香炉里插。个头矮,够不到香炉,所以略显不快地拒绝着贾旺的帮助,自己吭哧攀上桌旁的椅子。太过努力的缘故,屁股响了一下。贾旺就笑骂他一炷香三个屁恶多善少。神保认真地纠正爷爷:三炷香一个屁。不敢对神编谎!
李富贵忍不住又要笑。神保立刻拿眼睛剜他。李富贵的笑就残在脸上。
增加了一把椅子的高度,神保没费多少事就插上了香。末了的程序,还要作揖的。贾旺代劳,神保不答应,跟着爷爷照猫画虎。作罢揖,他模仿爷爷,伸出指头戳戳李富贵的肋子,小声说,你可以笑了。
自己倒先格格格地笑疯了。
李富贵说真格跟啥人学啥艺。
贾旺说,让孩子知道世上除了人还有天地神,免得将来混世魔王,什么事也干得出来。
上上香,贾旺端起架子,很像回事地开始给李富贵写符。贾旺写符气势很大,平时多么瞧不起贾旺的人,也会给镇住。
铺了花格油布的炕上,小炕桌早摆上了。贾旺盘腿端坐炕上,稳重得像一尊佛了。他拉开黑色的人造革皮包的拉链,取出正方形的黄铜墨盒。担心掉盖子,拿自行车内胎剪的皮筋束缚了墨盒。揭开盖子,给盒子里的海绵添上墨汁。房子里的香火味儿、半生不熟焦馍味儿就掺杂了似有似无的淡淡的墨香。手又伸到皮包里去,摸出个不是很粗的乳色塑料筒子。看得出来,是一枚高射炮弹的外包装,大概从村头打冰雹的炮点讨来的,或者顺手偷来的也未可知。拔开筒盖,从筒里好几支毛笔中抽出一支。待笔头泡醒、饮饱了墨汁,墨盒沿儿上复蹭瘦了,举到光亮的地方,拿指甲用心十分地拔去笔尖一根长出来的毫毛。第三次,他的手伸入革皮包里。一只罗盘探出头来,旋即又给塞进去了。手在包里不露锋芒地翻,弄出一些响声。响声一点也不空灵,不像铃铛,确实是铃铛响。手出来了,这一回什么也没捞着。索性拎过包来搁在大腿上。笔管墨盒上滚地搁不住,横咬进嘴里去,腾出另一只手帮忙。包里东西似乎很多,很杂,壅得很,手在里头腾挪不便,于是歪了脑袋,别扭地拿眼睛向包里睨视。横亘在嘴里的笔管左右着他的头颅,是个不小的妨碍。一不小心,笔尖到底戳上白布衬衣,窝弯了,肩膀印上了一朵墨花。也不是很在意。好歹总算找着了需要的东西:一个曾经也许干净过的小白布袋子,一沓撒金宣纸。宣纸一些空白着,一些写满了工整的蝇头小楷。复又润了笔,坐得愈发地端直了。吸了吸鼻子,定了定神,开始在净的宣纸上画符。才写了一笔,猛地记起了什么。笔管再次咬进嘴里,双手乱拍身上有口袋的地方。找眼镜呢。写符怎么能不戴眼镜呢?不是花镜,是那副场面上才戴的水色石头镜子。据说戴上这副镜子白天能看见星星。然而贾旺没有给过谁验证的机会。这么金贵的眼镜,镜盒子却很不堪,蒙在上头的条绒布棱已磨平、磨损了,看得见瓤子上的铁锈。寻着了眼镜,不慌了,甚至还为刚才的手忙脚乱歉意地露齿一笑,尽管口里衔根笔的笑是很不像样子的。开始从容不迫地拿一块布仔细擦拭眼镜片子,眼睛盯着只写了一笔的符,似乎在考虑接下来怎么写。不是担心鼻梁,也许倒是担心鼻梁会硌疼了眼镜,于是张大嘴巴,同时朝上翻翻眼珠子,将鼻梁的皮肉抻平了,才稳稳的把眼镜架上去。一滴口水沿着笔管滚下来时,贾旺也戴好了眼镜。皱了皱鼻子,感觉眼镜妥帖在鼻梁上了,再接着写符。
写好了符,拿过蘸过朱砂的笔在上头又描了描,点了点。做完了这些,贾旺两手扶着炕桌沿儿轻轻吁了一口气,脑袋又像鸟儿那样转动了。转动的结果,看见了那个布袋子,拎起来一抖,哗啦啦抖出许多的印章。各式各样的印章,长的方的圆的椭圆的菱形的不一而足。拣出一枚较大的印章来,给上面哈了口气,摁上印泥,手按手地符上盖了。在写着小楷字的一页纸上也盖了。小楷字是贾旺闲时就写好了的,写了好多张,用的时候抽出一张,盖上章子就可以了。他说这是一道冥文,鬼神全认可的。然后,他抬起头,用眼睛和额头示意李富贵靠近来。
李富贵赶紧拧身坐到炕沿上。
贾旺将盖了印章的冥文和符一并交给李富贵,生怕别人听见似的小声交待:这道文书,■了这个戳子,相当于国务院签发的通行证,拿回去在当院里烧了,你母亲就能拿到。有了它,她在那边走州过县畅通无阻。
李富贵别过脸去假装咳嗽,趁机打发掉一个浮上面颊的笑。倏地,他的脸上换上痛苦的表情。原来他被贾旺捣了一指头。他是个瘦子,即所谓骨吃肉的那种,脱了衣服肋骨历历可数。贾旺的话也直往李富贵心里最软的地方捅:你母亲不容易啊,一个寡妇家,把儿子养大了,该享清福了,自己却钻了土。常言说死了就了了。看来死了还了不了,还得为后代儿孙牵肠挂肚。你看你母亲,担心你出事,当了鬼还借口传言哩。
谁都知道,李富贵是个孝子,他听了贾旺的话眼圈红得厉害,忙岔开话题,问符贴在什么地方。
贾旺说,你们住哪个房,贴哪个房里的山墙上。
贾旺老伴拿根筷子戳着刚出锅的热馍,又沿着筷子戳过的地方掰开来,掰成四牙,码在暗红漆木的盘子里,把白糖煞了的西红柿凉碟也放入盘里,整了两双筷子,端了盘子要往炕桌上放。贾旺赶紧收拾起自己的东西。一只苍蝇闻见馍香栽了下来。贾旺一巴掌■走了苍蝇:李支书,吃馍。李富贵没心思吃馍,眼睛不时地往窗外瞟。贾旺家上房坐东向西,窗含西岭,坐房里能观落日。贾旺朝窗外一看,果然日头搭须弥山畔儿了。他晓得李富贵惦记媳妇,就也撂下筷子,说声不吃了,脚伸到鞋里就走。
神保骑黑狗背上,双手抓住狗耳朵。老黑狗烦得要死,然而敢怒不敢言。李富贵说逮牢了,不敢松手!说罢几步跨出院门,忙忙钻进轿车里去。
贾旺走到轿车旁,忽觉尿胀了。还有半个太阳缠绵在山脊上不肯落下去,贾旺于是隐身到猪圈后去。撒尿自然要避人的,但贾旺还要刻意地规避开太阳。在他看来,缀在天宇上的,除了人造卫星,其余全是神明,不可以不敬畏。天是父,地是母,人只是山川皱褶里寄生的虱子,翘啥尾巴哩?他甚至不许神保拿手指太阳、月亮和星辰,吓唬他指头会生疮。有时情形所迫,不得不面向太阳小解时,也不敢让那物儿直冲着太阳,斜着那么一点。也算得上个技术活儿呢,得考虑风向和角度,吊儿郎当,往往要打湿脚面梁的。
贾旺撒尿,神保也跑过来凑热闹。他看见爷爷没有自己尿得高,就建议爷爷抬起一条腿试试看。贾旺问哪是为啥呀?神保说黑狗这样才能尿上墙的。没顾得上贾旺笑出声,身后突然传来橐橐的脚步声。扭头一看,儿媳妇端着猪食盆走了来。他急忙湿淋淋地装了进去,龇着牙草草把裤子提上了。
神保发现贾旺省略了一道手续,便大声提醒他,说,爷爷,你的小鸡没摇头呢!
贾旺头也不回地钻入李富贵的轿车里去了。
庙门口站着一个老大的绿塑料瓶,贾旺斜着瓶洗了手,才就着很粗的蜡烛点燃一股香,每个神像前插了。逼仄的庙宇里立刻被香火气息弥漫了,有些呛,李富贵将嗓子眼里一个痒痒小心小声地咳在掌心里。
神像有画的,有塑的。多为神话或历史人物。贾旺上了香,跪地上烧裱、奠酒,打衣袋里掏出一对像木楔却比木楔精致的物什儿,比大拇指略粗而长短仿佛,一面平一面拱的。沿平的一面合起来,囫囵一个圆锥体、一个差强人意的小陀螺。这东西叫角子,羊角尖做的,是贾旺与神沟通交流的工具。
诚惶诚恐,贾旺开了口。像给自己,也像给立在一旁的李富贵,以及看不见的神扼要地说了李富贵家着火的经过。最后说人肉眼凡胎,眼前路墨黑,恳请爷爷明示起火原因。
村人将庙神叫爷爷,是个尊呼。
贾旺说毕,双手齐眉高捏了角子,开始打卦问神:是李支书家祖坟里的事吗?问罢松开手,角子跌成两瓣,扣在铺了青砖的地上,拱面全朝上。是阴卦。阴卦表示否定,等于神说不。
贾旺替神摇了摇头。
略一思忖:他家盘炕砌灶没择黄道吉日,随便动土了吗?
两瓣又皆是平面。平面是阳卦。阳卦也是否定。
往上推推帽檐:他女人洗换不勤脏内裤冲了灶神吗?
阳卦。神说不是。
……
黔驴技穷了,多少有点。
活动活动跪疼了的膝盖,翻起眼珠,口里念念有词,不晓得在心里怎么动员神。想。但不是抓耳挠腮地。想起了一个什么问题,又似乎站不住脚,兀自摇了摇头,没好意思问神。好一阵子,老式电话里那种声音猛地又响了起来: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爷爷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难道李支书本人要出事了吗?
问到点子上了,出了一个神卦:一瓣扣,一瓣仰。神卦表示肯定。也就是说神支持了贾旺的假设。
白眼仁多黑眼仁少,猛地仰头盯了李富贵一眼。
李富贵的身子矮下去半截。
或许正因为这个假设被神肯定了,贾旺突然开始跟神顶牛了,说,不可能,他为官清廉两袖清风,能出什么事?爷爷如果没有冤枉他,请爷爷再赐一个神卦。
神也不含糊,铿锵地又出了一个神卦。
李富贵的身子再一次矮下去半截。
贾旺愈发犟了,脊背上的衣服褶皱横竖变换,构成一些硬硬的线条。老式电话里的声音直钻耳朵,像钉子划过铁皮:两卦容易三卦难,爷爷果真灵验,就连给三个神卦,我们才心服口服。
话落卦破。神卦!三个神卦!
扑通,李富贵跪下了,鸡啄米似地磕头,嘴里埋怨贾旺了:贾会长,你这不是拿我赌咒嘛!我会有个什么事哩?
贾旺杵了李富贵一指头:爷爷说你有事,不是我说你有事。搞清楚■。
架到火上烤了。快说怎么禳解呢,啊?李富贵顾不得肋子疼,急忙问道。
贾旺说我哪儿知道,这得问爷爷。
贾旺重新恭顺起来,表情宛如抿着耳朵的狗,口吻也不复张狂,涎着脸,说,爷爷,李富贵的事可以禳解吗?
神说不可以的。
贾旺说可以禳解嘛,爷爷还跟凡人较量?谁没有个七差八错?有错就改,改了就是好同志嘛。他八升的肚子,撑死也吃不了一斗,吃了也得吐出来,对不对,爷爷?
他跟神磨起来,可笑地透着点赖皮样,手指头都带着表情,给神戴了一打高帽子,不时还拍拍神的马屁。似乎这时候的神要么脑子不太整齐,要么就是不谙世事。
毋宁说他的诚心感动了神,不如说神被他磨烦了,所以当卦再落下时神改口了。贾旺趁热打铁,劳动神今夜就起驾,去李富贵家里驱除邪祟。神也答应了。贾旺把帽顶有汗碱的旧蓝帽子转了半圈,帽檐转到后脑勺上,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头,爬起来作了揖,拿手去揉搓麻木了的膝盖。
李富贵问:我媳妇怎么办?
贾旺说,马不跳鞍子就不跳么。
怎么讲?李富贵问。
贾旺说,你没事了,她的病自然会好的。根子在你哩。
李富贵趴在地上给神许愿,说若果自己过了这个坎儿,砸锅卖铁也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贾旺听了,提醒他说,许愿许骆驼,还愿还羊羔子,神会不高兴的,对神可不敢耍花腔打马虎眼。
李富贵想说什么,腰带上的手机响了。接完电话,他说媳妇闹腾得厉害,自己得赶紧回去。他塞给贾旺一沓钱,说是香火钱,急急走了。
贾旺说没签名呢!
李富贵折回身来,低声说他不要签名字,也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给了香火钱。突然手一抖擞,戳了贾旺一指头。贾旺半个身子麻了,哎呀一声手抚了腰,冲李富贵溶入暮色里的背影哑着嗓子喊:
招呼几个人抬法剑。这两天吃了荤腥和夜里行了房事的,一个也不要!记下了?
李富贵说声晓得,车屁股红红地一溜烟跑了。
香火钱交给贾旺是不合规矩的。换句话说,今天,贾旺如果黑了李富贵的香火钱,谁也不会晓得。所以,香客定要亲自把钱投入功德箱里,然后在功德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后头缀上钱的数目字,于神于己于贾旺都是个交待。
村庙里的功德箱是一口很深的木头箱子,没上漆,一丝不挂,看得见木头上的纹路、结疤。它缄默地、甚至有些难为情地站在地上一尊铁铸的大香炉旁边,是庙里一个必不可少的多余。用红油漆书写在上头的功德箱三个大字却突兀得很,是一种提示。箱盖上有一道口子,投钱币用的。窄窄的口子说明着意图,就是只进不出。钱怎么取出来呢?有门子呢。门子掩首上俨然地挂了一把金黄色的小锁子。锁子的钥匙不归贾旺保管,拴在另一个会长的裤腰带上。他比贾会长年长许多岁,腿子有病,不常到庙里来。他不来也不妨事,香客自会将香火钱投进功德箱里去;生怕神不晓得,不用贾旺督促,也自会签了自己的名字。香火钱也不多,随心布施,五块、十块、二十块的。有的不给现金,拿了香裱、馒头来。馒头献过了神,依例给立在一旁敲罄的贾旺留下两个,剩余的还愿的人自己拎了回去。
贾旺数了数手里的钱,拢共两千一百八十元。他着实地吓了一跳!李富贵企图破财免灾,才如此出手大方。但对神而言,这不啻是受贿么?他赶忙摇了摇脑袋,驱逐走了这些对神不恭的念头。
他踟蹰地挪到功德箱前,慢慢地往里头丢手里的钱,丢一张,停一停,又丢一张,又停一停,似乎在等待纸币落下去的回声。丢了几张,他狐疑地住了手,突然脸就黄成一张裱,像在心里很厉害的跟谁吵架。半晌,身子一筛,悚然惊觉了,害怕自己后悔似地三下五除二把余下的钱塞了进去。心里舒坦又似不舒坦,说不清楚,一团乱麻,打翻了五味瓶。一猛子做了,已不可更改了。可他知道说服自己还需要些日子。
拿袖口揩去额上沁出的细汗,想了想,在功德簿上手抖得很厉害地写下:一香客,善款两千一百八十元整。
善款什么意思?一知半解,只觉得只能这样写。
按说无须磕头了,贾旺却趴在地上又磕了几个头,咚咚地响亮,赎罪一般。
从地上收拾起自己,摇头苦笑了一下。用一根粗壮的无柄长麻鞭捆绑了两把法剑,随手拽死了灯泡。黑夜猛地扑进庙里来了。有一些星星,没有月亮。
但贾旺感觉到了,在那缀满星星的天幕上,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这个广袤的世界,看着这座庙宇,看着他。
他摸黑向李富贵家走去。
贾旺是车把式出身,抡一下麻鞭,叭!半架川听得见。
今夜耍麻鞭,一定叫李富贵把院子腾宽展。尤其要搬开太阳灶。李富贵当了村支书,贾旺就没有去过他家。但他知道李富贵家里有太阳灶。因为自己的帽子就是被太阳灶的聚光烧掉的。
【责任编校 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