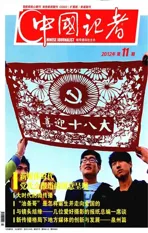从新闻集团拆分看国际新闻的中国视角
2012-07-27□文/文建
□ 文/文 建
(作者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国际新闻报道要体现“中国立场”、展示“中国视角”、宣示“中国观点”,这已经成为业界共识。但是,在当前新闻实践中,一些国内媒体对“中国视角”的把握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摇摆性”,要么过度亢奋,要么则完全失语。这种不稳定状态所折射的问题、背后的根源值得探讨。
国内媒体近来对新闻集团的报道,就较为充分地暴露了这种“摇摆性”。2011年“窃听丑闻”之后,国内媒体的本土化报道和解读形成一个高潮,一些专家评论认为“热闹过度”;而今年新闻集团“一分为二”之后,国内媒体上却几乎看不到有分量、有深度的中国化报道和解读,国内媒体集体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外媒依赖症”。这种巨大的落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研究维度。
“新闻系”的完胜
今年6月底,新闻集团宣布正式拆分成两家公司,一家负责娱乐,一家负责印刷出版。作为全球第二大传媒集团,新闻集团“一分为二”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和新闻价值不言而喻。那么,全球舆论是如何报道这一事件的呢?浏览全球媒体的报道,会得到这样一个清晰的印象:《华尔街日报》、道琼斯新闻社、福克斯电视台这些“新闻系”媒体堪称完美地主导了全球舆论,包括一些中国媒体在内的无数传媒机构沦为默多克的“传声筒”。
首先,从动态消息来看,“阀门”牢牢地掌握在“新闻系”媒体手里。对事件报道最早、滚动新闻最及时的,是道琼斯新闻社;报道最完整,信息最详尽的则是《华尔街日报》,全球媒体引用最多的消息,也源自这两家。福克斯电视台和天空电视台也分别成为美英两国受众了解这一事件进程的权威消息源之一。结果是,在动态消息竞争中,“新闻系”媒体几乎垄断了各种新闻资源,其他媒体只能亦步亦趋,或转发或改写这几家媒体的消息。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同默多克的主动配合功不可没:“拆分”消息出来之后,首家发布消息是道琼斯新闻社;印刷媒体中第一个获得默多克采访机会的是《华尔街日报》;电视媒体中得到这个特别待遇的则是福克斯电视台。面对“偏心”的默多克,即便是《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这样的专业媒体,也难有作为。事实上,这三家媒体中,仅《纽约时报》有机会采访到个别新闻集团内部高层,在报道中描述了新闻出版部门拆分前的焦虑,可勉强称为亮点。
其次,从分析和评论来看,“新闻系”也处于明显的主动地位。在中英文媒体上很难看到有别于“新闻系”媒体的分析,负面的评论更是少之又少。仅有的两条有分量的“异见”,一条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控制论”,认为默多克对集团控制力减弱才导致拆分,拆分反过来会增强控制力。另一条则来自彭博社,认为“拆分”时机选择有“文章”:消息公布之时,正是英国电信监管机构即将投票决定是否允许新闻集团继续持有天空电视台控股权之际。在以批评性和多样性著称的英美媒体,对一起财经新闻的报道口径如此统一、如此正面,也较为罕见。
毫无疑问,“拆分事件”再一次清晰展示了新闻集团的话语霸权。在和麾下媒体的互动中,默多克控制了全球媒体的报道议程,主导了舆论走势,这一事件演变为“新闻系”媒体的一场表演。
“被设置”的议程
回头看国内媒体的报道,也没有跳出新闻集团营造的宏观语境。
首先,从动态消息来看,国内、国外媒体的报道基本趋同,在新闻事实选择上,国外媒体的影响无处不在。粗略统计,新浪新闻频道6月26日至7月中旬约40条关于“拆分”的新闻中,直接注明消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有14条,来自彭博的有2条,来自《金融时报》的1条,《纽约时报》的1条,还有多条新闻虽未标注来源,但明显能看出也是辗转来自国外媒体。考虑到新闻集团强大的引导和控制能力,以及中国媒体现实的国际新闻信息采集能力,出现这种议程“被设置”的状况,似乎也并不令人惊奇。
但这一现象值得警惕。众所周知,对新闻事实的选择,也能体现媒体的立场。因此,多样化的消息来源、充裕的新闻事实供给,是营造健康的观点自由市场的前提和保障。就中国媒体而言,虽然大量转发国外媒体的新闻并不一定就会“被设置”议程,但前提是还有替代性的消息来源可用,而且还有选择消息来源的自由:既有主动选择的自由、也有主动放弃的机会。如果对国外媒体形成了习惯性的依赖,就有可能逐步丧失甄别的意识,进而失去选择的自由,最终沦为传声筒。
其次,在观点表达层面,国内媒体上也很难看到有本土视角的分析和解读。浏览国内媒体的报道不难发现,大量外媒分析被反复转载,国外专家的言论也被大段编译过来。这些报道既没有同中国有关的元素,也没有中国视角的分析,同中国读者的关联性很弱。这背后,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一些媒体把“拆分事件”当做了一条普通的国际财经新闻,没有在本地化上下功夫。其实,新闻集团是全球第二大传媒集团,“拆分”对全球传媒格局有深远影响,背后有很多文章可以做;这一事件所反映的传媒行业发展趋势,对我国也有很多启示,值得深入探讨;更何况,新闻集团在中国也有大量资产,同中国的贴近性也很强,这条国际新闻操作层面的“着陆点”也很多。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媒体对这一事件都不应该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许多媒体受认识水平和分析能力所限,没有找到可以超越西方媒体的独立视角。毕竟,要对这样国际化的新闻事件作出有新意的解读,不仅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水平,而且需要高度的自信。
此外,还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媒体在转发外媒报道时不加辨析、不加评论,这种“纯客观”手法若操作不当,容易成为错误观点的放大器。比如,许多媒体原汁原味地传播了默多克“拆分与窃听丑闻无关”的观点。如果读者不了解“窃听丑闻”的前因后果,很可能会信以为真。但事实是,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容质疑,默多克只是碍于面子不愿承认而已。就连《华尔街日报》也指出:“《世界新闻报》丑闻对公司其他部分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纽约时报》也把默多克的这个句子写进了标题,但作者在正文中这样质问:“默多克坚称,该事件和窃听丑闻没有任何关系。但扪心自问,他是否会认为这一举动跟丑闻没有关系?你不得不赞美他的虚张声势,甚至是吓唬。”另一个例子是,国内许多媒体大量转载外媒“默多克将继续拯救报业”的分析,把默多克描述为一个要矢志不渝地拯救报业的“危情骑士”——这恰好是新闻集团希望看到的结果,对新闻集团内部维稳和保持股价而言,这都是最理想的舆论。但事实是,作为征战商场的老将,默多克肯定能够分清情感与理智,肯定会把商业利益的考量放在个人情感之前。迫于各方面压力,并不排除他在拆分后卖掉纸质媒体的可能。

▲ 2012年2月25日,在英国首都伦敦郊外的印刷厂,一名工作人员在监督第一版《星期日太阳报》的印刷。新闻集团极为重视《星期日太阳报》的创刊号,希望以此赢回因《世界新闻报》关张而流失的读者。新闻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默多克坐镇英国伦敦“指挥”发行。(新华社/法新)
摇摆的中国视角
国内媒体在“拆分事件”中的失语,同一年前“窃听丑闻”后的兴奋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当时,媒体大量刊登专家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作出的解读、分析和评论,形成近年来国际报道的一个言论小高潮。这次报道数量多、角度广、持续久、势头猛,以致于有学者评论说,对“窃听丑闻”,中国媒体情绪过于激动,批判力度过大,是一种长期过度压抑后的反弹式亢奋。不可否认,这些评论中确实有不少民族主义的感情宣泄,也夹杂着带有政治批判痕迹的言论和观点,这使得“中国视角”的理性、客观性和专业性都打了折扣。不过,抛开言论质量与专业程度不论,这些报道鲜明的“中国视角”以及背后的原创努力依然是可圈可点的。
同样是关于新闻集团的重大事件,从过度亢奋到完全失语,国内媒体解读国际事件的努力从波峰跌入深谷。这巨大落差的背后,固然有两起事件的新闻属性差异——“窃听事件”,作为“丑闻”,显然更能满足大众的娱乐、猎奇心理,加之涉及政治内幕与道德伦理,传播元素更为丰富;而解读“拆分事件”,无疑需要更强的专业能力。但笔者以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许多媒体对“中国视角”理解不准确、把握不稳定、操作不专业。
“中国视角”当然要反对以美化欧美为出发点的“西方主义”,但我们也应该不鼓励用民族主义思维对抗全球化和西方话语权。“中国视角”应该倡导的是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话语权力观。这种视角的里子是中国利益,面子是个性表达。在操作层面,对我国媒体而言,当前首要的是树立自信,敢于发出与西方传媒不同的声音,敢于尝试个性化的表达;其次是实现自立,即大力提高国际新闻信息的采集能力,从信息源头上摆脱对西方的依赖;然后是自强,即培养大批熟悉国际事务、了解国际规则的传媒人才,有能力在国际新闻事件上大胆言说,自信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