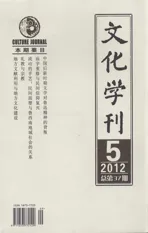民俗语言学应用研究概述
2012-03-20董丽娟
董丽娟
(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1)
民俗语言学,是脱胎于民俗学与语言学两个学科的有机结合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以民俗语言文化为研究客体的科学”,是“研究语言中的民俗现象和民俗中的语言现象,以及语言与民俗相互关系及运动规律的一门实证性人文科学”[1]。
一、民俗语言学的应用研究传统
作为一门具有多缘联系而富于应用性和广阔前途的新兴人文学科,民俗语言学成为现代学科的历史还很短,但从第一篇民俗语言学论文发表起,其迅速发展的态势已越来越突显出其研究亟待解决的课题,就是在继续完善和深化基础理论的基础上,这主要包括民俗语言学成果的应用研究及民俗语言学应用领域的研究,反过来,对这些民俗语言学成果开展的应用研究及民俗语言学应用领域的研究又会促进民俗语言学基本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成熟,为其不断深化提供科学依据和现实动力。
从发生学角度看,民俗语言学的兴起是在文化人类学的有关学说与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源于民俗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和视界的参与和语言研究中的民俗学方法的借鉴,是以二者直接需要和跨学科研究的需要为起点的,因此,可以说,从民俗语言学诞生之初,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就已经具有了关注现实、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的“应用研究”的基因。它突破了语言研究的狭小空间,把眼界放到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来,关照民俗事象中的语言现象和语言活动中的民俗现象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民俗语言学应用研究侧重于民俗语言学之于社会生活的应用研究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体现在其“功利”的目的上——为社会服务,对社会产生直接的效益,为现实生活提供可资借鉴的科学依据。民俗语言学的兴起表明了其研究应用的传统。1990年,“首届民俗语言学基本理论与应用研究研讨会”在辽宁千山香严寺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民俗语言学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基本理论框架和应用研究进行了交流和讨论,认为民俗语言学“使语言的全方位立体化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这种研究不仅能发现很多新问题,而且大大有助于语言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2]。1990年,民俗语言学的首创者曲彦斌在 《社会科学辑刊》第5期发表了题为《论民俗语言学应用研究》一文,文章阐释了虽然民俗语言学的学科历史不长,但就当时其理论构架所及及从现实中反馈而来的信息显示,民俗语言学的应用领域应该是非常广阔的。可以说,由此拉开了民俗语言学应用研究的序幕。之后,大量的民俗语言学研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不断地拓宽了其应用领域的研究。如比较成熟的领域有:“辨风正俗”、“公安言语识别和言语鉴定”、“对外汉语教学”等。
二、民俗语言学应用研究概况
根据中国知网统计,从1979年至今,全文方式检索“民俗语言学”共计得到473条的检索记录,其中涉及民俗语言学应用研究的相关文章161篇。从民俗语言学的研究的相关领域来看,涉及民俗语言学“辨风正俗”作用的有8条,“对外汉语教学”的有42条,“言语识别、语言鉴定”的有14条,“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有59条,“考古”的有21条,“文字改革和语言政策等”有17条,“交际习俗、公共关系”的有7条;从时间段及数量的分布上来看,1979年至1990年有15条记录,1991年至 2000年有 124条,2001至 2010年有273条,2011年至2012年有61条。自1990年后的20多年,民俗语言学的应用研究进入一个相对活跃的阶段。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类型,还是质量,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民俗语言学应用的空间不断得到新的拓展,显示了民俗语言学勃勃的生命力。最为突出的是,在继承以往成就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民俗语言学应用的研究突破了单一的语言学的视点,借鉴、导入了许多相关学科的思想、方法和成果,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到民俗语言学的研究中来,以自己的学科为基点出发,利用民俗语言学的全新研究材料、理论和方法,从多维视野开展综合性全方位立体式的“全息研究”。如比较成熟的公安言语识别,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金玉学结合本领域的研究分别调查、采录了一些至今仍在不同社会层面群体中流行的大量民间秘密语的鲜活语料,开设并编著了《警察应用民俗学》课程,在教材中特别提到对民俗语言学的应用研究。他还发表了一些颇有份量论文,如《论犯罪隐语常识在警务工作中的特殊作用》[3]、《论体态语言常识在警务工作中的重要作用》[4]等探讨民俗语言学的具体语类在警务工作中的具体应用情况和作用,在学界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对民俗语言学的应用研究实践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三、民俗语言学应用研究的特点
随着多学科的参与和导入,民俗语言应用研究的各个领域不断地获得开发和拓展,民俗语言研究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
(一)多学科的参与性
考察民俗语言学的研究队伍,我们不难发现,从事民俗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不只局限于民俗学、语言学这两个学科,民俗语言学往往被引入一些相邻的或相关的学科,除了与民俗学、语言学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还同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及公共关系学等诸多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领域有着广泛的联系。有的是从语言学、民俗学那里继承下来的是延续性的联系,如同民族学、社会学的联系,这是缘于它们在理论、研究对象与方法上的交叉;有的则是因为不同学科特定的研究视角,而这些则正是由于民俗语言学有可能为之提供某种富有价值、可资利用的观点、对本学科发展起到理论启示和借鉴的作用。
比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文章和论著有曲彦斌的 《略论语言与民俗的双向研究》提出“语言与民俗涵化运动而交织在一起或集为一体的民俗语言或语言民俗现象,孰为第一性”的问题,也就是“因民俗而生还是因语言而生的”,文章认为“两种情况均为客观存在。比较简捷的分析,是分别考察因民俗而产生的语言和因语言而生的民俗。应该说,这种微观的具体考察分析同对原生形态的语言与民俗总体的最初生成的宏观讨论虽有关系但并不矛盾”[5];黄涛的《语言研究的民俗学视角》[6]、《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7]、《作为民俗现象的民间语言》[8]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阐释了“民俗学视角的语言研究,不是把语言当作孤立的对象去分析它的语音形式、语法规律、词汇构造,而是把民间语言看作民众习俗的一种、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将它放到民众生活的沃土中去考察”;申小龙的《民俗事象的语言视界》一文探讨了语言与民俗的关系,认为 “由于语言与民俗在存在意义上的密切联系,民俗研究往往以语言研究为其发端”。“语言和民俗的密切联系首先在于语言是民俗的灵魂”,是“民俗历史的索引”,是“民俗心理的‘镜象’”[9];李志强的《民俗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则提出了民俗语言学和语言民俗学的研究中心不同,决定了其落脚点不同,“从民俗的视角去研究语言,和运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俗还是有区别的,民俗语言学不同于语言民俗学”,认为“现有的民俗语言学虽然提出了把语言和民俗研究进行‘双向、多方位’互动考察的设想,但是其最终的着眼点还是落在了语言学的研究上。语言民俗学,应该是以民俗研究为对象和重心,用语言学的方法去研究民俗事象的一个学科。在民俗语言学中,语言学是本体,研究的落脚点放置在了语言上,民俗在其中起着对语言的解释作用;而在语言民俗学中,民俗学应该是本体,是研究的中心,语言学则以方法论的方式,在对民俗事象的分析中被加以运用”[10]。这些都是民俗学者、语言学者基于自己学科的角度,对民俗与语言的关系与互动这个不可回避的命题做出的探究和回答。
(二)双向性
语言与民俗及其双向的涵化运动,是民俗语言文化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直观现实。民俗影响语言,语言的运用也影响着民俗,所以民俗语言学的研究不只是从民俗研究语言、从语言研究民俗的简单的视角问题,更是对二者双向互动的涵化运动加以描述和阐释,这其中既包括对因民俗而产生的民俗语言的研究,也包括因语言而生的语言民俗的研究,可以把二者视为一张纸的正反两面。
四、发展不平衡和诸多领域的空白
虽然民俗语言学的研究之初,就是源于跨学科研究的实践,是应跨学科研究的需要而生,因此从产生之初其应用研究就是受到较大关注的一个方面。近些年来,民俗语言学的研究由最初的青涩,逐渐趋于平和与成熟,学科理论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毋庸讳言的是,在应用研究方面,还表现出发展不平衡和诸多领域的空白,民俗语言的应用研究仍然是处于初级阶段,这些都是未来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是应用领域研究的不平衡。鉴于民俗语言学与多学科间的多缘性外部联系,随着民俗语言学基础理论的日趋完善和深化,民俗语言学的应用研究也日益显示出其广阔的应用前景,除了不断为相关学科提供可资借鉴的材料和方法,还在于通过渗透与传通对有关学科理论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的多缘性、多学科参与的特点,也导致了民俗语言学的应用研究很难形成比较系统、统一的开展,共识性的东西较少,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如在“对外汉语教学”、“公安言语识别和言语鉴定”、“辨风正俗”等学科领域的应用都有人在认真地研究,可谓硕果纷呈,收到的效果也是引人注目的。
如民俗语言学研究成果在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强,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股“汉语学习潮”。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语言在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理解中,起着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股热潮也促进了关于中国文化、中国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所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应在以往的语言内的基础上开出语言外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当下快速发展的汉语国际传播事业。”[11]其实,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与“民俗语言”的话题,早就有民俗语言学的学者做出了尝试和探索,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天津师范大学的谭汝为教授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较早地引入了民俗语言学知识,他于1997年开始给汉语言文化学院的外国留学生的高级进修班和本科班开设 《民俗和语言》的课程,引起了学生的浓厚兴趣。后又自编教材《民俗和语言》,分18课讲解民俗和语言的关系、汉字与民俗、语音与民俗、语法与民俗、修辞与民俗、方言与民俗、俗语与民俗、数字与民俗、人名与民俗、地名与民俗、颜色与民俗、生肖与民俗等。在此基础上,他主持了天津市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民俗语言研究”,并在2004年底推出了它的研究成果《民俗文化语汇通论》[12]一书。侯友兰评价它是 “开拓语言与文化研究新领域的一部力作”[13],刁晏斌评价它为“一部词汇与民俗文化综合研究的力作”[14]。《民俗文化语汇通论》是民俗语言学研究成果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得到融合与应用的最好范例。此外,谭汝为还有一系列的文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民俗语言对汉语教学的作用,如《民俗语言研究对汉语教学的作用》[15]、《民俗语言与对外汉语教学》[16]。此外,还有常峻的《民俗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17]、曲凤荣的《民俗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18]、王端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民俗语言与民俗解说》[19]、柯玲的《对外汉语教学的民俗文化思考》[20]等等,对民俗语言学研究成果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想法,有的甚至提出应“尝试以民俗事象为主线编写一套汉语教材”,颇具建设意义。
另一方面则还存在着诸多研究领域的空白需要去开垦拓荒。对于像一般的汉语教学、民族语言识别、考古、语言文字及语言政策制定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研究则显不足。
[1]曲彦斌.民俗语言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14-15.
[2]金石根.民俗语言学基本理论与应用研究研讨会在辽宁举行[J].汉语学习,1991,(1).
[3]金玉学,等.论犯罪隐语常识在警务工作中的特殊作用[J].文化学刊,2007,(1).
[4]金玉学,等.论体态语言常识在警务工作中的重要作用[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08,(2).
[5]曲彦斌. 略论语言与民俗的双向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3).
[6]黄涛.语言研究的民俗学视角[J].北方论丛,2000,(3).
[7]黄涛.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黄涛.作为民俗现象的民间语言[J].文化学刊,2008,(3).
[9]申小龙.民俗事象的语言视界[J].学术研究,1992,(3).
[10]李志强.民俗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J].民族论坛,2006,(8).
[11]鲁小彬.文化视野中的海外“汉语热”[N].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2-03.
[12]谭汝为.民俗文化语汇通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13]侯友兰.开拓语言与文化研究新领域的一部力作[J].江西社会科学,2005,(10).
[14]刁晏斌.一部词汇与民俗文化综合研究的力作[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5,(2).
[15]谭汝为.民俗语言研究对汉语教学的作用[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4).
[16]谭汝为.民俗语言与对外汉语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5).
[17]常峻.民俗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J].上海大学学报,2002,(1).
[18]曲凤荣.民俗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10).
[19]王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民俗语言与民俗解说[J].文化学刊,2008,(3).
[20]柯玲.对外汉语教学的民俗文化思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