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8副总师的精彩人生60年追梦大飞机
2012-01-10车军
◎车军
在互联网上,用任何一种搜索引擎,输入“顾诵芬”三个字,瞬间就会获得海量的相关信息。顾诵芬——中国著名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两院院士,歼8飞机副总设计师,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
今年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60周年,也是81岁的顾诵芬大学毕业开始从事航空事业60周年。
“仿制,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
2011年春天,由顾诵芬口述的自传——《我的飞机设计生涯》出版,人们捧之犹读“飞机设计苦旅”。虽然笔下文字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但呈现的却是“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的别样风采。那坦坦荡荡毫不张扬的叙述,是他60年工作经历的记录,亦是从事航空工业而磅礴九霄的情怀。
解放初期,苏联专家为我国援建过几个航空工业企业,其实当时中国的工厂充其量是复制厂,所必需的飞机设计规范等资料,人家不给。
可毕竟每一种飞机的诞生,都必须经过飞机概念设计和总体技术方案论证。我们难道甘心永远当苏联的复制厂吗?!当年,顾诵芬与领导和同事们痛彻心扉地感觉到,“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自己没有任何主动权”。
可喜的是,1956年8月当时的航空工业局下达命令,分别在沈阳112厂(即今“沈飞”公司)和410厂成立中国第一个飞机、发动机设计室,调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顾诵芬等到飞机设计室工作。徐舜寿任设计室主任,26岁的顾诵芬承担的是气动组组长的职务。
从此,在浑河之滨,一支荟萃新中国最优秀飞机设计人员的队伍开始聚集。“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贺铸《六州歌头》)”设计室不到百人,平均年龄22岁,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理想——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走到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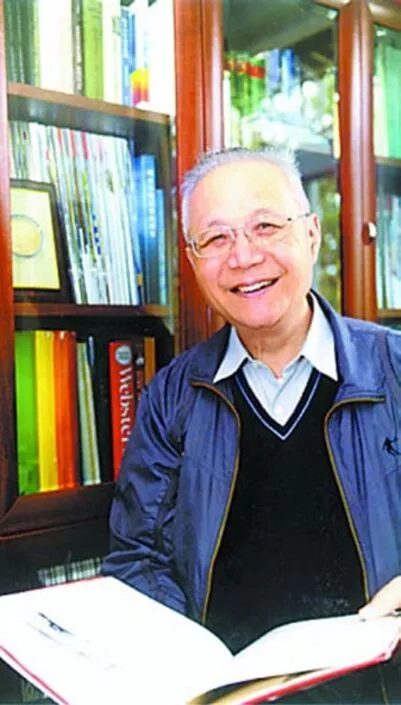
从小立志投身航空事业
顾诵芬1930年2月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顾元昌曾获朝廷“钦加四品衔,赏给正四品,封典覃恩,诰授中宪大夫”。父亲顾廷龙28岁时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39年7月,应友人盛情邀请,到上海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任总干事、董事。解放后,历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编著过多部大型重点图书。
家学如此渊源深长,国学大师的儿子为什么没有继承父业,而从事了科技工作?顾诵芬曾回忆说,“七七事变”爆发时,他正与父母住在燕京大学附近,7月28日那天,日军轰炸二十九军营地,轰炸机就从他家上空飞过,连投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二十九军的驻地离他家不到2000米,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
那一年他7岁,耳闻目睹,小小年纪就对飞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了他以后立志投身航空事业的缘起。
1951年8月,顾诵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分配到中央新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兄早亡,已是独子的他即将离上海远行去沈阳,令父母又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别离。父亲曾写日记说“舐犊之情,何能自已”,但仍全心支持儿子投身航空事业。
歼8定型,不会喝酒的顾诵芬酩酊大醉
1961年8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设计所(后称“601”所)在沈阳成立,军队编制,不久,顾诵芬从气动工程师的岗位升任一所的副总设计师,并被授予少校军衔。
1964年5月,歼8飞机开始设计之时,徐舜寿却被调离赴新任,黄志千成为新机的总设计师。黄志千与顾诵芬是“连襟”,他们的夫人是同胞姐妹。但非常不幸的是,就在歼8工作全面铺开之际,1965年5月20日,黄志千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时在开罗因客机失事而遇难,年仅51岁。
临危受命,顾诵芬等人组成的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1965年8月的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在沈阳接见了新机研制工作人员,顾诵芬跟随所里领导向贺老总做了汇报。贺老总听了他们的汇报,叼着烟斗,乐得胡子都翘了起来,激动地说:“就是要走中国自己的路,搞自己的东西。”还说,“歼8要早日搞出来”,“飞机上天,党、军队和人民都会感激你们的”。但令人悲愤万分的是,1969年6月,贺老总被迫害致死。之前,1968年1月,在“文革”中受尽摧残的中国飞机设计一代宗师、年仅51岁的徐舜寿溘然长逝。
歼8的研制在“文革”乱世中艰难前行。顾诵芬分管的任务繁重而艰巨,他对歼8飞机性能的关注和思考必须是全方位的。1969年7月5日,歼8首飞成功,人群一片欢腾。当大家欢天喜地去赴“庆功宴”时,顾诵芬却悄悄离开了人群,他赶着去思索下一步的试飞方案了。
顾诵芬一干起工作来就有股不要命的劲头。1978年夏天,歼8进行飞行试验,在当时没有所需测试设备的情况下,48岁的顾诵芬提出要亲自上天观察歼8飞机后机身流场,以彻底解决跨声速抖振现象。战斗机在空中机动飞行,会产生4~5个过载,这对从来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诵芬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而且,由于黄志千逝于空难,他的夫人和家人有了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因为不愿让亲人再承受对往事回忆的哀恸、惊恐和担忧。但是顾诵芬决心已下,说服领导、背着爱人,三次乘歼教6上天,用望远镜近距离仔细观察,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后来,顾诵芬带领设计团队提出了改进方案,终于彻底排除了跨声速抖振现象。
1979年年底,我国更新部队作战飞机迈出极其重要一步:我国飞机制造21年历程中一个辉煌里程碑的歼8飞机(白天型)完成设计定型工作。定型会一直忙到12月31日晚上10时才结束。定型会后,没有什么招待会,只是在二楼干部食堂,大家一起吃饭;顾诵芬与大家举杯相庆。要回家了,副所长一清点人数,找不到顾诵芬了。原来他已经大醉,正在厕所里吐呢!
顾诵芬不会喝酒,但那一天,他与众人一样,也用的是大碗。这是歼8设计者、领导者、生产者辛勤劳动得到国家、军队正式认可后的骄傲和兴奋,也是所有参与研制工作的人们实现久盼心愿后的欢乐和豪放。不会喝酒也不善于表达激情的顾诵芬,开怀痛饮。这是他自己的飞机设计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酩酊大醉。他想起走过的这么多年,经历的这么多事件;他想起贺老总,想起良师益友徐舜寿、黄志千……他们,竟没有看到歼8首飞,没有等到歼8定型这一天!
“我的余生就是搞这些工作了”
1986年,顾诵芬调到北京,担任了航空工业部第二届科技委副主任。
到北京后,顾诵芬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参加“863”专家委员会,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一些各界顶尖的科学技术专家一起从事关系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活动。
1987年7月,顾诵芬与国内科技界专家在北戴河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邓小平高度评价了科技界的成就,他说:“对你们在各自领域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这次接见在当时是一条轰动性的新闻。
到科技委以后,顾诵芬的视野更开阔了。他始终保持着抓紧一切空余时间看书的习惯,不断补充着新的知识。国外的技术发展最新动态,他了解得清清楚楚,至今81岁的人了,还依旧保持着在业内科学技术高水平状态。
60年来,虽然顾诵芬已在飞机设计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工程技术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并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但一向处事低调、淡泊名利的他作风依旧——每天很早到岗上班。他说:“我的余生就是搞这些工作了。发现对现有工作有用的书籍、资料,就组织或请人翻译。这些书,如果有人愿意看,大家还是会有收益的。”
“天戴其苍,地履其黄……前途似海,来日方长。”不老的顾诵芬,仍感于际天空阔,一腔壮志从未消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