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海寺壁画:明代非主流绘画中的典范
2011-10-11彭颢善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嘉兴314001
⊙彭颢善[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1]
⊙彭尊善[上饶师范学院, 江西 上饶 334000]
法海寺壁画:明代非主流绘画中的典范
⊙彭颢善[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1]
⊙彭尊善[上饶师范学院, 江西 上饶 334000]
在明代文人话语权的强势打压下,画工画由主流绘画变成了非主流绘画,而文人画反客为主成为主流绘画。本文将从“骨法用笔”、“随类赋彩”和“传移模写”三个方面来分析法海寺壁画,阐明这些并不具备与之抗衡的画工们依然创造出了典范之作。
法海寺壁画 非主流绘画 文人画 典范
明代画工画在文人话语权的强势打压下,由主流绘画变成了非主流绘画,而文人画反客为主成为主流绘画。相对于文人“集团军”,生活在底层的画工们不具备与之相抗衡的力量,但是这些画工们是否就此偃旗息鼓,或者是一蹶不振呢?也许法海寺壁画能给我们一个答案。
众所周知,文人画提倡“以书入画”,强调绘画以笔墨为中心,追求在笔墨的运用过程中抒发自己的性情与感受。可想而知,他们当然对“六法”中的“随类赋彩”、“传移模写”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着意之处是“骨法用笔”。那么,我们就从文人最在意的“骨法用笔”和最不在意的“随类赋彩”、“传移模写”这三个方面来分析法海寺壁画。
一、骨法用笔
“气韵生动”是“六法”的总的法则,所以谢赫将其置于“六法”之首,而“骨法用笔”第二,这足以说明中国艺术以线造型的特点。明代汪轲玉在《论古今衣纹描法一十八等》中也阐明了线描在中国古代人物画中的重要性。
如战国帛画《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就是以流畅单线勾勒为主,设色平涂为辅,生动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
来自于西域造型风格的“曹衣出水”,“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从早期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出,它流行于北朝时期,在莫高窟第272、275、263、254等北凉、北魏洞窟的壁画雕塑人物衣纹线条中都有所应用。“曹衣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线描技法,更是一种外来的造型风格。这种线描技法在魏晋南北朝时风靡一时,直接影响了隋唐时期的佛教绘画。”①
“高古游丝描”也是中国早期人物画传统线描技法之一。“顾恺之画如春蚕吐丝,初见甚平易,且形似时或有失,细视之,六法兼备有不可以语言文字形容者……其笔意如春云浮空,流水行云,皆出自然。”②足见此类线条的特殊表现力。敦煌莫高窟西魏第249窟窟顶白描画《群猪图》的线描即是比较典型的高古游丝描。第285窟东、北二壁的秀骨清像人物造型亦是以高古游丝描塑造,其人物褒衣博带,线描周密,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晕饰,更使其显得飘飘如仙,有顾恺之《洛神赋图》之遗风。
此外,早期壁画中的线描,还有行云流水描、琴弦描、铁线描等,行笔圆润流畅线条均匀,后来线条逐渐变粗,刚劲有力并富有弹性。
唐代的线描在继承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之上深化了线条的意蕴,创造了笔法丰富的“兰叶描”,进一步展现出了画家超凡的表现力。“兰叶描”为吴道子所用,清郑绩撰《梦幻居画学简明·论工笔》说:“如韭菜之叶旋转成团也,韭菜叶长细而软,旋回转折,取以为法……旋韭用笔轻重跌宕,于大圆转中多少挛曲,如韭菜扁叶悠扬辗转之状。”③如第103窟盛唐壁画中的《维摩变·方便品》,人物在神形兼备的基础上线描雄劲有力、略施淡彩,体现出“吴装”疏体绘画的风格,是敦煌唐代壁画中的精品佳作。唐代敦煌壁画线描造型疏密有致、柔中有刚,落笔、行笔、收笔都有粗细的变化,绘画气势宏大构思巧妙,运用高低晕染的设色技法,造成形象和情感内外结合的艺术特点,将外来艺术兼收并蓄,呈现出中国画及敦煌壁画线描发展变革的时代特征。
宋代是中国线描造型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历史时期。文人画的出现从内容到技法都给绘画带来了新的面貌。线描在技法上更进一步强调骨法用笔,将超脱自然的笔墨情趣揉入书法运笔之内涵,使画面充满诗情画意。如清恽寿平所说:“气韵自然,虚实相生。……今人用心在有笔墨处,古人用心在无笔墨处,倘能于笔墨不到处观古人用心……”④于是以书法运笔,墨分五色,追求“以形写神”、“贵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减笔画即写意画开始形成并逐步完善。
西夏、元敦煌壁画中的线描,除了继承唐、五代绘画中的各种线描外,又增加了一些运笔有更多变化的线描,如南宋梁楷从吴道子、李公麟笔意中化出一种“折芦描”的线描形式。此法画衣褶线描用笔锋较尖和细长的笔,转折处均着意顿挫,形成似芦苇被折之状。在唐代多用在天王、力士、老僧的上眼睑及菩萨的口角线上,如莫高窟第217窟的初唐比丘头像。“钉头鼠尾描”自宋至明清以来非常流行,其用笔方法犹如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之运笔,落笔力透纸背,先以侧锋顿笔,使起笔形如钉头,行笔中笔锋转中锋,收笔轻缓,线形头粗尾细,犹如鼠尾。南宋马远山石多用此画法,所以又称为“钉头鼠尾皴”。榆林窟第3窟和莫高窟第3窟的西夏、元代壁画中的人物衣纹、飘带及山水的线描和皴法中有见使用。明清画家陈洪绶、任伯年等多用此线描画人物衣褶等。
还有一个有必要了解的是“减笔描”,即“减笔画”,现在称为“写意画”中的运笔技法。宋代以后,线描在“骨法用笔”的基础上更强调以“书法运笔”来突出笔墨结构,将笔、墨、色融为一体,达到言简意赅的作用,至晚明则出现了明显的工笔与写意的分水岭,甚至成为两极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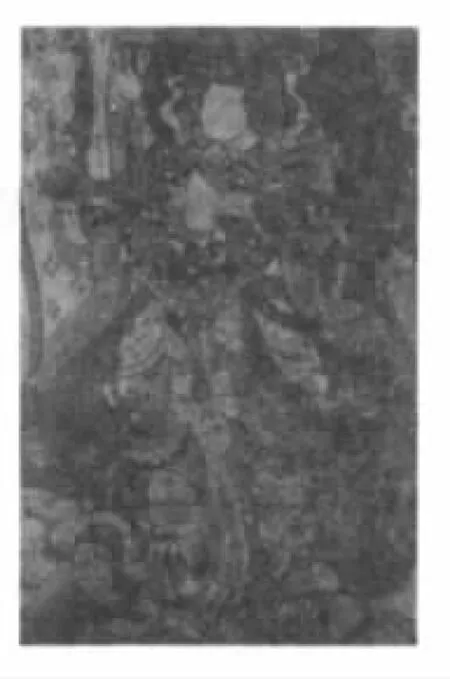
我在此扯这么多,为的是说明法海寺壁画沿袭了魏晋唐宋以来以线造型的原则,并在壁画中充分运用了各种线描技法塑造形象。
不同的线条,不同的描法,表现不同的物体和不同物体的质量感。即使是表现同一物质也要求通过运笔的轻、重、缓、急,行笔的提、按、顿、挫,墨色的干、湿、浓、淡,线条组合的疏、密、繁、简等,表达物体的转折结构和形体变化,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对事物的认识。这是中国画毛笔线描的基本要求,也是最终的要求,更是衡量作品优劣的重要因素之一。法海寺壁画就完全达到了线描表达的最高境界。尤其是水月观音像充分调动了线条表现功能。此画虽为工笔重彩,但色不压线,线条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人物的肌肤结构,根据人体骨骼肌肉的转折,在运笔的变化中巧用心思,充分表达了人物的形体结构和神情动态。如水月观音面庞的描绘,自颧骨处往双颊下行,行笔渐行渐提,铁线描的形质向游丝描转变,利用运笔提按带来的线条虚实感,这样的刻画让人感觉到观音的脸庞圆润光泽而富有弹性,就像少女般的脸。至下巴处又渐行渐按转换成铁线描的形质,充分交代出圆嘟嘟的下巴与其颈部的关系。特别是手臂的塑造,用铁线描略加晕饰就能变现出手臂圆润的立体感,充分发挥了线描的表达能力,运笔准确熟练,线条的变化也体现质感。观音手掌的描绘也很精湛,铁线描柔和的起伏交代了手的骨骼结构,兰叶描的运用刻画出了观音修长而丰腴手指。特别是观音手掌虎口处的描绘,兰叶描运用得非常准确而简练,线条自大拇指的腹部向手掌运行,至虎口处提笔运行,紧接着又按笔交代出大拇指与手掌的转折关系,最后迅速提笔出锋,圆润的手掌霎时栩栩如生。
法海寺背屏后面画有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分别有善才童子、最胜老人、驯象驯狮之侍从,其中最胜老人虽为陪衬,但画家花费很多的心思去着意刻画,运笔描绘十分考究。眼睛四周线条紧扎排列,眉宇间下笔轻按,至眉骨处急速旋转下行,线条紧劲,把最胜老人眉宇间全神贯注的表情完整无遗地表现出来。紧接着提笔右行到鼻骨处,过了鼻梁骨又渐按缓行,直到鼻孔一笔勾成。一笔之下,轻重变化,鼻梁的骨感和鼻头都自然真实地描绘出来,表现了老人饱经风霜,精神矍铄的风骨。眉毛、胡须、头发以轻起速行的用笔,一根一根地描摹,使毛发就像从皮肤里生长出来一样真实自然,蓬松飘逸。衣服裙带运用铁线描、钉头鼠尾描,舒展流畅,运笔豪率,表现出老人衣服衣褶线的组织有繁有简,疏密有致。老人右手紧握竹杖,竹杖运用折芦描,充分体现了老年人的干练,加强了人物年龄高迈、阅历丰富的感受。真是如神妙笔,其间韵致,只可细品意会,而难以言传。
最具神采的是水月观音像的白纱衣(见图),至少运用了兰叶描、钉头鼠尾描、游丝描等描法,既有顾恺之“春云浮空,流水行云”的自然之感,又有吴道子“衣带当风”中衣袂飘飘的雅致。其笔法之生动,形象之鲜明,说明明代画工对传统经典的继承与创新的能力。如果从白纱衣的用笔来看,说它是书法用笔并不为过,它的每一根线条都包含了书法的三种基本的运笔运动方式:“平动、提按、绞转。”⑤从书法用笔运动方式来看,“高古游丝描”就是“平动”的用笔方法,“钉头鼠尾描”就是“提按”的用笔方法,“兰叶描”就是“绞转”的用笔方法,但是为何晚明画工就能做到如此生动的形象塑造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他们坚持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这个原则。书法用笔介入绘画是为了造型形象的生动,它的介入有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临界点,书法介入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图而喧宾夺主了。这也就是我们在法海寺壁画中难以发现减笔描的原因,当然并不是说减笔描不好,而是在绘画中这种描法基本上不属于工笔重彩画这个体系。减笔描在倪瓒的绘画中就用得非常的恰到好处,既塑造了形象又表现了笔法。
法海寺壁画在线描方面,集高古游丝描、行云流水描、琴弦描、铁线描、兰叶描、钉头鼠尾描、折芦描等于一幅画面中,堪称现存古代中国壁画中为数不多的工笔重彩画经典作品。虽然由于佛教内容的限制,使作者不能随意在壁画中抒发情怀,发挥其他技法和创作优势,但仅仅在这新的笔法形式中就已体现出了晚明画工对宋以后书法运笔的深刻含意的理解,同时为世人提供了一个“以书入画”的最佳参照物。从这一点来说,法海寺壁画中的用笔并不逊于文人画,它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而且合度。

二、随类赋彩
“随类赋彩”在法海寺壁画的运用非常典型,充分体现了绘画以造型为中心,笔墨色彩等形式服务于造型的“六法”规范。
法海寺壁画的画工使用新的技法逼真地摹画出景物的不同质地与闪烁的光泽,在二维平面空间内虚幻地呈现三维空间的真实感,逼真地反映现实空间的幻觉以及追求物象的知觉相等物。画工在壁画创作中大量使用黄金。“据专家考证,用金方法就有七种之多。‘沥粉堆金’、‘叠晕烘染’的绘法,使壁画有一种金属感,把天女们的珠光宝气表现得淋漓尽致。(见图)壁画所用色完全是矿物颜料,壁画中的髭部位叠晕烘染竟达七层。通过特殊的处理,韦驮的兵器、武士的铠甲有一种金属的肌理和重量的感觉。”⑥观音全身环配璎珞珠串共有1400多个,完全以红绿蓝宝石真实的质感多层次积色,成为立体镶嵌在各个部位,有的晶莹透明,有的散发出五颜六色的光泽,流光溢彩,目不暇接。这些创作手法在我国历代壁画中绝无仅有。法海寺壁画经历了560年,至今仍然金碧辉煌,制作工艺的科学考究、使用材料的精细多样是其重要原因。
更为精妙的是观音披纱,在不足0.7平方米的画面用了近两万笔去绘制,可见笔墨工量之大,这在其他壁画中是见不到的。菩萨的开脸近一平方尺,这样大的面积把脸像画得英姿俊俏,层层晕染,皮肤粉嫩滋润,白里透红,如花似玉。在多纹罗裙白描的线条中,有一米左右长的线段几十条,这些线段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曲到直,就像流畅曲水,潺潺而过,一气呵成。罗裙着色近一平方米,在这一平方米的面积里,要随着线条画出深浅明暗70多条的罗裙皱褶,表现出了面料的丝质感,再作提花团荷,以表菩萨的衣着尊贵圣洁。观世音菩萨这幅画,人物塑造、体态结构、服饰刻画中赋色技巧以及白描线条的形式美无可挑剔,美轮美奂。至少目前还没有哪一处壁画能与这幅观世音菩萨画像相媲美,这都是因为服务于造型的笔墨色彩精细工丽所致,同时也表现了画工们“应物象形”的造型能力。
可以这样说,法海寺壁画中的形象个个精美,这是画工们在“骨法用笔”、“随类赋彩”等方面卓越能力所致。
三、传移模写
“传移模写”是魏晋至明清壁画人物造型方面使用较多的一种法则。如果要谈这个命题,我们无法回避“粉本”与“画稿”的问题。胡素馨说:“我们在敦煌石窟和塔尔寺建筑中看到工作方法的技术类同点。寺庙天花顶上绘画是很不方便的,画匠必须置画笔垂直于天花顶,他的头则处于很不舒服的角度,为画好复杂的花形和抽象的图案,他必须离被绘物体很近而无法后退,并且以好的角度观察它。粉本使这项工作变得容易、准确和有效率,与粉本相关的时间跨度可导致当代和中世纪关于画匠应用的其他结论。与绘制壁画有关,而与纸和丝绸上作画无关,敦煌发现的纸质和丝绸画都不是窟顶上复杂的重复出现的图案。敦煌石窟里描述性场景画明显是手画作品,通常见于易于绘制的墙面上。敦煌现存素描稿多是用于绘制壁画和丝绸的手画稿,显示出画匠们还用其他方式来绘制窟顶图案。这些画稿的数量表明,他们是绘制这些作品时参考这些画稿,而不使用粉本,粉本有其特定的用途。晚唐第107窟和五代第55窟破损处表明,在墙的底部,壁画是用黑墨以手画绘成的,著第一层色后再在其上覆另一层,同样用黑色。在纸卷上绘画,如果一图样被摹写,印描的痕迹将使每一特征都一致,因此,敦煌现存的佛是手绘的。”⑦
无论是著名的画家抑或是普通的画工,对于鸿篇巨制且技术难度要求都非常高的壁画创作,他们都需要以既往的粉本为参照,再从中加以富有个性的变化与改造。这些白描画稿的使用方式为:“除有将全壁整铺经变汇于一卷的大型粉本外,常是利用化整为零的办法,把它分为若干局部构图,以便于携带使用,对于图中主要人物,又多备有具体的细部写照。这两类粉本相互补充。画工先据前一类粉本安排构图,然后依照后一类粉本细致地去勾勒图像中的具体形象。……至于粉本的来源,看来也可能有两种途径,其一是依据前人留下的粉本,传抄模写;其二是选择前人已经制成功的壁画作品,对照速记模写。”⑧
所以,当时的画家与画师根据国内流行画样、外来画样制作,或者创造出新的画样,或者推广新的画样。曹家样、张家样、吴家样、周家样以及“文殊新样”⑨等,都曾在敦煌流传,并且可以找出其影响的遗踪。
同样,在法海寺壁画中,也可以找出魏晋唐宋时期的遗踪。法海寺壁画中的飞天(即香音神)手捧托盘花束,上裸下着罗裙,凌空飞舞的姿态与北凉时期敦煌第272窟顶北坡的飞天一般无二,只是北凉的飞天是裸体的,而此处的飞天上裸下着罗裙。五代时期的榆林16窟天龙八部之一、四天王木函彩画以及敦煌100窟四大天王与法海寺中的韦驮及四大天王形象也很相似,而且甲胄的造型也有类同之处。还有,法海寺壁画中最精彩的部分水月观音的坐姿与宋代敦煌431窟前室西壁门上的水月观音非常相似,二者都是右腿曲起,左腿盘坐,右手搭在膝上,左手拄触罗裙,体态潇洒风流,落座大方。不同的地方是法海寺壁画的水月观音是正面而坐,似乎在接受人们的礼拜抑或若有所思地在俯察人间,而宋代敦煌431窟中的水月观音是双目凝视,神情悠然自得,两者不同的神情跃然壁上,反映了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特征。这就是“粉本”和“画稿”的流传以及历代优秀画师在前人经典基础之上的创造所致,也说明传移模写在壁画人物造型中的扮演的重要角色。当然这也是宗教内容的稳定性决定了绘画内容的稳定性,壁画以稳定性的画面内容更能有利于传播它的宗教教义。难怪有的学者说:“法海寺壁画《帝释梵天图》与善化寺释梵天部彩塑沿袭着唐宋一脉相承的传统样式。”⑩
由于粉本的雷同、宗教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宫廷绘画模式的巨大影响和不同地区画工的频繁流动,中国各地元明时期的寺观壁画在风格上显示出极大的同一性。但是从法海寺壁画那明人武士般的天王形象和文人般的信士,以及那些让世俗人生活在传统里的小孩、妇女形象来看,无不让我们为之叹服。它那广袤雄阔、崇高肃穆的画境也让文人画家感觉到自己捉襟见肘的“小”画境。
四、结 语
明代画工画在文人话语权的强势打压下,由主流绘画变成了非主流绘画,但是画工画并不全然的偃旗息鼓,或者是一蹶不振。法海寺壁画的创作者在文人画的笔墨这个强项范畴中也做出了可以相提并论的成就。在文人画不屑一顾的“随类赋彩”、“传移模写”两个方面也深化和完善了“六法”的规范。其实有成就的画工并不止于这些,如晚明时期“波臣派”肖像画家曾鲸及其弟子们也创造了许多让文人为之欣喜的经典作品。
① 吴荣鉴:《敦煌壁画中的线描》,《敦煌研究》2004年第1期。
②③ 余昆编:《中国画论类编》,台北华正书局1984年版,第476页,第571页。
④ 沈子承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329页。
⑤ 邱振中:《书法的形态与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57页。
⑥ 王辉:《论法海寺壁画的人文主义精神》,《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⑦胡素馨:《模式的形成——粉本在寺院壁画构图中的应用》,《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
⑧杨泓:《意匠惨淡经营中——介绍敦煌卷子中的白描画稿》,《美术》1981年第10期。
⑨ 荣新江:《敦煌文献和绘画所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⑩ 金维诺、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237页。
作 者:彭颢善,硕士,嘉兴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服装设计;彭尊善,硕士,上饶师范学院副教授。
编 辑:古卫红 E-mail:guweihong007@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