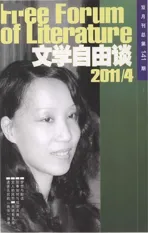扯住那苏格拉底的衣袂
2011-03-20文林雪
●文 林 雪
据传,在哲思风习浓郁的古希腊雅典,人们连走起路来也有一种哲人范儿,长袍曳地,双手背后,漫不经心中透出闲散和优雅,一会儿与碰到的人和风细雨地探讨什么,一会儿又演绎成流传千古的雄辩。后人甚至断定年轻的柏拉图就是这样遇上苏格拉底的。读读柏拉图的对话录,我们经常能找到类似的场景:苏格拉底有时在城中漫步,有时在角落里深思,有时也走在路上,他总会被那些欢快的、热情的年轻人在雅典随便什么地方找到,被当街拦住或者干脆被拉住衣袖,期待和他一起讨论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知识的本性是什么、善与恶的标准在哪里……
相对于真理、正义、知识、善与恶一直是古今中外伟大诗人的特殊激情所在和崇高的经验来说,诗人震海面临着所有生活在和平和平庸时代诗人共同的选择:要么不懈努力追溯人生终极意义、索要生活的真相,形成成熟诗人的使命感,并最终完成命运赋予的使命;要么在一个诗歌精神失血、历史承载力萎缩的当下疼痛、绝望。
诗人震海的诗集《蓝镜》中的组诗《大海落叶》,是以回忆的语气和在场的身份开始的。它充满了对澄明之境的渴求,对永恒事物的谦卑。
被扯住的那苏格拉底的衣袂,俨然成为一种象征。
《大海落叶》里的诗作来源于诗人一年前的一次台湾之旅,而后才有后来持续近一年的灵感在智力、精神层面上的爆发。对于大多数内地人而言,“台湾”至今还是一个曾被异化了的地理名词。震海尽自己所能,在七天的时间里,跨越政治、历史和心理距离,不但尽力了解了她,还尽其所能,超越政治、地理、历史的概念之上,演绎出了故土般的生活的、感情的、有温度的诗篇。接纳、搜索、删节、连接、提纯、浓缩后,是一首接一首充满新鲜认知和活力的诗句。它们不拘泥于制造警句和严谨的节奏,而是像天气一样,有最自然的结构、开篇和句子。
当我欢快的双足登上这些幸福的音阶/快乐之岛,美丽之岛,落叶/之岛啊,此时于我的耳际传来/轻柔之声——大海上,纷纷扬扬/大海落叶,大海落叶纷沓而至
在这组诗中,虽然只是在某个侧面表达震海在现实之旅的观察和深思,同时,它们又是一幅幅眼睛里的风情,头脑里的记忆和心灵的剧场。从台北到高雄,从平原到山地,从腹地到海角,诗人沿着雨、风、阳光、飞鸟、叶子、梦、蓝天、旗帜、灵魂、秘密组成的意象行走,穿越那些风景里的民歌、同宗同系文化融成的河流前进。所有这些由现实到精神的阅读,形成了诗人诗作里精彩的情节。
然而,如果《大海落叶》只是一组他乡之诗域外之诗,只是描写了风景、心路在打破隔绝后的欢呼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有隐痛,有历史真相,被修改记忆的复原,有诗人书写的、诗人自己和台湾正过着的生活——“这就是台北,可辨依稀的容貌,今日/的安逸,和清新的未来。我猜测/有多少行人,像我,频频而顾/这些路人,用我的眼睛,频频粉刷/和见证我未读过的历史和沧桑”,诗人在繁复的词语意象的后面,也努力在为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和群体共有的孤独和痛苦——往事、人物找到了共同的渊源。“大海的深度”好比人生中不可言喻的命运,生存中不可预测的残酷和荒谬,都可以在文化的河流里洗净伤口,镇静灵魂。使本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如同珍珠的同胞,用一根柔弱又强韧的文化将珠子串起来,从而完成心灵对信仰、宗教、民族和社会及人群的归属。
震海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即使生得太晚,即使错过了苏格拉底,错过了《天问》,错过了唐诗宋词,错过了民国、二战、国共合作又不合作等等历史,诗人还是亲历了一个特殊时代被逐渐唤醒的记忆。它缓慢、低垂,是真正的历史老人的步态,却还是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我们今天拥有在乡村级的民主和社区的公平的最底线。
与60年代出生,且储存过敌对政治记忆的诗人相比,他的对立情结几近于无。一切都在变化,不变的,是诗人的心智和情怀。不止此岸内地,在彼岸台岛的作家诗人们也在以一种新的言谈方式,对历来奉为神圣的政治信仰、历史诠释甚至民族潜意识,作大胆的嘲谑与质疑,从而以一种新的观照方式向根深蒂固的文学文化传统,向一切威权,一切成规,作深层次的颠覆。相比较逐渐解密的历史档案和不断公开的回忆录,好的诗歌只能是一种隐语。
一个诗人在一个由权力、媒介和被商品时代消费着的大众共同构成的暴力时代,会被怎么塑形塑身塑造灵魂?因其问题和答案都日益呈现,所以这个我们身处的时代才使命迫切,意义深远。
被扯住的那苏格拉底的衣袂,已然成为一种象征。
问题是,那趋前去拉扯苏格拉底衣袂的人,如今何在?
震海在写出《蓝镜》中的那些诗作的时代,除了真理模糊,正义消退,理想和激情作为一种集体失缺,已经使中国社会泪腺萎缩、泪水稀薄。上世纪80年代,作家王朔在对小说写作诸多“惊骇性”的突破中,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塑造了“橡皮人”形象。20多年来,“橡皮人”由一类人物的初步定义,到一种疾痼积患俨然到了晚期的社会人格,再到一种文学价值批量沦丧,书写能力集体尽失,审美趣味每况愈下,越来越“完善”到一种“橡皮主义”:理想被“归零档”,包括梦圆梦灭梦醒,精神被“格式化”,精神幻灭的人群,无关痛痒的写作,不着血肉的文笔——如何能使一个人人都奔波在“成功”路上的时代慢下脚步,数数心跳和大地的共鸣?如何在板结而滞重的阶层之间,插进一根旋转的流动的杠杆,使财富成为贫穷的明天、尊严成为卑贱的终结?在橡皮时代,谁还能在阅读时,让眼窝奢侈地潮湿?谁还有本事用一本诗集、一首诗让别人的眼泪在飞?谁还肯去追溯发问?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和震海有过几次针对诗歌话题的交流。和许多青年诗人一样,震海也认为每个诗人对时代都是负有使命的。都有责任表现和担当自己的时代。这当然是一种相当进取的态度:诗人用诗句探索着轰轰烈烈向前奔跑的社会,努力寻找能安放人类灵魂的伊甸园。并通过对公平和正义的追寻,成为支撑个人信念和群体的动力。诗人们都在被多变而复杂的写作方式吸引,都在尝试文本创新,和词语神秘的内在节奏。在世俗化的商业泛滥被普遍接受、诗人文化身份却逐渐流失的现实中,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越来越貌似某些诗人生存策略的转折,而不是最后的灵魂倾诉。消解荒诞的轻浅谑浪,自以为是的冷漠隔世,诗歌越来越像一个个遗梦幻灭。真理和日常生活对应在文本内部,日益成为难以跨越的障碍。如果诗人不具备“规避”的能力,或许就会在起步之初被“套牢”。
年少的路人啊/你可认识我,来自大陆的一阵轻风/一把伞,一些零星的形象,一样迷人/翔实、年少而透明的笑语。
——《纪念之初》
车子开得飞快,人和静物都擦肩而过/就这样发生了无数次,一座座山/就像这样翻来覆去地飞逝
——《灵界之门》
在这些轻盈的诗句中,诗人震海似乎找到了对策。自古以来,一直就有“轻文学”和“重文学”两种形态之争,既然有学者研究诗句之间的“张力”,那也应该有相对应的“浮力”:“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卡尔维诺语)。作家们在旅途中数度被景色、影像、音乐感动得眼眶湿润时,震海已经把那些珍贵的、在橡皮年代难得一现的眼泪,播洒到他的诗行里。
从组诗的标题《大海落叶》,到这组诗呈现出的缤纷繁复的意象,诗人震海把诗歌历史中某种无限探索的对象,变成日常生活中可以企及的目标。少有狂躁,更无夸张,只有对那些被分裂的生活中人们无法躲避的沉重命运表示出来的一种苦涩的认可,这不仅仅存在于祖国曾命定遭受的那种极度的、无所不及的受压迫的处境之中,也存在于我们大家曾所处的人类命运之中,我们都是幸存者。往事沉重,大海苍茫,星空伟大“在夏季的夜空中浮动着暗暗的花香”。只有凭借智慧的灵活和机动性,我们才能机智地从一个花香涌动的角度重新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
1977年1月10日,《新观察家》刊登了贝尔纳尔-昂利·莱维对罗兰·巴特的一次访谈,在问及欧洲习惯于用盐来比喻当今知识分子时,罗兰·巴特做出了如下表述:在我看来,我要说知识分子更像社会的垃圾,严格意义上说的废物。乐观主义者会说知识分子是一种“见证”,我要说,它只是一道“痕迹”。无用,却危险;一切强大的体制都会试图协调知识分子。一种人们为在一个受到控制的空间内限制语言的幻想和繁盛而保持的令人讨厌的增补。
还是要说古希腊。苏格拉底灿烂之后,后期的诗人转而聚集在雅典独裁者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的朝廷了,柏拉图成为锡拉丘兹(Syracuse)的暴君狄奥尼修斯(Dionysius)的谋士,亚里士多德则亲自担任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意大利的文人簇拥在科西摩·梅第奇(Cosimo de'Medici)和洛伦佐·梅第奇(Lorenzo the Magnificent)的周围。伊拉斯莫(Erasmus1466-1536年)是尼德兰人文主义的卓越代表,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旗帜,和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在写著名的小册子时,留出一只眼盯着有朝一日成为君主高参的前景。为了同样的目的,伏尔泰陪伴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旅行,狄德罗则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朝廷逗留。
从被扯住的那苏格拉底的衣袂里,诗人啊,掉出来的是一粒糖,还是一粒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