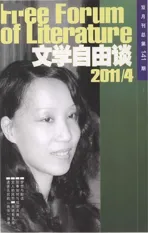遗害无穷的“荐书” 浪潮
2011-03-20文/狄青
●文/狄 青
王小波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银河的第一封情书,是写在一张五线谱纸上的。王小波是这样写的:“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在那样一个年代,文学普遍还被喜爱她的人轻拿轻放,写作者也好,阅读者也罢,面对字纸,内心除了敬惜之外,纯净的心思如同是在拿文火小心地去煨一只得来不易的肥羊腿,生怕加了猛火下了猛料而伤及了味道。没有人会怀疑,王小波的文字足以启开的不止是李银河一个人的心扉。然而,那可能也只是带有那个时代标签的文字。如果时光真如网上那些穿越小说一样可以由上世纪80年代直接转换到当下,王小波还会写这样的情书吗?我是存疑的,这与王小波的文学追求和文字功底无关,却与时代的口味有关。相对应于人们当下普遍的重口味而言,情书无疑显得做作、不直截了当,越是优美动人的文字越是显得矫情,倒有些像了委婉的拒绝。情书的功能早已被短信、QQ、MSN、飞信私聊所取代,尽管没有一点闪转腾挪的铺垫,上床也好,一夜也罢,都可以被精打细算的男女双方在网上轻易搞定,但这也正好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口味相近。君不见在“非诚勿扰”上,连生几个孩子都由初次见面的男女双方事先拉勾上吊地沟通好,还有什么是不好直截了当摆在桌面上谈的呢?情书无疑属于冷兵器时代,配合那个时代的是小米稀饭和咸菜,我们当下要的恐怕就是这样浓得窜鼻的重口味。
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让我们的社会由神圣转入世俗,也让文学的口味变得越来越不靠谱。这是因为,当文学对它所处时代的精神生活显得无足轻重的时候,为了想方设法融入时代,为了本能的自救,再淡定的文学从业者也可能会慌不择路,这无疑也是一种文学的“祛魅”。“祛魅”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原意是指现代技术以及科学世界观对世界一体化解释的解体。祛魅已经成为一种与时代合拍的世界观,指向主体在文化态度上对于中心、崇高、权威、经典、宏大叙事、确定化的颠覆和解体。于是,被祛魅的文学像是被去了势,变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它不仅嫁接了庞杂众多、纷乱无序、既相互敌对又充满共谋的不同语流,还对各种极端的口号、不负责任的臆说照单全收,因为信手拈来,因为不负责任,大众审美就成为文学的“应召”,随时可以被弃如敝屣,又随时可以反客为主,权力、精英和大众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亲密无间地结合在一起。为了讨好大众强势文化,当年北大一教授语出惊人:“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个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的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所以,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
是的,纯粹的精神性天生不具有精神强力。科技、金钱和商业运作的有效性,令文学作品变得越来越产品化,文学批评也越来越像是从属于产品销售的说明书和操作指南。而当代文学的种种无疑令人疲惫,却还要强打起精神来鼓吹,靠什么?和风细雨不行,蹑手蹑脚更不行,那就来重口味的。当性爱、惊悚、悬疑、青春、官场、职场以及底层题材的重口味轮番上场亮相之后,形式上的“重口味”就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事实证明,“形式主义”至少在当下的中国还是屡试不爽的。就像月饼,原本就是土作坊做出来的百果馅月饼,被裹上印刷精美的包装盒,再系上金丝带,就从乡下的副食店移转乾坤进了城市的五星级宾馆,至于消费者吃到嘴里的是什么东西,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既然读者喜欢哲理,又不想太动脑筋,我们就给提供简单哲理,比如《心灵鸡汤》,比如放大版的《心灵鸡汤》——《狼图腾》。简单的一本书,一本简单的书,无非是狼群生态,丛林法则,为了弄得“深邃”,为了达成一部分人想要哲理又不想太动脑子的需求,便硬要往中国古代哲学上拉扯。在这些年“形式”上的重口味“轰炸”中,于我而言好的一面是,原本已经多年看不到的一些作家的文字突然开始撞入眼帘,比如马原、孙甘露等人,甚至还有书商把徐星也给搬了出来,这几位都是我年少时喜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即使放到当今也是排在前排的作品。他们当年作品中的先锋性也成为了回荡在今日文坛上空的绝响。没错,我喜欢他们当年的小说,但这并不代表我喜欢他们当下卖力帮忙推荐的作品,而且我怀疑,对于某些明显与他们当初创作风格不符的作品,他们是否看了抑或是否认真看了,于是这就变成了坏的一面。
在封面、封底、腰封上印上圈内名人的推荐语,这曾是多年前书商操作美女作家作品的惯用手法。被证明肯定还是管用的,否则不会在当年的基础上不断变化、发展。但区别也明显,细心人发现,在当年,大凡美女作家的小说,基本也就是那么几位在摇旗呐喊;而大凡网络写手的作品,也基本就是那么几个人在推波助澜,比较固定,而且他们的所谓“推荐语”也还“老实”,没敢往“大”了说,换去推荐者名姓看着也都差不多,甚至口气、体例、风格,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差错。这就像当年流行的一种专为领导干部们研究出来的“书法速成”法,据说悟性差的一个月也能秉笔挥毫了,悟性强的不出一周就能给饭馆酒店以及基层单位题词去了。
作家陈河写的《沙捞越战事》我至今没有看内容,当初引起我注意的是这本书的腰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我孤陋寡闻,还以为是茅奖又评完了一届。结果下面却还追加了几个字,当然也是最关键的几个字——“谍战专家麦家”,原来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全力推荐”这本书。这令我想起某年去西北,在一小镇墙上惊见一标语——大力开展群众性爱!便以为看错了,转过去仔细端详,结果发现墙的拐弯后面还有几个大字——国卫生运动。我当然不会幼稚地认为这本书因为麦家的推荐就会变得更好抑或更坏,但是不是由此会变得更好卖我没有发言权。或许是,也或许不是。我发现,文学书籍以名作家推荐为卖点的占绝大多数,而且由最初的一个名作家推荐一本书,变成如今“百名作家震撼推荐”抑或“两岸三地数十位作家联手推荐”,仿佛作家成了一群爱打群架的人,不仅相互借胆儿,而且仿佛人越多越有声势。
作家联手推荐之外,是那些没有考证似乎也根本无法最终考证出处的“推荐语”,比如“全球排名第一的文学畅销书”、“首季销量突破××万大关”;或是“你不可不读的书”、“一生必读”、“2011年最感人、最震撼、最荡气回肠的情感类长篇小说”,而且后面还缀上“令席绢无语,令琼瑶叹服”。
岩井俊二在日本文学界和电影界具有双重影响,他的电影作品《情书》曾在日本及国际上赢得许多观众,其散文化的情节处理,被奉为电影文学化的经典之作。而岩井俊二的小说原作被翻译成中文后,销量也不错。然而,就是这本《情书》,封面上比作者岩井俊二的字体要大出几倍的汉字却是“著名作家安妮宝贝作序推荐,青春偶像郭敬明的偶像清新唯美第一书”的腰封文字,不仅混乱芜杂,而且诘屈聱牙,读起来像读绕口令。郭敬明是偶像,而岩井俊二则是郭敬明的偶像,偶像的偶像,相当于师傅的师傅,等于祖师爷啊!这书还能不收藏?但问题是,原本为人为文都十分“低调”的岩井俊二被人如此包装以后,倒像是日本青春娱乐界的掌门人了。
还有《德语课》这本书,其腰封上是这样写的:“德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杰作;世界五十大小说之一;一部××(一名知名写手)借了舍不得还的不朽杰作;一部S.H.E随身携带的好读经典。”“世界五十大小说”不知道是谁评的,××借了舍不得还,我看有几种可能,一种是忘了还,一种是没工夫去还。至于S.H.E嘛,我倒奇怪,这三个蹦蹦跳跳的小丫头,往来于两岸三地唱歌走穴,随身换洗衣服化妆品卫生巾都未必有地方放,却还要带上《德语课》这本书?如是,这三个小丫头显然是铁杆文学女青年无疑。
再说余秋雨的那本《问学》。腰封也很雷人,“古有三千弟子《论语》孔夫子,今有北大学子《问学》余秋雨,五年来唯一新著,创制中国文坛散文式文化通史,用最具个性的文笔精心淬炼华夏五千年文化,从学者到先生,秋雨治学的感动进阶”。对余秋雨文章的斤两不是本文论述范围,但问题是,这样去“推荐”,有可能给余先生起到的是反作用。最近台北“故宫博物院”搞《富春山居图》的合璧展出,余秋雨又受邀到台湾大谈中国古代绘画,有人会不会由此再为余秋雨扣上一顶“中国古代绘画品鉴大师”的称号呢?
“中国著名高校文学院院长联合推荐”,却不知道是哪几所高校的文学院,又是哪几位院长?“中国十省市作协主席唯一推荐”,到底是哪十个省市的作协主席?又或曰为什么是十省市却不是二十省市?“铁凝、阎连科、刘震云、张悦然、饶雪漫等倾情推荐”,不仅老中青三代走到了一起,而且几个人横跨体制内外,像是把法国大菜和小豆冰棍捆绑上桌,不伦不类。“周华健、郭德纲,张大春”喜爱的一部书,整个一个关公战秦琼,只是不了解郭德纲和张大春相互知不知道。“十年来国内最具影响力最神秘的作家年度压轴大作”,“最具影响力最神秘”到底是谁评选出来的呢?“唯一揭示玛雅末日预言真相的小说!”连玛雅人的故乡中美洲十几个国家都没能出一部揭示玛雅人末日预言的小说,万里之遥的我们填补了空白。“一本让丹·布朗等文坛大腕惊惧不已的新人处女作”,好在没把丹·布朗给吓死。“一本众多日本名女优爱不释手的小说”,这是一本什么小说,难道是性爱秘籍不成?
随着名人荐书的盛行,一本书往往需要多个名家“联合推荐”,不仅“腰封”越做越大,有时连封面都放不下了,只能改为封底或扉页乃至目录页。作家联名推荐除了体现集团优势之外,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比如当今到医院去看病,原本几粒药片能解决的问题也得输液,不光是医院要赚钱,主要是人的身体有了“耐药性”,几粒药片显然不管用了。再比如说炒菜放作料,大家放一样的作料肯定不行,品不出区别来呀!既然如今食客的口味越来越重,那原先放“少许”的,这回就干脆撒一把,至于有没有副作用,谁还管得了那么多!
某书腰封上印着“著名作家王安忆翻译的第一本书”,令王安忆愤慨不已,当着媒体直言“绝不属实”,“想把腰封扯下来”。某书因为未经陈村同意就把他也列为推荐作家之一,陈村斥之为漂亮的脸上贴了“狗皮膏药”,恨不得给它撕下来。出生在台湾、于香港茁壮成长的梁文道原本只是搞文化研究的,近年不知怎么打入了文学圈。想来可能是和他常年参与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录制有关。“锵锵三人行”隔三差五就会邀请海峡两岸一些著名或根本不著名的作家上镜,梁文道能够与这些作家坐而论道,要走入文学圈自有捷径。大约就是在一次“锵锵三人行”的节目中,梁文道倒起了“苦水”,他说:“我有个绰号叫‘腰封小王子’,我常常在书的腰封上面被列名,成为推荐人。但有时候,一本书我完全什么都不了解不知情,却被写成‘梁文道倾情推荐’。终于有一回,我忍不住了,按照书上的电话找到出版社编辑。那个编辑非常镇定轻松地回答说:‘梁先生,我们很尊重你,但是您真的以为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叫梁文道吗?’”梁文道还说:“那个编辑说了那样的话,我当时就呆住了,人家说得对呀,确实全中国不止我一个人叫梁文道。我也没办法,只好说:那很抱歉,打扰了。”
在这件事情上,梁文道先生显然无辜,但在法制社会中长大成人的梁先生完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推荐署名权”。但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而只是倒倒“苦水”而已,我以为恐怕还是在“被署名”的问题上比较暧昧。一些无名作家接受在自己书籍上印上其他作家的名字,无疑是自我宣传的一种需要,但对“被署名”者来说又何偿不是一种宣传和炒作呢?说双赢靠谱,说互惠互利也不为过,这也正是为什么“被署名”的作家有那么多,却至今没有一个站出来为自己的“推荐署名权”打官司的缘故。这一点不由得让我想起美国作家爱默生来。当初写《瓦尔登湖》的梭罗要在他的书封面印上爱默生写给梭罗的一段话,因为当时爱默生已经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作家,却被爱默生给拒绝了。但是这并没有妨碍爱默生与梭罗成为一生的好朋友,梭罗可以吃住在爱默生家里,爱默生依然在经济上给予梭罗很多帮助。我想,作家爱惜自己的羽毛,说的不仅仅是爱惜自己的作品,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而这种负责说到底还是对文学负责,对其他的作家和读者负责。
推荐文学书籍的多半是作家,这个好理解,但这些年来,从梁文道到“康熙来了”的主持人蔡康永、从盖房子的王石到演电视剧的姚晨,从央视主持白岩松到拿诺贝尔奖的杨振宁,荐书的名人从文化圈到娱乐圈,甚至延展到了科技界、房地产界。虽说文学在当下已经失去了用一种路径的演变来加以概括的可能,文学介入公共空间的方式也变得模糊和可疑,但是,总不至于要一些与文学隔着千山万水的人来对文学作品品头论足吧!
我对阎连科先生的作品一直是关注的,虽然说不上多么喜欢,但绝对谈不上反感。但是,他的《我与父辈》我没有看,没有看的原因与这本书的推荐语有很大关系。阎连科《我与父辈》腰封上的推荐词是这么说的:“万人签名联合推荐,2009年最感人的大书,最让世界震撼的中国作家阎连科,千万读者为之动容,创预售销量奇迹,超越《小团圆》。”如此夸张,当真是字字惊天动地,句句扣人心弦,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我想要知道的是,这“万人签名”从何而来?那“最让世界震撼”又如何界定?而且此处还带出了《小团圆》,《小团圆》又是何方圣书?超越《小团圆》难道是文学作品高低的惟一一个抑或是众多标准之一吗?于是又联想起香港版的《为人民服务》一书来,那上面对阎连科的说法也超出了我的理解范畴。相比而言,阎连科的《风雅颂》一书的封面还算“干净”,但腰封上“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的名号看了还是觉得多少有些刺眼,谁封给阎先生的这个名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师”一词,我看还是少提为好,哪怕仅仅就是为了忽悠之需。
2006年,莫言在写完《生死疲劳》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读者喜欢,我写的时候只能根据自己的感受来写。说句不好听的话,一个作家在写作时不应该考虑读者。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就这样写好了。”对莫言先生的话,我是赞同的,但有意思的是,这本《生死疲劳》以及莫言先生其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当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那些白纸黑字的“推荐语”,没有一句不是在讨好读者。这当然未必是莫言先生能左右的。我只是想,文学的重口味,总有一天会害了读者的肠胃和消化系统,到时候,我们又该拿什么去调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