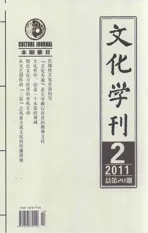“人类第一部《中国史学史》”
——读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有感
2011-03-20朱志先
朱志先 张 霞
“人类第一部《中国史学史》”
——读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有感
朱志先 张 霞
内藤湖南(公元1866年—1934年)是日本“中国学”创始人之一,著有《中国上古史》、《中国上古的文化》、《中国近世史》、《中国史学史》、《燕山楚水》等著作。内藤氏《中国史学史》一书,由马彪翻译,2008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史学史》是“内藤先生晚年最为倾注心血的著作”,在内藤湖南众多著作之中,“可谓名著中的名著”。此书是对内藤氏20世纪20年代在京都大学所授“中国史学史”讲义的整理,被誉为“人类第一部《中国史学史》”。全书共有十二章,详细梳理了上古至清代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为更好了解内藤氏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笔者试从其所著《中国史学史》内容入手,发掘其研究思路,进而窥见其史学史意识。
一、内藤氏《中国史学史》内容简介
在中国,梁启超1926年——1927年最早提出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及撰写体例:“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遗憾的是梁启超仅设计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框架,将其付诸于实践的则是1944年在重庆出版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而内藤氏的《中国史学史》是后人对其1919年——1921年和1925年讲授《中国史学史》讲义的整理。另外,内藤氏最早在京都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是1914年——1915年,从时间上看,内藤氏应该是近代第一位系统讲授“中国史学史”的学者。
尽管内藤氏《中国史学史》是系统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开山之作,但其对中国史学发展史的探究,内容十分翔实,且以通识的眼光充分考析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史学的发展演变状态。此书共分十二章,第一、二、三、四章分别论述“史的起源”、“周代史官的发达”、“记录的起源”和“史书的渊源”。主要阐述了作为史学史研究的基本元素:“史”、“史官”、“记录”、“史书”在先秦时的渊源流变,可谓在论述秦前史学史;第五、六、七章分别是“《史记》”、“《汉书》”及“《史记》、《汉书》以后史书的发展”。主要阐述《史记》、《汉书》的著述目的、编撰体例及《史记》、《汉书》对后世史书的影响,并探讨了后人对《史记》、《汉书》的研究情况;第八、九、十、十一、十二章分别论述了六朝末唐代的史学变化及宋、元、明、清的史学发展状况。其间不仅详细论证了唐、宋时期史学发展变化的原因及表现,而且对元、明、清三代史学进行了各有侧重的梳理。
二、内藤氏《中国史学史》的撰写特点
如果仅浏览内藤氏《中国史学史》目录中各个章的标题,似乎觉得和中国的史学史著作差别不大。其实不然,中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的史学史著作,绝大多数是以史籍解题或史籍举要类型出现的,基本上是按朝代为主线,对相应的史官、史家及史学名著进行阐述,较少关注史学发展的整体性,而且论述的内容往往局限在横向联系上,缺乏贯通的纵向探讨。内藤氏《中国史学史》是其晚年学术研究的结晶,从其著作中可以发现他非常推崇杨慎、钱大昕等人博学且善于考据之人,很崇拜章学诚等人极具史识能力之人,以至于为章学诚撰写年谱。由于深受中国杰出史学家学问的影响,内藤氏《中国史学史》中充分展现了其对中国学人研究成果的借鉴与批判。当然,这与内藤氏科学的研究方法、缜密翔实的资料梳理功夫是密不可分的。具体而言,内藤氏《中国史学史》在内容上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在宏观上,能够把握史学史发展的整体态势。
史书的撰写形态基本上分为私修与官修,即一家之著述与众人之合撰。对此问题,内藤氏指出:“虽然直至唐代的历史著述还大多是私家著作,即是作为一家之学的产物,但是从唐代开始已经变为召集众人的编纂。”由于从唐代开始,史书编纂是在官方的监督下运作,导致“监修国史这一职务,是个实际上与史书编纂无关,仅仅徒具虚名的高官,没有负责著述的人物却在主要位置上署名,于是史学越发成为单纯的官府工作,已不再具有史官的精神了。这一点是至唐代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另外,清人所修《明史》在二十四部正史中属质量上乘之作,但后人对《明史》持许多批评意见,诸如,《明史》中没有立《道学传》便深受桐城派的质疑。内藤氏认为,《明史》编撰者此举“是出于反对朱子学的观念而不立《道学传》的”。并且“反对朱子学的学风、尊重实录的学风、否定朱子《纲目》笔法等等,实际上都是编纂《明史》时的主要意见,此时是北宋以来数百年间史论一变的时期”。内藤氏言语精辟地概述了《明史》撰写的主旨。再如,对于清初考据学兴起之后,学术风气的趋向,内藤氏依据乾隆《盛京赋》、纪昀《乌鲁木齐赋》、汤运泰《金源纪事诗》等,论道:“乾隆以后的历史学、地理学,在出现了考证化的同时,又有着文学化的倾向,这些著作所显示的是一种试图将学问予以艺术化的趋势。”
内藤氏从宏观的角度对史书撰写形态的流变、史书修撰体例的各异及清初学风的趋向,都予以精湛的概括,恰如其分地归结了历史现象变迁的原因。
其二,在微观上,对具体史学要点能予以细致入微的剖析。
关于“史”字的最初含义,内藤氏援引许慎、段玉裁、罗振玉、江永、王国维等人之说,一方面赞成江永在《周礼疑义举要》中把“史”字解释为手持薄书的形状;另一方面指出王国维所言“史”最初为盛书的器皿是不妥的。内藤氏依据铜器上的铭文,指出:“‘史’最终也应当看做是武器,直至殷代,史的主要职掌仍是射礼,是负责射箭命中次数的职务。”
内藤氏对于历史事实的考证有着严密的论证方法,像对《周礼》中“五史”的论析,他指出应该参照其他文献进行考证。对《周礼》中“大史”一职,他认为应“根据《尚书》的《顾命》、《礼记》的《曲礼》、《王制》等的旁证”,并且“关于大史所掌的职务,也是必须将各种记载对照考证的”。另外,因《周礼》中“大迁国,抱法以前”没有旁证,内藤氏指出对于“大迁国”,不能依周初在洛阳建成周,或周室东迁等原因,“就认为由于对这些周初之事早有预见而设置了此职务”。看来,内藤氏是非常注重互证、旁证及孤证不立的考据方法。内藤氏学识广博,且有此类严谨的研究方法,所以他新见迭出,且见有所据。
再如,对于《诗》的解释,大多史学史著作中仅是简单介绍《风》、《雅》、《颂》三种体例的表现形态。内藤氏则是从小的方面着眼,依据《三家诗》、《毛诗》、《鲁诗》等,参依崔述、范宁等人的观点,深入考究了《诗》中《风》、《雅》、《颂》产生的时间、相应所蕴涵的寓意及《诗》中所包含的史料价值。
其三,在横向方面,善于比较异同。
对于同一时期史学要籍的解读,内藤氏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较其异,存其同。对新、旧《唐书》的评判,历来是学者所关注的。内藤氏主要从古文文体的特点、史料搜集、文章体例等方面详细比较二者的不同,指出《旧唐书》的优点是忠于史料,但照搬实录的做法“可说是史家的堕落”。而《新唐书》虽然在史料的准确性方面不如《旧唐书》,但“《新唐书》创造出了史书体例上的新形式,这是其最显著的特点。可以说具有正史编纂上划时代的意义”。再者,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和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皆为地理学著作,内藤氏对两书的评判是:“如果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相比较的话,《天下郡国利病书》不过是单纯对材料特别是政治材料的汇集,若论具有完整编纂主张的话,是不及《读史方舆纪要》的。”
其四,在纵向方面,能够融会贯通。
史学史,即是阐述历史现象发展变迁的历史,是动态的,不是僵化的。因此,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说,对史学名著的阐释,不能仅局限于对其作简单介绍,而是要洞悉名著本身的价值。这就需要论及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史学典籍对后世在体例、撰述思想等方面的影响;其二,后世对这些著名史学典籍的研究状况。内藤氏基本依纵贯、打通的思路来解读史学经典。比如,在论述《史记》时,内藤氏首先论及《史记》的产生背景、著述目的,其次讲述《史记》的撰写体例及其对后世史著的影响,再者纵贯古今论析后代对《史记》内容及编纂法的评论。诸如,明代归有光、清人章学诚、邵晋涵、方苞等对《史记》的评点和研究,内藤氏皆有精彩的归纳。这一切,建立于他认为“《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正相当于史部的发端之作,就当初这样一部难以划分归属的一家之言,在后世竟成为了将史书发展为史部书籍的奠基之作了”。
再如,内藤氏在谈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时,能够联系到中国历代的修谱之风,其论曰:
由《宰相世系表》可窥知唐代谱学的真实形态,并由此了解古代、唐代、宋代各代在对待姓氏态度的差异。本来在中国,古时候是以根据宗法制定系谱为主体的,并没有几十代那么长的系谱;至唐代修长谱的风气盛行;至宋代欧阳修、苏洵所制族谱又回到了古代短谱的做法;而至近代再次兴起崇尚修长谱之风。
三、内藤氏《中国史学史》的史学史意识
内藤氏《中国史学史》能够自成一体,在广征博引中彰显史学现象的本貌。它既能在宏观方面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又能从微观方面洞悉史学个案的精髓;既能融汇众家之长,又能在众说之中独显己见。这不仅需要渊博的学识、丰厚的知识积淀及敏锐的学术眼光,更需要有明晰的史学史意识,否则此著便成为史籍解题或目录学之类的著作模式。对于内藤氏在《中国史学史》中所体现的史学史意识,大体有以下五点:
第一,具有明晰的史学史意识。
有关《春秋》三传的探讨,内藤氏认为:“至于这三传的成书,亦有许多形成史可言。”他注意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春秋》三传,应该从史学史的角度关注其发展形成史。内藤氏在比较《史记》与《竹书纪年》有关“纪年”的问题时,提出:“即便《竹书纪年》确有其书的话,也无法证明此书中的纪年就比《史记》更准确。但是从史学史上来看,此书毕竟是将纪年与事实统一之史学体例诞生的时代标志。”对《史记》的评价,他从《史记》的思想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出发,认为:“《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并且认为:“关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以及作为《史记》成书后的结果在史学史上所表现怎样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在论析王夫之、胡承诺的史论特点时,内藤氏认为:“王夫之、胡承诺的观点虽然在当时并没有表露出来,但是其在清朝史学史上的价值是绝对不容忽视的。”由上可见,内藤氏在论析中国传统史学现象时,不是拘泥于对历史典籍和历史人物本身的探讨,而是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予以度量。
第二,以动态发展的视野来研究史学现象。
《史记》作为一种开创性著作,其体例、笔法等对后世著作产生很大影响。内藤氏从班固《汉书》、皇甫谧《帝王世纪》、欧阳修《五代史》等来分析其对《史记》的借鉴。同时,各代之人对《史记》皆有评论,内藤氏主要从刘知几、郑樵论起,最后归结到清代的方苞、邵晋涵、纪昀、章学诚等。他认为:“直至清代才逐渐出现了对《史记》能够作出精密评论的人物”,且其中邵晋涵之评论,“可以说是有关《史记》总体所进行近代式评论的权威之作。”内藤氏不仅对史著作动态的分析,对史官职责的变迁亦如是。如对《起居注》官员职责的变化,从六朝开始延及宋代,他指出:“负责记《起居注》的官职起自六朝时期,是古史官的遗存,不受天子约束,成为了一种一直延续至唐初的自由记事风气。”但到宋代,“《起居注》的记事编纂之后要呈天子过目,然后再送交史官,最终失去了记录《起居注》本来的意义。”更为精辟的是,内藤氏没有仅停留在史官职责的变化上,而是由此引申到政治对史学的影响,其论曰:
由于直至唐代都是贵族政治,所以史官也是即便仅限于一代为官,忠于职守之风仍然强盛。但是毕竟史学却在逐渐衰败,作为世袭、家学的史学已经不复存在,记史转为由宰相监督,作史不再是史官的自由了,《起居注》也失去了意义,正确史料的形成在唐代已经失去了保障,史学成为了权力者摆布的对象。这表明,在中国向君主专制政治转变的同时,历史著作也发生了变化,应该说是耐人寻味的变化。
第三,关注时代变化对史书体例的影响。
有关《新唐书》中《宰相世系表》和《新五代史》中《义儿传》、《伶官传》,内藤氏没有像方苞那样仅从笔法上来论及欧阳修,而是认为此种体例“都是就那个时代特点而设置的,以此反映时代的特色”。而对于《新唐书·艺文志》中载录作者未见之书,内藤氏认为这是历来《艺文志》、《经籍志》体例的破坏,其错误的原因在于,“《新唐书》写作的当时正处革新的时代,虽然一切立足于复兴,但是由于这种精神又不够彻底,所以也往往出现错误”。再如,《资治通鉴》改变了宋初《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为帝王提供参考的类书之体例,而用编年体,在内容上更加注重史书的劝诫功能。内藤氏认为:“这是由于天子的生活已经从中世贵族的生活转变为新型的独裁君主生活,因而出现君主应当具备特别修养的需要。”时代的变迁影响到史书体例的变化,内藤氏此种论断颇有见地。
第四,关注史学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有关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文化之间的变迁,内藤氏从宏观方面论述其内在的连续性。内藤湖南依唐代《贞观政要》为例,指出此类著作在唐、宋时代逐渐流行起来并延续到明、清,“如《时政记》的成书,特别是到了宋代更有《宝训》、《圣训》之类的盛行,此《宝训》、《圣训》之类著作,大体上从宋代开始一直流行至明清,在明代称《宝训》,在清代称《圣训》,都是对天子诏敕中最优秀内容的类编”。有关元、明文化的联系,内藤氏认为:“明代初期尚存元代遗风,盛行编纂大型著作。大体上说,不论元代还是明代,其朝代的推移与文化的推移多少是有其不一致的地方的:虽然朝代换了,但文化确实一脉相承的。”而论及明代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时,他指出:“明代的金石研究尚未形成真正的学问,只不过是从宋朝到清朝之间的衔接而已。”另外,内藤氏言及明代史学对清代的影响时,注意到杨慎等人在研究方法、逻辑思维方面的先河作用。如其言杨慎在考据学方面和章潢等在策学领域的成就时,指出:“这些明代类书的代表作,后来还成为了顾炎武《日知录》的前驱。一方面是杨升庵的考证之风;另一方面就是这里所说的经世实用类书的编纂方法,这两方面都是清朝考证学得以形成的动力。”
第五,注重学问“中心”的影响。
内藤氏在论及中国社会变迁时,提出有名的“唐宋变革论”,指出此两个时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显著作用。他在研究中国史学史时也是非常关注“中心人物”。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在总结清朝史学时,内藤氏认为黄宗羲、顾炎武是清朝史学得以兴盛的基础,“前者是浙东学派的鼻祖,后者乃是浙西学派的开山。清朝的史学就是以此二人为中心兴起的”。但由于黄宗羲、顾炎武皆为明代遗老,“所以并未露出表面,而是由那些与此二人相关者为中心人物的”,黄宗羲一方是“弟子万斯同成为了《明史》编纂的第一个核心人物……他在北京成为了众多学者的中心”;而“顾炎武一方成为中心人物的是他的外甥徐乾学”,他在南方聚集了一大批学者。因此,“这两个学者集团与清朝的所有学者都有关系,并有此产生了清朝前半期的学派”。
在探讨清代的考据学时,内藤氏认为在乾嘉考据学中,钱大昕乃是核心人物,其做学问时重视对材料的选择,“而这一特点又受到误解”,导致出现了单纯以考证为学问的风潮。因此,“在乾隆至嘉庆间的所有史学都是以钱大昕为中心的,其中与钱氏学风最接近的是浙西学派的人物,而最远者当属章学诚。大体上是以钱大昕为中心,进而再由钱氏之学出现了分科进展的趋势”。对乾隆年间金石学的研究,内藤氏指出:“作为一般风潮来说,毕竟是以书法与古玩爱好为主,其核心人物是翁方纲。”对于清代西北地理学的研究,内藤氏认为当时的学者都是结为互相交流的同伙,“从徐松到魏源是形成了一个团体”,在清末又形成“以盛昱为中心这个团体的学者,多少对塞外方面有所研究”。
内藤氏《中国史学史》是后人对其“中国史学史”课程讲义的汇集,作为讲义一定程度上受到授课人喜好之影响,因此,在内容的安排上便出现详略不同的问题。诸如,有关明、清部分几乎占有整部《中国史学史》的一半,而对六朝史学则论之甚少。作为一部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来说,这样的布局似乎不妥。总之,内藤氏《中国史学史》是构建于对中国史学发展史同情理解的基础上,以一种“会通”的视角再现中国史学流变的姿态,正如谷川道雄所言:“本书中他(内藤湖南)提到历代中国学者的见解,并屡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时也批判以往的见解,这应该说正意味着他是把自己也置身于中国史学史之中的。”(《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
(作者系咸宁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刘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