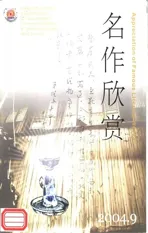革新技巧与言说存在——从《转身》论格致散文的叙述
2010-08-15陈庆瑜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州510032
□陈庆瑜(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州 510032)
叙述对于小说意义重大,20世纪的小说更对叙述进行了深入的实验和创新,叙述时间、叙述人物、叙述视角等的流动变化刺激了小说的生命力,给读者带来新鲜的阅读体会。同时,叙述的丰富内涵更成为探索作者创作“潜意识”乃至社会潜在文化心理的着力点,可以说叙述在小说家手里已经从一种单纯的表达工具、艺术技巧上升到作者思考世界、呈现世界的方式之一。相比而言,散文方面的叙述乏善可陈。众所周知,传统散文对叙述并没有投入太多关注,优秀的散文家当然也很在意叙述的艺术,如李光连先生在分析散文叙述美时所列举的“切割故事”、“淡化情节”、“善补插”、“贵转折”、“妙蓄笔”、“巧伏应”,但这都只是把叙述当作一种艺术技巧罢了,而且常年没有更新,对一个传统的散文家来说,只有情感或哲思才是散文的灵魂,而叙述,那是小说家的事情。观念的陈旧保守使散文叙述越来越失去激情,沦落平庸,如陈剑晖先生所讲:“叙述观念的革命对于小说来说早已是老生常谈,但对于散文来说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①在这个背景下,格致散文的叙述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
作为新散文作家,格致对叙述有一种酷似小说家的迷恋,叙述在她笔下不仅显得比传统散文更加摇曳多姿、引人入胜,而且具有丰富的心理意蕴,耐人寻味。《转身》是格致的惊世之作,它清晰地展现了作品与传统散文迥然不同的叙述艺术,也隐藏着格致迷恋叙述的心灵秘密,本文将以《转身》为主要文本,着力探讨格致散文叙述的特点。
一、对传统叙述技巧的革新:
《转身》首先引人注目、令人困惑的是一个强奸未遂的故事怎能讲述得如此从容不迫,甚至富有诗意?与暴徒的激烈对抗、对往事的深情回味、对生命的优美联想三者如何在同一篇文章里相安无事,不仅没有互相排斥,反而彼此升华?
那段日子住在乡下,宿舍以及工作单位都是平房,我的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楼梯,也就没有出现恐惧。
这段文字写于两年前,是我的一篇小说的开始部分。……于是,在一个光线烂漫的午后,我从一大堆手稿中艰难地找到了那篇小说并重读了它。②
这是《转身》的开头,很明显,《转身》内含了作者两年前一篇小说,两年前,作者就将遭遇强奸犯的经历作为一篇小说的素材详细记录下来。这篇小说在《转身》中被多次引用,它以小一号的字体出现,保证了形式上的独立,对它的节选清晰,易于辨认。所以《转身》实际是两个文本的叠加:内文本——两年前的小说,外文本——《转身》,这正是机关之所在。
强奸未遂的故事被集中在内文本,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尾在内文本中清晰展现,时间顺序是内文本的叙述依据,气氛紧张、节奏紧促、在场感强烈则是它的总体特征。外文本以阅读内文本为线索,记录的是作者阅读过程勾起的回忆和引发的联想,它的写作者已经从当年的恐怖事件中脱身离开,隔着一段岁月的安全距离重新审视往事,所以外文本的叙述不像内文本那般紧张激烈,它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回忆和联想固有的散漫、从容、信马由缰。以阅读的方式将两个文本相互叠加又保持相对独立,一方面双倍扩展了文章的含量,使《转身》克服了传统散文一事一议单薄羸弱的缺陷;另一方面更使两种不同的叙述风格并行不悖,而不同风格交替出现又使《转身》走出传统散文叙述波澜不惊,从一而终的简单模式,叙述显得张弛有度,富于弹性。
在变换叙述风格的同时,格致紧紧控制着叙述的节奏。两个文本交叉进行,读者的心时而陷入前途未卜的事件,时而被诗意的联想带到遥远的过去,而每一次转折作者都会有意识地强调节奏的变化,叙述更加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以内文本在《转身》中的第三次引入为例。外文本——“仅仅是几年的时光,楼梯已不再通向欢乐和希望,而是埋伏着恐惧和杀机。”如同一个惊悚片的预告,格致动用了两个对人的安全感造成最大威胁的词:恐惧、杀机,它们和欢乐、希望形成鲜明的对比,预示着一个恐怖的情景即将出现。当读者已经准备好跟随叙述下一步就迈进地狱大门时,意想不到的是门打开了,想象中的刀山火海、妖魔鬼怪竟没有出现,眨眼间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日常生活——内文本将外文本抛给它的悬念放到一边,慢条斯理地讲述那天晚上“我”去那里洗衣服,为什么要到那里洗衣服,洗好的衣服如何包好抱在怀里,从危险边缘回到日常生活,紧张的节奏一下子恢复舒缓。接着,经过一系列细节的详细描绘,内文本终于走到了强奸犯出现的时刻,时间、地点、人物、气氛一切准备妥当,危险一触即发,读者期待中的高潮眼看就要到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格致又将一切掐断,内文本戛然而止。“这和六十年前,我母亲遇到的麻烦极其类似”,叙述转向外文本,事件的相似性使格致陷入了遥远的回忆和充满传奇色彩的往事中去,六十年前一个野花摇曳,清风徐来的春天迎面扑来,叙述的语调从慌张步入抒情,节奏再次从紧张走向舒缓,格致又完美地制造了一次变奏。
纵观《转身》内外文本的十次切换,格致始终清楚明白地控制着叙述的节奏,紧张——舒缓——紧张,循环往复,张弛有度,音节鲜明,鼓点饱满,这不能不说是格致有意而为之,这种精心的安排在传统散文中是很少见的。传统散文的感染力多来源于抒情性的表白或描写,而在格致的散文中叙述则更受倚重,如同音乐,节奏的快慢刚柔使旋律呈现出激情奔放或缠绵缱绻种种风情。小文本节奏紧张,有利于传达事件给作者造成的极大冲击,外文本悠然舒展,流露的则是作者对往事的释怀,恐怖的事件被时光抚平,作者试图对它作出智性的消解和思考。
风格和节奏外,叙述距离格致也是用心经营:
一强调在场感,拉近距离,反之扩大距离是格致主要的调节手段。
格致在内文本中详细记录了事件发生的一切细节,几乎是事无巨细悉数入笔,读来有一种强烈的在场感。譬如事件发生地点的光线,格致就对它作出了仔细的界定——混合着月亮和街灯两种光亮。鞋与楼梯的摩擦声、湿衣服包裹落地的闷响、歹徒“就找你”三个字的余音,这些极轻微、极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都被格致耐心地拓印到纸上。细节越是精致繁密,事件就越显得具体清晰,叙述的距离越来越小,读者的在场感随之加强。
外文本以内文本为线索,思绪蔓延,涉及到幼年时哥哥将我从噩梦中唤醒、若干年前与喜欢的男人在松花江边拥抱,甚至六十年前母亲的传奇经历。外文本的切入体现出时光的远离,回忆的笔调将内文本记录的事件不断推回原地,在场感逐渐淡化,由此产生了叙述距离的弹性伸缩,使《转身》从内部开拓出一个很大的空间,这样广阔的叙述空间和复杂的时空交错通常只存在于小说,在一人一事的传统散文中也是难得一见的。
二推远事件与作者的关系,拉大距离,反之缩小,如:
母亲的家住在古城乌拉街,但在乡下有些田产。显然母亲的家是个地主。地主的第三个女儿,也就是我的被唤作三姐的母亲在春天的时候想到乡下的老家玩几天,也许只为取一副鞋样。③
有几个词颇值玩味:显然、地主的第三个女儿、被唤作三姐的母亲。母亲的家庭是否为地主这应该是作者很清楚的,但格致却故意放弃她的知情权,把自己放在一个陌生人的位置,忽略亲密的母女关系,依靠母亲的家在“乡下有些田产”这一客观事实判断母亲的家世。地主的第三个女儿——强调的是母亲作为女儿的身份,被唤作三姐的母亲——强调的是母亲在兄弟姐妹中的位置,这一切都在剥离母亲为人母的身份,力图将母亲还原到六十年前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形象。格致推远自身同母亲的关系,也就推远了读者与其母亲的关系,距离扩大了,读者和作者一同站在宽大的时光之河彼岸看一个青春少女的传奇经历,一切与现在毫无干系,浪漫而遥远,如同天地初开的神话,这正是格致对母亲往事的心理感受。可以说,格致无需动用太多修辞,单是拉开叙述距离就自然而然地酝酿出理想的情调与气氛了。
二、叙述深化为存在与思考的方式:
《转身》乍看是一个强奸未遂的故事,因为这样的事件太具爆发力和冲击性,以至于它成为《转身》最抢眼的部分,实际上《转身》重点做的是对这段往事的增补和分析工作。虽然两年前的小说已经非常翔实地记录了一切,但格致还有很多话想说,很多细节要补充,譬如对楼梯的感情、母亲类似的经历、对自己当时超乎冷静的分析等等,所以她要写下《转身》。作为作者固执的第二次叙述,《转身》表现出作者对叙述不同寻常的执著和迷恋,而且她的叙述无比细致耐心,不允许丝毫遗漏,仿佛其中潜藏了某种秘密的安慰和快感。后来我从《格致答湖南〈文学界〉》中找到了答案。在同周晓枫进行比较时,格致说她们作品的精神纹理不同,“她(周晓枫)的花纹细腻讲究;我的看上去基本不是花纹,而是伤口”,伤口这个词让我心头一惊。格致还说:
我的精神或肉体,总是受到冲击和震荡,而这种冲击或震荡一时又无法平复。它给我制造了持续的痛感、久难愈合的伤口。我总是有写作的欲望。我发现,通过写作,我能很好地疗治自己。写作越来越像止痛药,像甲酚那酸。我可能都已经上瘾了。④
上瘾证明了我的感觉。伤口再次出现。对敏感而脆弱的作家而言,被强暴挟持无疑是外部世界对其生命个体一次沉重的打击,它留在生命中无法忘怀就像一个伤口暴露在空气中无法愈合,需要精神上及时的治疗。回忆往事就像观察伤势,分析往事则如研究病情,格致对事件的不断重述相当于对伤口一次又一次的察看、清洗、上药。叙述成为格致精神上自我救赎的绳索,她试图借助叙述将伤口从生命拓印到纸上,叙述越仔细,伤口转移得越彻底,这正是《转身》的创作动因,也是格致迷恋叙述的心灵秘密。
因为叙述是对心灵的疗伤,所以一方面格致非常重视叙述,另一方面,精美的叙述又随时面临被打断的厄运——每当在叙述的路上意外碰到其他伤口,格致就再也无暇兼顾叙述的完整和连贯性。格致的另一篇散文《逃生之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文章一开始写道:
我从我家那张有三个抽屉的书桌上回过头,母亲坐在我身后的火炕上,她正在给弟弟做一双鞋。母亲没有抬头,但她指出了我正在读的日文的发音错误……
母亲怎么懂日文?我的疑问从那张书桌上发出。我要交代一下我们家的这张书桌。⑤
疑问被突然晾到一边,格致开始有关桌子的漫长回忆,这是很长很长的一段,长到几乎让人忘记“母亲怎么懂日文”这个疑问。直到格致再次续道:
从那张书桌,从父亲梦想的基石上回过头。
日语的后边牵连着母亲的少女时代。我坐在那张著名的书桌前朗读讨厌的日文,坐在苇席上缝衣服的母亲对少女时代的追述就会绵绵不绝。⑥
我们才重新捡起被悬置在开头处的疑问。当叙述碰见书桌,因为书桌牵连着父亲的梦想,而充满梦想的父亲却英年早逝,所以格致无法绕过这张书桌,她必须将它讲完才能继续前进。格致就像她另一篇散文《在道路上》的李援朝,如果不将道路前方的石头清除干净,他的脚步就无法前行。巧妙的是,李援朝曾经是个军医,他将生活幻化成战场,将道路幻化成战友的肢体,他以为他清理的石头正是战友们身上的伤口。我不由得想,难道《在道路上》是格致对写作的隐喻,李援朝捡拾石子就像格致进行叙述,它们的本质都是疗治伤口:
车轮,实际上正从一个血肉身躯上碾过,从一个战士被子弹洞穿的肢体上碾过。所有的道路上都埋伏着石子,所有的道路都已被子弹打穿。而这一切,只被李援朝一个人看到。他们,只是看到李援朝在捡拾石子。⑦
正如,我们只是看到格致对叙述的热爱。
在做以上探讨的同时我还被卷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格致对虚构叙述的热衷。譬如《转身》讲述母亲往事的一段:
十六七岁的我的母亲走在一九四几年北方春天的乡村路上。柳树一定是绿了,还有江水,流得很急,若说野花的话,应该只有蒲公英开放了。东北大地随处可见的细碎的蒲公英的黄花在母亲绣着牡丹花的鞋边摇曳。⑧
“一定”、“若说”、“应该”暗示作者正处在想象和构思的状态,她在设想一个怎样的春天才配得起十六七岁的美丽少女,甚至一个美丽的少女应该穿一双怎样的绣花鞋。显然,格致在叙述母亲的经历时加进了明显的参与态度,她在按照自己的感觉强行修改和美化故事。这样的例子很多,对于虚构格致也不做丝毫掩饰,这是完全违背传统散文真实性的基本原则的,可是这些段落读起来却并不让人觉得虚假,反而有一种生命的痛感在里面,充满着格致对母亲的向往、对早逝的父亲的仰慕。格致就像一个捡麦穗的小姑娘珍贵地收集生命记忆的点滴,然后用虚构性的叙述将一切串联起来,排列出秩序,建构出合理,模糊零碎的事件在她笔下渐渐变得清晰明了,甚至如她想象般优美动人、环环相扣、因果相连。可以说,虚构不仅包含了格致对事件的理解和阐释,还蕴藏着她关于世界和生命的理想,正如她对父亲的想象及塑造,至此虚构成为了格致搭建精神家园的有力工具。正是这种精神内核的支撑,格致的虚构才显得真诚动人,无意中也对传统散文完全摈弃虚构的态度提出了挑战,督促我们对虚构进行新的审视和界定。
叙述在散文中一直不受重视,而且功能简单,技术保守,如陈剑晖先生所讲,正是散文艺术革命的突破口,格致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技巧上,她革新了传统散文的叙述艺术,从风格切换、节奏变化、距离缩展等进行多方面创新;内涵上,格致将叙述当作疗治生命创伤的良药和营造安全理想的个体存在空间的手段。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对格致来说,叙述或许也是她诗意的栖居之地,这一点可能成为格致对传统的散文叙述观念更深层面上的革命。
①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②③⑧ 格致:《7个人的背叛》,南帆、周晓枫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页、第9页、第9页。
④ 《文学界》2008年第8期。
⑤⑥⑦ 格致:《从容起舞——我的人生笔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页、第205页、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