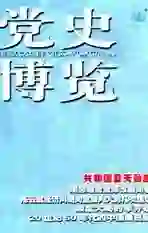一个场景,两个转折,两种心境
2009-11-30王香平
王香平
武汉,作为与毛泽东家乡湖南长沙毗邻而居的九省通衢,注定要在毛泽东的生命轨迹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这里,是青年毛泽东离开长沙后涉足的又一个大城市;这里,是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的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中心城市之一。作为政治家,毛泽东与武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诗人,武汉特有的地理人文景观成为他不可多得的素材源泉。一个产量不多的诗人,却有两首佳作诞生于此,不知是毛泽东的慷慨,还是江城的幸运。也许是机缘巧合。正是这两首相距近30年于同一场景创作的不同词作,形象逼真地传达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那种特有的心理轨迹。
一
1927年,对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旋涡和拐点。而对丹心救国的革命家毛泽东来说,更是经历了求索道路上前所未有的苦闷与挣扎。一首《菩萨蛮·黄鹤楼》以寥寥40余字便淋漓尽致地道足了其中三味。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浩浩荡荡的长江横亘东西,相会于汉口的粤汉线和京汉线纵贯南北。俨然一座天然的地理坐标。当年伫立黄鹤楼上的毛泽东,正处在这东西南北的交会点上。原本一个客观的地理形貌,却被诗人冠以“茫茫”、“沉沉”等颇具感情色彩的叠词,不管是形容时空之邈远广阔,还是状写物象之厚重凝滞,都说明在毛泽东胸中,交会的不仅仅是东西南北。更是风云变幻的革命,是波谲云诡的政治,是“心潮起伏的苍凉心境”。
尽管大革命还没有宣告失败。但在1927年的春天,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却涌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反革命逆流。作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居然向上海的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中共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也惨遭北方军阀杀害。风云骤变的革命形势,毫不留情地将一贯善思慎度的毛泽东推到了十字路口——一个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历史关口。国民革命的命运何去何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道路何去何从?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又一个叠词“苍苍”,外加一个“莽”字和一个“锁”字,显然,毛泽东的忧虑、痛楚和迷惘已然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看不到希望的曙光,摸不准前进的道路,一种前所未有的苍凉与悲怆几乎要将诗人整个吞噬。
是客观的革命形势确实已到了如此严酷的地步,还是作为诗人、政治家的毛泽东敏感多虑的神经使然?革命实践的发展很快便证实了这一切。进入1927年4月,革命形势陡转直下,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到汪精卫的“七一五”叛变,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的现实粉碎了所有爱国志士的革命理想。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在何方?谁能够担当挽中国革命于倒悬的大任?一首于大革命失败前夕吟哦的《菩萨蛮·黄鹤楼》传达出毛泽东未雨绸缪的问询与思索。这是一个政治家深刻而敏锐的洞察力所在,更体现出一个革命者、爱国者为寻求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而发出的深长悲叹和陷入的无限苦闷。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以革命为己任的毛泽东,自然不可能把希望寄托于富有美丽传说的驾鹤仙人。“剩有游人处”的自我定位,不仅表现了诗人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痛楚,也暗含了毛泽东还将立足现实进行不懈奋斗的决心。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便成为诗人主体决心和追求的进一步表白,同时也为全词苍凉凝重的基调增添了一股激昂向上的力量。尽管看不清来路的方向。但探索和拼搏的劲头不会因此而减弱。相反,与狂风恶浪搏击,逆反革命潮流而动,这本身就是毛泽东一贯的秉性和风格。
面对形势的瞬息万变和革命的险恶危机,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而压抑,思想上有如千斤重担。说明他对中国革命的艰难、复杂和曲折是有充分估计和清醒认识的。在革命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中,一些反动势力赤裸裸地暴露出其冷酷与血腥的面孔。
1927年5月21日,一个叫许克祥的小军阀,只用一个团的兵力,就把湖南看似强大的农民运动彻底击垮,把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力量全部打人地下,这就是历史上的“马日事变”。这一事变,从反面印证了毛泽东于两个月前也就是1927年3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中国革命所作的描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事变,也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道路探索的步伐。于是。“七一五”叛变发生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为新内容的路线方针。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一语惊天下地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著名论断。随后,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基础上,毛泽东亲自领导农民暴动,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然后又率部向井冈山进军,从此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多年以后,毛泽东曾对《菩萨蛮·黄鹤楼》自注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到“找到了出路”,前后不过4个来月,大革命失败的阴霾还没有完全散尽,中国共产党就找到了自己前进的道路。这一转折完成的速度如此之快,跨越的时间如此之短,固然有紧迫的斗争形势使然,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本质揭示、对客观情势的深刻洞察、对革命出路始终抱持的高度审慎与思考,则成为至关重要的主观因素。
因此,奔腾不息的浩渺江水和凝然伫立的千年楼台,这一动静相宜的天然场景,无疑成为大革命失败前夕虽不是党的最高领袖却堪称革命先行者的毛泽东忧患沉思与崇高情怀最直观而生动的历史见证。
二
近30年后,依然是黄鹤楼,依然是长江,这一似乎与毛泽东精神相通的地理景观,当它又一次担当起作为诗人毛泽东情感表达的客观物象时,记录下来的却是毛泽东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
30年时间,历史跨越了两个时代。当毛泽东徜徉在“九派引沧流”的长江中尽情舒展自己的筋骨、领略长江的风采时,他已然是一位建立了人民政权的共和国领袖。亲历新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禁不住唱出了心中的赞歌,一曲《水调歌头·游泳》充分展露出诗人对新中国建设的憧憬与豪情。这是1956年6月。
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后来被称做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目标、新纲领、新思路,似乎在向人们昭示着触手可及的美好前景与未来。
5月3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在武汉,63岁的他第一次横渡长江。“今日得宽馀”的诗人身心是愉悦的、轻松
的、舒展的。因此,《水调歌头·游泳》的基调悠闲明快、乐观豪迈且充满希望。
同样是长江,30年前是“烟雨莽苍苍”,30年后是“极目楚天舒”;同样是龟蛇二山,30年前是“龟蛇锁大江”,30年后是“龟蛇静,起宏图”;同样借用神话。30年前是“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30年后是“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世事变迁,风物依旧,而人的心境却殊然迥异。
然而,历史的诡谲便在于,当人们确认已是“山置水复疑无路”时,“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景往往并不遥远;而当人们笃信目标近在咫尺、成功指日可待时,通向成功的道路可能还很漫长甚至会布满荆棘。充满曲折。
1956年,确实是容易激发人们豪情壮志的一年。从1921年建党开始,历经35年奋战的中国共产党终于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航程。毛泽东击水新唱《水调歌头·游泳》,抒写的是诗人的宏图梦想,也是抒写中国人民的凌云壮志。尤其是“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诸句。不仅畅想了20世纪中国人的三峡情怀与建国理想,更成为激励几代中国人矢志奋斗的经典名句。
今天,当三峡大坝巍然屹立在长江西段时,似乎唯有“高峡出平湖”才能表达人们的无限惊叹与由衷赞美。然而,不经意间,整整半个世纪的光景过去了。掐指一算,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1927年到1949年走了22年,而“更立西江石壁”的实现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以后。
看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似乎并不比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好走易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并非像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由此可以看出,1956年的毛泽东心态确实是超乎寻常的自信和放松了。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表面上写当时正在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实际上也泛指整个社会主义建设o 1957年5月21日,毛泽东对身边秘书林克说:“《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桥飞架南北,只有我们今天才做到了。”在古今对比中,一种超越前人的高度自信油然而生。“天堑变通途”。所谓“通途”,在毛泽东心中,意指通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恐怕也在情理之中。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必然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出一条宽阔的“天堑变通途”的康庄大道来。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在表现诗人豪迈和畅想的同时,也给人一种节奏的紧迫感、紧张感。因此。当诗人借用孔子“逝者如斯夫”感叹时光易逝而传达出只争朝夕、奋发进取的强烈愿望和广泛号召时,我们分明能感受到诗人主体内心一种力争上游的急迫与热切——那就是希望社会主义建设能够一日千里,一往无前。
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从1955年夏季以后,在农业合作化和对手工业、个体商业的改造方面已经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的问题。1956年初的经济工作中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况。
当然,作为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自然是希望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民能够早日体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早日享受到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成果,但历史的发展毕竟有着它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何况,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项前所未有的全新事业。也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究竟怎样走,要以怎样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去走?作为历史性地改变了20世纪中华民族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就必定一帆风顺?显然,处在1956年转折关头的毛泽东,有的是梦想,是激情,是豪迈,但似乎又缺少了什么。也许是一种忧患意识的缺失,那就是对未来道路上可能会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缺乏思想上的预设:也许是冷静的分析和认识不够,那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探索和思考不够。
畅游长江3个月后,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新结论,即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据此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
尽管这一符合客观发展要求的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转向全面建设的重大历史转折,但路线的制定与具体实施毕竟是两回事。当1956年过去后不久,中国这艘社会主义的东方之舟便开始了20多年的曲折航程。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过去20多年,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认真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工作积累的问题很多。”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来路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真正转折,居然走了如此漫长曲折的一段道路,让人痛惜而又启人深思。而作为共和国的领袖和主要决策者,毛泽东通过《水调歌头·游泳》一词所表现的他在1956年的思想与心境,不能说与这一转折实现的艰难漫长毫无关系。
三
江泽民说:“英雄造时势,时势也造英雄。在人民创造历史的同时,不可否认,对历史事件的成功或失败,某些个人起关键作用。”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在1927年和1956年两个转折关头通过《菩萨蛮-黄鹤楼》和《水调歌头·游泳》这两首词作从一个侧面表现出的不同心境和思想轨迹及其与后来历史发展的重要关联,也许对我们对后来者永远都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