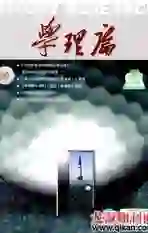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刑事立法制度改革探讨
2009-07-09陈在上
陈在上
摘要:作为对“严打”的理性反思,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为契机,重塑我国的刑事立法制度,以期发挥我国刑事法制的最大制度理性。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立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4—0096—02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发展成为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
2005年12月5日至6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罗干同志要求政法机关要更加注重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更加注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并明确指出“宽严相济是我们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 2006年10月11日,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一节中指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显然,如果仅对司法领域而言无疑是准确的。罗干同志的讲话是总体而言的,所以将宽严相济表述为‘基本刑事政策,二者并不矛盾。只要看一看刑事政策理论,问题就不难解决。”[1]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对以往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我国1979年《刑法》第1条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确定为刑法的制定根据。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指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们党和国家同犯罪作斗争的基本政策。这项政策是从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使命出发,根据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中存在着不同情况而制定的。[2]尽管高铭暄教授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内容的阐述,受到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的影响,但其强调对犯罪分子区别对待,既包括惩办的一面,同时又兼顾宽大的一面,从而取得与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效果,这完全符合立法精神。[3]随着1997年刑法删除了第1条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规定,使“严打”取得了更为瞩目的地方。但是,从“严打”的运作模式来看,其强调的往往是从重从快,法治的底线正义需求可能会被击破,造成执行方式的合法化问题突出。从其效果来看,“严打”的实行往往起到的是“扬汤止沸”的短期效应。犯罪是社会深层次原因和转型时期的特殊矛盾造成的,严打只是治标之策而不是治本之道。[4]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继承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提出的时代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2005年12月提出的,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提出的。其次,两者的侧重点存在差异。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在表述上侧重点在“惩办”,“宽大”处于次要地位。“惩办与宽大两个方面,对犯罪分子来讲也不是等量适用。宽大是相对于惩办而言的,没有惩办,宽大也就无从谈起。”[5]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侧重点在于“宽”。对此,也有学者指出:“现代法治理念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和谐地调和人权保障与法益保护之间的关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现代法治理念的一部分,其主张重点在宽,以适当有利于行为人为出发点…”。[6]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内容
我国学者多主张“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试图在“宽”与“严”之间寻求一定的平衡、协调与结合。[7]为了更好的理解我国刑法中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我们需要从以下方面来把握:
1.宽严相济之“宽”。“宽”的解释有“宽大,不严格,不苛求”。[8]宽严相济之“宽”,是指对于犯罪施以轻缓的刑事政策。具体表现为:对于有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必须依法兑现;对于有酌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也必须依据政策兑现;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六种情形,坚决不以追究刑事责任;扩大非监禁刑适用等等。
2.宽严相济之“严”。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严”的第二个解释是“严厉,严格”。宽严相济之“严”,是指对于犯罪以及刑罚施以严格的刑事政策。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
3.宽严相济之“济”。宽严相济之“济”,蕴含着结合、配合、补充、渗透、协调、统一、和谐之意,亦即协调运用宽松刑事政策与严格刑事政策,以实现两者的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有机统一。[9]客观地说,达到“济”的理性平衡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中心价值所在。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其核心是把握好区别对待的“度”。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的生存空间。对此,贝卡利亚也作了论述,指出:“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地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样的刑罚,那么人民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了。”[10]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刑事立法制度改革
(一)合理的消减死刑罪名
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共有67个死刑罪名,死刑罪名(尤其是非暴力犯罪死刑)显属较多。其实,自从贝卡利亚2个世纪以前提出废除死刑的呐喊以来,全世界已经越来越多的国家从立法上或司法实践中废除了死刑或死刑执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极力主张仍然保留死刑的所有国家应确保死刑不适用于非暴力的经济犯罪、非暴力的信仰自由或者内心的表达”,[11]也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曾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判处死刑必须慎重:“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12]西方学者,大都是从人的生命只能是目的,而不能作为手段的角度来论证人的生命的不应被国家权力剥夺。笔者认为,非暴力犯罪、主观恶意不大的犯罪、社会危害性不是很大的犯罪,都可以取消死刑。
(二)延长死缓、无期徒刑最短执行期限、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最长执行期限
与死刑立即的执行相比,死缓、无期推行、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执行却表现得较为随意,往往表现得过于轻缓,真乃是“生死两重天”。如果说我国刑法中涉及到死刑过多、过滥,法律规定过于“严”的话,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执行,法律规定却过于“宽”。根据我国《刑法》第50条的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死缓的下限是2年+15年=17年;根据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无期徒刑的下限是2年+13年=15年。有期徒刑上限为15年,数罪并罚上限为20年。以上确有过轻之虞,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有必要进行重塑。笔者建议,可以根据被追诉人适用死缓的原因而适当延长执行的期限,可以制定上限,例如30年以下;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可以据以参考使用;至于有期徒刑可以适用并科原则,不宜规定上限。
(三)构建中国社区矫正制度
正如英国学者葛德文所言:“杀一儆百式的惩戒不但必然导致残忍,而且是不可能收敛的,因而断然否定一般预防作为刑法目的的正当性”。[13]鉴于此,社区矫正制度已被各国广泛采用。根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统计的数字,就缓刑和假释两项,2000年,加拿大适用的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新西兰为76.15%,法国为72.63%,美国为70.25%,韩国、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了45.90%和44.48%。这与我国监禁人数占绝大多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近几年的缓刑和假释分别为15%、2%,管制的适用就更低,几近废止。而目前我国的狱内在押犯超过154万人,[14]从北京市、上海市试点的情况看,可谓效果甚佳。截至2006年3月底,北京市已解除矫正4833人,重新犯罪率为0.046%;上海市已解除矫正6000多人,重新犯罪率不足1%。[15]笔者认为,应当适时地修订刑罚的种类,将社区矫正作为一个刑罚种类列入刑法中,这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性归依。
(四)构建刑事和解制度
由于刑事和解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也有利于加害人的再社会化,从而减少刑事诉讼中的对抗,减少上诉以及社会积怨,在刑事案件结案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政策基础。这是由于,宽严相济就是要求我们对待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和过失犯,对失足青少年,以及认罪、悔罪,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所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说是为刑事和解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依据,从而可以有效指导刑事和解的立法工作。笔者建议,在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法修订中,以宽严相济基本形式政策为指导,适宜地增加刑事和解制度的内容。
参考文献:
[1]马克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J].中国法学,2007(4).
[2]汪明亮.“严打”的理性评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3.
[3][4]陈兴良主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8.
[5]杨春洗主编.刑事政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237.
[6]赵秉志主编.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上卷),载刑事政策与刑法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329.
[7]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86-87.
[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33.
[9]赵秉志.和谐社会构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1).
[10][意]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法[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5.
[11]邱兴隆主编.比较刑法第1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190.
[1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98.
[13][英]葛德文.政治正议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37.
[14]翁里.中美“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比较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7(6).
[15]但未丽.社区矫正:在探索中前进[N].《光明日报》2006-7-13.
(责任编辑/彭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