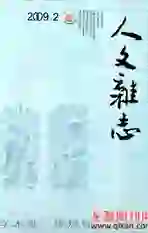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终价值目的
2009-05-11张周志
张周志
内容提要 社会正义的实现,归根结底是作为目的自身的人的全面发展。而以往的历史哲学,包括中国传统德性思维的人本理想,以及西方近代以来的制度理性思维,大凡都以抽象人性论的先验预设为前提,表面上把某些个人及其思想、动机和目的抬高到历史本体的地位,但实质上却造成现实具体的人的历史空场。所以,每每是见神不见人、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只有扬弃关于人的一切异化,让人真正回归现实生活的此在,社会正义理想的最终价值目的才能实现。
关键词 人本理想 社会正义 异化扬弃 价值目的
〔中图分类号〕B82;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2-0020-09
文明的发展和社会正义的实现,归根结底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同的社会发展理论,由于对于人的本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不同,必然在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本质力量发挥作用的┕程等问题的认识上主张也不同。而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对于社会正义与人的历史地位的关系的理解问题。
在人类认识史上,对于人的认识,以及人的本质和人的历史地位与社会正义的关系的认识、主张和观点可谓众说纷纭。但是,总的来说,在唯物史观产生以前,以往的社会历史理论,即使富含人本思想的理论学说,也大凡都是从抽象人性论的先验预设出发,甚至以人性异化为代价,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正义的实现,诉诸于上帝、神、制度理性等等外在或先验的东西。
唯物史观则明确主张,只有扬弃关于人的所有异化,使人真正成为人自身,才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高价值目标。因此,社会正义及其实现的关键就成为人的异化扬弃的问题。
一、西方哲学的正义认知中的人本觉悟及其困惑
1、古代本体思维中人被自然和上帝双重遮蔽
作为西方理性主义思维传统源头的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基本上都是自然哲学家),一开始就把思维的兴奋点集中在人以外的对象世界,即自然界,并用宇宙构成论的分析思维方法,以究根穷理的形而上学玄思的方式进行终极发问,试图揭示构成宇宙万物的终极原因的“始基”,由此形成了自然理性的传统,奠定了古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的基础。
按照这种思维传统,即使希腊第二期哲学家们开始研究人事,诸如对于人以及人类社会,包括社会正义、中道等等的研究,照样采取像研究自然界那样的对象性思维,用主谓宾式的陈述句形式表达。为此,亚里士多德把正义界定为勇敢和不撒谎,柏拉图把人界定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①等等,也就不奇怪了。在这里人生社会的事理情理和道理,自然包括人性和社会正义在内,当然应该遵循外在超验的物理、天理和命理。
*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4C003Z);陕西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07JK141)
① 史称柏拉图的鹅。
到了中世纪,这种规范一切的物理、天理和命理,集中体现到全能的上帝身上,由此形成了影响旷日持久的上帝一元论的神本思维。奥古斯丁坚定基督教哲学的立场,主张异教绝不会有比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基督教提供更好的解决诸如社会正义等人生问题的方案。他坚定地认为,研究哲学就是为了获得幸福,而上帝则给人指向幸福之路,因而,只有遵循基督救世主所指引和给出的道路,人才能获得幸福,从而实现社会正义等。奥古斯丁认为至福是一切哲学活动的目标,基督教的信仰和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达到至福的惟一的、最好的道路。坚信信仰先于理性,原因在于如果没有信仰,理性就无力达到自己的目标——幸福,更无法实现社会正义。人们只要坚定上帝存在的毋容置疑性和上帝全能的信仰,严格地按照这一先验正确的大前提进行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的三段式的推理,人生此在的一切真谛,当然包括人性和社会正义在内,都不假外求了。这种把人生此岸的幸福和秩序等现实问题,交给彼岸的神去安排和仲裁,自然是见神而不见人的神本思维。
2、超越自然和神本后人的理性回归和感性丢失
十六、十七世纪以降,欧洲的人文主义、自然科学两场运动的思想方法,实现了西方思想以人的思维认识为中心的认识论转向,从而超越了以自然和上帝为中心的本体论思维。但是,由于这两场运动的精神宗旨不同,也造成了西方近代生活世界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世界观的分化,惟其如此,使刚刚从自然和上帝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人,又面临被科学理性和感性快乐的双重遮蔽。
作为近代自然科学运动开先河者伽利略,用数学化、理想化研究自然的方法,奠定了近代哲学的科学理性精神的基础。他主张,“在这个世界中的对象不是单个地、不完全地、仿佛偶然地被我们获知的,而是通过一种理性的、连贯的统一的方法被我们认识的,随着对这种方法的不断运用,我们最终能彻底认识这里的一切对象的自在的本身。”(注: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页。)“他发现了数学的自然、方法的理念,他是无数物理学的发现和发现者的先驱。伽利略发现一直被称之为因果规律的东西,即‘真正的(被理想化和数学化了的)世界的‘先天的形式,‘精确的规律性的规律,按照这种形式和规律,在‘自然(被理想化了的自然)中所发现的一切事件都必定服从于精确的规律。所有这一切都既是发现又是掩盖,以致我们现在把它们当作不言自喻的真理。”(注: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转引自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页。)至此,人的一切当然要符合科学理性原则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信条。
近代哲学思维的真正认识论转向,直接肇始于笛卡尔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黑格尔认为,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曾经说,笛卡尔这个人,对他的时代以及对近代的影响,我们绝不能以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四,商务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7页。)。这个基础就是“思”。“我思故我在”标识近代思维彰显“思想是存在之家”。
然而,在笛卡尔那里,人除去理性自识的“思”以外,什么也没有了。人的感性自我完全丢失在理性的“我思”中。即使人的全部意义就是理性的“我思”,这一“我在”的栖身家园也被证明不是坚不可摧的。例如,约翰•洛克于1690年出版的《人类理解论》就认为,在求知问题上,虽然理性主义者巧妙地设想人们最终可以获得完整的知识,但是,新的探讨却表现出不甚乐观的结果。他不像理性主义者那样预先设定人类知识的范围,而是强调认识过程中感觉——经验的因素。所以,洛克的方法标志着贝克莱、休谟和穆勒所要推进的经验主义传统的开始。洛克的知识论的新方法的第一步是严格地把知识放在经验论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必须批驳笛卡尔和莱布尼兹的固有的理念。他认为,人们从各个方面都承认,人一出娘胎就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能够发展并使我们得以学到不少东西的资质,但是不能设想未经教育的心灵会有潜在的内容。因此,心灵起初犹如一张白纸,使它具有思想内容的是经验。作为思想内容的理念,无论是感觉理念还是生自心灵自观的反思理念,都来自感觉经验。
然而,按照经验主义的思想,人的一切又完全诉诸于感觉经验,因而,人是动物,人是机器云云就不奇怪了,现实中,一切跟着感觉走就司空见惯了。人在感性的体验中再次丢失自我。为此,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等等人的异化就成为现代性的常态。人类如何超越这种由自身创设出来的自身异化,这正是康德批判性哲学的起点。
3、康德的“批判”能否实现人的自我超越
康德用批判理性方法拯救作为自我超越的主体的人,必须面对作为理性动物的人和作为自由的人的矛盾。特别是上帝隐退以后成为新的价值标准的科学理性与作为目的自身的人的自由的矛盾冲突问题。
对此,康德首先以价值多元的视域,区分了科学领域、道德和宗教领域、艺术审美领域的三个理性原则,即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其次是试图通过理性自身所具有的批判能力,协调理性与自由的矛盾。为此黑格尔曾概括:“康德的哲学是启蒙运动的理论总结。”康德认为:“…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注: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转引自《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页。)可见,自由是理性存在的唯一方式,没有自由就没有理性。
用邓晓芒先生的话说,在康德哲学中自由的本质特点是:自由是自律和自我批判的前提。在康德看来,理性只有是自由的,它才能够进行自律,进行自我批判。如果理性是自由的,而不进行自我批判和自律,那么它就会绝对化(注:邓晓芒:《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康德响亮地提出人是目的本身,这就决定了他作为近现代人本思想的顶峰人物。但是,无论如何,康德哲学中的人,仍然仅仅是一个只有理性,而不能还原为活生生的当下此在的具体的人,因此,康德的批判理性,照样不能实现人的自我救赎。
4、人在西方现代性视域中的工具理性异化与价值理性堕落
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现代性时代,实质上是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它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这一现代性观念,在思想方法上,是当代人文思想家们沿着康德理性主义的理路,强调只有“公开的”运用理性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的思想,从体现精神文化变迁方面理解现代性,从而规定了现代性的两面旗帜——理性和自由。例如,马克斯•韦伯从宗教与形而上学世界观分离的角度出发,主张现代性构成人的三个自律的活动范围:科学、道德与艺术。与此相对应的是三个重要方面的基本精神: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审美的艺术,它们共同规划人类生活。由此构成后继所有关心人的本性、人的自由、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的现代思想家所不能回避的根本性问题——科学理性、制度理性、审美理性。
在现代性的三大理性领域,表面上是作为目的自身的人的一切都实现了,但实质上,作为当下此在的感性具体的人,在现代性世俗化的科学理性、制度理性和审美理性的规范性面前,自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不是自己。
如何拯救现代性中丢失的人自身?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的视域对于“现代性”重新诠释,希冀超越自康德以降关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两分法的思路。他从历史积淀的思想出发,认为“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
地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因而,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改良无限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性是一个方案、一项未竟的事业。现代性方案的设计,也就是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审美的艺术方面规划人类生活。现代性设计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
哈贝马斯采用一种批判性的总体性的社会理论,高度评价早期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批判它在当代社会中的衰落。他并不否认文化的现代性也面临困境,但现代性的原初动机并不要为此负责,它不过是现代性社会化的后果,同时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问题。哈贝马斯担忧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拒斥将会导致理论和政治的危险后果,因而他竭力维护他所说的现代性具有尚未释放的民主潜力。尽管哈贝马斯并不认为现代性完美无缺,但他坚持认为现代性在其早期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后期出现了问题,他为现代性作的辩护就是要激发现代性的潜力,使之在当代生活实践中依然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理论逻辑和事实上,现代性确实具有双向维度,其一是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的规定性: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其二是思想文化方面的规定性: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
但是,毋庸讳言,现代性的这两个方面在后继的发展中确系都出现了问题,科层等级的绝对政治理性,消费主义的经济理性,操作主义的技术理性等等,要害在于人自身在经济理性、政治理性┖涂蒲И技术的工具理性面前全部泯灭,人死了,传┩持识分子为天地立心的道德理想完全丧失殆尽了。
5、西方后现代的文化多元论也难以实现人的自我救赎
西方现代性尽管竭力高扬主体的旗帜,但实质上是人作为价值目的本身全部被工具理性的价值手段异化。针对西方现代性理论中人的空场,1979年利奥塔《后现代的条件》的发表,意味着后现代思潮、心态和生活方式被提升为一种哲学理念。这种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文化现象,旨在通过反思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试图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思想、文化及历史传统,提倡一种不断突破的创造精神,主张文化多元和文化重建。
但是,后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化具有的不一致性、非同构性、不可通约性、不可翻译性等完全反对理性的立场和方法,主张人们只能通过隐喻、换喻、借喻和象征等方式言说,而不可能通过理性的途径发现真理。
把这种非理性的东西极而言之,导致了后现代主义从主张文化和价值多元的出发点,到大胆宣告理性终结,明显带有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因而,在后现代性的视域,一切都可以被超越和被解构:哈贝马斯用“科学技术与人性”的对立解构当今世界的阶级对立;丹尼尔•贝尔用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新阶层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后工业社会中握手言和;海德格尔因看到现代技术异化而反对技术理性;马尔库塞对于那种“没有目标而造反,没有纲领而拒绝,没有未来应当如何的理想而不接受当前的现状”(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页。)的“单向度”(注:在马尔库塞看来,由于“单向度”的人泯灭了想象力和个性理想,完全工具性地实现地活着,他们没有对于崇高的追求和对于标准的选择。)的人的超越;利奥塔对于现代性的“宏大叙述”的超越(注: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试图对“为代表人类普遍解放所提供合理性”的全部现代知识传统提出根本性的挑战和全面改写,即消解和重建知识论。他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思辨型、解放型(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人类的解放学说、财富的创造学说等)的“宏大叙述”方式丧失公信力。所以“现代合理性”就解体了,它正在被具有各自不同价值定位和实用标准的指代性、规定性、描述性等等“细节叙述”所取代。);福柯对于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的“理性和主体性”的天然合理性和论证合理性的怀疑,而大胆消解对于客观规律和普遍真理的(注:福柯认为,人类除了自己的历史以外一无所有,客观规律和普遍真理是不存在的,人们想通过科学实践揭示完整的、客观的、独立的世界图景是不可能的,所以探索科学合理性的努力必然是徒劳的。)做法,如此等等,后现代主义,不仅不能从西方现代性的人的空场中找回人自身,而且使人变得越来越模糊,人越来越不认识自己,更不认识其类的共同此在的本质。
二、西学传统正义理想中人的空场
由于对于人究竟是什么,人能够做什么,以及人生此在的意义等人自身的前提问题的模糊,必然对于人类社会的正义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社会正义等问题含混不清。事实上,在认识史上,对于正义究竟是什么的思想观点,真可谓古今中外聚讼纷纭。并且,在社会正义的实践途径上更是特色多样,从而使人们对于正义的希冀和追求变得扑朔迷离。犹如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的形态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看这张脸并试图揭开隐藏其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②③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2、252、264页。)
1、传统自由主义的秩序正义论以先验人性预设为前提
在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中,正义的意义往往与社会的秩序密切相关。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正义被视作政治秩序的首要品质。亚里士多德最早用平等来定义正义,他区分了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认为前者从道德的善的应然层面上关注诸如财富、资源、荣誉、权力、报酬等等的恰当分配;后者则从法的规范和状态的秩序层面确保人的正当权利被侵犯后的恢复和矫正。
这种秩序正义的思想,在古希腊自然理性和中世纪神本思维的形式理性传统中不断得到强化,成为西学传统中关于正义问题的主流思想,一直影响到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关于现代性作出经典规定时,仍然一脉相承地把制度理性优先作为现代性的重要前提条件。即具有合理性的公平秩序,是确保社会正义的先决条件。博登海默认为:“秩序,一如我们所见,所侧重的是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而正义所关注的却是法律规范和制度性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增进人类幸福与文化建设上的价值。”②
但是,西方学者在进一步探索正义的根据时,几乎都从先验人性论的层面上予以诠释。乌尔庇安认为:“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不变的意志。”西塞罗说,正义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东西的人类精神。”③
西方现代性以降,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先验人性论的思想。在古典自由主义看来,社会正义就在于从秩序上保护包括财富在内的个人的自由权利。如斯宾塞所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干他所想干的事,但这是以他没有侵犯任何他人享有的相同的自由为条件的。”Herbert Spencer, justice, New York, 1891.P46.)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仅受到所有其他人的类似的自由限制——是一条符合社会组织的通则。”(注:Herbert Spencer, Social Statics, Robert Schalkenbach Foundation, 1970.P79)这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是社会正义的基础的观点,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是实现和确保社会正义的基本途径。
然而,这种以竞争手段解决社会正义的自然人性论的主张,难以回避对于社会正义的最大伤害恰恰是人的利己本性的事实。马基雅维里认为:“一切人都有恶的本性,只要一有机会,人们就要按照这种本性来行事。”(注: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80页。)所以,权力和腐败天生就是孪生兄弟。因此有人“以获取私人利益为目的滥用公共权利”(注:参见世界银行关于腐败的定义,转引自杨夏柏主编:《反腐败研究》第六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9页。),或者“因个人(个人的、家庭的、私人集团的)金钱或地位上的利益而偏离公共职责,或者是由于私人影响而违反权力行使规则的行为。”(注:参见约瑟夫•S•内伊关于腐败的定义,转引自杨夏柏主编:《反腐败研究》第六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0页。)社会的腐败现象,就像“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注:在《汉书•食货志上》中关于腐败的原始陈述,意指谷物腐烂发霉。)的自然现象一样,均缘于人的自然情欲的利己本性。
2、新自由主义“优先原则”的正义观仅仅是一种人性的觊觎
于是,在传统自由主义不能回避财富即是善的主张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正义问题时,新自由主义就开始标榜其“正义优先于善”的主张。那么,这种观点真的能够解决社会正义问题吗?
只要看一下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罗尔斯的理论尴尬,就不会对此空怀希望了。罗尔斯给出的纯粹形式正义的两个原则分别是:“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兼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不仅在正义的储蓄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而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公平平等原则)。”
②③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1、61、62页。)罗尔斯认为,在社会政治领域,“按照第一个原则,这些自由对于所有的人都应该是一律平等的,因为一个正义社会的所有公民都应拥
有相同的基本权利。”②而第二个原则则适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它可以确保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的机会公平。在两个原则的关系上,罗尔斯强调两个优先原则:一方面,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另一方面,第二个原则中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第一个原则)。“这一次序意味着:对第一个原则所要求的平等的自由制度的违反不可能因较大的社会经济利益而得到辩护或补偿。财富收入的分配及权力的等级制,必须同时符合平等公民的自由和机会的自由。”
③即是说,政治的平等自由优先于经济的平等。尤其是第二个优先原则,表面上看有克服功利主义局限性的作用,特别是明确反对功利主义主张的苦乐之间可以等量置换,从而经济财富带来的快乐足以抚慰政治和道德上的损失的非人道思想。罗尔斯主张:无论如何,平等公民的自由和机会平等是无条件的,它决不会与经济利益进行等量交换。这听起来很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但试想一想,假如一个连经济的平等交换权利都不能保障的社会,人们还能奢望侈谈政治平等吗?所以,新自由主义的正义观也不过是一种妄想而已。
与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一样,当下西方思想领域的多种正义理论,都没有直接面对利益分配、环境责任和代际伦理的严肃现实,如应得原则(社会正义就是赋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要素公平原则(社会分配不应仅仅根据个人努力和贡献的大小,而且应根据影响经济产出的所有要素进行分配)、平等原则(人与人相互依赖构成的社会共同体中,每个人都应获得无贡献大小差异的社会财富)、需求原则(因为财富的意义在于需求,所以每个人的需要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最终根据)等等,大前提都是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
三、人的自身觉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主体前提
1、康德超越“自爱原则”的“道德律令”的正义警醒
社会正义究竟如何实现?自由主义那种仅仅诉诸于人们追求幸福的本能,并希冀这种自私的本能在自由竞争中达到公共正义的途径和方法,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人们对于任何具体幸福的追求而产生的心理愉悦,都是“出自一件事物的实存的表象的愉快,只要它应当作为对这个事物的欲求的规定根据,它就是建立在主体的感受性之上的,因为它依赖于一个对象的存有;因而它属于感官(情感),而不属于知性,后者按照概念来表达表象与一个客体的关系,却不是按照情感来表达表象与主体的关系。”⑤⑥⑦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 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26、26、26-27页。)这种幸福“……隶属于自爱或自身幸福这一普遍原则之下。”⑤它是人的本能,是任何“……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对于不断伴随着他的整个存在的那种生命快感的意识”,“而使幸福成为规定任意的最高根据的那个原则,就是自爱的原则。”
⑥自爱原则,不仅不能实现社会正义,而且恰恰相反,它往往是造成公共正义失序的罪魁祸首。因为“一切质料的实践规则都在低级欲求能力中建立意志的规定根据,并且,假如根本没有足以规定意志的单纯形式的意志法则,那甚至就会没有任何高级的欲求能力能够得到承认了。”⑦只有受纯粹意志法则规定的道德律令这种高级欲求能力,才能使人们产生“高尚的兴致情趣”康德用语。),“使人心旷神怡之际同时陶冶这种情感。”
③④⑤⑥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 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48、49、49、49-50页。)(但是。这种高尚的兴致情趣也往往被“无知之辈”用来“招摇撞骗”)康德用语。)诉诸于后一种高级欲求能力,社会公共正义问题才有可能解决。
因为“幸福原则虽然可以充当准则,但永远不能充当适宜做意志法则的那样一些准则,即使人们把普遍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客体也罢。这是因为,对这种幸福来说它的知识是基于纯粹的经验素材上的,因为这方面的每个判断都极其依赖于每个人自己的意见,加之这意见本身又还是极易变化的,所以,这判断尽可以给出这样一些最经常地切合于平均值的规则,但却不是这样一些必须任何时候都必然有效的规则,因而,没有任何实践法则可以建立在这判断之上。”所以“幸福原则并不为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颁布同样一些实践规则,哪怕这些规则都置身于一个共同的名目‘幸福之下。但道德律只是由于它对每一个有理性和意志的人都应当有效的,才被设想为客观必然的。”③
所以,对于社会正义而言,追求幸福的“自爱的准则(明智)只是劝告;德性的法则是命令。但在人们劝告我们做什么和我们有责任做什么之间毕竟有一个巨大的区别。”④“然而德性法则却命令每个人遵守,就是说一丝不苟地遵守。”⑤
康德根据上述关于幸福与德性原则的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区分,明确指出:“每个人应当力求使自己幸福这个命令是愚蠢的;因为人们从不命令某人做他已经免不了自行要做的事。人们只须命令他这样的做法,或不如说把这种做法提交给他,因为他不可能做到他想做的一切。但以义务的名义命令人有德性,这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因为这种规范首先并不是恰好每个人都愿意听从的,如果它与爱好相冲突的话,至于他如何能遵守这一法则的那个做法,那么它在这里是不待别人来教的;因为在这方面凡是他想要做的,他也就能够做到。”⑥
可见,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发现了作为目的自身的人的道德行为的动机,不是来源于经验和外在规范,而是我们对于先验的道德律令(“绝对命令”)的觉悟。“绝对命令”是经验主体道德行为所依据的先验道德原则或规律。它遵循三条原则:其一是:“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30页。)。其二是:“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手段。”⑨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1、83页。)也即应该把人当成目的。其三是:“每个有理性东西的意志的观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的观念。”(即“意志自律”)⑨康德认为,人只有以意志的先验道德律令指导其道德行为,才能体现善良意志,而不能仅仅按照自然人性的经验感受去追求幸福。但是在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发生矛盾(“德”与“福”的矛盾)时,他就让道德与幸福的完美结合的“至善”来解决这一矛盾。尽管一个人或一代人无法实现德福的统一而达到“至善”,只有世世代代的人(即整个人类)通过无止境的进步才能不断接近它,但是,只要我们始终有这种以理性的愿望为基础、追求理性的自我满足的“至善”的道德意识的觉悟,包括社会正义在内的“至善”目标就不假外求了。
2、中国传统儒家德性成人的正义内在根源论
无论如何,那种以感性的自然人性为出发点,先让人人在经验感受的快乐驱使下变成自私势利的小人,然后再想方设法用制度设计让你回归君子,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西方现代性理论,包括经济理性、政治理性和交往理性的诸多努力,在理论上都难自圆其说,实践上都难以产生深远的现实效果。
因为人如果缺少了正义之公心,就会时刻算计如何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无论外在的制度安排多么科学合理、甚至无懈可击,只要他诚心钻营就会有隙可乘,而规避制度的惩罚则会成为这种文化诉求下所有人的平常心。
与之相反的是,有诚信和正义之心的君子,则以自律的道德之心规范自己,处处循规蹈矩,即“君子怀刑”。至于有意钻营制度的空隙,连闪念一想,都会被自己的内心德性所唾弃。如果有人敢越雷池一步,自然被视作寡廉鲜耻,公共伦理应共诛之。
中国古代的儒家智慧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参透了正义发自人的内在心性,而不是来自外在规范。《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注:见《大学九章释齐家治国、大学十章释治国平天下》,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0年。)
中国古代的思想智慧以主体内在生命体验的方式,早熟性地觉悟到人生德性智慧,为社会正义及其实现,找到了内在的文化本体论根据。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人生道德智慧,从内在心性的道德悟性层面,诠释人的外在行为及社会义理的合理性根据的思想方法,对于现时代人们真正实现社会正义,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文化在开端处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注: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3页。)人对于自身德性的认识并不像认识外界自然那样,需要不断的积累见闻,而是诉诸于直觉悟性的慧根,所以北宋张载云:“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主张宇宙大道就在日常伦用中,所以“天道远,人道迩。”因此,对于人生和社会智慧的觉悟并不必然依赖于知识的多寡。有时甚至恰恰相反,经验知识与人生德性智慧有时会呈现反比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先哲的人生智慧的早熟,正是在天人关系紧张、人对天无知而敬畏的状况下,人类对于自身心性和德性的直觉内省的结果。这些先哲主张以德配天,替天行道,追求天人合一;而人只要有了体道、知道的主体觉悟,行道、布道、守道的实践行为就自然言行化成了。正可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种着眼于生命道德的人生智慧,以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为出发点,觉悟到“性命天道相贯通”的直觉悟性的体道途径的重要性,把主体的德性觉悟,视作体天道、知事理、顺人心的先决条件。故此必先说“正德”,然后才可说“利用”与“厚生”。即是说,只有内在心性的德性实践的功夫到位了,外在的政治实践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对于社会正义而言,先有了正义之心性觉悟的内在意识,之后才有社会正义的行为努力和制度安排。如儒家重视道德人格的生命,强调使生命“行之乎仁义之途”,从而以精神生命的涵养来控制情欲生命,以悲悯之情追求最高的道德价值。“致中和”就是为了使“天地位”,使“万物育”。这里的“位”可以理解为有差异的正义秩序,它是确保发展(“育”)的重要前提。
今天,伦理意识自觉的问题仍然是制度安排的形式正义问题的前提条件,人们只有广泛地达到了对社会正义的伦理觉悟,社会正义的制度规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结语:人的现实回归是实现社会正义的自觉途径
马克思从对于契约论的人性异化的批判开始,到对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异化批判,直到对于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异化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提出人的本质异化的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等的一系列批判,终于从西方近现代人的空场下的社会正义理论中跳出来,回到了人生此在的当下,明确宣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从自然、神和理性那里回归现实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旗帜鲜明地声明,只有在现实社会关系的不断合理性的变革中,争取和谐发展,社会正义的追求方能逐步变为现实。
难以忘情于功名利禄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本性,如《管子•禁藏》所云,“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卡尔•马克思一语道破天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注: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页。)尤其是在霍布斯发现的“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注: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4页。)在这三种造成人类争斗的主要原因领域,这种自私“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当人们声嘶力竭地高唱正义之歌,殚精竭虑地用制度安排呵护正义秩序时,不正义的幽灵仍然无孔不入地通过那被公开神圣化的私欲竞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自然人性论下的西方正义思想(包括现代性思想)论域中,人类与自己思想的游戏玩笑。
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正义学说进行了尖锐地批判,他指出,自由不仅仅在于排他性权利,而重要的是人类积极能动地控制自己生活条件的实践努力。为此,在社会正义即人类争取自由的实现途径上,人们要不断扬弃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和金钱拜物教。这一思想也大大启发了凯恩斯主义,“尽管凯恩斯理论迥异于马克思理论,但与后者有重要的共同之处:两种理论中,衰退都是由经济运行有关的原因引起的,而不是外部力量的影响。这一特征是凯恩斯理论有资格担当反资本主义意志的‘辩护者的角色。”(注:J•A•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0页。)
马克思的学说,使我们对于社会正义的思考,从传统思辨学说的天国世界的抽象人性论和先验人性论,回到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的思想、动机及其行为的考察上。承认“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8页。)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63、12页。)“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④所以,社会正义既不是自然人性的先验禀赋,对于它的主观认同不能觊觎自发的原始意识的体认,因而先验唯心论的人性预设的方法论理路是无效的。又不能仅仅诉诸制度的工具理性的外在他律性强制,所以制度万能论和法律至上论的方法论理路也不是绝对有效的。而必须在人们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具体地、积极主动地、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断协调中,自觉认知,认真实践。这不仅有赖于制度合理性的不断完善,而且需要伦理意识的高度自觉,更为重要的是实践行为的躬行履践。
事实上,就几百年自由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而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其对于人类福祉的增进,而且也有在资源、财富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不正义的马太效应的加剧。这种把感官快乐与财富、道德的善及社会正义划等号的做法,严格说来是一种伪善。因为它造成的社会结果往往与其理论宣称的预期大相径庭。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怀疑这种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善恶主张,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福利理论,究竟能否真正实现社会正义。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理想,还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度评价的傅立叶等西方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提倡的“社会和谐”,都仅仅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而非是一种积极的实践活动和过程。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才第一次明确┨岢觯要在制度安排和具体实践中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社会正义从理想到现实的重大飞跃。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责任编辑:张 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