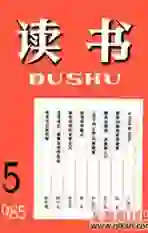国际问题研究的硕果
1985-07-15郁进
郁 进
岁月不居,重庆朝天门码头下长江嘉陵江汇合处,四十多年来浩浩荡荡地流逝了多少水!对于当年教育和引导我们年轻人的《新华日报》的记忆,依然很鲜明地萦绕在心头。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覆盖在重庆上空的白色惨雾更浓重了。我那时曾在一篇短文里这样写道:“浓雾充塞了山国,锁着江流,压着山峦,塞着人们的嘴,好象连呼吸也感到不自由。”这是一个沉闷和压抑的低潮时期,也是一个寻觅和追求的理智时期。当时重庆有九家大报,《新华日报》是插在敌人心脏地带的一把尖刀,在广大进步群众的心目中,她是照临国统区的一张“北斗报”。夜沉沉,雾茫茫,她象一座放射巨光的灯塔,为人们指示着前进的方向。在反共狂潮下,报纸的出版发行受到严厉的压制、封锁和检扣,而广大读者每天都殷切地盼望着报童到来。一九四二年秋季,报纸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整风改版,贯彻大众化通俗化的方针,新闻报道和副刊都有特色,新辟的专栏多姿多采,更密切地联系了群众。乔冠华以“于怀”笔名写的“国际述评”栏,就是这次改版后的新措施之一。
在《新华日报》上写国际述评的作家中,前有卓芸(章汉夫),后有余伯约(夏衍),而以于怀执笔的时间最长。他从一九四三年一月到一九四六年三月,每两周一篇(只在一九四四年四月至八月因病中辍),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重大战役、重要国际会议和世界战争全局的关键性问题,还评论了战后一年间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起初作者曾署“洛木”笔名,不久便以“于怀”的名字吸引着读者,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专栏。
于怀的“国际述评”写得既有深度,又活泼生动,向大后方人民传播了党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鼓舞了争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信念。关心时局的读者,用来作为时事学习的材料,在许多小组和读书会中被人们传诵着。部分述评在一九四三年出版过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形势比人还强》,一本是《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一九四五年的国际述评,曾以《从战争到和平》的书名出版过单行本。现在这些文章全部搜集起来,题名为《国际述评集》,作为《新华日报文选》丛书出版。这本述评集的意义还不止此,从学术质量看,是我国学者关于国际问题研究的硕果之一,对于如何普及国际知识,剖析国际形势,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今天重读这些述评,不仅引起很多回忆,而且仍然是一次有益的学习。
循名责实,国际述评既需要叙述,又需要评剖。这些两周一次的述评,都是紧跟着发展中的时事匆促写出的,但在材料的搜集和对材料的分析两个方面,都可见到作者的学力和识见。当时重庆与外界联系困难,国际资料的获得有很大的限制。作者力求做到能够占有比较全面的材料,而不单单是几家外国通讯社日常电讯的排比。正面的材料固然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作者在研究中也不轻轻放过反面材料,剥开假象,从中找出有关国际形势演变的焦点。对于问题的分析,经常从战争的全局去考察战争中发生的任何一个新的问题。纵笔分析和判断问题时,则又力求做到应有比较充分的根据,不说过头话,有多少根据说多少话,避免根据不足或是缺乏根据的论断。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谨严的治学态度。
打开述评集来,我们在热情生动的叙述中看到作者严肃的评剖。例如:一九四三年二月日军从瓜达康纳尔群岛撤退后,三月间又对盟军发动大轰炸,日军在南太平洋的动向即入于扑朔迷离的状态,守乎攻乎,议论纷纭。作者在《法西斯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一篇中作了透彻的说明,两方面都估计到。一九四三年夏季苏军展开大反攻,以巨人的步武从一条河流跨到一条河流。由于德军败退的速度,有些人天真的问起德军是在败、还是在退?作者具体地分析了那绝不是“自动性多”的“退”。对于一九四四年日军在大陆中原、湘北和珠江河谷的大规模攻势,作者指出敌人的企图不止于夺取交通线,而且要在它那“基本海面”的大陆部分生根。所有各种分析,早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无需重复引述和申论。这里我想试从另一角度来看于怀的国际问题论著。
在我国,用科学的观点方法进行国际问题的研究,除开二十年代的一些政治文献应予另论外,大致可以认为是从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前后开始的。这中间胡愈之是前驱先路,他从外国文学的译介转向政治外交的研究。他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发表的《国民外交与国际时事研究》一文提出了问题。与此同时,他发表了国际问题研究的十篇论文,从叙利亚问题、比萨拉比亚问题、棒喝运动、裁军问题、国际联盟到石油战争、坦及尔问题与苏丹问题等。他以本名和“伏生”笔名发表的国际问题论文,在上海引起了中外报刊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更刺激了对于国际问题的探讨。自觉地以呼号救亡为己任的韬奋,这年十月十日在他主编的《生活》周刊第六卷第四十二期的刊头上,用黑体字印上了“国庆与国哀”五个大字。在这一期上,胡愈之发表了《一年来的国际》一文。一开始就说:“过去的一年,才真是一个昏黑的年头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短促的和平时期,现在已渐成过去了!人类的第二次大悲剧的序幕,已在逐渐展开了。”文章列举了一年来发生的多少灾难事变后指出:“可以归结到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普遍全世界的经济大恐慌。”“因各国经济的极度恐慌,帝国主义对立的形势,亦愈益尖锐化。”“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与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了。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非常举动,实亦出于同一的原因。”这个时期国内报刊对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注意,当推胡愈之主持的《东方杂志》,经常发表有关的论述和资料。在这家杂志上,我们看到了张明养(常署名为“良辅”)、金仲华(笔名为“余孟如”)等的论文,后者开初主要是写妇女问题;接着便读到冯仲足(笔名“宾符”)等的文章了。
在风云变幻的一九三四年,胡愈之为生活书店创建和主编了《世界知识》,从此在国内形成一个园地,为普及世界知识、提高国际问题研究水平而努力,吸引和组织了不少进步作家撰稿。这中间有金仲华、毕云程、钱亦石、张明养(此时笔名为“张弼”)、沈志远、冯宾符、吴景崧、郑森禹……等,夏衍也以“韦
解放前,在我国出版的报纸中,对于国际新闻版着意经营、确具特色者,首推重庆《新华日报》。那时候延安还被封锁,正是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外国党报党刊以及华侨进步报纸建立了联系,取得了不少英、美、印度等地的剪报材料,以及俄文的英文的报刊,从中摘出适当的内容,加以翻译或改编,使读者了解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民主斗争的情况,形成《新华日报》国际新闻版所具的独特的格调。报纸有关国际问题的专论,经常传达党的看法和主张,文笔简练,大都说理透彻。版面还有时评、短评、各种国际资料,乃至拾零花絮,读者很表赞赏。所有这些,担任总编辑并负责国际新闻版的章汉夫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编译和资料室同志也主动提供稿件。如果说,这好比是一支才能卓越、配合谐和的乐队的话,那么,乔冠华则是其中的“第一小提琴手”。这样的看法并非溢美吧?
“国际述评”的文字优美动人,热情洋溢。那些大标题,往往用抽象的或形象化的语言,明确指出或者暗示当时国际局势的焦点。例如:《胜利必须在地上争取》、《形势比人还强》、《人创造了形势》、《怒吼吧,莱茵河!》、《八月秋高风怒号》、《钟声为谁在响》、《站在命运的河边》,以及《雾伦敦》、《控诉赫尔利》等等,都使读者可以立即把握住问题的实质,同时予人以信心和鼓舞,激励着争取民主自由、团结进步的斗志。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激情和人们的喜怒忧乐。”那时,阅读《新华日报》是我们年轻人的“必修课”,不仅自己反复阅读,而且拿到同学朋友们中间传阅。在党的直接指示之外,我们就靠着阅读《新华日报》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指导青年运动的专文,是我们进行工作的南针;社论、“国际述评”及“国内述评”,是我们认识时局的导师。我们正是从这些评论的字里行间,侧耳谛听党的声音,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喜悦和鼓舞啊!记得我们青年组织的同志说过,有一次,报纸在壁山全部被没收,有位同学却秘密带了一份到学校,星夜将登在那天报上的于怀的“国际述评”《原子弹》一篇抄录张贴,引动了学院里许多同学来围观。这就象在死水一潭中投下了原子弹,给反动当局带来多大的震惊和恐惧啊!
于怀的“国际述评”,剖析国际形势时,在重大问题上总是与国内争取民主团结进步的斗争密切呼应着。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研究世界局势正是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国。依我体会,我国进步文化界的国际问题研究,一向是和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的斗争密切相联的。回溯我国近代的国际问题研究,我以为应当从清朝道光年间林则徐编译《四洲志》、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算起。林则徐是我国近代第一批面向世界的先进人物。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在林译《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后又扩充为一百卷。那正是英国发动鸦片侵略战争时期,用魏源的话说:“海艘迭警,不胜漆室之忧。”(《与邓显鹤书》)我国的先进人士,无不关怀国家命运,注意世界大势。《海国图志叙》明白指出当时研究外国的目的性:“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书中提出要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主张,学习的方法和主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国际问题的研究,启发了此后国内不断出现的要求变法图强的思想家和活动家,而且此书传到日本,也受到东洋先进人士的重视,对于日本的维新有所影响。夏衍在纪念《世界知识》创刊五十周年的文章中也说:“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要了解中国现状,就得了解世界,要抗日救亡,就得了解正在形成中的德日意三国同盟,也还得了解美英法等国和日本的关系。”解放前,《世界知识》每期开篇的“
于怀才情横溢,学有根底。这种国际时事文章,其生命常如花丛中的粉蝶,而他的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当时起过良好的作用。作者曾埋头精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在南部德国土宾根大学求学时,用他自己的话说,还“啃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撰写“国际述评”的同时,又翻译了原籍德国的反法西斯军事评论家M.威尔纳关于要求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著作。据闻周恩来当时对这个德籍评论家的分析很重视。
当我还在研读国际政治的学生时代,在重庆临江路亦代同志的宿舍里认识了于怀,其后得知还有乡谊,家人且有往来。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王府井大街看到攻击他所在的单位的大字报,血口乱喷,那是对无产阶级、对文化、对大革命的肆无忌惮的亵渎,我不禁为他捏一把汗。忆我少时,读过梁启超《盾鼻集》中《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文,说洪宪帝制运动时,其人一手执黄金,一手执白刃,闹得国中道德堕落,最为坏人心术。予生也晚,没有经历洪宪帝制运动的实感,还认为是任公神来之笔。经过“文革”的动乱,才体会到对国家的损害,对人才的扼杀,对世风的败坏,当远甚于洪宪的作乱。今天重读于怀的《国际述评集》,不能不痛惜他的早逝。“文革”毁坏人,长才未尽展,逝者长已矣,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国际述评集》(新华日报文选),乔冠华著,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版,1.8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