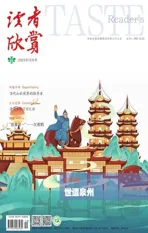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2023-12-24黄种酷摄影张艺欣
文/黄种酷 摄影/张艺欣
泉州,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节点城市、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时期中国与世界对话的窗口。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6项世界遗产。
10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践行,泉州再次走进世人视野,成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热土。如今,循着历史的脉络,回溯曾经的辉煌,我们清晰地看见泉州在朝代更迭中的变迁,看见一座跨越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名城”正从这里乘风远航。

蟳埔女
中世纪光明之城,现代与传统交织
晨曦中,蟳埔滩涂布满赶海人的脚印。头戴“簪花围”,耳佩“丁香钩”,身着“大裾衫”,腰上别着“小红包”的蟳埔渔女忙着下海捕捞鱼虾,上滩涂敲蚵,挑海鲜贩卖……她们穿梭在集市之间,也行走在街巷里,靓丽的身影在城市的车水马龙里格外显眼。
陈敬聪先生的《蟳埔女》一书中记载,蟳埔女贩卖海鲜最早可以追溯至清代乾隆年间。诗人写诗赞美蟳埔女“家住鹧鸪大海汀,阿姨少小贩鱼腥。罗巾竹笠新妆好,不插闲话鬓越青”,描绘的正是蟳埔女从小进城贩卖鱼虾的场景。蟳埔村东北有座鹧鸪山,明天启七年(1627年)于山上置“鹧鸪口铳台”,到清康煕年间,从祥芝迁移过来的巡检司又名“鹧鸪巡检司”,因此蟳埔的妇女便被称为“鹧鸪姨”。她们因独特的服饰和头饰,与惠安女、湄洲女并称“福建三大渔女”。“鹧鸪姨”也成了泉州人对蟳埔女的一种亲切称谓。
簪花围是蟳埔女特有的头饰。蟳埔女把浪漫和春天“戴”在头上,用鲜花盛放的样子去迎接每一天。她们如行走的花束,用热情和勤劳在滩涂上播种希望,她们是泉州这座现代与传统交织的城市中一个真实的存在。
海边那些用蚵壳建造的房屋,先前你可能未曾见过,这些正是蟳埔渔女的居所—蚵壳厝,在泉州的蟳埔村、法石村及泉州沿海一带均有分布。这些贝饰古民居独具特色,构造巧妙而神奇,是东南沿海乃至全国都绝无仅有的一种建筑形式,构成了闽南沿海古民居的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

蟳埔女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拥有3个海湾和12个支港,海岸线绵长,冬天港口不结冰,是一个天然的良港群。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繁荣于隋唐,鼎盛于宋元,衰落于明清,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的走向。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的实行,使统治阶级加强了对南方广大地区的控制,岭南的广东、广西等沿海地区被纳入统治范围,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广东番禺、徐闻,广西的合浦等港口出发,途经东南亚各国,到达印度半岛,在印度与西方的希腊、罗马商人对接,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体系。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战争频仍,大批缙绅﹑士大夫及庶民百姓“衣冠南渡”,最终在泉州沿江而居,落地生根。纷乱的铁蹄让原本生活幸福的晋人不得不舍弃家园,为了慰藉去国怀乡的忧思,他们把择居地的两条江分别命名为“晋江”和“洛江”。每逢重九,他们便会在曾经的渡口登高北望,以此寄托离人的夙愿,并将登高北望的山峰唤作“九日山”,从此,晋人在这里经山略海,用智慧的双手徐徐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绝美画卷。“衣冠南渡”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人口、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以及成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从而带动了泉州的整体发展和繁荣。

有“天下无桥长此桥”美誉的安平桥

洛阳桥
勇敢的晋人开辟出新航线,贸易途经印度洋,最远处抵达红海、波斯湾一带。但由于战乱对经济社会和海外贸易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比较缓慢,没有取得规模性的突破。直至隋唐,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隋唐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泉州、广州为主要出海港,经南海到东南亚各国,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半岛,再经印度洋到达红海、波斯湾沿岸各国,以及东非、北非地区,形成了一条十分稳定的远洋航线。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丝绸、瓷器、茶叶和铜器、铁器是出口物资的“四大宗”,中国商品、中国文化、中国符号也随之输往世界各地。
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大,泉州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宋元祐二年(1087年),宋朝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宋元时期,泉州的海外贸易与社会经济发展达到鼎盛,市舶司建立后,凡涉洋经商船只及货物往来,可用小船,溯晋江,沿破腹沟、过水关,直达市舶司报关。
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峰期,是东西洋之间进行国际贸易的一个交会点。这样一座无可比拟的港口城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人们称之为“光明之城”。
意大利商人兼学者雅各·德安科纳冒险远航东方,就是为了寻找中国大都市“光明之城”泉州。他经历了万般险阻,终于在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抵达泉州,并在泉州停留了5个月之久。雅各·德安科纳在其手稿中记录了他在泉州逗留期间的所见所闻,描述了南宋末年泉州的政治、经济、民俗等方面的情况。由于雅各·德安科纳比马可·波罗早到中国,他所记述的南宋泉州的社会文明远远超过当时的欧洲。因此,当他的手稿被英国学者大卫·塞尔本发现并翻译成英文出版后,这本《光明之城》立即引起国际汉学界广泛关注和激烈辩论。这是继《马可·波罗游记》之后,又一部引起国内外学者大辩论的有关泉州的中世纪游记。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他奉命护送科克清公主到伊儿汗国,离开元大都后一路南下,“离福州,渡一河,在一甚美之地骑行五日,则抵刺桐城,甚广大,隶属福州”。因五代十国时期占据泉漳17年的节度使留从效重修城垣时在城周遍植刺桐树,所以泉州也叫“刺桐城”。刺桐花是泉州的市花,颜色十分鲜艳,给人一种红红火火的热闹感。“刺桐城的沿海有一个港口,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驶往各地出售。”“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我们透过马可·波罗的游记看那时候泉州港的繁盛之况,可见泉州在元代港口贸易之兴盛无出其右。不管是雅各·德安科纳还是马可·波罗,他们对泉州均推崇有加。雅各·德安科纳寻找他向往已久的“光明之城”,马可·波罗邂逅东方第一大港,这两位中世纪的旅行家对泉州港的繁华不吝赞美之词,让我们对宋元泉州港的兴盛充满神往。
八闽形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
“明清时期看北京,宋元中国看泉州。”泉州申遗的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包括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磁灶窑址、德化窑址、顺济桥遗址等。这是中国第56项世界遗产、福建第5项世界文化遗产。自此,泉州多了一项桂冠—世遗之城。
其实,早在此前,泉州就已名声在外,它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素有“八闽形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海滨邹鲁”“文献之邦”等美誉。截至目前,泉州市拥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36项,成为全国唯一拥有联合国三大类非遗项目的城市。

洛阳桥
古代泉州人以海为生,向海图强,出海和回航都需要顺应季风规律。泉州夏季偏南风,船舶从南部海域回航;冬季偏北风,船舶从泉州出海。因此,每年夏四月、冬十月,百姓会在九日山下的昭惠庙向海神祈求风信顺利,保佑航行平安,这就是泉州古老的祈风传统。
由于海外贸易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巨大,宋代官方极为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来泉州经营海外贸易的番舶靠风驾船,在春夏随东南风而来,秋间则顺西北风而去。每年番舶扬帆之际,泉州郡守、市舶司有关官员及泉州知名人士都要登九日山昭惠庙,在通远王祠为番舶祈风,并勒石记之。海外贸易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人们对船舶的航行安全更加小心翼翼,除了在通远王祠为番舶祈风,还会在真武庙望祭海神。
明万历《泉州府志》中记载:“玄武庙在郡城东南石头山,庙枕山嗽海,人烟辏集其下,宋时为郡守望祭海神之所。”1533年,晋江县令韩岳在真武庙树起一块刻有“吞海”二字的石碑,寓意真武大帝法力无边,吞纳大海,保佑航海平安。同时,也显示出泉州人经风斗浪、远渡重洋的豪情壮志。石碑底座大石酷似乌龟,另一边的突出部分酷似蛇头,契合真武大帝的“玄武”形象。“吞海”二字寄托着所有靠海为生的人朴素的愿望—不要海吞船,而是船“吞海”。
生在海边的人们将航海安全视为最重要的生命保障,每一次远航都会做好各种准备,由此可以看出泉州人对大海的敬畏,对生命的珍重。始建于宋庆元二年(1196年)的天后宫原为顺济宫,是泉州人奉祀海神妈祖的重要场地。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为发展海上贸易,元世祖派遣正奉大夫宣德使蒲师文在泉州天后宫举行祭祀和褒封妈祖的典礼。自此,妈祖得到朝廷的重视和认可,妈祖信仰成为沿海一带渔民和商人的又一重要信仰。
清代,私商贸易和向东南亚各国及我国台湾移民的热潮在泉州港兴起,妈祖信仰也随着泉州商人和移民的足迹更为广泛地传播。泉州港也开启了兴盛的征程,逐渐跃升为东方第一大港口。在繁华如斯的泉州港,帆樯林立,万舸争流,商贾云集,梯航万国,可谓“市井十洲天下人,涨海声中万国商”。

安溪茶山
商旅的队伍沿着天后宫到南门(德济门)外准备过江,除乘船外还可以从桥上走过。因顺济桥离天后宫(顺济宫)近,人们就把跨江的这座石桥当作过江的首选,并将其命名为“顺济桥”。
顺济桥始建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泉州知府用外商修建泉州城楼的余资所建。顺济桥桥面为梁式石桥,长约500米,宽4.6米,现存船形桥墩及桥墩遗址约30处。顺济桥是继洛阳桥、安平桥这两座著名的桥梁之后,泉州古代桥梁修建史上的又一杰作,承载着一支又一支商旅。
随着时光的流逝,顺济桥的一部分桥墩倒塌,成了“断桥”。它静静卧在江面上,见证着泉州的繁华,向世人诉说着这座城市不平凡的过往。
海上丝路新盛景,世遗泉州见传奇
自晋人“衣冠南迁”,泉州这座城市在朝代的更迭中不断融合、变迁,儒释道、伊斯兰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在泉州广泛传播,共融共生又彼此独立,足见泉州人的包容和大度。直到今天,泉州府文庙的先贤们身上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桑莲法界”开元寺依然肃穆庄严,老君岩造像苍髯飞动、脸含笑容、巍然端坐,清净寺见证了海外贸易以及舶来的宗教文化……

姑嫂塔
在烟波浩渺的泉州港,“繁忙”是这个港口的常态。随着市舶司的设立,泉州港的海外贸易进一步繁荣,泉州港的舶税收入也越来越重要,引起北宋朝廷的高度重视。因难舍泉州舶税之丰腴,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北宋将皇族宗室349人迁徙至泉州,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随即从江苏镇江迁到泉州,将旧馆驿内西侧的泉州添差通刺厅改成皇族居住地,“南外宗正司”司署设在古榕巷内水陆寺中。
“南外宗正司”规模不断扩大,北宋皇族宗室聚居地建筑富丽堂皇,司内设有睦宗院、惩劝所、自新斋、芙蓉堂,还有天宝池、忠厚坊等。同年,在泉州州治西南袭魁坊睦宗院东设立专门教育皇族子弟的“宗学”,学制二年。在泉州的宗室子弟初期仅349人,后逐渐壮大,至绍定年间(1228—1233年),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他们从中原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带来罗、绢、纱、绫等新产品,传入织、绣、彩、绘、染色、印花等先进技术及先进文化,促进泉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到南宋时期,造船业、纺织业、制瓷业空前发展。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在《诸番志》中记载,此时泉州的纺织品已远销东南亚诸国及坦桑尼亚。
磁灶窑、德化窑、安溪窑、东门窑、南安窑等著名窑口的陶瓷产品,安溪青阳下草埔的铁制品远销世界各地。当时,与泉州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近百个,数以万计的各国商人、传教士、使者、旅行家、贵族和平民纷至沓来,穿梭于泉州港的船舶中,甚至有不少人溯晋江而上,抵达泉州城郊的重要内港—法石港,在涨海声中装卸吞吐、通商贸易。法石港内的美山、文兴、圣殿、厂口和富美等十多个码头上,百货山积、帆樯如林,是泉州城内通过晋江水系连接泉州港出海口的重要转运码头。
如今,只有文兴码头、美山码头有迹可循,它们被合称为“江口码头”。而作为外港的石湖码头也承载着水运的重要转运功能,与江口码头共同构成宋元泉州港的水陆转运系统。石湖码头以所在村落“石湖”而得名。这里古称“日湖”,东方破晓,一轮朝阳从湖中升腾而起,所以得名“日湖”。12世纪,作为泉州外港航标塔的六胜塔建造之后,日湖又增添一处盛景,巍峨的石塔与秀丽的港湾交相辉映,故日湖又被称为“石湖”。
石湖半岛位于泉州湾中部,晋江和洛阳江交汇处的海口,三面临海,西侧为一半月形海湾,形成天然的避风良港。其对内可直达双江,对外扼守泉州湾主航道。随着泉州海外交通的兴盛,万寿塔、六胜塔两座航标塔相继建成,石湖码头的航运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