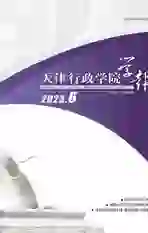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运作机理、实践悖论与路径优化
2023-12-06张明皓陈怡思
张明皓 陈怡思
摘要:数字技术通过赋能“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和“治理的现代化”,构成驱动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实践悖论表征为风险暴露、参与替代、技术依赖、公正偏离等,具体呈现为一种“负能”困局。为纠正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实践偏差,应构建全流程链式乡村数字风险防范管理体系,探索与乡土社会嵌合的多向度数字化参与模式,革除技术万能的思维屏障,建立公正导向的平衡治理机制,使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真正复归安全性、参与性、自主性和公正性,从而促进农村现代化深度转型。
关键词: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农村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23)06-0061-08
一、问题缘起
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与科技革命的强大驱动下,数字技术已经渗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数字资源成为基础性的战略资源,建设数字中国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在数字中国的版图中,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并将其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了数字乡村建设的任务目标和具体内容。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部署了“十四五”时期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执行任务。可见,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具有明确的政策依据,是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1]。同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而农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仅为105%,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具有明显的现实紧迫性。因此,必须把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契机,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核心优势。
对“赋能”(empowerment)一词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为改变黑人族裔无力感和无权感所提供的理论思路[2]。从适用范围上看,赋能涉及个体、组织和社群等多个层面,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学科领域得到广泛研用。赋能的核心要义是个人或组织获得过去所不具备的能力或实现不能实现的目标[3],具体表现为赋能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得到提升[4],其对生活的决定权和控制权等得以强化[5]。在赋能概念原型基础上,相关研究也产生了对“数字技术赋能”的理论阐释。数字技术赋能是数字技术提升个体和社区影响力的动态过程[6],具体指向的是提升人群或组织的数字治理技能和行动能力[7]。在进行数字技术赋能正向功能探讨的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数字技术的“反治理”面孔[8],即数字技术容易产生隐私泄露、伦理冲突、惩罚失效等社会风险[9],招致形式主义泛滥等社会治理问题,产生技术异化风险[10],因此我们需要对数字技术的复杂性影响进行审慎考证。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在本质上是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匹适互动过程。当前“数字技术下乡”已呈显著发展趋势,数字技术日益嵌入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引发乡村物理空间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11]。在上述背景下,须最大限度发挥数字技术优势,系统审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运作机理、现实限度和支撑路径,探求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深度嵌合之道。
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运作机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2](pp.44—45)数字技术正广泛渗透于农村全面现代化转型过程,成为推动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运作机理具体表现为数字技术赋能的“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和“治理的现代化”三维向度之耦合。
(一)运行基点:数字技术赋能“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包含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尺度、行为方式等的现代化转型,是个体从传统社会的依附状态逐步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正如英格尔斯提到,“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13](p.8)。数字技术赋能“人的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提升个人的数字化素养以及信息应用能力,增强个人的社会参与能力和对生活的决定权。这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赋能农民综合素养提升。在“数字技术下乡”背景下,农民拥有了知识学习和技能提升的多元渠道和场景。数字技术促进了信息互联共享,增加了农民信息获取的方式,开拓了农民的思维视野,使农民逐步具备学习知识和技能的主动意愿,将农民从“信息贫困者”转变为“信息富有者”,实现了农民数字化素养的提升。二是数字技术赋能农民知情权和社会参与能力。数字技术延伸了社会治理的触角,使社会治理具有透明化的优势。数字技术叠加了乡村熟人社会网络的信息传播优势,使村级公共事务信息得到即时化和可视化的再现,使农民具备对村级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同时,数字技术使乡村转变为“超联结社会”[14],通过再造虚拟社区公共领域,连接原子化的村民,重构乡村内生秩序。数字技术媒介的秩序构建打破了农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失语状态,强化了农民的监督权和参与权,实现了农民自身话语权的增益。三是数字技术赋能为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提供了资源和条件。数字技术通过与外部资源的联通使农民具备了更好的生活资源和条件。如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产业链全过程和全环节,可以推动农业附加值提升。同时,电子商务平台也可实现农产品出村进城,有助于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数字技术调节了农民自身与外部环境资源获取的关系,使农民自身具备对生活的控制权。数字技术赋能“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复归农民的主体性价值,增强农民参与社会生活和决定自身发展方向的行动能力。
(二)條件支撑:数字技术赋能“物的现代化”
数字技术赋能“物的现代化”包含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平台载体的数字化和乡村产业的数字化三个基本层面。一是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在供给端上,这主要表现为宽带网络、物联网、云计算等系统的搭建与普及,也包括对乡村传统路网、电网、水网和物流网络等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和升级。在应用端上,这表现为对智能终端、技术产品等的使用和扩展。基础设施的数字化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最为基本的运转条件。二是平台载体的数字化。数字服务平台依托信息技术的跨域性,使民生服务集成化和在线化。首先,平台载体的数字化可全面联通政府部门信息,推动政府信息数据共享,从而突破信息壁垒。其次,推行平台载体的数字化有助于全力整合多个政务平台,有助于建设线上线下一体化和公开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提高政府服务乡村的能力。最后,平台载体的数字化可实现乡村村务、政务和党务的在线整合,充分集成乡村网格化监管、村务监督、法律咨询等功能,满足农民差异化的生活需求。三是乡村产业的数字化。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乡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有机衔接。一方面,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有助于创新农业产业新业态,构建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管理体系,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变革;另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可实现对销售流通的全流程追踪,有助于深化精准营销,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而倒逼农业结构调整,破解农产品增产不增收的困局。总之,数字技术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有效运转条件,通过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平台载体的数字化以及乡村产业的数字化,全面实现乡村“物的现代化”,为农村现代化提供扎实推进的物质基础。
(三) 目标导向:数字技术赋能“治理的现代化”
数字技术赋能“治理的现代化”是在数字技术手段驱动下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变革,具体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赋能对乡村治理行政化的实质改进。乡村治理行政化包含一种管制型治理的思维,政府和社会之间表现为层级强制的权力关系。数字技术有助于建立“去中心化”的权威结构,推动乡村治理的权力格局向分散化和扁平化过渡。数字技术赋能下的乡村治理体系并非呈现“中心—边缘”结构,而是呈现为开放流动的网状结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界限因技术信息沟通而消解,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也得以突破信息闭环的僵化结构,实现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场景的民主协商。数字技术赋能有助于改变乡村治理行政化的权力基础和社会基础,实现向乡村治理社会化迈进。二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能力的整体跃升。对数字化信息的采集和深度分析有助于挖掘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共识性需求,强化乡村的自我决策能力。同时,数字技术的社会化特性打破了多元主体的信息区隔,为合作治理搭建了基础平台,抑制了政策执行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增强了乡村对政策的执行能力。另外,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事件模拟和舆情监测,可为乡村应急管理提供风险预案,增强基层的应变能力。数字技术赋能形塑了乡村韧性治理格局,全面扩充了乡村治理的综合能力。总体而言,数字技术赋能“治理的现代化”在于全面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并充实乡村治理能力,建立多元主体共融型的治理共同体,从而以“智治”推动乡村“善治”。
总体而言,数字技术赋能“人的现代化”在于为乡村建设提供自觉性和学习性的微观主体,数字技术赋能“物的现代化”在于推动农村基础设施网络、平台服务载体和乡村产业发展数字化转型升级,而数字技术赋能“治理的现代化”则旨在重点改变乡村治理原有的粗放性和非专业化状态,使之形成更具现代性的综合治理能力,从而为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提供可行方案。数字技术赋能可以推动乡村社会发生全面的现代化转型,构成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关键驱动机制。
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实践悖论
数字技术更新了乡村建设的手段方式,实现了多元主体、地域时空和资源要素的“数字整合”[15]。但数字技术在彰显赋能优势的同时,也伴生多重实践风险,甚至可能诱发“数字负担”。
(一)安全悖论:乡村建设多环节伴生数据暴露风险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前提是将农业农村各领域的模糊性信息转化为标准化、格式化的数据资源。在大数据时代,密布的监控感知系统对农民行为进行数据识别和采集,并通过数据挖掘和数据关联处理使农民的行为轨迹实现全景敞视,这本身会使人的生活空间无所遁形。一方面,数据的精准识别、采集和追踪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有助于抑制基层权力“跑偏”,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16],为政府强化乡村治理和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提供基础支撑。另一方面,海量数据的安全储存及隐私泄露问题也为乡村建设带来新挑战。数据存储漏洞、数据违规使用、敏感信息违规采集等都将引发严重的隐私泄露风险,且技术弥补和政府反馈的迟滞性将会使数据风险不断演化扩散,农民个人权益将受到严重侵犯。数字技术的规范化之维和数据风险之维相互扭结伴生,因此在乡村建设中,政府要设置严格的数字风险把关机制,将数字风险消除在可控范围内。
(二)参与悖论:脱离乡村实质民主的“开放假象”
公众参与是“善治”的核心特征,自觉的公众参与将增进公共事务治理的有效性,打破公共权力的封闭性和单向度。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延伸增强了民众参与能力,打通了“在场”与“不在场”的时空界限,有助于推动多元主体协商民主与扁平化共治行动网络的达成[17]。数字技术也拓展了民众进行反馈和权力监督的空间,有助于增强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效能[18]。然而,数字技术在改变民众参与方式和强化民众参与能力的同时,也产生了隐蔽的“参与替代”情境。这主要表现为数字技术赋能所取得的增益效果被乡村精英分子所“俘获”,而乡村中的“数字失能者”尤其是老年农民等群体则被技术区隔和挤出,难以享受数字技术进步带来的便捷性和可及性。同时,数字技术企业由于垄断了技术研发、应用与运营环节,往往拥有相对强势的话语权,形成“数字霸权”[19],导致政府和民众对数字技术企业的依赖日益强化。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一方面,数字技术创建了协商共建共治的平台,使乡村多元主体有效参与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及其衍生的平台系统极容易营造一种“开放假象”,在程序民主得以保证的同时却形成了隐蔽的参与替代,从而偏离实质民主的真正价值。
(三)自主悖论:技术依赖塑造的基层形式主义和“增负”怪圈
数字技术可以减少信息传递层级,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信息不对称。同时,强大的数据挖掘和算法分析能够为精准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自主性。借助数字化工具,农业农村领域多元模糊性信息在被过濾、加工和集成处理后可以转化为政府决策的重要支撑,有助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态管理,提升公共资源下沉服务效率。数字技术转变了单线条的乡村治理模式,开创了多线型的任务平行处理模式,增强了乡村建设的组织动员效率,提升了乡村建设决策的自主性。然而,数字技术在促进乡村建设自主性决策机制构建的同时,也衍生了“技术依赖”的思维和行为惯性。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技术创新的盲目崇拜,认为技术进步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技术时代的人同时在深深地着魔,着魔于技术的无限制发展,着魔于技术的进步而忘记了事物和人自身存在的状态,使人和世界日益走向对立。”[20]可见,这种技术万能论的思维偏见忽略了数字技术赋能的内生局限及其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嵌合性。二是形成“数字化形式主义”痼疾。在日益强化的“数字管理”的指标偏好下,乡村数字内容生产往往变异为可视化的数据“留痕”,开发数字平台、扩大发文量和转发量等成为基层工作人员的重要工作。这种量化的“数字政绩”虽然迎合了上级政府的监督考核,但难以真实反映乡村建设境况,其内容生产脱离群众的实际需求[21]。三是数字技术成为“增负”平台,形成内耗局面。基层工作人员需要将数据信息录入多种政务APP,完成多个平台的打卡任务,其正常工作时间被平台数据录入所挤压,“指尖工作”任务量和基层工作人员的机械劳动大幅增加,“技术赋能”异化为“技术负能”[22]。
(四)公正悖论:乡村数字治理的公正偏离
数字技术保证了治理行为的透明性和可回溯性,便于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有助于避免政府权力运行的偏误,保证民众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出现乡村矛盾纠纷时,数字技术也可辅助司法系统,帮助实现案件审理的智能化,提升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公开。然而,数字技术赋能在增益乡村建设公正性的同时,却造成公正偏离的境况。一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犯罪逃逸”。例如,部分人员利用数字平台从事违法诈骗行为,其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强、调查取证难等特点,违法人员很容易产生逃逸行为,受害人权益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保障。二是责任划分的模糊性。在因数字技术造成风险暴露事件时,相关方责任无法被准确评估,技术设计者和使用者的责任推定面临极大困难。“谁来负责”成为防范乡村系统性数字风险亟待解决的难题[23]。三是“算法偏见”造成的公正困境。在完成复杂任务时,需要编制特色算法辅助数据搜寻和模型选择,但算法设计容易渗入开发者的意图偏见以及数据偏见[24]。这些隐性偏见可能会导致“大数据杀熟”以及数字服务的阶层区隔化、代际落差化和性别排斥化等实践症候,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乡村建设决策的公正性,从而放大“数字鸿沟”,防碍乡村建设成果的平等共享。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25](p.776)数字技术赋能实现了乡村建设价值层面和应用层面的效果跃进,但也造成安全悖论、参与悖论、自主悖论与公正悖论,为乡村建设带来了系统性危机。因此,需要洞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现实限度,探索预防数字技术异化风险的全面规制之路。
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路径优化
在全面推进乡村建设中,要把握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时代契机,消解数字技术赋能的多重悖论,克服“唯技术化”倾向,融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构建动态平衡的乡村数字治理机制,切实增进乡村公正。
(一)构建全流程链式乡村数字风险防范管理体系
乡村建设的平稳运行需要正确处理数字技术研发、应用和扩散等各阶段的外溢风险,建立全流程链式风险防控机制。一是强化负责任的技术研发,加强乡村数字风险的源头治理。我们需要对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风险保持清醒认知,强化科研系统的伦理规范性,明确研发规范和界限,建立数字技术研发风险预估和风险约束机制,严禁研发具有明显风险特征的数字技术,从源头上堵住数字技术风险漏洞,保证乡村建设数字化标准的规范性。二是强化对数字技术多维应用的影响评估,构建全景化的乡村数字风险监测中枢。数字技术的运行过程与场景嵌入极易衍生多维风险,亟待建立集成化的风险自动识别系统,以强化乡村数字风险监测,解开数字技术运行“黑箱”,从而保证乡村建设平稳运行。同时,建立参与式数字技术评估体系,鼓励全社会参与乡村数字化建设评估,实现对乡村数字风险的透明化监控。三是提高数字技术系统的适应水平,提升乡村数字风险冲击韧性恢复能力。为防止在乡村建设中遭遇数字技术风险,亟须构建强大的韧性恢复能力系统。一方面,需要压缩风险处置流程,实现对风险事件信息的全面覆盖,激发关键技术元件的备用响应机制,防范系统性失灵风险;另一方面,需要构建数字技术风险智能规避机制,避免同类型数字技术风险的重复发生,保持乡村建设运转的有序性,提高乡村应对复杂数字技术风险的动态适应能力。总之,针对数字技术风险的演化规律,亟须在技术研发、应用和风险恢复方面构建全流程链式防范机制,使乡村数字风险得以分散与规避。
(二)探索与乡村社会有机嵌合的多向度数字化参与模式
消除主体间的“数字鸿沟”,构建与乡土社会情境相嵌合的数字化参与网络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应有之义。一要强化数字技术应用与民意的精准整合,增强数字技术瞄准精度。农民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数字技术的整合性和灵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这需要推动数字技术与村庄内生社会基础相契合。一方面,数字技术要坚持敏捷治理导向,构建智慧介入、弹性构造和循环迭代的场景应用。这需要重点推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基层民主协商领域,精准识别和聚合农民需求,保证数字技术更新与农民需求同频共振,规避数字内容生产与需求的分离。另一方面,开发多元化的数字服务以有效满足农民日常生活诉求,增强农民与国家治理的情感联结,强化对农民认同的整合,促进数字治理的“在地化”適配。二要保证各方话语权,构建平等协商和共享开放的数字化参与格局。在乡村建设中要注重构建多元行动者扁平化数字参与网络。政府和市场在将数字技术引入乡村社会时,要营造各方对话反馈空间,深化多元主体的数字化链接,破除信息壁垒,促使信息交流畅通,弥合信息“富有者”和“贫穷者”势差,推动话语权平等化。同时,在推动数字技术下乡的过程中,政府要着重打破技术精英垄断,引导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强化民生需求导向的数字服务开发,实现技术资本的透明化运作,保证技术性知识的开放性。三要强化数字化应用能力培训,全面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地方政府应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返乡创业人员、返乡大学生和农村青年等本土人才为重点培育对象,聘请信息服务机构、龙头企业、合作社和电商公司等开展技术培训。培训应紧密结合农村生产生活实际特点,增强实用性,积极鼓励培训对象利用数字技术干事创业。同时,选优配齐技术人才团队,加强对乡村数字化系统的运行维护,促使乡村数字红利得到充分发挥。总体而言,要立足村庄需求导向,增强数字技术与社会基础的内生整合性,推动构建多轨并行的数字化参与模式,弥合多元主体“数字鸿沟”。
(三)革除技术万能论的乡村数字治理思维屏障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要坚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融合的原则,实现对技术进步的“祛魅化”,改变技治主义和技术万能的思维倾向,塑造数字技术应用的公共化取向。一是立足公共精神本源,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数字化建设理念。乡村数字化建设要立足公共精神,“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宜人生存与发展的条件”[26](p.56),将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向往作为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根本追求,消除简单将人视为冰冷数据的管理方式。在乡村数字建设中要真正树立起负责任的、体现人本关怀的数字治理理念,使数字技术进步成为服务人、提升人的重要载体,而不是陷入“唯数据论”“唯技术化”的“理性铁笼”。二是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协同发展,构建有效的数字治理体系。推进乡村建设要把握技术逻辑与治理结构的深度互动规律,强化数字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效应。这需要以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突破政府“结构壁垒”,构建条块和层级协同化的数字治理机制,完善多元主体便捷参与的共同决策机制,克服“数字形式主义”痼疾。三是理顺乡村数字化建设任务执行流程,切实推动基层减负。要竭力克服“技术增负”问题,推动全流程再造,合并同类型数字平台和治理事务,简化数据录入和审批程序,真正推动基层减负增效,消除治理内耗[27]。总体而言,在乡村建设中要竭力革除技术万能论思维,将数字技术深融于乡村公共利益维护和治理结构中,真正实现数字技术对农村现代化的有效赋能。
(四)建立体现乡村公正增量的平衡治理机制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必然涉及农村整体性社会结构转型。在乡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重点建设平衡治理机制,以技术进步带动公正增量,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平衡数字技术效率提升和挤出效应的关系,拓宽公正实现渠道。全面推进乡村建设将大规模集成使用数字技术,这虽然会提升农业农村生产经营效率,但也可能会产生“机器换人”的后果,短时间内会造成数字技术对农村劳动力的挤出效应,降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28]。因此,建设平衡治理机制的目标就是要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扩大乡村数字经济规模,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创造农村新型就业渠道,推动更多农民走上技术和管理岗位,使农民在数字技术进步中同步实现利益保障。二是平衡数字技术推广和安全的关系,构建兜底责任机制。政府在乡村技术推广中应同步规划数字安全工作,推动乡村数字化系统同步植入信息风险预警系统,增强乡村数字化系统的风险净化能力。同时,在发生乡村数字风险暴露时,政府要履行兜底责任,切实维护受害农民的合法权益。三是平衡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关系,克服“算法偏见”困境。随着5G时代到来,创新数字技术发展也跨入新阶段,政府在乡村建设中应从完善数据录入、模型构建和训练校验等环节入手,持续促进算法运行机制合理化,同时推动人工嵌入和算法运用协同发展,解蔽算法运用中的群体偏见和排斥问题,推动乡村多元群体平等共享数字红利。质言之,构建平衡治理机制就是要在技术进步中兼顾公正价值导向,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促进数字包容,夯实乡村公正基础。
总体而言,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应坚守安全性、参与性、自主性和公正性原则,系统防范化解乡村数字风险,同时以农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切入点,不断增进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情境的嵌合度。从根本意义上,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要着重实现技术进步的“祛魅”,把握数字技术创新与公正增量的耦合性,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促进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
五、结论与讨论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结构的赋能再造,继而助力乡村全面现代化的过程。数字技术在驱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也伴生一系列实践悖论,如产生数据泄露风险、参与替代、技术依赖和公正偏离等问题。数字技术异化为损耗农民主体性价值和增加治理负担的“反力量”。据此,在全面推进乡村建设中要树立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思维,彻底摒弃技术万能的理念取向,嵌入全链条乡村数字风险防范管理体系并探索多向度数字化参与模式,以数字技术应用促进乡村公正增量,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与农村现代化转型深度统一。
当前新兴数字技术形态不断涌现,为新时代乡村建设注入了强劲动能。在推进新时代乡村建设中,我们要系统把握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内生整合性,正确处理好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数字权力与农民权利、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增强数字技术的敏捷性和回应度,使数字技术成为支撑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坚实载体。
参考文献:
[1]沈费伟,叶温馨.数字乡村建设: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
[2]Soloman B.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J].Journa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1987,(4).
[3]Gretchen S.Giving Peace a Chance: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Empowerment,and Peace[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7,(8).
[4]Marc A Z.Taking Aim on Empowerment Research: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Psychological Conceptions[J].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990,(1).
[5]Evelyn H,Lena M.Empowerment in the Midwifery Context—A Concept Analysis[J].Midwifery,2011,(6).
[6]Maarit M.Digital Empowerment as a Process for Enhancing Citizens’ Participation[J].E-Learning and Digital Media,2006,(3).
[7]鲍静,贾开.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原则、框架与要素[J].政治学研究,2019,(3).
[8]刘永谋.技术治理、反治理与再治理:以智能治理为例[J].云南社会科学,2019,(2).
[9]何哲.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风险与治理[J].电子政务,2020,(9).
[10]容志.技术赋能治理的异化风险及其防控[J].人民论坛,2023,(3).
[11]师曾志,李堃,仁增卓玛.“重新部落化”——新媒介赋权下的数字乡村建设[J].新闻与写作,2019,(9).
[1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13][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殷陆君.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4]魏钦恭.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从多元异质到协同共生[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15]郭明.互聯网下乡: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J].电子政务,2020,(12).
[16]馬丽,张国磊.“互联网+”乡村治理的耦合、挑战与优化[J].电子政务,2020,(12).
[17]胡卫卫,申文静.技术赋能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逻辑与运行机制——基于关中H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
[18]韩庆龄.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J].电子政务,2023,(5).
[19]王文彬,赵灵子.数字乡村治理变革:结构调适、功能强化与实践进路[J].电子政务,2023,(5).
[20]宋文新.技术何以走向人性的反面——论技术悖论产生的根源[J].长白学刊,2006,(6).
[21]丁波.数字赋能还是数字负担: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及治理反思[J].电子政务,2022,(8).
[22]胡卫卫,陈建平,赵晓峰.技术赋能何以变成技术负能?——“智能官僚主义”的生成及消解[J].电子政务,2021,(4).
[23]谭九生,杨建武.智能时代技术治理的价值悖论及其消解[J].电子政务,2020,(9).
[24]孟令宇.从算法偏见到算法歧视:算法歧视的责任问题探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6][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7]杨秀勇,何晓云.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检视[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
[28]吴海琳,曾坤宁.乡村数字化贫困风险的生成与抵御[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责任编辑:李堃]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Practical Paradox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Rural Construction
Zhang Minghao, Chen Yisi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Digital technology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by empowe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people, things and governance. The practical paradox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rural construction are characterized by risk exposure, participation substitution,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and deviation from justice, presenting a “negative empowerment” dilemma. To correct the practical devi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rural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full-process chain for rural digital risk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explore a multi-dimensional digital participation model integrated with local society, eliminate the thinking barrier of technology omnipotence, establish a fair oriented balanced governance mechanism, enable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rural construction to truly restore security, participation, autonomy, and fairness, thereby promoting deep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rural construction, rural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