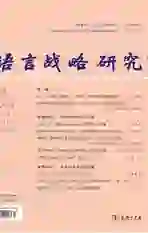汉字与中国式思维
2023-06-30章启群
章启群
提要文字不只是语音的记录,还具有独立的价值。各种文字本身及其书写方式,都具有民族性的心理和文化特征。相比于拼音文字,汉字作为现存使用者最多的表意文字,其独立价值更加显著且重大。最新研究发现,汉语母语者阅读中文词汇可以诱发大脑顶中区产生汉字阅读独有的脑电反应。这说明拼音文字与拼义(即表意)的汉字阅读植根于不同的感官通道。由此可以推断,汉字与康德所论的“图式”具有很高的重合度和同构性,这是汉语使用者的一个思维优势。汉字是“有生命的图式”,由汉字使用生成的“中国式思维”与形象思维相关,但并不属于列维-布留尔所谓的原始思维。这个思维方式是中国人的“心灵词典”,外化为中国文化、艺术、哲学、宗教甚至科学等,蔓衍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在内则构成中国人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
关键词汉字;中国式思维;脑电波;康德图式论;有生命的图式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6-1014(2023)02-0005-15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30201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Peoples Mindset:
Assumption of Research of Chinese Characters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
Zhang Qiqun
Abstract The character is far more than a visual means for recording spoken languages. It has its own value. Di?erent script systems and ways of writing manifest di?erent national psyches and cultures. In comparison with alphabetic script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s the most widely used writing system based on ideography that survives history, is especially unique and signi?cant in standing for its own value and meaning.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search, when read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he natives would produce a unique effect in electroencephalogram called the centro-parietal N200, which shows a possibility that the ideography-based script and the phonemic script are based on the di?erent sensory mechanisms, and the former in nature is closer to the “scheme” proposed by Kant. This can be considered as a meri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users. In this study, I argue tha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should be seen as “the living schema”, and as the result, the Chinese way of perceiving reality is associated with imagery and concrete visual thinking, but this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the primitive cognition pointed by Lucien Lévy- Bruhl. On the contrary, this type of cognitive process can be metaphorically called “the ment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people, which manifests itself in Chinese culture, art, philosophy, religion even science, and permeates every faculty of Chinese society, forming unique ways of perceiving the world.
Keyword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way of thinking; EEG; the “schema” by Kant; the living schema
在全球现存仍在使用的几千种文字中,汉字是成熟文字中唯一截然不同的表意文字。这是个奇特的例外。a 而从甲骨文算起,中华人使用汉字的历史已有3000多年。汉字的这种特殊性,对于中华民族思维方式是否产生本质的影响?因此,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在整体上是否具有独特性?
这是个极为重大的课题。因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生活,实质上是民族思维方式的外化,延伸到文化、藝术、哲学、宗教甚至科学各个方面,蔓衍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神经末梢;这种思维方式在内则构成一个民族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心灵词典”。b
本文试图讨论这一问题。相关话题首先涉及汉字与思维是否具有直接的关系,其次涉及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本质和定性问题。近年来有学者运用科技手段,从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的角度,极大地推进了汉字与思维关系研究的深化(张学新2012;张学新,等2011,2012)。但从根本上说,思维问题属于哲学认识论范畴。
一、问题1:汉字能否直接影响思维?
语言与思维不能分离的密切关系毋庸置疑。过去语言学界的主流观念认为,语法是语言言说的逻辑规则,语音是意义的直接表达,而文字只是语音的记录。由于文字具有言说“不在场”的本质特征,因此文字不仅没有独立的价值,而且流逝了“在场”言说的原初思想本义。这就是西方学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语音中心主义的观点。而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不仅表音效果不佳,而且繁难不易识读。文字尤其是汉字在语言中的价值和意义,一直受到轻视。c 这种偏见不仅遮蔽了汉字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和思想文化巨大影响的视野纵深,也阻断了关于汉字与思维深层关系的思考和研究。
因此,论证汉字与思维的关系,必须证明:第一,文字不只是语音的记录,还具有独立的价值;第二,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其独立价值更加显著且重大。如此才能揭示汉字对于中国式思维的直接影响,实现本文的主旨论证。巧合的是,20世纪西方哲学界的一个争论热点,就是关于文字与语音以及语言的关系问题。其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观点,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他对于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彻底颠覆了传统语言学观念。他认为书写甚至比言说更具有意义的本原性。他的代表性论著《论文字学》对此做了系统而精深的论证。这个论证实质上也是文字与思维关系的基础论证。因此,阐释他的理论恰恰可以实现笔者的第一个意旨。当然,作为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思想极为深邃、驳杂,经常有言不尽意或不可言说的意指。因此,以下文字只能大致梳理和叙述他的理论,遗漏甚至误读在所难免。
德里达认为,在语言和言语表达中,最根本的是意义。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语音(语词)是一种能指,意义即是所指。而在德里达看来,任何语词(语音)都是多义的,每个语词的这些意义都处在流动和流逝之中。例如“商都”一词,其义既指商场,也指商朝的都城。这两个意义在“商都”的词义内涵之中潜在地双向流动。语词作为能指,只是留下暂时的语音或文字(例如“商都”)的“印记”和“痕迹”。而所指,即可理解的意义,也是暂时存留于直观意识的充分呈现中。例如,我们在购物时就把“商都”理解为某一商场;而在考古或历史学讨论中,则把“商都”理解为“商代的都城”。德里达把这种对于语言言说或文本的理解现象,称为“分延”a。而所谓“痕迹”,实质上暗含了语词多种意义的流动和流逝。因此,“纯粹的痕迹就是分延”,而且“没有一种形而上学概念能够描述它”(德里达1999:65)。
同时,作为语音或文字呈现给我们的“印记”和“痕迹”,既非一个物质性或者材料性质的东西,也不属于文化或心理等纯粹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但是,正是在这种“印记”和“痕迹”的特殊领域中,世界的活的经验在阅读或倾听的时间化过程中,彼此之间却显示出意义差别(例如“桌子”不同于“猪”),因此构成系统的文本意义世界。此外,这个差别还表现在语词所指意义与现实世界的不同之上(例如“桌子”一词永远不同于现实中的具体桌子)。这种语词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实质上是语词之间、事物之间等一切区别的条件,也是所有其他痕迹(语音或文字)的条件(德里达1999:92)。因此,
痕迹事实上是一般意义的绝对起源。这无异于说,不存在一般的意义的绝对起源。(德里达1999:92)
德里达这个提法可谓振聋发聩。因为,“痕迹”既可能是语音也可能是文字,而且其意义是流动而非固定和确定的。这对将语音作为意义来源的索绪尔语言学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彻底颠覆了语音中心主义的固有观念。从这个新的立足点来重新审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就不难发现,文字的功能及其所传达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语音的记录,而是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德里达研究了原始语言的发生过程。人类学田野考察发现,文字没有准备阶段,是在一瞬间出现的。这种飞跃表明,文字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处于言语之中,而是处于言语之外(德里达1999:184)。因此,人类从言说到书写,就不能是一种简单的语音记录过程。甚至可以说,“原始的言语乃是文字,因为它是一种法则,一种自然律。最初的言语在自我显现的最深处被理解为他者的声音,被理解为命令”(德里达1999:23)。這种声音与文字的关系,是语言自身的一个整体运动,也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程。虽然声音与文字的天然统一是约定俗成的,但是,约定俗成这一观念,在可能产生文字和文字领域之外,是不可思议的(德里达1999:61)。
其次,从语言言说的过程来说:
声音印象是被听到的东西,它不是指被听到的声音,而是指声音被听到的过程。被听到的过程具有现象学结构,它的顺序完全不同于世界上的真实的声言的顺序。(德里达1999:90)
这是语言言说过程中的本质现象,但经常被人们熟视无睹。其实,很多学者也曾认识到这一点。例如卢梭说:“写下来的是言语而不是声音。”(见德里达1999:457)索绪尔也说:“发音器官问题在语言问题中是次要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并非言语,而是创造语言的能力,即创造与不同观念相适应的不同符号系统的能力。”(见德里达1999:93~94)德里达(1999:8)进一步指出:“从任何意义上说,‘文字一词都包含语言。”德里达还列举出颠覆语音中心论的极为有力的证据——聋哑人的无声语言,即手势语。
考察手势语也可以发现语言言说的本质现象。列维-布留尔(1985:153)指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德里达(1999:344)认为,手势乃是原始文字的要素。“在此,手势是言语的附属物,但这种附属物不是人为的替补,它是对更为自然、更具有表现力、更为直接的符号的重新定向。”(德里达1999:341)因为从表现力来说,手势语是象形文字的隐喻,是可见的符号和一种情感语言,更是情感的直接反映。手势语本质上如同象形文字的轮廓,它分隔本身并标出图形,既形成画面也形成音乐的节拍。当然,文字本身并非言语的图画或记号,既外在于言语又内在于言语。因此,手势语本质上已经成了文字。可见,甚至在与雕刻、版画、绘画或文字联系起来之前,在与能指(书写符号)联系起来之前,书写符号概念就已经包含人为“痕迹”的要求,构成了所有意指系统的共同可能性(德里达1999:63)。
因此,德里达认为:
我们所说的语言就起源和目的而言,似乎只会成为文字的一种要素,一种基本的确定形式,一种现象,一个方面,一个种类。(德里达1999:10)
文字是语言的前夜。(德里达1999:347)
此外,文字作为符号,也与事物之间具有直接对应的关系。德里达(1999:68)说:“物自身是一种符号。”而且,“自从有了意义也就有了符号。我们只用符号思维。”(德里达1999:69)文字的最初出现就具备这种作为符号的功能。从此人们把握外在世界就离不开符号。著名学者巴尔特认为:“语言学并不是一般符号学科的一部分,甚至也不是它的一个享有特权的分支,符号学恰恰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见德里达1999:71)尤其是作为信息传达的手段,如果出现人们“不在场”的情况,就需要一种“替补”的东西。这时候的文字就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文字“是在言语确实缺席时为逼言语出场而精心设计的圈套”(德里达1999:208~209)。
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来说,“不在场”是常见的。因此,文字作为一种语音替代物,使信息传播、社会交流、情感表达等等成为可能。从积极的角度看,“写”往往更能反映语言的清晰 (差别)性,而“说”却常常掩盖甚至取消这种清晰(差别)性。因为词与物只有在文字的系统结构中才能产生和表明二者对应的参照界限。历史进步与文字系统发展具有明显的关联。科学、文化、艺术概念本身,产生于文字发展史上的某个时代,只有根据文字范畴才能设想整个自然体系和人类社会的体系。“历史性本身与文字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與超越具体文字的一般文字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而长期以来,我们正是借这些具体文字的名义谈论那些没有文字、没有历史的民族。在成为历史、历史学的对象之前,文字开创了历史的领域、历史演变的领域。”(德里达1999:38)在同一语言系统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因此,“文字的进步是自然的进步。它是理性的进步。”(德里达1999:393)“替补”的文字是一种文明的需求,弥补了文明的短缺。
可见,没有文字,这一切难以想象。因此,一方面,文字越来越成为这种自然和社会结构的别名,需要把它放在永恒的“在场”中加以思考;另一方面,文字补充在场,取代在场,也遮蔽了在场。这当然是一个永恒的悖论。在当下,我们生活的世界实质上就是文字的世界:
现在我们往往用“文字”来表示这些东西:不仅表示书面铭文(inscription)、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的物质形态,而且表示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的总体;并且,它超越了能指方面而表示所指方面本身。……它不仅包括电影、舞蹈,而且包括绘画、音乐、雕塑等等“文字”。……所有这些不仅旨在描述与这些活动发生次要联系的符号系统,而且旨在描述这些活动的本身的本质与内容。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生物学家们今天将生命细胞中最基本的信息过程与文字和程序联系起来。最后,不管控制程序是否有根本界限,它所涵盖的整个领域也是文字的领域。假如控制论可以单独排斥包括灵魂、生命、价值、选择、记忆等概念在内的所有形而上学概念(不久人们还用这些概念将机器与人对立起来),它就必须保留文字、痕迹、书写语言或书写符号概念,直至其历史-形而上学的特点显示出来。甚至在被确定为人(具有人的一切显著特征以及它们包含的整个意指系统)或非人的特点之前,书写语言或书写符号就是这样的因素,是一种并不单纯的因素。……属于人们不应当称之为一般经验,甚至称之为一般意义的起源的东西。(德里达1999:11~12) 德里达这里揭示出我们生活世界与文字的关系,其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难以充分阐释。但我们从中至少发现,文字与民族文化思想以至于思维的深层内在关系,具有铁一样坚实的逻辑。
就文字本身而言,德里达(1999:439)认为:“言语及其文字的历史包含在两种无声的文字之间,包含在作为自然的东西和人工的东西而相互关联的广泛性的两极之间——包含在象形字(pictogramme)和代数之间。”他把西方拼音文字比作代数一类的事物,认为象形文字则直接展示了所指的对象物本身:“直接的象形字——象形文字——表示事物或所指。”(德里达1999:433)“一种绝对的象形字通过不加节制地消耗能量而复制整个存在物,一种完全正规的书写符号使能指的消耗几乎为零。”(德里达1999:415)德里达还指出,语音中心主义与对西方拼音文字的虚假自信和傲慢直接相关,它的致命伤在于:
逻各斯的特权是表音文字的特权,由于特定的知识状况,逻各斯的特权也是暂时比较经济、比较有代数性质的文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时期是完全抹去能指的时期:人们以为自己是在保护言语并且提高言语的地位,其实人们仅仅是被技艺的图形所吸引。(德里达1999:415)
“技艺的图形”就是拼音文字的代表元素希腊罗马字母。从这个崭新的视角来看,各种文字本身及其书写方式,都具有民族性的心理和文化特征:
这种文化笔迹学,……涉及个人的书写法与集体的书写法的结合,涉及书写符号“话语”与书写符号“代码”的结合,但我们不应从意指意向的角度或支撑的角度,而要从风格和涵义的角度去考察这种结合;这些问题还涉及不同的书写符号形式与不同质料的结合,涉及不同的书写质料的外形(材料:木头、蜡、皮、石头、墨水、金属、植物)或工具(刀尖、毛笔,等等)的结合,涉及技术的、经济的、历史的层面的结合……;涉及各种风格在这一系统中发生变化的限度与意义;涉及书写法在形式和物质上受到的各种关注。(德里达1999:129~130)质言之,文字是民族心灵和文化大历史的书写。中国人运用毛笔和刻刀,在陶器、青铜器、木牍、竹简、绢帛和纸张上书写的汉字作品,自然积淀了民族性的集体心理和智慧,呈现出民族心灵之光。
二、问题2:中国式思维是否属于原始思维?
人是有语言的动物。b 文字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飞跃。考古和人类学证明,文字是人类由渔猎社会进入农业社会的产物,因为农业能支持的人口密度20~30倍于狩猎采集群体。当一个部落群体超过150人时,就需要有简单的社会分工,例如农业耕作、制陶和打磨石器等。此时面对面的信息处理很难维持,信息必须符号化才能远程交流。符号化自然与文字相关。与之相应的还有权力支配的开始,例如发布和管控信息。权力支配并不完全起源于农业社会,但农业社会把权力制度化、暴力化了。因此,“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斯塔夫里阿诺斯2010:59~60)。
可见语言文字的发展,与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是同步的。a 因此,对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评判,也自然与人类历史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但是,从思维的角度评判一种语言,绝不能以当下的使用状况作为衡量标准。人类学田野调查发现的现代土著民族语言,例如澳洲和太平洋菲吉群岛、安达曼群岛的一些土著语言以及印第安语等,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语言,在思维层面上都属于原始思维。而有些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的语言文字,例如古代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赫梯语、古埃及语、古波斯语以及中亚的吐火罗语、于阗语等,被学者们称为“死语言”,但在思维层面上则不属于原始思维。因为这些语言文字的使用时代,都是铜铁文明发达的时期,尽管使用这些语言文字的民族后来在历史中消失了。
西方学术界不乏对象形文字特别是汉字思维有积极评价的学者,例如莱布尼茨说:“……汉字也许更具有哲学特点并且似乎基于更多的理性考虑,它是由数、秩序和关系决定的;于是,只存在不与某种物体相似的孤零零的笔划。”(见德里达1999:116)但在语音中心主义观念下,对汉字思维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甚至否定的。例如卢梭《语言起源论》认为,人类的3种书写方式与人类据此组成民族的3种不同状态完全对应。早先远古人类描画物体的书写方法,适合于野蛮民族;使用字句式的符号的方法,适合于原始民族;而使用字母适合于文明民族。(见德里达1999:3)黑格尔也认为,比较而言,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他把对中国哲学文化的否定与汉字思维的否定结合一体:“中华民族的象形文字仅仅适合对这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进行诠释。”(见德里达1999:34~35)
对汉字与思维关系最尖锐刻薄的评判,应该是列维-布留尔的人类学经典著作《原始思维》。列维-布留尔认为,汉字思维属于比较低级的原始思维,中国人运用的概念是“神秘的”和“模糊的”。因此,
中国的科学就是这种发展停滞的一个怵目惊心的例子。它产生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如烟海的百科全书,但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扯淡。怎么可以在许多世纪中付出这样多的勤劳和机智而结果却完全等于零呢?这是由于许多原因造成的,但无疑主要是由于这些所谓的科学中的每一种都是奠基在僵化的概念上,而这些概念从来没有受到过经验的检验,它们差不多只是包含着一些带上神秘的前关联的模糊的未经实际证实的概念。这些概念所具有的抽象和一般的形式可以容许一种表面上合逻辑的分析与综合的双重过程,而这个永远是空洞的自足的过程可以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列维-布留尔1985:447)不能否认列维-布留尔对原始思维的论证的巨大意义和价值,也不能简单否定他对原始思维的界定的充足证据和严密推理。但可以说,列维-布留尔对汉字思维的界定和评判,完全出于无知。因此,本节所论证的问题不仅仅是拨正他对于汉字思维的偏见和谬误,更是为了解释文字与思维的深层关系。
列维-布留尔说:
可以把原始人的思维叫做原逻辑的思维,这与叫它神秘的思维有同等的权利。与其说它们是两种彼此不同的特征,不如说是同一个基本属性的两个方面。……它不是反逻辑的,也不是非逻辑的。我说它是原逻辑的,只是想說它不像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它首先是和主要是服从“互渗律”。(列维-布留尔1985:71)
在原始民族的思维中,逻辑的东西和原逻辑的东西并不是各行其事,泾渭分明的。这两种东西是互相渗透的,结果形成了一种很难分辨的混合物。(列维-布留尔1985:100)
首先使人惊异的是原逻辑思维很不喜欢分析。(列维-布留尔1985:101)显而易见,所谓原始思维的主要特征,第一是不遵循逻辑和分析推理,虽然不是反逻辑和非逻辑的;第二是“互渗律”。
列维-布留尔特别强调,所谓“原逻辑的”不能等同于“不合逻辑的”。因此,不是说原始思维是“非逻辑的”,即与任何思维的最基本定律背道而驰,而是说原始思维不像现代人的思维那样去做认识、判断和推理。原始人思维中的综合,几乎永远是不分析和不可分析的,没有清晰的逻辑判断、推理和清晰的概念分析。
所谓“互渗律”,实际上是近似于泛神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原始人来说,纯粹的物理现象是没有的。流着的水、吹着的风、下着的雨,任何自然现象、声音、颜色,原始人感知这些,从来就不像我们所感知的那样。他们不把这些现象感知成事物之间处于一定前后关系中的复杂运动。就是说,原始人虽然用与我们相同的眼睛来看事物,但是却用与我们不同的意识来感知事物,因为原始人的知觉在根本上是神秘的。构成原始人知觉的必不可缺的因素的集体表象,具有神秘的性质。此外,原始的思维趋向和过程,是以与现代人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凡是在我们寻找事物原因的地方,凡是在我们力图找到确定事物发展前行因素的地方,原始思维却专门注意神秘原因。“它可以毫不踌躇地认为:同一实体可以在同一时间存在于两个或几个地方。”这就是原始思维服从的互渗律。在这些场合下,它对矛盾采取了完全不关心的态度,而这对于我们的理性来说则是不能容忍的。(列维-布留尔1985:2,34~35)
“互渗律”也不是联想问题。与此相反,记忆在原始人生活中起的作用,比在我们的智力生活中大得多。“他们只要在什么地方待过一次,就足可永远准确地记住它。不管多么大多么难通行的森林,只要他们判定了方向,就能穿越过去而不致迷路。”(列维-布留尔1985:106)尽管如此,列维-布留尔也认为:“即使在相当低级的社会集体中,抽象概念就已经形成着了,尽管它们在一切方面都不能与我们的概念相比,但它们终究是概念。可是,它们仍然必须遵循产生它们的那个思维的一般趋向。所以,它们也是原逻辑的和神秘的,它们只是逐渐地、十分缓慢地消除原逻辑的神秘的因素。”(列维-布留尔1985:446)而且,“原始语言常常表现了惊人的语法复杂性和词汇的丰富性,它们属于与我们所熟悉的印欧语型或闪语型极不相同的类型。要把握土人们的那些有时使我们大惑不解的观念的微妙之处,要探明这些观念怎样在神话、传说、仪式中彼此联系起来,那就绝对需要掌握他们的语言的精神和细节。”(列维-布留尔1985:414)
列维-布留尔的人类学史料来源于澳洲和太平洋诸岛上仍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土著居民。从汉字的发展源头来说,甲骨文已经属于晚期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是一个成熟的文字系统。大部分甲骨卜辞的文义今日被破解,其中展示的逻辑和义理,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没有理解的障碍。汉字这个系统至今没有断裂。而且,从西周开始,中国的政治和学术精英都崇尚理性。先秦诸子都是理性主义者。战国时代的名家就是纯粹的逻辑学家。他们的一些命题,例如“白马非马”等,至今仍然是语言哲学研究的问题。可见,列维-布留尔纯粹是由于对汉语著作的无知,才对汉字思维做出了荒谬的判断。
而且,列维-布留尔认为,人类的思维至今仍然在进步,人们所运用的概念仍然是可塑的,并能够在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变化。但从根本上来说,人类永远摆脱不了原始思维。首先,在现代使用的大量概念中,仍然存在着原始思维不可磨灭的痕迹。要使所有的概念都只表现事物和现象的客观属性和关系,根本办不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概念能像科学理论中所使用的概念那样纯粹、准确。近代以来一些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所追求的,就是试图建立一种精确透明的纯粹的语言。而这些科学概念一般说来是很抽象的,只表现现象的某些属性和它们的某些关系。那些我们最熟悉的概念,差不多永远保持着符合原逻辑思维中集体表象的某些痕迹。例如,我们在分析灵魂、生命、死亡、社会、秩序、父权、美等概念时,无疑会发现这类概念中包含若干尚未完全消失的互渗律的关系。其次,即使我们假定,神秘的和原逻辑的因素终于从大多数概念中排除出去了,也不意味着神秘的和原逻辑的思维必然随之而绝迹。“实际上,那个力求通过纯粹概念的智力的加工而使自己表现纯粹的概念的逻辑思维,不是与那个在早期的表象中得到表现的思维齐头并进的。”(列维-布留尔1985:448)因为原始思维并不仅仅由一个机能组成,或者由一个纯粹智力的机能的系统组成。它当然包括还没有分化因素的一个复杂得多的智力机能总和。这其中,认识还掺杂着运动的和情感的因素。因而,这些原始思维因素的一部分,将无限期地保持在人类思维之外,并与它并存。可见,“逻辑思维愈进步,它对那些在互渗律支配下形成的、包含着矛盾或者表现着与经验不相容的前概念的观念的斗争就愈严重”(列维-布留尔1985:448)。这个斗争永远不会终结。
因此,
在人类中间,不存在为铜墙铁壁所隔开的两种思维形式——一种是原逻辑的思维,另一种是逻辑思维。(列维-布留尔1985:3)
我们的智力活动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在它里面,原逻辑的和神秘的因素与逻辑的因素共存。(列维-布留尔1985:452)
即使在今天,在我们已知的一切社会中,尤其是其中包含了信仰、道德和宗教习惯的那许多集体表象,就是这种互渗感的集体表象。因此,不管哪个民族,无论是何种宗教信仰,都具有类似宗教的超验幻象、民族的偶像和历史积淀的心理情结。对于基督徒来说,“认识上帝的任何合理企图似乎都必须是既把思维着的主体与上帝联合起来,同时又把它推离很远。合乎逻辑要求的必要性,是与人和上帝的那些不可能不带着矛盾来想象的互渗对立的。”(列维-布留尔1985:450)从这个视角来看,列维-布留尔(1985:452)宣称:“假如我们的思维既是逻辑的又是原逻辑的,假如确实是这样,那么,各种宗教教义和哲学体系的历史今后就可以用新的观点来阐明了。”
列维-布留尔虽然对于中国式思维做出了极为荒谬的评判,但是,他在提出了人类思维两级(原逻辑的与逻辑的)的基础上,还指出这两种思维虽然此长彼消但却长期共存的事实,揭示了人类思维的某种本质。这个思想对于语言文字与人类思维的研究,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问题3:脑电波 N200与康德图式论是否有关联?
汉字与思维关系研究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是最近张学新团队使用相关电位技术,第一次发现了一个中文阅读特有的脑电波。
基于充分的文献调研和研究结果,顶中区 N200被确认为是一个中文词汇识别特有的脑电反应,是过去三十年中文心理学研究努力寻找的一个神经标志。作为一个反映中英文词汇加工本质区别的神经指标,N200的存在,证实了中文、英文词汇识别涉及本质不同的脑加工,特别的,中文词汇在其识别的早期阶段,存在一个极强的视觉加工过程,而这个过程英文中完全没有。(张学新2012:35)
人的大脑对于汉字和字母文字都有早期词形加工的程序。过去有些实验使用核磁功能共振技术,发现中文词汇识别激活的脑区跟英文差别不大。但这些实验都定位于腹侧颞下回的 VW FA 区域附近。张学新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脑电和核磁记录的信号反映了词汇识别的不同层次。在对字形线条、角度、朝向的分辨等基本的视觉特征加工上,中英文可能差别不大。而在词形的整体辨别上,英文词汇识别仅确定一个刺激,即分辨几十个字母的一维排列组合,其结构编码相对简单。这只是完成了类别识别,却不能区分不同的字母串,因此不是在个体词形水平上的真正识别。作为对比,中文词汇从数量上需要区分50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从结构上需要在部件、单字和多字层次上抽取复杂的二维形状信息,并编码各部分间的位置关系,有些类似于复杂的空间和场景知觉,较为复杂。脑电波 N200与词形整体分辨相关,加工过程相对高级。因此,其对应的脑区与 VW FA 不同,而位于更高级的皮层联合区。N200对刺激重复非常敏感,说明它已经实现了对个体词形的识别,至少早于字母文字。这可能是因为中文阅读利用了高度并行的、加工能力更强的视觉通道,而不是强调串行加工、能力较弱的听觉通道。
语音和文字,都是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人类知觉只能利用视、听、触、味、嗅这5个感官系统感知。味觉和嗅觉只能感受信号,不能产生信号形成语言。触觉分辨能力差,感知速度慢,与其对应的盲文实质上是字母文字,在词汇丰富性和沟通效率上无法比拟于正常语言。正常用于語言功能的主要是听觉和视觉。这其中,人类的视觉功能最强,我们关于世界的概念和知识,主要是视觉知识。拼音文字利用语音共性,发展了一套完整记录语音的手段,成为记录语言的有力工具。尽管拼音文字在形式上是视觉符号,但阅读者仅仅分辨几十个简单的字母符号,并没有充分发挥视觉系统的信息加工能力。因此拼音文字在根本上植根于听觉通道,本质上是语音信号的转写,不能摆脱语音信号的一维线性和语音基本单位数量有限的局限性。只有汉语拼义文字,充分利用了人类信息加工能力最强的视觉系统,成为真正的视觉语言。
美国心理学家奎廉在1968年提出,人脑中的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跟其他的概念相互关联,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一个概念可以用其他相关概念的复合来表达。这个观点描述了人脑表达世界知识的根本规律。文字要实现拼义,必须充分利用视觉系统的信息处理能力。汉字不重表音,摆脱了语音的束缚,可以利用能力更强的视觉信息加工,充分发挥人类视觉最出色的、二维空间的图形识别能力,在二维空间里构造出足够的字形来表达义基。
N200的发现表明,以汉字为基本单元的中文词汇识别在早期就存在一个针对词形的加工过程,涉及相当广泛、高级的视觉加工,而这个加工过程在以字母为基本单元的英文词汇识别中并不存在,这就提示前者相对于后者更注重视觉处理,跟拼义理论认为中文相对于英文是更为彻底的视觉文字的核心观点是一致的。(张学新,等2012)
拼音文字与拼义的汉字,二者植根于不同的感官通道,切合于不同的科学规律,构成成熟文字仅有的两个逻辑类型。而且对人类而言,从逻辑类型上不会再有第三种更丰富、更有效率的文字符号系统。这样来看,
汉字和字母文字有本质不同的脑加工机制,这就找到了区分中、西方文字的一个神经指标,也可以说是区分中西方文化的一个神经指标,相应引发的拼义符号的概念,为理解中西方思维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张学新2012)
而且,汉字阅读的重复启动会使 N200的幅度增强。进一步的文献检索发现,对物体图片、英文词汇的大量研究都未曾报道过类似的 N200现象。除了英文这类拉丁字母,不懂韩文的中国大学生观看韩文字符时,脑电波 N200也不出现。韩文从视觉形态上跟汉字非常相像,也是由简单笔画构成的方块形状。这表明 N200脑电活动反映的不是表面的视觉特征,而是汉字更深层的属性。有报道认为:
研究发现人们看图形的时候也并没有出现脑电波 N200,这说明汉字根本不是图形,而是一种非常抽象的视觉符号。(霍文琦2012)
汉字研究的这项重要成果,让我们联想到康德的“图式化”理论。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对认识问题的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分析康德“图式化”理论,对于探讨汉字思维特征,不同于语言学、心理学、脑科学、人工智能等实验学科研究,但却具有根本上的意义,因为哲学关于思维的思考是更本质、更彻底的。
康德在描述人的认知过程时认为,人的知性(understanding)给杂多的感性表象(即现象)赋予统一性,形成概念。例如,我们开车行至一片杂草丛生的裸露土地时,便知这是“荒野”;行至高楼林立、马路宽阔、红绿灯闪烁的地方,便知这是“城区”。这里的“荒野”“城区”都是概念。概念是对于感性杂多的表象给予规定,从而形成知识。事物呈现的表象统一性即是单个事物的特征,例如“树”“房子”之类。但康德认为,在概念和经验对象事物结合形成知识的时候,必须要借助一个手段。因为概念本身不涉及任何具体对象事物本身。因此,
必须存在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必须与范畴,另一方面又必须与显象处于同类关系之中,而且它使得范畴在显象上的应用成为可能的。这个起居间调停作用的表象( DiesevermittelndeVorstellung)必须是纯粹的(不包含任何经验的事项),而且一方面是理智性的,而另一方面却是感性的。这样一种表象就是先验图式。(康德2022:232)
我们要将这种形式的且纯粹的感性条件——在使用一个知性概念时我们要将其限制在该条件之上——称作该知性概念的图式,而将知性对这些图式的处理称作知性的图式化。(康德2022:233)“图式”一词德文为 Schema。a 至少从黑格尔开始,哲学界就把康德的“图式化”阐释为范畴的运用功能。b 因此可大致以为,没有图式,纯粹知性概念不能运行于经验对象事物即表象之上,知识不能出现。当然,图式也限制范畴(康德2022:240)。由此可见图式在认识中的关键作用。但是,这种图式绝不是图像。康德(2022:234~235)举例说明:
关于狗的概念意味着这样一条规则,根据它我的想象力能夠一般地描画出四足动物的形状,而不必局限在经验向我提供的某个唯一的特定的形状之上,也不必局限在我可以具体地表现出来的任何一幅可能的图像之上。……相关的图像是生产的想象力的经验能力的一种产品,而感性概念(作为关于空间中的图形的概念)的图式则是纯粹的先天想象力的一种产品,好像是它所给出的一种字母组合图案一样。正是通过并且根据先天想象力的这种产品,诸图像才成为可能的。但是,诸图像必定总是只有借助于它们所标示的那个图式才与相关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而就其本身来说它们与这个概念并非完全等同。与此相反,一个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式则是某种根本不能被带入任何图像的东西,而仅仅是这样的纯粹的综合,它是按照相关的范畴所表达的一条关于统一性的规则进行的,而该统一性又是根据诸泛而言之的概念得到的。这里关于“图像”与“图式”本质区别的思想,为学界所共知。纯感觉图像即是作为对象事物的形象(显象),与概念图式为根本不同的东西。不仅如此,图式也不是数字或几何图形:
处于我们的纯粹的感性概念(即数学概念——译者注)之基础的地位的不是对象的图像,而是图式。根本没有任何三角形的图像任何时候会适合于泛而言之的三角形的概念。因为,这样的图像不会达到该概念所拥有的普遍性(而正是那种普遍性使得该概念适合于所有三角形,无论是直角三角形还是斜角三角形等等),而总是仅仅局限于这个范围的一个部分。三角形的图式不能在任何其他地方而只能在思想中存在,而且意味着一条联系着空间中的纯粹形状而言的想象力的综合的规则。(康德2022:234)
如果我一个接着一个地放置五个点:·····,那么这个东西是五这个数的一幅图像。与此相反,如果我只是思考一个泛而言之的数(这个数现在可以是五,也可以是一百),那么这种思考是对如何做如下事情的方法的表象,即依照某个概念在一幅图像中表象一个数目(比如一千);这种思考并不是这幅图像本身——在一千这个情形中我很难综览这幅图像并且很难将其与该概念加以比较。现在,我将这个关于想象力之设法为一个概念谋得一幅图像的一般程序的表象称作该概念的图式。(康德2022:233~234)
很显然,“三角形的图式”不是我们任意图画的三角形图形。处于数的概念基础的不是图像(例如“·····”),而是图式。这种属于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式,虽然不同于几何图形,但绝不是抽象概念本身。而康德认为数学公理的直观也是图式的作用:“关于广延的数学(几何学)及其公理便建立在生产的想象力在生成形状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这种前后相继的综合基础之上。这些公理表达了先天感性直观条件,而只有在这些条件之下外部显象的纯粹概念的图式才能出现。比如如下公理:两点之间只可能有一条直线;两条直线围不成任何空间,等等。”(康德2022:255)这类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式,可以理解为点、直线、曲线之类的抽象图形,以及数字意象,属于“某种根本不能被带入任何图像的东西”的图式。
所以,康德所论的“图式”应该具有不同层次的分别。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式,含有点、直线、曲线以及数字意象,例如“点和线条”“5”“一千”等图式。这类或可以称为“理性图式”。超出此类概念的余下部分的图式,可能更加感性、具象,与事物的显象更加接近,例如“狗”“盘子”等概念的图式。这一类或可以称为“感性概念的图式”。“感性概念的图式”并非与“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式”对立。图式作为范畴的运用,不是感觉经验过程中被动刺激的产物,不是生产性的想象力重现表象的结果,而是先天纯粹想象力的创造,是思维的先验功能。
对于图式稍作了解之后,再看康德描述的认识过程中,图式在思维中的具体功能和作用。
首先,认识始于感性直观。而所有直观均基于外在事物的刺激。感性直观对于现象事物的综合,康德称之为“形象的综合”。它与理智的综合不同,但相互联系,而且必然与思维的知性连接起来。这一切都是先验的,即不需要经验的知识积累(康德2022:182)。感性直观在杂乱的对象中迅速形成具有统一性表象的这个瞬间过程中,统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个感性直观中的杂多的所予必然属于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的统一性,因为只有经由这种统一性,直观的统一性才是可能的。”(康德2022:176)这也是知性的作用。知性就是运用范畴的能力。但知性在运用范畴的时候,对象事物的显象并不是必须被归属于范畴之下,而是必须被归属于范畴的图式之下。所以,尽管在原则本身中我们使用范畴,在具体实施原则时,我们则将范畴的图式置于范畴的位置之上(康德2022:272~273)。而只有运用范畴即概念,我们才能达到知性认识(理性认识),把握世界。
当然,感性直观离不开想象力。想象力也是“图式化”的催产婆:“这样的图式是想象力的一种先验的产品。”a (康德2022:235)同时,感性直观被给予概念,而概念就是语词。在这里,作为概念的感性基础的作用不可忽略。因为,“只有我们的感性的且经验的直观才能给它们(指概念)设法找到意义和意指。”(康德2022:180)这里关键的还是感性的作用。虽然“在没有图式的情况下,诸范畴仅仅是知性相对于诸概念的功能,而根本没有表象任何对象。它们是从感性那里得到这种意指的,而感性在限制了知性的同时也现实化了知性”(康德2022:241)。而图式化的过程最后也是在感性直观统觉的统一性中完成的:
经由想象力的先验的综合而进行的知性的图式化最后只是归结为内感能力中的一切直观杂多的统一性,因此间接地归结为统觉的统一性——作为对应于内感能力(一种接受性)的功能的统觉的统一性。(康德2022:239)
综上所述,康德认为,在普遍的认知过程中,从感性直观到概念形成,图式是个关键的中介。b 图式不是事物的图像,也不是几何图形,但绝对不是抽象的概念。这样,我们自然就会发问:康德所论的“图式”与让阅读者形成脑电波 N200的汉字,是否具有关联?或者是否至少具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四、起点推论:“有生命的图式”与“中国式思维”
康德所论的图式,是知性的一种“先天表象”功能。张学新团队发现的 N200,是汉字阅读产生的特殊脑电波。前者是哲学的分析和推断,后者是科学实验的结果。两者之间还需要很多研究、分析、设计和实验,才能证明二者的实质性关联。我们不能对此做出轻率的评判。笔者以下只是做一点谨慎的逻辑推断:
康德所说的图式属于人脑的一种功能,并且明确说这种图式“好像是它(概念)所给出的一种字母组合图案一样”,是想象力“设法为一个概念谋得一幅图像的一般程序的表象”。N200是汉字阅读人脑功能的结果。实验证明,人们对于拉丁字母的英文阅读不能产生 N200。那么,作为让阅读者产生 N200的汉字与康德所说的图式,特别是“感性概念的图式”,是否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或同构?如果对于二者做一个大胆的链接,那么,汉字阅读至少比拼音文字的阅读,具有更为快捷地进入思维的可能。根据康德的理论描述和张学新团队实验结果,我们至少不能完全排除康德所论的图式具有与汉字高度重合或同构的可能性。退一步说,汉字与拉丁字母或其他字母相比,应该高度接近这个图式。如果这个判断确定无疑,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汉语阅读和使用者,与拼音文字阅读和使用者,在思维运行中有一个重要分别。这个分别对于汉字使用者,自然是个思维上的优势。由此,我们對于汉字与“中国式思维”的认识和研究,至少有个新的起点。
其实,把西方拼音文字呈现的认识过程与汉字呈现的认识过程作一比较,也可以发现一些特点:
拼音文字:事物表象—声音(字母文字)—概念(由声音转换为概念)—思维;表意汉字:事物表象—概念(汉字由视觉直接进入概念)—思维。
这就是张学新团队实验中一再强调的,汉字阅读主要是由视觉通道进入思维,表明汉字进入思维比起拼音文字进入思维是个快车道。人类视觉通过视网膜对于电磁波的感知,所获得的信息量远远大于听觉靠耳膜对于声波感知所获得的信息量。 a 或者我们可以对这个快车道做个简单的比喻:
汉字阅读如同一个标有阿拉伯数字的挂钟,拼音文字阅读如同标有罗马数字的挂钟。日常生活中,一般人们在观看钟表时,对于阿拉伯数字的反应比罗马字的反应都略快一些。 b
由于日常使用汉字的中国人更依靠视觉功能,因此对声音的听觉功能,相对西方人不敏感。c 这个特点在某些场合就凸显出来。第一是戏剧。中国戏曲与西洋歌剧的发声方法不同,发声表达的目的也不同。西洋歌剧以展示声乐美为主,歌词为辅。而中国戏曲以表达唱词内容为主,声乐为辅,讲究吐字清晰。而且在中国各种戏曲的剧场中,很早就用字幕映出唱词。现在技术手段进步,连道白也有字幕,极大地方便了观众对于演员说唱内容的理解。第二是诗歌。中国诗歌主要靠阅读。甚至在朗诵时,特别是古诗词,听者一般是先转换为文字(正式表演时也打字幕),再领悟其意义。在这两种情况下,声音近似于纯粹音乐,是辅助性的。
主要依靠视觉功能的汉字阅读,此外还对于“中国式思维”产生哪些影响?这也是个十分宏大的问题。 d 关于汉字构造的特点与思维的关系,尤其是汉字的“六书”造字法,经常被用来阐述中国人思维特征及其艺术价值,相关研究数不胜数。这里不再重复。笔者只是从哲学角度,略谈一点汉字与形象思维的问题。 e
许慎《说文解字·序》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这里说到汉字构造的根本特征:“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取自人情物态。汉字本身表意,因形示义。由于汉字象形,因此也表情。但是虽然汉字“象形”,本身并不纯粹按照物象写实,而是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但汉字也不是几何类的图形。可以说,汉字是一种“图式”。例如:“旦、人、门、口、花、木”等字,是所指对象事物的简练、抽象形象;而“哭、笑、卡、凸、凹”等笔画勾勒出的字义,令人神会,甚至忍俊不禁。可见汉字图式是“有生命的图式”。这种“有生命的图式”出现在具体文本中,经由视觉而对情感产生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例如: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天安门诗抄》)这里的“鬼、叫、哭、笑、豺狼、酒、眉、剑、鞘”等字,自身形状就有表情。如果用甲骨或金文,则形象更加栩栩如生。但若翻译成英文:“ghost ,shout ,cry ,laugh,jackal ,alcohol ,eyebrow ,sword, scabbard”,即使对精通英文的汉语阅读者来说,效果也可谓天壤之别。
除了表情,汉字还有色彩词汇,视觉效果犹如丹青。比较一下以下诗句中英文大意: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
At sunrise riverside ?owers are redder than ?re, in spring green waves grow as blue as sapphire.(引自百度翻译)
至少就“日、江、花、红、火、春、水、绿、蓝”等字的视觉联想而言,白诗大江奔流、红霞万朵、岸柳拂面的意境,如绚丽鲜花。 a 而英译的诗歌意象,则瞬间褪色,绚丽鲜花变成了没有光泽的纸花。反过来:
O, 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Robert Burns: A Red, Red Rose )
哦,我心爱的人儿,是一朵彤红,彤红的玫瑰。(拙译) b
这里汉字(“爱、人、红、玫瑰”)的视觉联想,则是由纸花变为鲜花之感。因此,为了视觉美感,汉语诗歌经常用假借字:
千村薜荔人遗矢(屎),万户萧疏鬼唱歌。(毛泽东《七律·送瘟神》)
这里“矢”与“屎”所指一样,意义一样。如果用“矢”(箭)的本义则诗意不通。使用“矢”是避免“屎”造成恶心的视觉冲击,引起不好的心理反应。因此,汉字文本尤其是诗歌也有“尽意莫若象”和“得意忘象”之论。 c
作为“有生命的图式”,汉字具备了艺术的根本特征,本身就是艺术作品。汉字的这个特质是中国书法、篆刻艺术所具的根本合法性。中国书法将汉字的书写,通过点、线笔画结构和整体布局,在黑白墨意之间,展示一种韵律和画蕴,并与所书文字内容融为一体、相互彰显,令人体悟自然和人生的真谛。中国书法作为一个艺术门类,与中国的水墨画相近。而中国“书画同源”之说是学界共识。因此,中国造型艺术主流的书法、绘画,与汉字的特征具有密切关系。当然,中国书法是有意味的“图式”,不是对世界物象的直接摹写,因此与水墨画具有质的界限。(有些书法把“龙、虎、荷”等字摹画成具体物象的形态,不仅极为肤浅,甚至可以说违背了书法的基本原则。)相比之下,无论哪一种拼音字母文字,最多只能进行表面的美术化,即做成花体字。而中国书法所具备的艺术功能,是所有其他文字的美术化(花体字)所无法企及的。
汉字阅读的这个定势影响到思维,与形象的思维相关。这种思维的焦点,是在想象与现实世界的交汇处,产生与艺术和美的沟通和关联。因此,作为这种思维的外化,中国文化被认为在整体上具有一种“美丽精神”:
印度诗哲太戈尔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小册里曾说过这几句话:“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陷于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一种天赋。因为只有上帝知道这种秘密。我实妒忌他们有此天赋,并愿我们的同胞亦能共享此秘密。”(宗白华2011:207)
这当然也是一个世纪难题,需要深入探究。
必須强调,汉字与形象思维的关系不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也不能等同于“文化基因”。所谓“文化基因”,主要指通过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主动或被动、自觉与不自觉而置入人体内的最小信息单元和最小信息链路,大致表现为信念、习惯、价值观等。a 汉字阅读对于思维的影响,与“文化基因”有所交叉,但绝不能等同于“文化基因”。因为,一种思维方式,只能是思维所具有的特征。由于思维与科学创造的密切关系,因此,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诗的国度、艺术国度,也是数学的国度、科学的国度。 b
《淮南鸿烈》云:“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古人把汉字的诞生看作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现在笔者也惊叹汉字诞生的神奇!汉字与中国人具有先验的一体性。由汉字生发的“中国式思维”,以及生长其上的中国思想文化,是一株茂密的参天大树。这里面还有许多奥秘等待发掘。
参考文献
陈琴 2010 《日本近代文字改革及文字使用概况》,《江西社会科学》第6期。
德里达 1999 《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黑格尔 1983 《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霍文琦 2012 《汉字是独一无二的视觉文字》,《中国社会科学报》2月24日第1版。
康德 2022 《纯粹理性批判》,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列维-布留尔 1985 《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钱锺书 1979 《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斯塔夫里阿诺斯 2010 《全球通史》(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苏秉琦 2013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士元 2018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指标》,《社会科学报》5月10日第5版。
维柯 1986 《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 2022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世英 1987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学新 2012 《拼义符号:中文特有的概念表达方式》,《科学中国人》第23期。
张学新,等 2011 《汉字拼义理论:心理学对汉字本质的新定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张学新,等 2012 《顶中区 N200:一个中文视觉词汇识别特有的脑电反应》,《科学通报》第5期。赵传海 2008 《论文化基因及其社会功能》,《河南社会科学》第2期。
宗白华 2011 《艺境》,北京:商务印书馆。
Dyson, F.1999.《杨振宁——保守的革命者》,杨振玉,范世藩译,《二十一世纪》(香港)8月号。 Hockett, E. C.1960. The Origin of Speech. Scienti?c American 203, 88–96.
责任编輯:王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