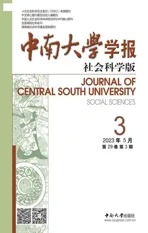补强的全球正义: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正当性基础
2023-06-10毛俊响王欣怡
毛俊响,王欣怡
补强的全球正义: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正当性基础
毛俊响,王欣怡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在重大公共危机背后,国际社会的结构性不公正问题突出,一种“重复”波动失序状况已经向国际社会敲响警钟。在此困境下,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正当性证成,可以通过对既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探寻疫苗全球共享与公平分配正当性的有效理念。现实中,世界主义理论、国家主义理论、矫正正义理论都难以支撑起当下疫苗全球公平分配所需的理论框架。相比之下,全球正义理论虽有瑕疵,但存在明显优势。经由对全球正义的再思考,补强的全球正义,这种问题导向的理念框架“破而后立”,在补充与修正中展现出对现有体系的超越。进而,补强的全球正义凭借合理的理念构造与疫苗再分配的制度设计在逻辑自洽与实践自洽的论证中阐明,可以为疫苗全球公平分配提供正当性基础。
补强的全球正义;疫苗公平分配;正当性基础
一、“重复”波动失序: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现实困境
(一) 疫苗全球分配的“重复”波动失序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世界各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2022年12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确诊病例超过6.41亿,死亡人数超661万,已经接种超过130亿剂疫苗[1]。其中,高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率达到76.37%,而在低收入国家,这一数据仅为21.36%。这些数据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不断变动,彰显着在重大公共危机背后,国际社会的结构性不公正。在全球秩序逐渐恢复之际,各国需要从“大流行病”(pandemic)中吸取教训,审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凸显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以对疫苗问题的探究,尤其是以对疫苗分配不公正问题的探讨为焦点来审视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反思其背后隐含的结构性不公正问题。
对疫苗分配不公正状况的考察,可以通过量化相关因素的方式进行。忽略摇摆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国际社会面对疫苗公平分配时的选择简要概括为“阻碍”与“支持”,以二者关系反映疫苗公平分配的实际状况。当国际社会对疫苗公平分配的阻碍效应(obstacle effect,OE)小于对其的支持效应(support effect,SE)时,分配就体现出公平性、秩序化;相反,当阻碍效应大于支持效应时,疫苗分配就会呈现出混乱和失序的状态。即:当OE<SE时,疫苗的公平分配可以实现;反之,当OE>SE时,则会出现分配失序的局面。此时,当OE越大,SE越小,疫苗分配所呈现出的失序状况(situation of disorder,SD)就会越严重,疫苗分配不公正的程度就会越深。换言之,失序状况(或者说不公正的程度)与二者之间的差值成正比关系。反映在现实中,表现为部分国家面对疫情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私利至上、疫苗抢夺、疫苗囤积以及责任缺失。因此,疫苗公平分配的失序状况(或者说不公正的程度)可以假定为:
SD=(OE−SE)
公式中,除了作为比例系数的(>0),影响最终判断的是OE以及SE的值。对此,我们可以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来进行阐释。在主观方面,“分配意愿”可以被视为影响对外选择的内在因素;在客观方面,“实际能力”则是制约主体行为的关键指标。这二者是影响主体选择的主要因素。由此,阻碍疫苗公平分配的整体意愿和实际阻碍能力越强,支持公平分配的意愿和促进能力越弱,分配就越容易失序,从而出现疫苗分配不公正的状况。如图1所示,假定生产要素在一定期间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疫苗分配的失序状况会随着时间发展呈现出波动且重复的状态。在O点,疫苗被生产出来,富裕国家基于需求,通过实力压制并开始抢夺疫苗,较贫穷国家则因为实力悬殊难以获得疫苗,分配失序局面开始出现。在OA段,由于尚未满足自身需求,富裕国家不断阻碍分享和进行实力压制,继续抢夺、囤积疫苗;而较贫穷国家的灾难持续蔓延,疫苗在国际社会的分配失序程度不断加深。由于外部企业疫苗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自身大量的疫苗囤积,到A点时,富裕国家已获得足够的疫苗并完成疫苗接种,基本满足自身需求。尽管支持公平分配的意愿开始增多,但促进能力有限,较贫穷国家仍陷在深重灾难之中,国际社会面临的失序程度近乎达到顶峰。此后,在从A到B的过程中,由于自身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供应基础进一步扩大,国际社会支持公平分配的意愿不断提升,富裕国家对疫苗公平分配的阻碍效应也开始降低。现实中,富裕国家向较贫穷国家分配疫苗,较贫穷国家获得更多疫苗,分配失序状况得到缓解。到B点时,较贫穷国家基本完成免疫,人类基本度过该次危机。之后,随着新的疫情出现,新一轮的失序循环又将开始。
现实中,在疫苗分配、使用的初期,面对这种暂时性“稀缺”的公共卫生产品,部分国家为最大限度地保证自身利益,利用经济力量不受规制地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疫苗采购,破坏全球合理调度,导致分配失序。国际社会整体的不公正程度开始提升。这种失序的后果最先在最不发达国家上演,表现为健康权保障的缺失乃至不断攀升的死亡率。这部分国家在疫情中的失控最终又会反作用于国际社会,导致疫情在国际社会的持续蔓延,进一步引发混乱,加深疫苗分配的不公正程度。尽管作为公共卫生产品的疫苗随着供应基础的扩大不断被生产出来,但这种走向混乱和失序的过程也只是得到了局部减缓。在人类实现全体免疫之前,存在的情况只会是“富裕国家从免疫运动中受益,而较贫穷的国家则缺乏拯救生命的疫苗”[2]。世卫组织在2020防范流行病国际日的视频讲话中就曾警示人们,COVID−19不是最后一场大流行病,大流行病是生活现实。假若国际社会长期存在结构性不公正,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之下,作为其突出表征,疫苗分配不公正的问题会持续存在。“我们无法确定下一次大流行何时袭击我们,但绝对可以肯定它会再次发生。”[3]当新的灾难来临,在危机和利益的驱使下,新一轮的争夺又会开始。这条由不公正的疫苗抢夺展现出的“警示线”将再度波动出现,赫然昭示着由国际社会结构性不公正带来的全球性危机。目前,虽然这种分配不公正的循环只是一种预设,但暗含着对国际社会的预警,提醒我们去探寻疫苗公平分配的正当性。

图1 “重复”的波动失序状况
(二) 疫苗全球分配失序的成因
这种全球疫苗分配困局的形成缘由,可以从两方面解读。一方面,狭隘的国家理念制约共享意愿与公平分配。这种国家理念主要体现为国家利益至上和西方中心论。就国家利益的维护而言,部分国家将利益至上作为行为基准,通过大量抢占、囤积疫苗而迅速恢复实力,意图稳定国内社会秩序、保持国际经济优势及恢复“被减损”的全球领导力。在这些利益的驱使下,部分国家无视疫苗共享的急迫现实,秉持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大量抢夺和囤积疫苗,最终导致分配失序。就身份认同的形构而言,部分国家仍然相信西方中心论,其凭借传统的优越感进行划界,认为“西方”世界天然的先进、完善,不需要去迁就“非西方”的需求。至今,这种意识仍然存在于不少国家的思维习惯中,为疫苗民族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一个现实的表现就是,部分西方国家在占据优势公共卫生资源、享有先进疫苗研发技术的同时,刻意忽视“非西方国家”对疫苗公平分配的需求,拒绝关键医疗技术的共享。
另一方面,在狭隘的国家理念尤其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影响下,现有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及疫苗分配机制操作“失灵”。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最重要的平台,WHO在应对疫情时显现出诸多问题:体系内部政治化倾向明显,尚无便捷的公共卫生预警、报告机制,缺乏有效的危机评估框架。此外,现有分配机制——新冠疫苗全球供给计划(COVID−19 Vaccines Global Access Facility,COVAX)和“公平优先”伦理框架①在构想与实践之间存在较大偏差。COVAX机制的问题在于:“只要疫苗的供应分配仍然受到限制,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就很难启动那种像发达国家日益发展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4]“公平优先”伦理框架则错误地认为要同等对待不同地区的国家,而不是公平地回应它们的不同需求[5]。因此,面对疫苗分配失序的紧张局面,在全球范围内建构疫苗公平分配的理念共识与正当性基础,不仅能够克服来自狭隘的国家理念的阻碍,亦能为后续具体制度设计和规范实施提供指引。
二、单一理论路径: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既有理论阐释与批判
面对疫苗分配失序的困境,是否存在某种既有理论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提供疫苗公平分配的正当性基础?答案是否定的。有学者提出,单一的世界主义或国家主义都不足以解决问题,但通过优势互补或理论结合,解决复杂矛盾便成为可能[6]。在此,通过对当代世界主义观念、矫正正义理论、国家主义观念、全球正义理论的阐释与批判,我们可以窥到破解失序危机的理论路径,进而探寻疫苗全球公平分配困境的解决之道。
(一)当代世界主义观念:“一元论的博爱”
当代世界主义观念是近四十年才提出的概念,它以对人类的“博爱”为核心理念,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古典世界主义中“世界公民”的观念及近代世界主义中“世界主义价值”和“秩序”的构想。具体到观念内部,除托马斯·博格提出的当代世界主义三要素②之外,很多学者对当代世界主义“存在”的认识和理解多有差异,但在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层面却是相通的[7]。其一,当代世界主义主张以博爱对抗歧视和偏见。世界主义的大多数定义都强调,人类被认为具有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是承认共同体成员身份的基础。例如,Pauline Kleingeld和Eric Brown就将世界主义解释为“所有人类,无论其政治归属,(可以或应当)是一个社区的公民”[8]。其二,当代世界主义认为分配应该基于“世界性”平等的理念。在这一视角下,支持者们认为,所有人行为的基础与人类共同体存续的基础在于同等价值的理性与人性[9]。因此,在他们看来,缺乏全球分配正义原则是令人惊讶和失望的。在疫苗分配问题上,当代世界主义本源中内含的对平等的崇尚,符合疫苗分配失序状态的纠正需求。具体来说,博爱观念可以影响疫苗分配的主观意愿,增强支持效应,促进疫苗公平分配进程。当代世界主义的支持者们认为,即使国家、民族、文化不同或者在政治体系、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人们在疫苗分配环节也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作为特定“财富”的疫苗应该基于“世界性”的平等理念被分配。
虽然这一观念展现出对疫苗公平分配意愿的支持,却容易在疫苗分配实践中将特殊与普遍问题混为一谈,出现一元论的倾向。当代世界主义理论源于斯多葛学派的理性与自然法理念以及康德的普遍道德法则,这些理念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普遍主义色彩,容易使当代世界主义陷入将问题普遍化的情景模式中;而“世界性平等”观未将特殊情况纳入考量,片面分析难以关照世界各地的复杂局面。此外,当代世界主义提出的分配模式由于太过理想化而缺乏可行性。例如,“公平”的判断以何者为标准?在全球与区域分配政策出现分歧时,何者优先?可见,世界主义者致力于建构较为公平的全球理论以应对疫苗分配中的失序状况,但它倾向于将一元论的均衡准则不加区分地从地方正义运用到全球正义,所产生的全球正义制度会显得狭隘而不那么宽容。
(二) 国家主义观念:“狭隘的利益观”
国家主义将国家本身作为行为的目的,将国家理性、权力争夺、利益博弈通过对现代国家主权的理解而渗透在对公共卫生产品的认识中。Jan Aart Scholte指出,国家主义意味着治理的任何意图和目的都可以简化为国家[10]。奉行这种理念的人们普遍相信,“追逐权力和利益是人性使然,实现权力和利益是国家目标,诉诸普世伦理道德是海市蜃楼”[11]。以全球为舞台,国家主义追求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权威,推崇权力与利益争夺,拒斥对话与合作,格局较为“狭隘”。在疫苗分配问题上,国家主义通过阻碍分配意愿,强化疫苗公平分配的阻碍效应,致使疫苗分配走向混乱和失序。甚至,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为富裕国家抢夺、囤积疫苗提供了理念支持。疫苗分配之初,许多高收入国家罔顾人类共同利益,绕过COVAX机制,独立与疫苗生产商达成双边协议,一定程度上威胁着疫苗的供应;部分国家基于自身考量在COVAX投入大量资金“争夺”疫苗,而他们购买的疫苗已远超其可能的使用范围[12]。
对国家利益的过度强调,导致国家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感缺失,富裕国家在疫苗分配中的能为、应为而不为强化了疫苗公平分配的阻碍效应。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和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呼吁国际合作与团结,而非局限于狭隘的国家利益,强调面临这一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富国有责任帮助穷国[13]。否则,这会加深国家在疫苗分配上的不团结,持续扩大疫苗接种鸿沟,助长国际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长远来说,这将使国际社会追求整体发展的努力付诸东流。
(三) 矫正正义理论:“僵化的补偿模式”
矫正正义理论在道德和法律双重领域追求“得失之间的适度”,即当事人双方在实质正义支配下所应有的状态。亚里士多德估算不同的人在分配中所受影响的数值,将这些结果分别称为“收益”和“损失”,而追求二者之间均值的就是矫正正义。在亚里士多德的设想中,矫正正义意在恢复遭受损失的人、以他人为代价牟利的人的原有状态。这种平等不会根据政治制度差异而有所不同[14]。矫正正义解决问题的途径从道德领域迁移到法律领域。法律只考虑造成损害的程度,将诉讼双方视为平等主体,否认双方先前的优势是其原有权利的基础[14]。以此为前提,矫正正义对疫苗公平分配的阐释主要围绕补偿展开。历史上,发达国家凭借殖民掠夺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通过巩固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加深实力落差。当疫情发生时,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强大的国家实力抢夺甚至囤积疫苗,通过知识产权严格把控治疗剂与医疗用品的使用,而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却因为实力差距难以获得疫苗,甚至被限制获得治疗药剂与设备。在矫正正义的视域下,发达国家应该对“恢复原有状态”负责,这不仅包括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还要求发达国家对疫苗进行公平分配。
尽管矫正正义理论关于补偿的分析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在判断疫苗公平分配的“补偿”缘由、程度、范围上都存在“僵化”的风险。对历史的过度强调使这一理论存在较大的阐释漏洞,它难以解释为什么历史上未损害弱国利益的强国亦有必要公平分配疫苗的问题。在补偿限度上,矫正正义也难以衡量疫苗的分配比例和分配范围。若依靠其对“得失”的判断,则极易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自身意愿,其通过政治操控和舆论控制可以轻易摆脱这种束缚并作出对自身有利的回应。此外,矫正正义在应对疫苗公平分配问题时的适应性有限,因为“这个概念基本上还是当年亚里士多德所留下的那样”[15]。
(四) 全球正义:“微瑕的正义理念”
有关全球正义的探讨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现代意义上的全球正义却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对全球制度秩序问题的分析之下。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深入讨论的基本前提,全球正义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西方全球正义传统,围绕正义、责任负担和基本人权展开。在正义的基本问题上,全球正义超越了罗尔斯以国家为基础解决问题的基本设定,着眼于全球制度秩序的正义问题。罗尔斯曾在《正义论》中复归并进一步概括了以洛克、卢梭、康德为代表的契约论,从中抽象出其“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16]。拓展到国际领域,他仍以“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来论证国际正义的基本原则[17]。全球正义继承了罗尔斯对世界性平等的批判,但强调全球正义并非扩大版的社会正义[18]。因为,全球正义已然“看到”:罗尔斯将对国际正义问题的理解建立在以主权国家为模型的封闭社会的假设之上[19],然而在现实中,主权国家已不再具有罗尔斯意义上的封闭性。COVID−19已经暴露出重大的全球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在应对疫苗分配不公正的背后,深刻反思结构性不公正的问题。
全球正义中的责任负担主要围绕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展开,表现为对不平等、不公正行为的补偿。全球正义的一种观点认为,无论过去或现在,造成损害后果的民族应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戴维·米勒就曾通过对战争、贫困以及移民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后果责任与补救责任[18]。托马斯·博格则分析认为,穷国所受损害不仅源于自身更源自不公正的全球制度秩序,而这种不公正则是发达国家违背消极义务的体现。他提出,发达国家对穷国应承担的,除援助义务外,还应包括消极的不伤害义务以及补偿的责任[20]。联合国大会前主席Maria Fernanda Espinosa曾提出,如果发达国家不与较不富裕国家分享疫苗专利和技术,不加强旨在促进全球疫苗公平分配的多边倡议,所有国家仍然越来越容易受到新的COVID −19疫情和未来大流行病的影响[21]。就此而言,在应对疫苗全球分配不公正的问题时,全球正义对发达国家“补偿”责任的阐释展现出道德上的约束性。
全球正义中的基本人权被视作衡量标准和道德底线。全球制度秩序不公正的判断标准对各国来说可能不尽相同,而损害达到何种程度会引发补偿也难以确认。全球正义的原则是:将符合基本人权、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作为衡量标准,通过援引国际人权法尤其是《世界人权宣言》中的论述展现全球制度秩序的基本道德规范。“如果一个制度秩序可预见地导致了一个实质性的和可避免的人权缺失,那么,就此而论,这个秩序以及对它的实施就是在违反人权。”[22]在社会权视角下,发达国家保障基本人权的义务基于两点现实依据:其一,先前限制疫苗流通、垄断疫苗供应的行为导致了部分国家健康权的减损;其二,疫苗研发过程涉及对人类整体遗传基因资源的分析利用,较贫穷国家可以对使用其基因资源的主体主张权利。因此,以基本人权来划定补偿标准是适当的。概括来说,全球正义的核心主张在应对疫苗分配不公正,进而反思国际社会的结构性不公正问题时,具有更强的针对性;能够反驳绝对分配平等的观点,明确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责任,具有道德上的约束性;推动将基本人权作为衡量标准,设定国家合理的补偿限度,具有更强的可接受性。由此可见,全球正义在理念对比中展现出与疫苗公平分配问题良好的适配性与合理性。
尽管优势明显,但全球正义能否支撑起证成疫苗公平分配正当性的理念框架仍需进一步论证。首先,全球正义是否逻辑自洽?宏观来看,全球正义主要基于以下逻辑:①全球疫苗分配制度秩序中存在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②这种疫苗分配不公正源于内、外部因素,并已影响其他国家基本人权的实现;③造成损害后果的民族或国家需要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这种责任的限度为保障基本人权的实现。从整体来看,这一逻辑基本自洽,但也存在一些细节问题:其一,逻辑①中全球正义关注的问题只有在大量出现之后才得到关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其二,逻辑②和逻辑③中,全球正义将补偿责任限定于“基本人权”的实现,忽视了基于人的尊严的其他必要权利,如政治权利和自由、发展权、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其三,逻辑②和逻辑③中的分析以“存在实质损害”为前提,基于弱者视角,难以解释在发达国家视角下进行疫苗公平分配行为的必要性。其四,逻辑①、②和③中都将基本人权的实现作为衡量标准,这一标准对于受侵害国来说能否与所受损失的程度相匹配,都有待进一步讨论。其次,全球正义是否实践自洽?就当前而言,全球正义已然暴露出一个关键问题:缺乏可行的方案设计。例如,如何推进疫苗公平分配的理念认同?如何进行疫苗资源的再分配?如何促使部分国家履行责任?总体而言,尽管全球正义也存在现实问题,同绝大多数理论一样难以实现实践自洽,但它基本逻辑自洽,在理念对比中展现出明显优势。因此,全球正义可以作为应对疫苗分配不公正问题的主要理念基础。
三、补强的全球正义: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正当性选择
一种可行的理论应内核稳定,直面来自理论与实践的挑战。全球正义对疫苗公平分配正当性的阐释不能仅仅依托“正义”的逻辑框架,而应在合理借鉴优秀观念的基础上进行补强,以较为完善的理论模型应对疫苗分配失序的困局。
(一) 全球正义再思考
在对既有理论的阐释及批判中,全球正义凭借较强的针对性和道德约束性显现出更多描述疫苗分配正当性的可能,但逻辑内部的细节问题及实践中的方案缺失让这一理论尚存瑕疵。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全球正义再思考的方式,实现全球正义的“破而后立”。即,以全球正义的基础理念—— 罗尔斯正义理念—— 为初始的问题讨论模型,坚持问题导向,为应对疫苗分配失序探寻更合理的理念路径。
问题一,关于全球性。与现行的全球正义理念相比,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最大缺失在于固守国家体系观念,在面对全球疫苗分配的制度问题时难以突破国家或民族界限。这个问题似乎在全球正义中没有争议,但正如我们对全球正义逻辑①的质疑那样,国际社会往往在出现大量侵权的事实之后,这种全球疫苗分配失序的问题才显现出来。2022年9月,柳叶刀COVID−19委员会在《关于COVID−19大流行给未来的教训》中提出,国际社会在应对大流行病方面的延误代价高昂[21]。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是确保“错误”(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错误)不再重演的关键一步,包括在分享拯救生命的疫苗、提供信息和发展地方能力方面[23]。由于国际合作不充分、预警机制不完善,国际社会未能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工作,以致大多数国家措手不及。倘若全球正义在实践中能够预设或与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其他风险监控与预警机制相联系,某些全球性问题便能被防患于未然。
问题二,关于“人”的理念。罗尔斯契约主义人权观被隐含在正义理论之下,关于“人”的阐释并不明确。相比而言,全球正义将基本人权保障作为衡量标准和道德底线。但由于全球疫苗分配中隐含的结构性不公正以及偏见,这一标准难以经受事实的考验。基本人权的限度只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它或许能够保障人的基本需要,但难以促进发展,对促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来说,更是如此。人权框架中所载明的伦理原则承认,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获得健康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第14条声明,“享有最高可能水准的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意味着获取最高可能标准的医疗服务[13]。在“人”的理念上,当代世界主义的“博爱”观念强调对人的考虑和关怀,更多地关注“人”的整体性需要。并且,这种博爱、忠诚的特征来源于全人类的道德领域,而非基于民族、种族和阶级的特定群体[9]。因而,“博爱”观念能够补强保障“基本人权”视角下的观念瑕疵,从道德层面为人权保障增添价值理性,亦能为对抗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疫苗民族主义”提供一定的理念借鉴。
问题三,关于全球正义的双重视角阐释。从同情贫穷国家及弱势群体的视角出发,全球正义基本建构了理想情景,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这种解释仍显匮乏。例如,当一国的当下或历史行为没有实质侵害另一国家并使其遭受苦难,那么贫穷国家便不能以此主张他国对其难以获得疫苗的弱势地位进行补偿。在此情境下,全球正义便容易成为一种着眼历史追忆的单向正义,变得片面和局限。为克服这种问题,全球正义的双重视角阐释尤为必要。若将全球正义在贫穷国家视
角下对疫苗公平分配的阐释理解为“补偿论”,那么在发达国家视角下的这种阐释则可以被解释为“相互依赖论”。这种相互依赖着眼于在新的全球系统性风险下对国家间关系的清醒认知。首先,传染病这种全球系统性风险属于全球共同议题。全球系统性风险即整个系统的潜在损失或损害,由于存在某些薄弱环节,这种风险往往在各个单元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作用下被加剧,表现出严重性、传导性和共同性[24]。疫情之前,全球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为大国政治对抗、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气候环境恶化。自2021年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忽视大流行病等长期风险将带来灾难性后果。2023年初,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2全球风险报告》,在全球风险感知调查中显示,流行性疾病已经成为人们所担心的在“未来十年内全球最严峻的风险”之一。由于每个国家都暴露在全球系统性风险之中进而变成潜在的“受害者”,应对COVID−19等传染病应是全球共同议题。其次,由于世界各国的高度关联性和耦合性,援助他国也是一种自我防护。在全球系统性风险的背景下,由于国际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国际经贸交流的频繁性、全球风险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在单一国家建构“防御围栏”或局部设立防御体系难以应对大流行病的严峻挑战。而不平衡的防控举措产生的“薄弱环节”则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不断扩大,致使世界各国承担加重后的共同风险。反之,在应对大流行病时,通过疫苗公平分配促进疫苗的流通性和可及性,提高贫穷国家的疫情防控能力,减少全球范围内的免疫落差,能够填补“薄弱环节”并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作为在建构世界秩序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主体,发达国家将更多地感受到来自全球发展的制衡。现实维度下,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在新的全球系统性风险下相互依赖。通过疫苗公平分配,它们在提升全球公共健康水平的同时,亦降低了自身面临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因而,相较于带有单一补偿色彩的全球正义,双重视域下的全球正义能够兼顾贫穷国家的基本诉求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具有更强的道德色彩和说服力,更能为疫苗公平分配的必要性提供理念支援。
问题四,关于补偿限度。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补偿责任是与分配正义相联系的。他提出了保守的援助义务,却没有解释具体的补偿限度。全球正义虽提出保障“基本人权”的限度并列出模糊的人权清单,但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在2022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到来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表示:“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相互交织的人权挑战。”[25]例如,饥饿和贫困正在加剧,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增多,种族主义和歧视现象肆虐。对此,矫正正义中“得失之间适度”的观念能够支持国际社会作出更合理的安排。作为对实质正义“缺失”的弥补,“得失之间适度”要求对不公平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15]。其中,“适度”的标准将超越“基本人权”限度,根据实际损失情况适度调整。具体到疫苗公平分配的制度设计中,它强调国际社会成员的具体存在状态,关注国家由于疫苗分配失序所受损害的程度差异。在责任履行的限度上,这种方案将以保障“基本人权”限度为底线,以补偿所受侵害为重要标准,要求达到分配失序所受损失与获得补偿的相对平衡。
问题五,关于实现路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从整体上看是乌托邦的,缺乏将理论化为现实的具体设计,全球正义同样如此。尽管托马斯·博格曾提出过全球制度秩序的改革方案,例如全球资源红利方案、国际资源特权改革,但争议颇多,难以应对当下疫苗分配失序的困境。基于现实需要,全球正义在实践层面的详细设计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其一,推进疫苗公平分配的理念认同。这一目标的达成关键在于摒弃狭隘的“国家利益至上”和“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实践中,还可以通过在WHO发起疫苗公平分配的宣言及倡议,对充分履行分配及补偿责任的国家给予肯定和赞扬、加强公平分配宣传等方式肯定疫苗公平分配的重要价值。其二,进行疫苗资源的再分配。在全球伦理学视角下,只有基于公正、有益和公平原则的医疗资源的宏观和微观分配,才是合乎伦理的[13]。现实中,依据供需逻辑和利益博弈,疫苗的初次分配已经基本满足发达国家的免疫需求,但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获取疫苗仍困难重重。2022年12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在由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举办的国际技术研讨会上提到,“尽管我们在过去三年中取得了大量成就,但严重的全球不平等现象仍然阻碍了应对工作”[3]。为扭转这种困局,发达国家有必要促进疫苗的流通和可及性,推动疫苗在穷国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应以保障“基本人权”为底线,兼顾损失与补偿相适应的重要标准,从国家疫苗需求的急迫性和限度出发,进行合理且适度的再分配。其三,促使国家切实履行责任。这需要为国家责任履行设定具体约束。对此,较好的选择是在公共卫生治理机制中设定具体制度和实践方案。在进行机制自身去政治化改革外,这些制度设计包括在WHO内设置疫苗生产与再分配的大数据统计平台,对疫苗流向进行大致把控;由WHO主导,在疫苗生产商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疫苗流通的便捷渠道;设置疫苗再分配的计划及目标,赋予国家具体的担当指标,通过专门的媒体路径定期进行公示。因为这些具体设计更多地体现为鼓励性,可以缓解履行国的抗拒心理,促使其支持疫苗再分配方案的落实。到2022年底,ACT−Accelerator(Access to COVID−19 Tools Accelerator,获取COVID−19工具加速计划)已经启动了为期6个月的计划,通过与行业伙伴、民间社会组织合作,继续提供疫苗、检测和治疗的途径,增多世界各国公平获得疫苗和治疗剂的机会;WHO建立了世卫组织大流行病和流行病情报中心,提出了关于建立更强大的防范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架构的10项重大建议,启动了一项新的国际文书谈判;世界银行设立了疫情大流行预防、准备和应对的金融中介基金,以便在世卫组织的技术指导下提供催化资金,填补疫苗供给的资金缺口[26]。毫无疑问,国际社会正从这场大流行中吸取经验教训,直面国际社会在分配结构上的不公正。
(二)补强的全球正义的基本逻辑与内涵
经由对全球正义的再思考,一种问题导向的理念框架逐渐展现出来,为我们更好地阐释疫苗分配正当性奠定基础。由于这一框架建立在对全球正义的再思考之上,其关键要素囊括在现行全球正义之中,其基本设定符合全球正义的基本逻辑。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更完善的理念框架称为补强的全球正义。它对全球性问题的阐释遵循以下基本逻辑:①全球分配制度秩序中存在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造成了实质损害;②这种不公正基于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了其他国家基本人权的实现;③在双重视角的阐释下,补偿/援助以保障“基本人权”为限度(在“补偿论”下,还要求实现损失与补偿的相对平衡);④设置相关制度和实践方案,助推疫苗公平分配的落实。由此,补强的全球正义可以通过对不同观念的清晰定位实现内部协调,通过制度设计及实践安排产生外部效能。
补强的全球正义理念框架的内部逻辑呈现出这样的形态:在全球系统性风险的背景下,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奠定了这一框架的理念基石;“正义”“人权”“责任”要素建构起这一框架的核心理念;“博爱”与“得失之间的适度”观念是理念框架的重要补充。其理念框架的内部关系及定位展现为:一个中心、两个重要补充。其中,经补充和修正的正义理论处于这一理念框架的中心位置,它兼具贫穷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双重视角阐释,基本包含现行全球正义呈现出的合理理念,并对再思考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补充与修正。通过对“人”的理念的补强和对“基本人权”最低限度的合理调整,“博爱”观念与“得失之间的适度”观念成为这一理念中心的重要补充。由此,体系内部不同成分获得明确定位,展现出理念的内部协调。
此外,补强的全球正义理念通过具体操作产生外部效能。在制度设计上,这些详细设计结合大数据技术,要求建立旨在早期防范和阻断全球性问题的风险监控与预警制度;设置疫苗再分配制度,在补偿/援助中保障“基本人权”,兼顾“补偿论”下损害与补偿相适应的重要标准;建立责任履行公示制度,对促进疫苗分配及补偿/援助的国家给予肯定,对助推疫苗再分配的情况给予赞扬。在实践安排上,它要求推动WHO主导并发起疫苗公平分配的宣言及倡议;在国际媒体加强公平分配必要性的宣传,推进疫苗公平分配的理念认同;在疫苗生产商与部分国家间建立疫苗流通的便捷渠道,保障疫苗供应。这些安排针对制度中的现实问题,展现出补强的全球正义理念在操作中的合理性。
基于上述逻辑阐释,这种补强的全球正义可以作为疫苗公平分配的正当性选择,它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二重意涵。在认识论层面,补强的全球正义理论作为人类实现全球性公共事务治理,尤其是进行全球性公共利益分配时所依凭的正当性基础,存在以下几个关键维度:在正义理念上,补强的全球正义肯定了经补充和修正的正义理论在理念框架中的中心地位,敏感于各个国家之间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以及国际社会的结构性不公正;在“人”的观念上,这一理论框架以“基本人权”为衡量标准,通过“博爱”观念对这一标准下的前见进行修正,对抗歧视与偏见;在基本限度上,它在补偿/援助中强调“基本人权”保障,兼顾“补偿论”下损害与补偿适度平衡的重要标准;在视角选择上,它关注到各国处于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时代背景,着眼于贫穷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双重视角,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在价值指向上,这种全球正义理论主张克服利益博弈,摆脱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强调“正义、人权、责任”的核心价值,表现出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
在方法论层面,补强的全球正义理论理性地作用于国际关系主体的交互行为,希冀推动在收入水平差异巨大的国家间稳固建立良性互动渠道,意在通过积极的制度性安排调节人类对全球性公共利益分配的分歧与冲突。它将通过具体的操作安排,敦促不同国际关系主体在面对全球性公共问题时能够且必须作出符合全球正义规范要求的承诺与行动。具体到公共卫生产品的配置上,全球正义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布局和资源配置,意在解决不平衡、不平等的问题,体现为各国在现实维度对疫苗的分配、占有的公平性和平等性。
四、逻辑与实践的双重自洽:疫苗全球公平分配正当性的重新证成
根据弗里德里奇·哈耶克的说法,经济、社会和政治理论赖以建立的标准和基本概念是人们可知的有限性,理性地建立一种能够解释大量事实知识的规范需要大量参考“第三方”材料,经过漫长的试错过程,这一合理规范才被选择出来[27]。补强的全球正义是否自成体系且自洽?能否从理念走向现实,证成疫苗公平分配正当性?还需要从逻辑自洽和实践自洽两个层次进行探讨。
(一) 补强的全球正义的逻辑自洽
科学研究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上,其本身就是遵循自洽性的,而仅依据主观基础,最终会归属于不可证伪或证明,理论自然会不攻自破。探讨逻辑自洽性也就是去审视某一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之间、由这些假设逻辑推导出的结论之间以及基本假设与结论之间彼此的相容性、非矛盾性[28]。简言之,逻辑自洽的判断取决于是否存在逻辑内部矛盾,即按照自身的逻辑推演,可以证明自身至少不是矛盾或错误的。对此,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审视。
宏观视角的考察着眼于理念的包容性问题,即能否对抗歧视或偏见,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作为当下全球基本共识之一,这种包容性发展旨在推进公平、公正发展、减少全球不平等并促进全球发展成果共享[29]。以此为标准对补强的全球正义进行审视后发现,自逻辑起点开始,这一理论就显现出多极化世界中较强的包容性。它着眼于三个关键命题:①历史上的非正义行为导致现代部分国家陷入贫穷,为实现公平、公正发展,发达国家需要对穷国适度补偿;②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不公正的全球疫苗分配制度秩序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平等,为填补发展落差,发达国家需要对穷国进行疫苗或技术援助;③世界各国都处于新的全球系统性风险(传染病)之中,发达国家援助他国也是一种自我防护,进行疫苗公平分配是必要的。其中,补强的全球正义关注全球发展的不公正、不平等,倡导基本医疗用品的流通性和可及性,其重点就是强调疫苗的公平分配。具体来说,这一理论从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现实需求中衍生出来,自始就具备面对全球多元文化的理念假定,内含着对全球包容性发展的价值肯定。在理念构成上,作为核心观念的人权本身就展现出道德性要求[30];“博爱”同样强调,不论个人拥有何种文化背景,都应充分享有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在阐释视角上,它兼具贫穷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双重视域分析,避免了单一视角解读的局限。在补偿/援助的设定中,它要求以保障“基本人权”为底线,不强调国家的先前优势,而关注客观损失的程度。在理念目标上,它与世界总体发展趋势相契合,指向平等、正义、人权与发展等人类共同价值。由此,补强的全球正义能够克服歧视,包容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人民,呈现出理念包容性。
微观视角的考察展现为对阐释细节的审视。在此,我们借鉴阎学通教授提出的国际关系分析中的逻辑自洽规则[31]来进行审视。这些规则存在的目的是确认分析过程中所陈述的道理不存在矛盾,它存在以下几项要求:其一,在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上,遵循时间的先后顺序。这一理论对疫苗分配争议的问题产生、方案分析以及路径选择的时间逻辑遵循因果律,不存在用后发生的事情去揭示先存在的原理的现象。其二,在不同变量的选择上,要求“以事物的变量解释其变化”“自变量与因变量二者的变量值变化形成对应关系”。补强的全球正义理论中的限度要求便是如此。当发达国家对穷国进行补偿并分配疫苗时,这种促使穷国满足基本人权需要并实现免疫的进程就逐渐加快,针对不断减少的需求,发达国家的补偿程度也就相应降低。其三,在对现象的论证上,要求具备适足的必要条件。这一理论对疫苗公平分配存在双重视角的阐释,既包含弱国视角下的“补偿论”,也包含发达国家视角下的“相互依赖论”,能够从强弱双方视角出发对分配的必要性进行合理阐释。其四,在解释因素上,要求“以特殊性因素解释特殊现象”“以共性因素解释普遍现象”。这同样与补偿限度的设定原则一致。其中,特殊性在于关注特定国家所受损害的不同程度,设定差异化的补偿限度;共性在于坚持“基本人权”的底线以及“博爱”的普遍道德要求。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补强的全球正义具有较为合理的理念构造,能够逻辑自洽。
(二) 补强的全球正义的实践自洽
作为疫苗公平分配的正当性基础,补强的全球正义不仅应理念自洽,还应实践自洽。实践自洽表现为事物对实践活动良好的适应性,要求在价值实现的过程中与实践进行良性互动并自我发展。就此而言,补强的全球正义的实践自洽便存在一个重要的考察指标:能否克服实践障碍,实现自我发展。
现实维度下,疫苗公平分配需要借助国家力量逐步实现,但如何促使国家切实履行责任属于实践难题。补强的全球正义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设置疫苗再分配制度,为国家责任履行设定具体约束。这一制度设计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囤积“富余”的疫苗,目的在于保障疫苗能够被顺利分配给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再分配制度以保障“基本人权”为底线,从国家疫苗需求的急迫性和限度出发,对这些国家进行补偿/援助,以实现合理且有效的疫苗分配。在实现路径上,疫苗再分配制度要求在WHO内设置疫苗生产与再分配的大数据统计平台,对疫苗流向进行大致把控;单独设置疫苗再分配的计划及目标,直接赋予相关国家具体分配指标,通过专门的媒体路径定期公示。同时,补强的全球正义可以设立公示制度,对积极实现补偿/援助的国家给予肯定和赞扬,对阻碍进程的国家进行警示。此外,在疫苗生产商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疫苗流通的便捷渠道也是保障公平分配的重要方案设计;发起疫苗公平分配的宣言及倡议,在国际媒体加强公平分配必要性的宣传,也是推进疫苗公平分配理念认同的可行安排。这些预设的实践安排可以用以解决疫苗分配制度中的实践障碍,促进实践自洽的实现。
这些制度设计亦彰显出自我发展的协调机理。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与发展,疫情防控及风险监测的效率也将获得较大提升,这种制度与科技的协调将为疫苗分配实践提供技术支援;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被赋予的相关职责与现实的疫苗需求相适应,有助于宏观把控疫苗流通情况,这种制度与专门机构的协调将为疫苗全球公平分配提供组织保障;公示制度在履行信息公开使命的同时,亦饱含着对世界各国民众知情权的尊重,这种制度与公民社会的协调将为疫苗全球共享提供群众力量。可以说,补强的全球正义提出的制度设计存在着支持自我发展的协调机理,有益于增进其克服实践障碍的现实可能,进而保障实践自洽的实现。至此,这一理念的内在逻辑自洽与外在实践自洽表明,补强的全球正义理论可以为疫苗公平分配提供正当性基础。
五、结语
概言之,在重大公共危机背后,国际社会的结构性不公正突出,“重复”波动失序的现实状况已经向国际社会敲响警钟,让我们去探寻疫苗公平分配的正当性。从既有理念的分析来看,无论是世界主义理论、国家主义理论、矫正正义理论,都难以担负起建构新理念以提供规范指引的重任。相较来说,虽然全球正义自身在解释疫苗公平分配争议时尚存瑕疵,亦无切实可行的详细方案,但瑕不掩瑜。经由对全球正义的再思考,一种问题导向的理念框架展现出来,这就是补强的全球正义。其合理的理念构造展现出逻辑自洽,其制度设计能够实现实践自洽。因而,补强的全球正义具有应对疫苗分配失序困局、证成疫苗公平分配正当性的现实可能。此外,这一正当性基础能为后续国际社会继续开展分配机制的法律制度设计、监管模式研究、知识产权问题讨论以及其他争端解决等提供理念支撑和制度借鉴,亦能为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带来理念和价值引领。
① “公平优先”伦理框架认为,疫苗分配存在三个基本价值观:造福人民并限制伤害、优先考虑弱势群体、对所有个人给予平等的道德关注,并将分配分为三个阶段。
② 托马斯·博格认为,当代世界主义立场包含三个要素:一是“全球正义的终极关怀单位是个人”;二是“对每一个个体的终极关怀都是平等的,与其所属的群体无关”;三是“个体彼此的终极关怀不仅限于国家同胞之间,这种特殊的地位具有全球性”。
[1] WHO. WHO Coronavirus(COVID−19)Dashboard[EB/OL]. (2022−12−06)[2022−12−06]. https://covid19.who.int/.
[2] UN. Vaccine hoarding will prolong COVID warns WHO, as agency mulls early Omicron data[EB/OL]. (2021−12− 09)[2023−04−08].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12/1107542.
[3] WHO. WHO, WIPO, WTO call for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to support timely access to pandemic products[EB/OL]. (2022−12−16) [2023−04−08]. https:// www.who.int/news/item/16−12−2022−who--wipo--wto- call-for-innovation-and-cooperation-to-support-timely-access-to-pandemic-products.
[4] TALHA K B. Challenges in the rollout of COVID−19 vaccines worldwide[J]. The 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 2021, 9(4): 42−43.
[5] DAL-RÉ R, CAMPS V. ¿A quién habría que vacunar primero frente a la COVID−19?[J]. Medicina Clínica, 2021, 156(4): 177−179.
[6] ABUMERE F A. Global justice and resource curse: Combining statism and cosmopolitanism[M].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2021: 115−130.
[7] THOMAS W P. Cosmopolitanism and sovereignty[J]. Ethics, 1992, 103(1): 48−75.
[8] DOCKSTADER J, etc. Cynic cosmopolitanism[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2021, 20(2): 272−289.
[9] DAVID H. Cosmopolitanism ideals and realities by David Held[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40.
[10] SCHOLTE A J.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86.
[11] 秦亚青.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导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5−26.
[12] The Lancet. Access to COVID−19 vaccines: Looking beyond COVAX[J]. The Lancet, 2021, 397(10278): 941.
[13] UNESCO. Statement on COVID−19: ethical consideration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EB/OL]. (2020− 04−06)[2023−04−08].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 223/pf0000373115_chi.
[14] IZHAK E. Corrective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From aristotle to modern tim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8.
[15] ELEFTHERIADIS P. Corrective Justice among states[J]. Jus Cogens, 2020, 2(1): 7−27.
[16]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6.
[17] RAWLS J. The law of peopl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7−38.
[18] 戴维•米勒. 民族责任与全球正义[M]. 杨通进, 李广博,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 54.
[19] 刘莘. 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J]. 哲学研究, 2008(11): 88−96, 129.
[20] 向青山. 论涛慕思•博格的全球正义理论[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2.
[21] SACHS D J, KARIM S S, AKNIN L, etc. The Lancet Commission on lessons for the future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J]. The Lancet, 2022, 400(10359): 1224−1280.
[22] 涛慕思•博格. 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M]. 刘莘, 徐向东,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446.
[23] WHO. Countries begin negotiations on global agreement to protect world from future pandemic emergencies [EB/OL].(2023−03−03)[2023−04−08]. https://www.who. int/news/item/03-03-2023-countries-begin-negotiations-on-global-agreement-to-protect-world-from-future-pandemic-emergencies.
[24] 王宏伟, 钟其锡. 系统性风险:新时代必须着力防范的重大风险[J]. 中国减灾, 2022(19): 52−55.
[25] UN. Guterres: Put human rights at the heart of efforts to reverse today’s damaging trends[EB/OL]. (2022−12−09) [2023−04−08].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2/12/1131597.
[26] WHO. 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launch of The Lancet COVID−19 Commission Final Report[EB/OL]. (2022−09−15) [2023−04−08]. https://www.who.int/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launch-of-the-lancet-covid-19-commission-final-report---15-september-2022.
[27] 徐向东. 全球正义[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630−635.
[28] 张国启. 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自洽性及其当代意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 137(11): 101−109.
[29] 高景柱. 国家兴衰、包容性制度与全球平等—— 以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理论为例的分析[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1, 23(2): 3−10.
[30] 毛俊响, 盛喜.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确立:基于横向人权义务的补充分析[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3(4): 27−36.
[31] 阎学通. 国际关系分析中的逻辑自洽[J].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2): 3−4.
Reinforced global justice:Justification basis for the global fair distribution of vaccines
MAO Junxiang, WANG Xinyi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Behind major public crises, the structural injus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obvious. And vaccine's global distribution of "repetitive" fluctuating disorder has been ringing an alarm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is dilemma, to realize the legitimacy of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vaccines globally, we can explore the effective concept of global sharing and fair distribution of vaccines by critically analyzing existing theories. In reality, theories such as contemporary cosmopolitanism, nationalism, and corrective justice are all hard to sustain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quired for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vaccines globally. In contrast, the theory of global justice, despite its defects, has manifested its obvious advantages. Reinforced global justice, a question-oriented conceptual framework, via reconsidering the global justice, has demonstrated its transcendence over the existing system through modification and amendment. Furthermore, reinforced global justice, with its reasonable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and system design of vaccine distribution, illustrates in testifying logical self-consistency and practical self-consistency that reinforced global justice can provide a legitimate basis for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vaccines globally.
reinforced global justice; fair distribution of vaccines; legitimacy basis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3.03.007
D990
A
1672-3104(2023)03−0065−12
2022−11−03;
2023−04−1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际法问题研究”(20&ZD20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研究”(20AZD104);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一般项目“疫苗全球共享与公平分配的正当性基础”(CX20210134)
毛俊响,男,湖北黄梅人,法学博士,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基础理论、国际人权法;王欣怡,女,山东潍坊人,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国际人权法,联系邮箱:752450120@qq.com
[编辑: 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