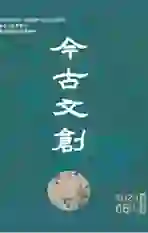苏珊 · 桑塔格与大众文化
2023-05-31苏舒
【摘要】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争端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在纽约知识分子群体中暗潮涌动。20世纪60年代桑塔格直接挑明了两者之间的战争,公开为大众文化代言。她提出的“新感受力”理论重新评估了艺术的价值,打破原有的高级—低级文化对立的秩序。她还积极参与社会文艺活动,以文艺批评为武器干预公共生活,试图改造中产阶级文化属性。尽管为大众文化发声,但桑塔格并不反对高级文化,她的理论只是提供补充性的标准,并且暗含一种新的智性层面的精英主义。但她的尝试颇具前瞻性,为未来新文化的生发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苏珊·桑塔格;大众文化;高级文化;精英主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5-012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5.040
一、高级与低级文化之争
20世纪4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复兴了现代主义文学,以现代艺术为代表的高级文化成为学院派守护的对象。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以及欧文·豪(Irving Howe)大力扶植现代主义。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社会进入长期的经济增长期,社会福利有了增加,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改变,这促使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但美国中产阶级并没有能创造出属于自己阶层的文化,所以他们在面对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时都保持着一种自卑的心态,这使得当时的中产阶级文化呈现出一种暧昧模糊的姿态,成为多种文化的杂糅。在这种背景下,纽约知识分子群体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开始出现了分歧。格林伯格、麦克唐纳、欧文·豪等人都对大众文化嗤之以鼻,依然试图维持一种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立场。但希尔斯(Edward Shils)及胡克(Sidney Hook)等人开始为大众文化辩护,认为大众文化实际上代表了工人阶级的进步。到了20世纪60年代,青年运动、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层出不穷,此时的纽约知识分子已经更迭到了第三代,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菲德勒(Leslie Fiedler)首次正面为大众文化辩护,认为应当打破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并且认为通俗文化可以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主体 [1]。但要突破传统高级-低级文化对立的文化秩序,还需要一把开战之火。
二、桑塔格声援大众文化的理论
当桑塔格在1964 年至1965年间发表《关于“坎普”的札记》《反对阐释》《论风格》和《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等文章时,一场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之间的战争被直接挑明。桑塔格则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代言人,向高级文化公然发起挑战。“新感受力”是桑塔格在这场论争中提出的关键概念,被用于论证大众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优势。“新感受力”产生于科学文化与文学—艺术文化的交融之中,是吸纳了大量科学与技术因素之后的艺术实践。这种“新感受力”也是人类借助技术拓展自我之后所形成的新的思考、感受和评价方式。“新感受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美国人们的实际生活方式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到达了新的阶段,但现有文化尚未跟上变化的速度,人们对新阶段生活的感知方式和评价体系仍显得落后,因此培养“新感受力”以更新人们的意识显得极为迫切。在形成“新感受力”这一诉求下,艺术的最高价值不再是诉诸道德领域指导人们进行具体的生活方式选择,而是焕新人们的意识和感受力,拓宽人们对艺术审美的认知以及对生活方式的想象。因此“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分野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因为两者都拓宽了人们的生存体验和感受方式。甚至“低级”文化在补充人们的意识运作方面还有更大的作用:在一种体现科学技术性的层面上,“低级”文化较之传统的“高级”文化有着更为丰富的实验,“低级”文化做出了更多弥合科技与艺术之间鸿沟的尝试,从而比“高级”文化体现出更为开放和多样的未来性特征。
而“坎普”则是桑塔格大众文化阵营的先锋军。桑塔格这样定义“坎普”:“坎普的实质在于其对非自然之物的热爱:对技巧和夸张的热爱。”[2]蒂凡尼的灯具,20世纪20年代装饰夸张的女装,斯戈皮顿公司出产的电影,都可以被当作坎普的典型代表来看待。而坎普文化相对高雅文化所具备的优势则体现在它的民主精神,坎普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发掘“优等”趣味和“劣等”趣味,强调的正是一种平等民主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意味着以一种没有等级的视角看待各种文化以及各种生命经验,从更偏向于审美的角度理解人的境遇,而非仅仅涉及价值判断。只要是能够激发人们感受能力、拓宽人们意识的艺术都是有价值的艺术。这也表明,如果用能否培养“新感受力”这一标准去评价艺术,那么无论是代表高雅文化还是低级文化,主流文化还是边缘文化的各类艺术都具有着无可置疑的价值。而以“坎普”艺术形式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尽管受到许多学院派的打击,但也更能提供新的感受养料和思想资源。因此桑塔格积极为大众文化发声并助推其发展。
三、桑塔格声援大众文化的文艺实践
大眾文化是桑塔格文化理论提出的落脚点,也是她进行文化政治实践的根据地。提出思想理论之后,桑塔格积极投向了当时的社会文艺活动。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出现了以先锋表演为中心的文艺探索活动,桑塔格则借此潮流,为“百老汇”之外的实验剧撰写评论,推动格林威治村的先锋文艺活动向纵深发展。她声援色情文学,认为色情文学的情色代表着充盈生命力的爱欲,而爱欲和死亡则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命题,以此说明色情文学包含着严肃的关乎人类根本生存状态的问题。与之相呼应的,她也支持性解放运动,认为性革命和政治革命之间有着一种深刻的共鸣,微观而言是对旧左派的一种否定,宏观而言则涉及到对旧有资产阶级道德规约的反叛。[3]除了提出理论和观点,桑塔格还积极营销自己,打造个人文化品牌。她的名字不仅出现在文化精英关注的杂志上,她的照片还登上《时尚》这种与大众流行文化接轨的杂志上。离开象牙塔的文化斗士身份已经足够引起关注,她还采用一种激进和战斗的姿态来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以此来塑造个人品牌和标志性形象。人们通过她大胆率性又颇带犀利气质的形象感受到了新文化带来的清新气息和旧文化的摇摇欲坠,一种兼具两性魅力的另类知识精英的形象与另类文化紧密相连。由此桑塔格本人也成为了新文化的先锋和偶像,并与“站在对立面”的反讽态度联系在一起[4]。
桑塔格以文艺批判深入政治实践的意图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即使是关注作家写作,桑塔格的关注重点也并不落在作家的个人力量比如美学形式、个人特点,而是关注作家们介入公众生活的能力,关注他们的独特审美经验对公众行动能力的激活功能[5]。所以桑塔格支持另类文化的意图也包含着政治实践这一意味,她以支援另类文化的方式唤起人们的审美能力,并企图以此影响公众的行为选择。从理论的提出,到支援先锋文化和亚文化的活动,这一切都表明苏珊·桑塔格的野心并不止于在理论层面上挑战高级—低级文化的传统秩序,而且是要汇入改造资产阶级文化属性与生活方式的大潮,从实际行动上挑战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原有的社会文化结构,重新书写和定义资产阶级的文化生活方式。
四、桑塔格与高级文化
尽管桑塔格极力支持,但这并不代表她本人反对高级文化本身,她反对的是所谓高雅文化与另类文化形成的高下区别的判断。首先,她支持另类文化并不是想要取代或者推翻高级文化,而是想要提供一种补充性的文化,推动更为多元的文化局面的出现。正如她在论证“坎普”文化时所提出的坎普趣味反对的是二元对立的好—坏标准,它无意证明哪一种文化的好坏优劣,而是要提供一套补充性的文化标准。所以桑塔格反对的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评价标准,反对的是僵化的高级—低级的二元对立思维,反对的是在一个急需新的时代精神和感受方式的时代,人们依然陈腐地沿用过去的文化。而她对大众文化的极力支持,正是为了开拓和补充高级文化占绝对领导权的局面,提供一套补充性的思路。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补充性并不是温和地在旧有的文化秩序中为大众文化谋求一席之地,而是带着强烈的民主精神,要求建立一种各文化都相对平等的文化新格局。只有平等的地位才能为各个文化的对话与竞争创造条件,使得它们有机会发生碰撞和融合,从而滋生出新的更符合未来新感受方式的文化。
其次,桑塔格的精英主义意识非常浓厚,即使是为大众文化做辩护,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依然是采取了精英式的论证和话语方式。尽管桑塔格试图“削平”高级文化与低价文化的分野,从一等程度上体现出民主的精神,但如果深究她所提出的新的文化秩序的构想,会发现这里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精英主义。她原本来自精英文化的阵营,康德、尼采、艾略特、布勒松等人都是她旁征博引的材料。为艺术独立性辩护时,她再三强调审美能力,也就是一种需要智性和感受力双重结合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一定能通过学院派的知识培养和文化传承获得,而是通过感受能力与审美视野的双重提高才可能获得,可以说这种审美能力只属于感觉敏锐且意识前卫的少部分人群。桑塔格看似是在削平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的差距,为大众文化地位的提升提供了可能性,但也具备着隐形的筛选标准。这条路子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亲民,但这也是桑塔格文化斗争策略中的精明之处。要占领文化的领导权,需要争取的人群主要是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这一群体的显著特征是既享受安穩的生活,但同时又暗自渴望着一种冒险和创新的生活。他们既想要融入社会主流的生活方式,同时又希望能创造出独特和个性的生活方式。因此,桑塔格具有民主精神却又带有杰弗逊式精英主义的文化思想,调和了两种矛盾的需求,在当时受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欢迎。
最后,“削平”是桑塔格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化秩序,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使之更符合当下与未来的人们的生活感受方式,这是桑塔格的追求。但关于未来的文化秩序究竟是如何,桑塔格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论。一种平等的文化格局论调是桑塔格当时采用的话语方式和斗争手段,但并不意味着这是桑塔格认为最终的美国文化应当形成的结果。桑塔格撬动原有的标准,用一套新的话语和宣传方式对它形成冲击,从而形成裂缝,使得文化格局有重新塑造的可能。她是一位无畏的先锋批评者,一位对教条标准发起挑战的批评家,但她绝不是一位理论构建者,她并不构筑自己的理论堡垒。但她提供的智慧仍然是无与伦比的,那就是在一个需要变革的时代,勇敢地吸纳和包容不同的思想和文化,使得它们碰撞激荡也相互滋养,从而使得一种更新的文化在历史的选择中重生。
五、结语
美国20世纪40年代以来,伴随着纽约知识分子的活动,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争论一直不断。从高级文化优于大众文化的主流论断,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人为大众文化进行辩护,再到20世纪60年代一批知识分子为大众文化声援。大众文化始终在不断扩大自己的文化领地,而桑塔格的发声直接挑明了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争端。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言人,她提出“新感受力”的理论,认为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滋养人们的意识和感受,而非服务于旧有的意识形态。“新感受力”的提出试图削平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野,“坎普”文化则成为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体现出一种文化平等的民主思想。除此以外,桑塔格还积极投向了发表剧评、声援情色文学与性革命等文艺实践,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助力。这也表明桑塔格的野心不仅仅在于文艺领域,更在于以文艺批评的方式参与政治,从而改变资产阶级的文化生活方式。
但桑塔格从来不是高级文化的反对者。桑塔格自身的理论尽管具有平民精神,但本质上仍然是精英主义式的。这种暗含的精英标准体现在对人们感受力与智性层面的要求,但也精明地迎合了中产阶级对文化主流性和独特性的双重需求。她真正反对的是教条主义式的文化标准,她的理论是为了给当时的文化秩序提供补充性的标准,从而推动文化多元平等的格局出现,为各种文化提供平等对话与交流的机会,推动一种新的符合未来感受方式的新文化的诞生。从这种角度来看,桑塔格并不仅仅是激进的反对者或者平权主义者,她的思想中包含着一种远大的前瞻性,一种为未来文化发展扫除当前障碍的魄力,这也是桑塔格思想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曾艳钰. “纽约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批评之争[J].外国语言与文化,2017,1(02):42-53.
[2]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329.
[3]苏珊·桑塔格.激进意志的样式[M].何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4]柯英.苏珊·桑塔格:大西洋两侧最智慧的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131.
[5]张柠.批评家的公众关怀和审美气质——苏珊·桑塔格的“政治评论”[J].中国图书评论,2006,(11):18-22.
作者简介:
苏舒,女,重庆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20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