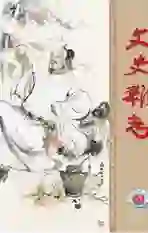东华门遗址与成都城市历史文化特色
2023-05-06谢元鲁
谢元鲁
摘 要:成都东华门遗址是汉至清两千余年的重要文化遗存。它展现了古代成都城市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特色,是蜀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而独具创造性的千年文脉的城市载体,是成都历史文化、天府文化的标志性象征,对于发展成都市品牌,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特色城市,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地理空间;文化空间;核心区域;城市品牌
一、东华门遗址的城市历史文化意义
(一)名称及遗址范围
东华门遗址因东华门街而命名。东华门即清代四川贡院东门。清朝灭亡后虽贡院不存,东华门街仍保留了清代贡院遗留的地名。东华门遗址考古发掘面积约为5.27公顷,约合80亩,西入后子门体育中心,东至体育场路,仅占成都城市历史文化核心区的很小部分。
东华门遗址大致包括自两汉六朝、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三个大时段经历两千余年的若干重要文化遗存,包括国内首见的五代宫廷御道、隋唐至两宋生态人文胜境摩诃池、明代规模最大的藩王府邸园苑区,以及南方地区少见的唐宋园林庭院等。
(二)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意义
截至2022年3月,国务院已将141座城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中,成都名列1982年公布的第一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列。
历代成都城市的中心区域,都集中在北起武担山,即今江汉路,南至红照壁,东起顺城大街,西至东城根街大约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是两江环绕明清城垣内的成都传统老城区面积(约10平方公里)的五分之一,为城市传统的核心区。因此,东华门遗址实际上是成都城市核心区域的历史文化浓缩与精华。东华门遗址揭示的历史文化,就是成都城市的历史文化。
东华门遗址的发现,是成都作为中国古都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城市建筑艺术的实证展示、时空标尺与历史记忆。
二、东华门遗址与成都城市地理空间特色
(一)确立超稳定型的城市格局
东华门遗址发现的从汉唐宋元明清延续2000余年的宫廷、官府和园苑遗存,展示了成都城市核心区域的超稳定型的结构。
秦汉时期,在秦灭巴蜀后,张仪、张若相继在成都仿照咸阳筑城,建成两个相连的城池,即由大城和少城组合而成的城市。其城垣周长达12里。少城是工商业区,大城是官府区和居民区。汉代的成都由于人口增加,商业繁盛,遂扩建外垣,开有18个城门。彼时城市人口众多,是西汉后期的全国第二大城市。扬雄《蜀都赋》说:“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可见汉代成都的盛况。
到三国蜀汉时期,随着刘备在成都即位称帝,成都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宫殿群。这一宫城在汉代成都城北部的武担山一带。蜀汉灭亡后,其宫苑到西晋时期,按照左思的《蜀都赋》描述,仍然有遗存。
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除公元3世纪初成汉在成都短暂建都,成都一直是西南的地方首府。杜甫初到成都,见到成都的城市布局说:“层城填华屋,季冬草木苍。”可见唐代的成都,具有大城与子城的双重城垣景观。
唐宋之际的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和后蜀两个王朝相继在成都建都,大规模地建筑宫苑,使成都城市中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皇家宫殿群与园苑,即著名的“宣华苑”。这是成都城市核心区发展的新阶段。蜀宫建筑及园苑是中国古代成都城市景观与建筑文化最高水平的代表作之一。
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封其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在成都的城市中心建设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蜀王府。王府四周以长达九里的城垣环绕,开创了成都城市核心区的最后一个古典辉煌时代。蜀王府气势恢宏,建筑华丽,所以民間呼之为“皇城”。蜀王府的选址大体上与唐宋宣华苑相同,并且利用宣华苑的部分水域。这座壮观秀雅的蜀王府,在明末遭到张献忠农民军的毁灭性地破坏,宫殿被焚烧,园苑被平毁,仅余正门门洞。清代平定蜀中局势后,在蜀王府旧址建贡院,作为四川全省科举考试和阅卷的场所。但民间按明代王府传统,仍称贡院为“皇城”,所在区域为“皇城坝”。这一称呼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和现代。
两千多年来,以东华门遗址为代表的成都城市核心区域,在城市变迁中出现三个特点:
位置稳定,始终固定在北起武担山,南至锦江滨的城市中心地域。《元和郡县志》载:“大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径(经)县南七里。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溉田万顷,蜀人又谓流江。”所谓县南,是指在今正府街一带的唐代成都府衙,距流江7里。唐制1里约等于现今415米。7里按今天与锦江的实际距离(约2.6公里)基本吻合,可见其位置的稳定。
范围稳定,核心区始终保持约2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
功能稳定,始终在宫苑—官府的不断交替中保持了城市功能。
可见由秦汉到明清的两千多年,成都城市空间格局无论怎样变迁,都表现出超稳定型的结构。东华门遗址的发现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二)依水布局的城市规划
东华门遗址发现的摩诃池遗存,是成都古代依水布局的城市规划的实体展现。
在古代成都城市风貌中,不仅有密如蛛网的河流,而且有众多的湖泊。从汉代开始,成都的城市规划开始依水布局。其中对城市风貌与建筑影响最大的是摩诃池。隋代蜀王杨秀在秦城中取土扩建子城,在城中取土筑城垣,取土之处形成湖泊。由于面积广大,当时胡僧认为其中有龙宫,称其为摩诃池。杨秀为何在城市中心挖湖取土建子城,一种解释是为减少工程量;但城中土质不好,筑城垣易崩颓,所以杨秀所筑子城到唐代后期即崩坍。而秦代张仪筑城时在城外取土。取土之处掘为几个大湖,遗迹于近代犹在,即为白莲池。由于土质良好,到宋代秦城垣尚存。杨秀当时开挖摩诃池,并非不知城内土质不好。他是有意识地在成都城市中心建设依水型的宫苑,展筑子城仅是次要目的。
唐代摩诃池水域面积可达数千亩。北宋时宋祁《过摩诃池》诗说:“十顷隋家旧凿池,池平树尽但回堤。”这是说摩诃池在北宋时水面仍有十顷,即上千亩面积。宋代陆游《摩诃池》诗自注也说:“摩诃池入王蜀宫中,旧时泛舟入此池,曲折十余里。”可见其在唐代水域应更为浩瀚。蜀王杨秀在成都子城内开凿摩诃池后,环湖一带成为蜀王的宫苑区,湖光波影,宫室壮丽。成都城内的宫苑湖泊水系开始形成。
摩诃池不仅在唐代成为成都官吏、文人的游览宴饮之地,在战乱时期,还成为成都百姓的救急饮用水源。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南诏再次围攻成都。在南诏围城的一个多月间,被困于城中的数十万军队和居民的饮水,主要依靠摩诃池的蓄水来维持。当时南诏入寇,“蜀孺老得扶携悉入成都,阇里皆满……城中井为竭,则共饮摩诃池”(《新唐书·南蛮列传上》)。在南诏军队围城期间,由于成都军民的坚强抵抗,加之南诏军队缺乏重型攻城设备,成都城这才免于陷落。
摩诃池之名从隋代一直使用到唐末,到前后蜀时,改摩诃池为宣华池。摩诃池在宋代开始淤塞,但仍有相当大的水域面积。摩诃池的水面直到明代还有部分存留。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今此池填为蜀藩正殿,西南尚有一曲水光。涟漪隔岸,林木蓊翳,游者寄古思焉。”摩诃池的开凿,使唐代成都城内的湖泊水系开始形成。
围绕城市中心的湖泊进行城市布局和景观建设的中国古代城市不多,除成都外,就只有北京、杭州、南京、扬州等城市。北京围绕什刹海、北海、中南海三海建设宫苑豪第,杭州城市以西湖为核心景观布局,南京沿玄武湖和莫愁湖发展,扬州沿以运河河道形成的瘦西湖发展,都是城市布局和建设的成功之作。
从秦代张仪建筑成都城垣以来,成都城市的发展格局是城市依托河流湖泊建设,但并不紧邻河流两岸。从秦汉到明清,成都的城市核心区距郫、流二江约有2公里多的距离,外城垣与两江之间留存较广阔的空间。之所以与河流保持一定距离,是为了防止洪水泛滥。古代的成都平原河湖沼泽密布,经常发生水灾。在有关秦汉时期成都的传说中,对成都城市西部的水患威胁也有较多的描述。如说后来城西圣寿寺内,“有秦太守所凿石犀,今在殿前。殿中有井,相传与海相通,所谓龙渊也”,如移动就会引发洪水。杜甫《石笋行》说,益州城西门的石笋“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说成都民间认为城西石笋为镇压水怪的海眼。杜甫在《石犀行》诗中又说:“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
除了摩诃池外,历代王朝对成都城市内外的河道进行了大规模地开凿与疏浚。唐德宗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开凿解玉溪,由成都城西北郊外的内江引水入城,沿东南方斜贯城中,经大慈寺南,于东南方出城与内外江汇合。宋祝穆《方舆胜览》载:“解玉溪在大慈寺之南,韦皋所凿。用其沙解玉,则易为功。”既然解玉溪中之沙可以解玉,说明溪水清澈透明,水质极为优良。
唐末宣宗时,白敏中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又在成都城内开凿金水河。《雍正四川通志》载:“金水河在成都城内,唐白敏中所开,旧名禁河。旧志云:王明叟、席大光、范成大相继修之。明初建蜀府,改曰金水河。”金水河源自成都西郊磨底河,经西门水门入城,流入城中心的清代贡院,再由东门外水门入府河。而清代贡院即唐代摩诃池和宣华苑旧址,可见唐末五代的金水河是注入摩诃池,再由摩诃池流出。由于摩诃池和宣华苑在五代前后蜀时是皇家禁苑,所以金水河在五代和宋时又名为禁河,水量很大,可以行舟楫。
由宋人李新《后溪记》和吴师孟《导水记》所记,我们知道,唐宋成都的城市水系,以解玉溪和金水河为主干,摩诃池为核心,派生出城内众多大小河渠,形成密如蛛网的城市水系,最后又汇入高骈筑罗城后,城中仍然存在的郫江故道,出城汇入锦江之中。这个水系是一个由西北向东南贯穿整个城市的河道系统,不仅为成都带来了清洁的水源,而且使城市建筑有了临水而居的灵气。唐宋时期成都城内的著名景观芳华苑与江渎祠,即充分利用了这一城市水文化内容与景观功能,成为唐宋时期的著名古迹名胜。
成都的城市水系经过唐代的修浚,基本定型,城内如网络的水道再加上绕城而过的内江与外江,隋唐至明清的成都,街巷临清溪,园苑环碧湖,是一个河流湖泊密集,街坊与波光辉映的依水城市。城市水系的形成,直接推动了园林的发展。当时的成都园林风格多以水景为核心,可谓无园不水,无水不景。
自秦汉以来,成都城因水而兴。水是成都城市的灵魂,水成为成都城市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东华门遗址区域发现的摩诃池,并非死水。它由郫江上游引水入湖,湖水再排入郫江下游。水滨高耸的楼阁是成都最负盛名的建筑,水上倾城的遨游成为成都人最喜爱的娱乐,是隋唐成都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正如高骈《锦江春望》诗所描述:“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
三、东华门遗址与成都城市文化空间特色
(一)城市建筑的古都气派
在东华门遗址区域发现的官衙—帝宫—王府—贡院的历史延续,包括冠绝于西南地区的高规格、高水平的建筑遗存,是成都城市建筑之古都气派的象征。
秦代成都城垣即历史上著名的大城与少城。秦城内有城墙把城垣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为大城,西为少城。大城为官署及居民区,少城为商业区。东华门遗址区域,在秦汉时期应属大城范围。成都秦城城市建筑风格仿照秦都咸阳,标准很高。
汉晋时期的蜀汉宫苑,位于东华门遗址区的北部,武担山之南,即今新华西路之南。西晋文学家左思《蜀都赋》说,成都“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把蜀都与魏都、吴都并列,可见成都在汉晋时期的城市风貌,在当时全国的城市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左思《蜀都赋》描述成都城市中心的蜀宫说:“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宣化之闼,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晖。”其宫内飞阁瞰江,华殿高堂,重门深院,金铺玉砌,外有宫墙环绕,豪华壮观之极。蜀汉宫城,成为西南地区历史上出现的第一座“皇城”。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封其子杨秀为蜀王,“因附张仪旧城,增筑南西二隅,通广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筑之城中之北也。”唐李昊《创筑羊马城记》说隋代成都子城 “壮观崇墉”,因此隋代蜀王府必然是富丽豪华。
唐末五代时,东华门遗址区域又成为前后蜀君主的皇家宮阙和御苑。前后蜀君主围绕摩诃池大兴土木,建筑宫殿御苑,沿池周绵延十里之多,称为宣华苑。宣华苑“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穷极奢巧。衍数于其中,为长夜之饮。”摩诃池与宣华苑奠定了隋唐至宋明时期成都城市的核心区域,时以湖泊为中心的宫殿园苑区的城市格局和建筑风貌蔚然成形。
明代蜀王府规模雄伟,是明代藩王府中最富丽的一座。它北起东西御河,南到红照壁,东至东华门,西达西华门,豪华程度可与北京故宫比美。其有两重城垣,外城周长达九里,内城周长五里,加上周边环绕的御河,面积约有1000余亩,几乎占当时成都城的十分之一。内城为宫苑区,宫殿建筑庄严宏大,参差错落,金碧辉煌。中轴线上的建筑主要有承运门、承运殿、端礼殿、昭明殿等;还有各种桥梁、牌柱、雕塑等景观建筑。根据明蜀惠王《惠园睿制集》的记载,蜀王府内苑的建筑有殿堂100余间,书屋精舍斋房也近100间,楼阁14座,轩142处,亭52座,总数超过400余处。外城外环绕御河,河上架三道拱桥,正对拱桥就是宽阔的御道和广场。御道宽约30余米,广场长约400余米,直达红色的砖墙影壁。是为明王朝在西南地区展示皇权威仪的建筑群落。
清代初年,由于明蜀王府已在战乱中毁灭,至康熙四年(1665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把蜀王府旧基改建贡院,其中有楼堂馆所如明远楼、致公堂、衡文堂、文昌殿等主考官的办公场所与住院,但主要为考生号舍。经清代历朝增建,清代四川贡院房舍总数达一万四千间。贡院四周筑城墙,城南为正门,城西为西华门,城东为东华门,城北为后宰门。
明代蜀王府与清代四川贡院的建设,对于成都城市景观和格局的变迁具有重大影响。蜀王府宫城与贡院为坐北向南,王府正门外为宽阔的南北向御道,一改秦汉以来成都城市街道的东北—西南向布局,从而形成了明代以后成都城市发展的南北中轴线。
成都的城市中心区东华门遗址区域,包括秦汉至明清的郡衙、州衙、府衙、县衙等地方官衙,隋代和明代的蜀王府,三国蜀汉、西晋成汉、五代前后蜀的皇家宫苑,清代的四川省级贡院,其建筑规格和建筑水平均居于西南地区之首,以壮丽而示威仪,具有中国古都城市的建筑气派。
(二)园林型城市风貌的代表
唐宋时期的成都是一座花木园林之城,而东华门遗址区域则是成都园林发展的代表。成都历代大规模的宫苑建筑,由于集中了当时最高园林艺术,同时又位于城市中心区域,成为历代成都园林型城市景观的集中表现。
唐代诗人杜甫来到成都后,对成都的印象就如其《春夜喜雨》说:“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又于《西郊》里说:“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他在《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中还说:“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可见在诗人心中,成都是一个花木园林众多、风光如画的城市。
唐代诗人刘象有《晓登迎春阁》诗赞美成都说:“未栉凭栏眺锦城,烟笼万井二江明。香风满阁花盈户,树树树梢啼晓莺。”在诗人的笔下,成都是花木园林之乡与诗情画意之地。而东华门遗址区域的宣华苑,是成都历史上宫苑园林的巅峰之作。摩诃池与宣华苑时代,展现了成都历史上最富有特色的园林建筑风貌与城市景观。
记录这一时期宣华苑风貌的诗文,以后蜀花蕊夫人的《宫词》为最。花蕊夫人是唐末五代极负盛名的诗人。她的百首《宫词》,有许多是对宣华苑风光的描写,如:“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牵丝两岸风。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来往碧波中。”“三面宫城尽夹墙,苑中池水白茫茫。直从狮子门前入,旋见亭台绕岸傍。”按照花蕊夫人的描述,唐末五代的宣华苑,沿摩诃池湖滨布局,湖面宽阔似海,岸边有连绵十里的水槛,湖中有岛屿,上建亭台楼阁,宫城寝殿环绕四周。湖内荷花竞放,湖边柳荫夹岸,花木宜人。摩诃池的湖水与成都城内外的河流相通,中间以水门相隔离,形成美丽的成都城中之湖。
进入宋代,即使是前后蜀的宫苑被废弃,摩诃池的水域有所缩小,但摩诃池及其周边宣华苑地区,仍然是成都城市中心最大的湖泊园苑区。范成大《晚步宣华旧苑》诗说:“乔木如山废苑西,古沟疏水静鸣池。吏兵窸窸番更后,楼阁崔嵬欲暝时。有露冷萤犹照草,无风惊雀自迁枝……”陆游《月上海棠》词也说:“斜阳废苑朱门闭,吊兴亡、遗恨泪痕里。淡淡宫梅,也依然、点酥剪水。凝愁处,似忆宣华旧事……”可见宣华苑的园林景观,到南宋时依然存在,任人游玩,凭吊兴亡。
元明时期,宣华苑与摩诃池被废弃,成都园林呈现出全城广泛分布的特色。其中明代蜀王府园林又成为成都园林的代表。明代的蜀王府园林景观富有蜀地特色,精致秀美,水景荡波,花木繁丽,鸟语花香,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又具皇家气派。正如明人曹学佺诗说:“锦城佳丽蜀王宫,春日游看别院中。水自龙池分处碧,花从鱼血染来红。”(《蜀府园中看牡丹》)王府中的“菊井秋香”,甚至被蜀王朱让栩称为“成都十景”之一。在“成都十景”中,“菊井秋香”是唯一的园林景观。
园林型城市在中国古代较为少见,除成都外,在同等规模上只有苏州和扬州可以相比。但苏州与扬州主要以私家园林为主,规模较小。而成都古代城市园林则兼有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之胜,城市的特色十分突出。
成都古典园林建筑风格和景观的特色,受发源于成都地区的道教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天人合一”的道家的自然觀,对成都园林影响的表现为崇尚自然、无为顺应、朴质贵清、淡泊自由、浪漫飘逸。这些风格通过园林的具体布局、景观的设置,与自然环境中的花木相融合等途径,呈现出富有诗情画意的艺术氛围,并成为这个城市的文脉与品格。
(三)封闭与开放的功能双向转化
中国的古代中心城市,城市的中央核心区域往往是单一的行政功能,很难有大幅度转变。而成都的城市中心区东华门遗址区域,却经历了若干次宫苑王府与公共园林的双向转化,这是成都城市功能独特文化的象征。
秦汉时期,东华门遗址区域所在大城,是蜀郡或益州郡衙和州衙的所在地;三国时期,是蜀汉宫苑的所在地;隋代是蜀王杨秀王府所在地。但唐代开始,杨秀所开凿的摩诃池,成为开放的公共园林、最负盛名的泛舟游览宴饮之地,吸引着达官显贵和文人骚客纷至沓来。唐代的剑南西川节度使如严武、武元衡、韦皋、高骈等,都曾在摩诃池上宴饮游览。杜甫在成都时,曾陪同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游摩诃池。他在《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一诗中描写了摩诃池的秀丽风光:“高城秋自落,杂树晚相迷。坐触鸳鸯起,巢倾翡翠低。莫教惊白鹭,为伴宿青溪。”唐德宗时的诗人畅当《偶宴西蜀摩诃池》:“珍木郁清池,风荷左右披。浅觞宁及醉,慢舸不知移。”可见唐代的摩诃池边古木参天,白鹭成群,荷花映日,鸳鸯戏水,池中泛舟,池边饮宴,为成都最佳去处。唐代成都著名的女诗人薛涛,也曾在池上泛舟赋诗。
五代前后蜀时期,东华门遗址区域成为前后蜀帝宫的所在地,围绕摩诃池建立了环湖宫苑群落,成为封闭的皇家宫苑区。但到宋代开始,这一区域又重新开放。东华门遗址区域成为宋代成都市民的游乐胜地。其中最著名的是西园。这是宋朝成都府路转运司在后蜀权臣故宅基础上营建的规模最大的园林。宋《岁华纪丽谱》载,宋代成都寒食节的西园,“每岁寒食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从观,太守令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廷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逾月而后罢。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
明代东华门遗址区域建为蜀王府,宫墙深深,再次成为封闭宫苑。明清易代后,蜀王府毁灭,遗址上建成贡院,成为四川全省的科举考试之地。民国时期,东华门遗址区域先后成为四川大学、师范学堂等学校的校址,再次成为公共建筑。东华门遗址区域在两千余年中出现多次功能转换,是中国古代中心城市里少见的现象。
(四)传承千年文脉的城市载体
城市文脉的传承,需要有城市物质形态的载体。这些载体包括城垣、建筑、街道、广场、宫苑、寺观和河流湖泊的地理环境等。由于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变化和生活功能的需求改变,能够完整地保存上述载体的城市很少。大多数城市仅能保存某一局部街区及分散零星的寺庙祠堂等古迹;而其保存下来的历史文化街区,大多并非城市的精华和象征性景观。因为在城市的变迁中,精华的建筑往往最易于遭到破坏,只有少数城市因为历史机缘,才能保存诸如宫苑殿堂和宗教建筑的文脉精华。
能够全面地、完整地代表城市历史文化传统和象征的载体,无过于城市中的皇家或王室所在的宫苑,或者宗教寺院的经典建筑。如果巴黎没有卢浮宫,北京没有故宫和颐和园,罗马没有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堡没有冬宫,这些城市都会黯然失色。就成都而言,最能够代表这个城市历史文化的象征与载体,莫过于“东华门遗址”。它是一千多年以来成都的城垣、建筑、园林、文物等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对于成都的文脉传承与城市品牌,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从东汉末三国蜀汉以来,作为皇家和王室宫苑,“东华门遗址”都是成都最重要的标志性人文景观。成都历史上虽有龟城、锦城、罗城、大城、少城、子城等城垣称呼,但龟城、锦城分别是秦代和汉代以后对整个成都城的别称。而罗城是唐代以后对成都主城垣的称呼。大城、少城、子城则是对秦代以后成都城内由城垣分隔的不同区域称呼。只有“东华门遗址”区域的城市核心区域建筑特色与文化传承,才是成都城市历史文化的标志。
2.“东华门遗址”位于城市的中心区域,规模与体量宏大,并且往往在成都的中轴线上,从而其建筑风貌与周边环境都成为四方注目之地,对城市景观和文化产生最大的影响力,是二千多年来成都城市历史文化的精华,是成都城市历史文化复兴的重要参照对象。
3.成都历史上最有名的宫殿园苑建设,都与水密切相关。广阔的河湖水域,成为“东华门遗址”的灵气之所在。隋唐五代的摩诃池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其水域广阔,河湖相通,烟波浩渺;还有宫苑沿水布局的大气象。就是在摩诃池湮灭后的明蜀王府,也是引城外的府河水入城,形成环绕王府的御河与金河及蜀王府的园林,是成都著名的水景观。
4.历史上的“东华门遗址”,由于多次成为蜀中王朝宫苑或藩王所在的王府,其建筑特色、建筑质量、园苑布局、生态环境、地理区位不用说均属第一流,故而博得历代文人学者的赞美歌颂。虽然因为时代的变迁至今不存,但仍然是成都記忆中的历史文化与城市风貌的象征。所以前后蜀的宣华苑尽管在宋初被拆毁,但留存的部分园苑如西园,在宋代依然成为成都的形胜游赏之地。
5.历代成都的“东华门遗址”,都是每一个时代的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结晶。深厚的蜀文化为遗址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因此,遗址不仅是成都历史文化的象征性标志,也是天府文化的象征性标志。
6.东华门遗址也是与四川和成都的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核心区域。两千多年以来,对成都和四川影响最大的历史名人以此为活动中心,写下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诗篇,如秦代的李冰;汉代的文翁;三国的刘备、诸葛亮;两晋的李特、李流、常璩、范长生;隋代的杨秀;唐代的唐玄宗、唐僖宗、杜甫、薛涛;五代的孟昶、花蕊夫人;宋代的范镇、苏轼、范成大、陆游;明代的朱椿、张献忠;清代的张之洞等。总之,要讲好成都故事,传承成都文脉,“东华门遗址”是最为重要的要素与载体之一。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