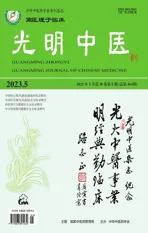欧阳卫权教授运用六经辨证治疗痤疮经验*
2023-04-05唐海燕欧阳卫权
唐海燕 杨 石 欧阳卫权
欧阳卫权,字衡之,广东省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师从中医大家李振华、李可、禤国维,中医功底深厚,尤尚推崇仲景学说,常年致力于《伤寒杂病论》及六经辨证研究,临证强调以六经为纲,方证为核心,万病识机,活用经方,特别善用经方诊治皮肤科及各科疑难杂症,创立皮肤病六经辨证理论体系和临证思维,并著书立说指导后学。笔者有幸侍诊余旁,撷取并整理其运用六经辨证治疗痤疮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
痤疮是好发于青春期并主要累及面部毛囊皮脂腺单位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临床表现为粉刺、丘疹、脓疱、结节、囊肿等,伴皮脂溢出。研究表明,80%~90%的青少年患过寻常痤疮[1], 3%~7%痤疮患者会遗留瘢痕,给患者身心健康带来较大影响[2]。现代医学认为此病病因是在遗传背景下激素诱导的皮脂腺过度分泌脂质、毛囊皮脂腺导管角化异常、痤疮丙酸杆菌等毛囊微生物增殖及炎症和免疫反应等[2]。目前西医治疗主要使用维A酸类、抗菌素等,其疗效和相关不良作用较大影响患者的依从性。
中医称痤疮为“肺风粉刺”, 历代文献多认为此病是肺经风热(或血热)上熏头面所致。早在《黄帝内经》论述:“汗出见湿,乃生痤痱……劳汗当风,寒薄为皶,郁乃座”。提出了风邪袭肺,郁而生痤的病因病机;之后文献更强调血热的因素,如《外科正宗》指出:“粉刺属肺……总皆由血热郁滞不散,所谓有诸内、形诸外”。以及《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曰:“此证由肺经血热而成”。皆认为其发生乃肺经血热,郁滞不散而致。
目前中医共识认为此病初发多由肺经风热、湿热内蕴,肺胃热邪上熏头面而致,久者痰瘀互结而出现结节、囊肿甚至瘢痕[3]。临床辨证分为肺经风热证、湿热蕴结证、冲任不调证和痰瘀结聚证,大多治以清热解毒利湿、凉血散瘀、化痰散结。上述病机理论和治则治法提纲挈领,将繁杂的临床辨治化繁为简,易于掌握推广。但临证日久即发现此法以局部皮损辨治为主,缺乏对患者体质分析,医者容易进入专病专证专方的思维定式。如过分强调局部皮损的红肿热痛,多责之于热而施以凉性药物而忽视患者整体的阴阳气血虚实,未进一步分析其“热”是真热还是假热,假热又是源于阴阳气血何者?且久用寒凉之品可损人阳气,导致部分患者体质更加虚寒,病情反复难愈。
欧阳卫权教授临证中运用六经辨证理论,强调局部皮损辨证结合整体辨证,注重患者的中医体质辨识,活用多个经方治疗痤疮,体现六经辨证、方证对应的灵活性,疗效切实提高,现将其思路精要和临床医案分享如下。
1 辨治思路精要
欧阳卫权教授致力于《伤寒杂病论》及六经辨证研究,临证思路概况为“先辨六经,后辨方证,方证须对应,勿忘整体”。他强调辨六经是辨证的第一步,而六经纲领是辨清六经的重要依据,医者需熟记方能在临证中灵活运用。而辨方证是第二步,即辨方的指征、依据和适应证。中医治疗是否有效,关键在于方证是否辨准确。病证与方相应,即是方证对应。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翼方》序文曰: “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符,需有检讨,仓卒易知”。现代经方大师胡希恕谓 “方证是辨证的尖端”,可见古今中医大家均认同方证是六经辨证的精髓。而辨方证的关键在于抓主证,欧阳教授特别指出,皮肤科患者就诊的主诉和主证的区别,前者常常是患者局部的皮损表现,而后者又称为“关键点”或“眼目”,多为整体病机状态的关键证候,即“见此证用此方”以达到方证对应。千万不可以局部皮损辨证代替整体,需综合分析方能确定最适宜的治法方药[4]。
2 验案举隅
2.1 当归芍药散方证刘某,女,23岁。2020年6月22日初诊。面部粉刺、丘疹、脓疱2个月。专科检查:面部较多粟粒大小的粉刺和红色丘疹,散在脓疱。患者面色无华,平素怕冷,手足不温,经量偏少,痛经,有血块。无口干苦,纳眠可,舌质淡,舌体胖大,边齿印,苔白根厚,脉细。四诊合参,辨证为太阴病之血虚水盛,予当归芍药散加减:当归10 g,川芎10 g,赤芍15 g,茯苓15 g,白术15 g,泽泻15 g,陈皮10 g,连翘15 g,白芷10 g。7剂,水煎服,每日1剂,早晚2次温服。外用四黄消炎洗剂外搽(广东省中医院自制药)。二诊:服药后患者粉刺稍变平,丘疹颜色变淡,脓疱消退,未见新发。继续予当归芍药散加减调整,服用1个月后,面部皮疹明显好转,遗留少许暗红色痘痕,且手足不温、痛经和经量少均有改善。
按:《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曰:“妇人腹中诸疾痛,当归芍药散主之”。欧阳教授在临床上常用本方治疗当归芍药散体质的中青年女性痤疮,汉方喻为“虚弱美人体质”,其主要特征为:整体体质偏弱,面白少光而偏浮肿;怕冷,冬天手足不温明显;多伴月经不调,或前后不定期,或经量少,或痛经,或血块;舌淡胖有齿印等。此方在皮肤科辨证运用时需重视对患者体质和整体病机的把握,特别强调四诊合参,方可对其虚性体质给予足够重视,才不会过度关注局部皮损的热象而妄用苦寒以致虚者虚之。即使局部可见红色皮损,内服药味佐以连翘、白芷即可,或外用四黄消炎洗剂以治外在之热。欧阳教授重视育龄期女性患者的月经问诊,通过询问月经情况更能了解患者的真实体质状况,在施方用药时亦可兼顾,方证对应用药之后体质改善之时亦即痤疮、月经改善之时。
中医临床是真实而复杂的,临床中确有患者属于当归芍药散证但腹痛较轻,无明显水饮,又兼见烦热者,且舌尖红,无胖大舌,欧阳教授则常用当归散,该方由当归芍药散去茯苓、泽泻,减白术、赤芍,加黄芩清郁热组成,该方辨证运用仍着重对整体的把握,即使有郁热也酌加苦寒药味即可。
2.2 茯苓饮方证黄某,女,27岁。2020年7月8日初诊。面部反复粉刺丘疹脓疱6年,加重3个月。专科检查:面部油腻,见较多粉刺、暗红色丘疹和脓疱。伴胃胀胃痛,纳食欠佳,月经推迟,便溏,日行2~3次,无口干苦,眠可,小便正常,舌质暗,边齿印,苔薄,脉细。四诊合参,辨证为太阴病,予以《外台秘要》茯苓饮加减:党参10 g,炒白术10 g,茯苓20 g,陈皮15 g,炒枳壳10 g,生姜10 g,白芷10 g,桔梗10 g,连翘15 g,生山楂15 g,川芎10 g,香附10 g。7剂,水煎服,每日1剂,分早晚2次温服。外用四黄消炎洗剂外搽。二诊:服用后患者皮疹好转,胃胀缓解,大便稍成形,未诉胃痛,坚持复诊用药2个月,上述症状均得以明显好转。
按:《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附方之《外台秘要》茯苓饮:“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后,心胸间虚,气满不能食,消痰气,令能食”。 欧阳教授常用《外台秘要》茯苓饮治疗脾虚痰湿阻滞的痤疮患者,但强调单纯原方收效较缓,临床需根据患者的兼夹症状进行专病药物辨证加减,常加白芷、桔梗、连翘以散结、排脓;面部油腻,加生山楂、神曲以消食导滞祛脂等以标本兼治,提高疗效。
2.3 葛根芩连汤合当归贝母苦参丸方证陈某,男,31岁。额部、面中部粉刺、丘疹伴压痛5个月。专科检查:面部油腻,额部、面中部可见多发粉刺、丘疹,压之疼痛。伴口干喜饮,大便黏,自诉解不尽,肛门时有灼热感,胃无不适,纳眠可,舌质暗,边尖红,苔薄黄中根部腻,脉滑。四诊合参,辨证为阳明病证,予以葛根芩连汤合当归贝母苦参丸加减:葛根50 g,黄芩15 g,黄连5 g,当归15 g,浙贝母15 g,连翘10 g,薏苡仁30 g,陈皮10 g,甘草6 g。7剂,每日1剂,水煎,早晚2次温服。外用四黄消炎洗剂外搽。二诊:服药后患者症状改善,效不更方,继续上方加减服用14剂。
按:《伤寒杂病论》曰:“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本患者皮损为面部阳明经循行部位,且伴口干喜饮,大便黏腻不尽,故选用葛根芩连汤。当归贝母苦参丸首载于《伤寒杂病论》,本是治疗妊娠小便难,但关键病机是内有湿热郁阻,故欧阳教授拓展移至面部油腻甚者,因面部油腻为湿热证,与下焦湿热小便难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用方之灵活可见一斑[4]。同时欧阳教授常用连翘代替苦参,考虑连翘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是痤疮治疗的常用经验药,且苦参更为苦寒,不易久服。使用本合方时需问诊患者的脾胃中焦情况,如脾胃虚弱者慎用。从葛根芩连汤、当归贝母苦参丸在皮肤科的灵活运用提示《伤寒杂病论》非仅仅辨治外感热病或内伤杂病之书,其开创的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体系是中医各科辨证的基石,可为中医皮科理论拓展和临床疗效的提高提供源头活水。
2.4 半夏泻心汤方证王某,女,35岁。2020年8月17日初诊。面部粉刺、丘疹散在脓疱3年,加重1个月。既往慢性胃炎史,纳食欠佳,心下痞胀,时有反酸嗳气,食冷易腹泻,口干苦,舌暗红,苔白,脉细。四诊合参,辨证为少阳太阴合病,予以半夏泻心汤加减:法半夏15 g,黄连3 g,黄芩10 g,党参10 g,干姜10 g,大枣20 g,炙甘草10 g,连翘15 g,白芷10 g。7剂,水煎服,每日1剂分早晚温服。外用四黄消炎洗剂外搽。二诊:服药后患者皮疹减轻,仍可见丘疹、脓疱,心下痞和反酸症状稍改善,仍诉口干苦,加量黄芩15 g,黄连5 g,皂角刺10 g。继续服用14剂,胃肠症状和痤疮均得以明显减轻。
按:《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曰:“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半夏泻心汤是半表半里阴证,证属少阳太阴合病,常表现为上热下寒、寒热错杂证。此病辨证的最大“眼目”是心下痞,需医者跳出单纯对痤疮的局部辨证,主动询问患者的纳食状况和相关不适,才能得出这一关键病机。结合本患者:上热为:面部红色丘疹、脓疱、口干苦;下寒为:食冷易腹泻。而寒热错杂则为心下痞、反酸嗳气。本例痤疮实质是寒热错杂的“心下痞”在面部皮肤的表现而已,本质为同一病机在不同病位的表现,此为内科辨证和皮科辨证的统一,也是整体辨证与局部辨证的统一,可实现一方同治痤疮和心下痞。
2.5 四逆散合透脓散方证及十味败毒散方证涂某,男,19岁。2020年8月13日初诊。面颈、腋下、臀部丘疹、脓疱、结节、囊肿和瘢痕8年,加重2个月。专科检查:面部油腻明显,面颈、腋窝和臀部见泛发暗红色丘疹、脓疱、结节和囊肿,部分融合成片,压痛明显,部分可探及窦道并见较多脓血溢出,部分见瘢痕增生。诊断:不全型毛囊闭锁三联征(聚合性痤疮、化脓性汗腺炎)。外院曾反复予以“异维A酸、抗生素、清热解毒类中药和囊肿多次切开引流术等治法”,上述病情仍反复发作。患者体质偏实,平素易于紧张焦虑,对此病甚是烦恼,易出汗,易累,手足不温,晨起口苦,大便时干,舌暗,舌尖红,苔薄,脉弦细。四诊合参,辨证为少阳阳明合病,予以四逆散合透脓散加减:柴胡15 g,枳实15 g,赤芍15 g,甘草10 g,黄芪60 g,当归30 g,川芎10 g,皂角刺10 g,金银花15 g,蒲公英45 g,连翘15 g,白芷10 g,没药5 g,蜂房20 g。7剂,水煎服,每日1剂,分早晚温服。外用四黄消炎洗剂外搽和消炎油砂(院内制剂)。二诊:服药后患者皮疹有改善,部分囊肿处可见脓血溢出,新发皮损明显减少,疼痛减轻,继续服用上方14剂。再诊,患者症状进一步改善,皮损面积缩小,时有少许新发,可见较多瘢痕增生,遂改以十味败毒散加减:荆芥10 g,防风10 g,茯苓15 g,川芎10 g,独活10 g,白鲜皮20 g,桔梗15 g,柴胡10 g,生姜10 g,甘草10 g,连翘15 g,薏苡仁30 g。继续服用1个月,皮损新发明显减少,症状趋于稳定,总体症状明显好转。
按:毛囊闭锁三联征由聚合性痤疮、化脓性汗腺炎和头部脓肿性穿掘性毛囊周围炎3个独立的疾病组成,同一患者同时发生3种疾病中的任意2种, 可诊断为毛囊闭锁三联征[5]。欧阳教授指出:中青年男性柴胡体质而偏实的痤疮患者,伴有长期紧张焦虑、熬夜,压力大,或手足不温,或腹痛者,临床上常将四逆散合方灵活运用,收效甚好。本患者病程长,长期用寒凉药使阳气郁闭而出现手足不温症状,合用透脓散以益气活血、托毒透脓。又因患者具有反复化脓疖病的体质,故后期病情稳定后予以日本汉方家华冈青州经验方十味败毒散改善体质。
临床上,如四逆散体质的中青年男性痤疮,因长期熬夜,紧张焦虑,出现疲累,眠差,兼见烦躁、心中燥热、口干、口腔溃疡、咽痛等,脉弦细无力,且使用四逆散或荆防败毒散疗效欠佳时,更应考虑阳浮于上,上盛下虚的病证。宜予以温潜之法,引火归元,予潜阳丹加龙牡、磁石潜阳以制其虚亢。故临证中,准确辨识方证,用药效如桴鼓。
3 痤疮随证加减特点
欧阳教授指出,准确的方证在痤疮治疗中固然重要,但临床单独使用经方原方治疗往往收效较缓,所以随证加减变化,效果更佳。一般可加连翘、白芷、桔梗散结排脓;面部油腻,毛孔粗大者,可加生山楂、桑叶以消食导滞祛脂;白头粉刺为主,加荆芥、防风、枳壳以疏表散结;炎性丘疹、脓疱较多,伴压痛,加蒲公英、金银花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暗红色结节较多,加量皂角刺至15~20 g以消肿托毒;结节、囊肿较多者,加百部、夏枯草、牡蛎、海藻软坚散结;结节、囊肿瘀暗,时有脓血水出,加三棱、莪术、蜈蚣等活血破瘀、通络散结;遗留暗红色痘印伴面部时有灼热者,加丹参、紫草清热凉血消斑等[4]。
4 结语
以上几个验案体现了欧阳卫权教授六经辨证、方证对应治疗痤疮的理论思想和临床经验。实际上临床用于治疗痤疮的经方还很多,如葛根汤、荆防败毒散、麻杏薏甘汤、逍遥散、柴胡桂枝干姜汤、大柴胡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五苓散、桂枝茯苓丸、温经汤等均有应用的机会。痤疮其实是一个症状,实质是人体整体病机或体质在局部皮肤的表现,临证中学会在纷繁复杂的症状中把握患者的主证,从而辨出方证,施以最适宜的方药,在随访中随证加减,避免专病专方的束缚,以期切实疗效的提高和临证思维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