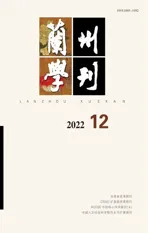弱家庭发展能力与农村男性失婚机制
2022-12-28李凤
李 凤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较女性多出3490万人(1)侯佳伟:《从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看我国人口发展新特点及新趋势》,《学术论坛》2021年第5期。,且多出的男性人口有60%都分布在农村地区。近些年,农村男性失婚率不断升高,由失婚男性引发的拐卖妇女儿童、性犯罪、婚姻家庭破裂等问题频繁发生,引发一系列社会风险。(2)刘燕舞:《负性生命事件、地域性贫困与农村光棍问题的形成机制研究——以大别山村为个案》,《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学界对失婚男性婚配困境成因持续关注,并形成以下三种解释视角。
一是宏观的人口视角。潘金洪(3)潘金洪:《出生性别比失调对中国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人口学刊》2007年第2期。分年龄组预测了2000—2050年出生性别比失调情况,结果显示截至2050年,人口性别比将高达117.17,适婚男性较女性将多出五千多万。李树茁(4)李树茁等:《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人口与经济》2006年第4期。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预测未来中国婚姻市场每年将会有120万男性过剩人口。李南(5)李南:《高出生性别比及其婚姻后果》,《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1期。认为在人口性别比失衡背景下,计划生育、女性外流使本地适婚男女青年比例愈加失调。二是中观的社会视角。王晓慧、刘燕舞(6)王晓慧、刘燕舞:《农村大龄青年婚配困难问题研究——社会剥夺的视角》,《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2期。从社会剥夺视角解释婚姻资源在不同阶层群体内部的不均衡分布状况,偏远农村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男性最容易失婚(7)杨华:《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杜姣(8)杜姣:《地域差异视角下农村光棍的形成原因分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邢成举(9)邢成举:《男性光棍构成差异的地域性解释——基于凤城和新县两个村庄的比较分析》,《青年研究》2014年第3期。、刘成良(10)贺雪峰等:《南北中国: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42页。从区域差异视角解读男性失婚成因。狄金华、张翠娥(11)张翠娥、狄金华:《找回家庭:对农村单身现象的再解释——对赣南茶村的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分析》,《南方人口》2013年第2期。提出“找回家庭”,从家风评价、家庭结构、经济实力等方面分析子代婚配困境。陶自祥(12)陶自祥:《代内剥削: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渝北S村长子打光棍的调查》,《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提出代内剥削,分析长兄如父伦理与外出务工机会差异形塑的长子失婚现象,李永萍(13)李永萍:《渐衰与持守:宗族性村庄光棍的生成机制——基于广西F县S村40例光棍的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5期。也认为宗族伦理纽带松动减弱了婚姻支持的代际合力。刘升(14)刘升:《“婚姻株连”:理解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框架——基于豫南Q村“光棍成窝”现象的调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余练(15)余练:《婚姻连带:理解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新视角——对鄂中和鄂东三村光棍成窝现象的解释》,《人口与经济》2017年第1期。提出婚姻株连、婚姻连带,解释未婚子代婚配困境的文化传递。桂华、余练(16)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提出婚姻市场要价的解释框架,农业剩余少、家庭积累能力弱的男性因婚姻支付失败而失婚(17)陈文琼、刘建平:《婚姻市场、农业剩余与光棍分布——一个理解农村光棍问题的中观机制》,《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6期。,婚姻的城市拜物教、贱农主义使贫困地区的男性更容易失婚(18)刘燕舞:《婚姻中的贱农主义与城市拜物教——从农村光棍的社会风险谈起》,《社会建设》2015年第6期。。三是微观的个体视角。阎云翔(19)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3页。通过对东北下岬村农民私人生活的考察,否认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农民家庭“有经济合作、无爱情”的评价,认为年轻一代已懂得通过语言、姿态追求爱情和表达欲望,择偶更加注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个人特质。宋丽娜(20)宋丽娜:《婚恋技术主义:农村90后青年的婚恋实践》,《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9期。认为浪漫革命中的情感体验十分重要,哄女孩、送礼物、制造惊喜等婚恋技术决定了男性是否能谈到对象。
笔者2021年在闽南蔡村调研时发现,村内30岁及以上的未婚男性有177人,占同年龄段适婚男性的11.5%,其中30—45岁的未婚男性占80%以上,即2010年以来村内未婚男性数量急剧增长。为何2010年以来该村会产生如此多失婚男性?失婚男性婚配困境产生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宏观视角指出了农村男性在婚配结构中的不利地位,但却不能解释特定区域、时期内男性失婚成因。中观视角从社会分层、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婚姻支付等方面解释男性失婚原因,但却不能系统解释婚恋图景变迁背景下男性失婚机制。微观视角强调了婚恋中的浪漫主义、个体主义倾向,但却不能解释顺利恋爱的蔡村男青年为何仍旧失婚。
已有三种视角将男性失婚视为社会、家庭、个体中某单一因素影响的后果,实质上个人既生活在家庭场域中,又受社会变迁的影响,个体婚配是个人选择、家庭再生产、社会变迁三者共同形塑的结果。费孝通(21)费孝通:《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87页。认为婚姻的意义在于建立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三角结构的继替演变以推进社会新陈代谢,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成为联结个人与社会变迁的中间环节。家庭视角成为理解男性失婚机制的重要中介。已有的家庭视角注重从家风、家庭结构、经济实力等静态的结构性要素去分析男性失婚原因,却不见个人、家庭、社会变迁之间的动态关联。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进入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全国性婚姻市场,中国农民家庭面临参与市场竞争的现代性发展任务。(22)张雪霖:《家庭目标、代际责任与乡村教育效果研究——区域差异比较的视角》,《教育科学》2019年第5期。它需要在社会转型中调整家庭发展策略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应对城市化进程下的家庭再生产目标。相比于家庭要素的静态分析,“家庭发展能力”呈现出家庭在应对转型期个体婚配危机时的伸缩性,动态展示了社会变迁、家庭再生产、个人选择对婚配困境的形塑过程。本文以家庭发展能力为分析框架,考察转型期婚恋图景变迁下,蔡村男性失婚的生成机制。
二、分析框架与田野介绍
(一)分析框架:家庭发展能力
“家庭发展能力”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话语。西方福利国家试图通过支持家庭发展、恢复家庭保障功能,将政府福利供给责任向家庭内部转移;我国在单位制解体后,保护丧失家庭依托的边缘群体并提出发展型家庭政策(23)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以恢复家庭基本功能、应对全球化挑战。吴帆、李建民(24)吴帆、李建民:《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分析》,《人口研究》2013年第4期。认为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所获取的资源满足每一位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需要的能力”,并从家庭支持、经济、学习、社会交往、风险应对等家庭功能的角度分析家庭发展能力。有学者(25)黄玲、郭显超:《家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的探讨》,《统计与管理》2018年第7期。认为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发挥功能,以实现家庭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还有学者(26)齐燕:《社会资本逻辑下的家庭发展》,《学习月刊》2017年第3期。将其定义为家庭发展所需资本的总和,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来分析家庭发展能力。基于以上指标的选择性组合,学界形成了“家庭发展能力”的多种分析框架。有人口学者考察了计划生育政策(27)石智雷:《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4期。、赡养老一辈(28)马健囡:《赡养上一辈对中年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路径——基于CFPS家庭配对数据的分析》,《人口与发展》2021年第1期,第36页。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还有学者分析了家庭发展能力对二孩生育政策(29)倪洪兰、杨春、陈雯:《家庭发展能力与二孩生育的相关性研究——基于江苏的调查分析》,《人口与社会》2018年第2期,第71页。、宅基地退出模式(30)吴泽斌、吴立珺:《农民家庭发展能力与宅基地退出模式双边匹配研究》,《农业技术经济》2020年第7期。的影响。
纵观已有研究,大多从家庭功能、家庭发展条件来理解家庭发展能力。实则是把家庭视作没有行为动机、情感伦理的客体,家庭发展等同于外部环境支持下被动的功能恢复,忽略了家庭自身的内在动机。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实践具有圣凡一体(31)桂华:《圣凡一体:礼与生命价值》,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2013年。的宗教意义,通过男系血缘继替,家庭成员生活在“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祖孙一体关系中,香火绵延的观念将家庭扩大到家族的无限绵延性。家庭再生产与家族绵延,是家庭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意义支撑。家庭发展能力即是家庭应对社会变迁,满足家庭成员发展需求而实现家庭再生产的能力,它揭示了个人境遇、家庭再生产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动态联系。李永萍(32)李永萍:《家庭发展能力:理解农民家庭转型的一个视角》,《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98页。将家庭视为包含人、财产、伦理规范的能动主体,从家庭资源、家庭结构、家庭目标三个维度来理解社会变迁中的家庭策略调适与家庭发展能力。本文借用李永萍对家庭能动性的解读,以家庭资源、家庭结构、家庭目标作为家庭发展能力的分析维度,解释农村男性失婚机制。家庭资源主要体现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家庭结构则体现为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家庭主体动员能力——代际支持与代内支持共同形塑的代际合力;家庭目标即为不同发展面向下的家庭再生产目标——家庭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化再生产,并基于家庭目标配置家庭资源。家庭资源是家庭发展的客观基础,家庭结构反映家庭在短期内的策略性合力行为,家庭目标调控资源配置及家庭长远发展预期,三者相互作用以形塑出不同程度的家庭发展能力。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1:

图1 家庭发展能力的分析维度
(二)田野介绍
1.蔡村社会概况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笔者2020年10月、2021年12月参与的两次集体调研,驻村时间30天,田野地点在蔡村。蔡村是闽南丘陵山区的一个行政村,距县城9公里,全村4438人,20个村民小组。2000年前,村内种植蜜柚、金枣等经济作物,并借助县城烟厂下岗职工的专业技术开办假烟厂,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镇前茅。2000年初期,假烟被取缔,村内大面积种植杨桃、青枣,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县城及厦门、泉州等地务工。蔡村是一个“蔡姓”单姓宗族村,村内大小房头十余个。村内有多座祠堂、5座伯公庙、2座宫庙,1999年筹资重修宫庙,2009年重修族谱,2021年筹资重修大宗祠堂。每年正月十五、三月三等日子,村民以家族、房头、门头为单位筹资举办祭祀活动、公共性庆典,以祈求子孙绵延、宗族兴旺发达。并在期间走亲访友、请客吃饭。
2.失婚男性及其家庭情况
当地人一般将30岁及以上的未婚男性视为单身汉,如表1所示,全村共有177名单身汉。2000年前,蔡村经济发展好,较多女性愿意嫁到本村,只有少数家庭政治成分差、身体残疾、患精神疾病的男性会沦为单身汉,失婚率较低。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男性沦为单身汉,约占全村未婚男性的80%,失婚率最高。本文随机选取30位30—45岁的未婚男性作为个案访谈对象。

表1 蔡村失婚男性分年龄段失婚率
如表2中30名失婚男性个人及其家庭情况所示。从个人婚恋经历来看,超过一半以上的男性因无力支付彩礼、房车等婚姻成本而失婚。从家庭结构来看,超过70%的未婚男性所在家庭为多子家庭,多子家庭中次子失婚率比长子失婚率高出30%,有一个家庭中出现了两个及以上的未婚子代。在多子家庭中,有1/3的子代在婚后提出分家单过,而未婚子代则继续同父代同住,形成了已婚子代分家单过的核心家庭,以及父代与未婚子代共居的核心家庭。失婚男性所在家庭,有近1/3的父母在子代适婚年龄段内离世、病重或丧失劳动力,未婚男性适婚期间的家庭结构并不完整。从家庭生计来看,80%以上失婚男性为初中学历,且在初中毕业之后到县城、厦门、泉州等地进厂打工,80%具备劳动能力的父代都在村务农,其余则从事农业合作社、养殖、开店等村内生意。从家庭资源来看,70%的家庭仍住在村内老房子里,没有进城买房,城镇化水平不高。从村内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来看,大部分家庭资源将会用于祭祀、庆典、红白喜事等公共性花费,以及休闲娱乐、请客吃饭等社交费用。

表2 蔡村失婚男性个人及家庭情况
三、蔡村适婚男青年婚恋图景
(一)男孩偏好与本地适婚男女比例失调
秉持着“亲上加亲、知根知底、家庭和睦”的婚姻观念,蔡村人倾向于村内、族内通婚。本地婚受到本地婚姻市场中适婚男女青年比例影响,而本地适婚男女比例与该村人口出生性别比有关。作为典型的宗族村,蔡村人有较强的传宗接代、香火延续意识,将生育男孩作为个体最重要的人生任务。村民常说:“没有生男孩就要断子绝孙,别人就看不起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计划生育阶段,生育次数、生育数量受严格限制,为完成生育男孩的人生任务,村民通过各种非正规手段人为选择婴儿性别,并将女婴送给外村亲戚养育,或与村干部合谋以实现生育更多男孩、多子多福的目标。如表3,80年代以来的人口出生性别比结构极度失衡,人口出生性别比均达到高度婚姻挤压值(120—130),2/3已超过高度婚姻挤压(33)倪晓锋:《中国大陆婚姻状况变迁及婚姻挤压问题分析》,《南方人口》2008年第1期。的上限值130。这群80后、90后男女青年的适婚年龄段正好在2000年以后,此时本地适婚男青年远多于女青年,较多男性无法在本地通婚圈内找到与之匹配的适婚女性。

表3 全村1977-199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
(二)女性外流与择偶梯度挤压
2000年初期,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厦门、福州及外省务工,适婚男女青年从本地通婚圈进入全国性区域通婚圈。受城市化生活方式影响,进城女性更愿意嫁给城镇男性或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男性。蔡村父母也认为女孩子最好的去处就是嫁到厦门、福州这样的省内大城市,其次再是省内其他市区、本县城,再次是嫁到本村,最次是嫁到偏远地区、外省。本村适婚女性及其家庭形成了“本省大城市—省内市区和县城—本村—偏远地区和外省”这样的择偶梯度。我们从20个小组中随机选取5个组,考察30—45岁女性的婚嫁情况,共85人,全部已婚。如表4所示,有超过2/3的女性都嫁到了村外,近一半女性嫁到了本县城、市区。一位32岁的外嫁女性说:“我初中毕业后和同学到泉州打工,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他家在隔壁县城,经济条件很好,我父母很满意。和我一起外出的很多女同学也嫁到了城里面。”

表4 五个组30-45岁女性嫁往地统计
可见,30—45岁女性外嫁、上嫁的情况较为明显,位于择偶梯度下端的农村男性受到挤压。(34)杨华:《东部农村大龄女性青年婚配困难问题研究》,《青年研究》2019年第5期。当本村男性进入城市择偶,受到城市男青年、经济条件较好农村男青年的挤压;当他们返回农村择偶,由于较多女性通过教育、外出务工、嫁入城市等方式外流,本地适婚女性急剧减少,女性基于自身“卖方市场”的优势地位而继续向上择偶(35)石人炳:《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1期。,在本地挑选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更优的本村男性,经济条件较差的本村男性再次面临择偶梯度挤压。
(三)城镇化生活预期与婚配成本高涨
20世纪80年代前,蔡村以本地介绍婚为主,婚前几乎无恋爱花销,结婚花销以少数生活必需品等实物为主,婚恋成本在两千元以下。80年代到2000年初期,送礼、游玩等恋爱环节的男女互动增多,在谈婚论嫁环节,男方家庭在村有房、少量彩礼成为硬性要求,婚恋成本在4万—10万之间不等。2000年以来,男女青年流入城市务工,电影院、餐厅、商场、KTV等娱乐消费场所,成为青年们培养感情、体验浪漫的重要场域;各种节日的仪式性消费、休闲旅游,也成为制造恋爱惊喜的载体。在结婚环节,村内新房、彩礼成为最低刚需,大多数女性提出了县城买房、高额彩礼、浪漫婚礼仪式等婚配条件。从恋爱到结婚,婚恋花销急剧增加。1988年的未婚男性CQS说:“我和她在厦门制衣厂认识,谈了六年后,我提出回村结婚,她希望我在城市买房发展。平时恋爱要花钱,家里帮大哥结婚后也没钱了,我哪里买得起房子。”1989年的未婚男性QYF也说:“我在广东打工时谈了一个江西女孩,谈了七年,叔叔去女方家提亲时,女方父母要求县城一套房,外加金项链、玉镯等首饰和8万彩礼。我是家里独子,父母在村务农,承担不起。”像CQS、CYF这样的未婚男青年还有很多,他们在城市经历了浪漫甜蜜的自由恋爱,但却因高额的婚配成本而止步于婚配环节。自80年代以来,婚恋成本不断上涨。尤其是2000年以来,男女青年以自由恋爱为主,恋爱中的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以城市化消费方式、娱乐方式为载体,对今后婚姻生活的想象表现为在城市生活的城镇化预期,男青年恋爱与结婚的成本在不断上涨。
总体来看,在婚姻市场性别挤压、婚姻圈的择偶梯度挤压、婚姻支付的竞争挤压共同作用下,转型期婚恋图景中的婚配危机主要表现为婚配成本高涨的经济压力、城镇化压力,个人及其家庭能否积攒足够的经济资源以支付婚配成本,成为影响男性婚配成败的关键因素。
四、失婚男性家庭发展能力
(一)家庭资源:“半工半耕”双弱的家计模式
本地家庭收入来源于务农与务工,年轻子代进城务工、父代留村务农,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36)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家庭之间的经济收入也因“半工”与“半耕”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
“半耕”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影响家庭收入,一是自然资源禀赋,二是人地关系。从自然条件来看,本村位于丘陵山区的冲积平原上,四周地形崎岖,土地细碎分散,机械化水平较低,农作物耕种、灌溉、管理的劳动力投入成本较高。地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交界处,终年高温多雨,仅适宜种植喜湿热作物。从人地关系来看,本地人均耕地面积不足2分,户均山林地不足5亩,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总的来说本地“半耕”条件并不优越,耕种面积有限且农业生产成本较高,目前以种植杨桃为主。杨桃种植需要较为精细的劳动力投入,涉及修剪枝条、8次施肥、打药、套袋等,若自家忙不过来就需花钱请工。60岁及以上的老年夫妇若不请工,能够经营管理的最大规模为5亩。据村民介绍,自2000年以来,每亩杨桃的纯收入在0.6万—2.5万元之间波动。失婚男性父母大多种植3亩左右杨桃,除去村内人情、公共性活动等费用,家庭农业剩余不超过2万。
“半工”收入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市场机会,包括东中西地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造成的客观机会差异,以及由个人文化水平决定的主观准入机会;二是市场意愿,即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和强度,表现为进入市场的劳动力数量、时间强度。从市场机会来看,本地属东南沿海农村,但村庄地处丘陵山区,以农业生产为主,当地并未形成发达的工业生产体系,县城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市最后一名,本地市场机会有限。80%的失婚男性多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市场准入的文化资本有限,只能选择进厂、建筑行业等劳动力密集型工作,月薪大都在5000元以下。从市场意愿来看,失婚男性所在家庭,部分父代因身体健康状况差或离世而丧失劳动力,其余父代大多在村务农,参与市场的劳动力数量仅限于年轻子代,并以就近务工为主。村内每逢红白喜事、公共性庆典,年轻子代会回村暂住,全年务工时间一般为5—8个月。失婚男性的市场参与机会有限且市场意愿不强,除去个人在城开支,务工剩余不超过2万。
(二)家庭结构:代际支持有限与代内伦理弱化
当我们问起父辈对子代的养育态度时,失婚男性CQS的50后父亲说:“读书看天赋,看你是不是读书的料,能读我们也会支持。儿子的婚姻是他自己的事情,我先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其他的不管,没钱帮小儿子买房子我们也着急,也只能顺其自然啊。大儿子成家了,再过几年我也该退休了。”可见,父代对子代教育持“天资论”态度,无过多阶层跃升期待与资源投入,更没有加入全国性教育竞争的意识。父代对子代的婚姻操心不操劳,他们根据自身经济实力选择性提供支持,但并不会因此而陷入无限的自我剥削中,实在难以帮助子代结婚也能顺其自然、不强求。但凡家中有一个子代顺利成家、传宗接代,父代就算是完成了一大半人生任务,可以宣告退休去过自己的生活,没有义务继续资助子代小家庭和抚育孙辈。总体来看,父代以生育男孩为人生任务,并全力将子代养育长大,但对子代的教育投入、婚姻资助、隔代抚育则持弹性态度。
45岁的失婚男性CZC在讲述家庭生活时说:“家里有5兄弟,老二抱给别人,我最小。兄弟们打工挣的钱都交给父母,父母管大家的生活。大哥出去上门了,三哥2003年结婚后分家单过,2006年四哥与打工女孩结婚到外地单过,同年父亲走了,现在就剩下我和老母亲。以前不管结婚没都是一家人住老房子,除非人太多父亲管不了或父母离世。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大家观念也不同了,都分家单过。”在“父子一体、兄弟一体”的联合家庭中,父代家长统筹家庭财产与生活,分家权也掌握在父代手中。当家庭规模扩展到父代无力统筹大家庭生活时,父代才会主动提出分家,一般为一次性分家,在这之前,已婚子代仍与父代同居共财,直到父母离世后子家庭方可自然分家。在一次性分家前,已婚子代、未婚子代同父代一起生活,已婚子代有赡养老人、帮扶兄弟结婚成家的义务,未婚子代能够同时获得来自父代、已婚兄弟的支持。2000年打工潮兴起以来,进城务工子代经济独立意识增强,兄弟之间、子家庭母家庭之间经济分化凸显。子家庭对生计独立的要求增强而向父代提出分家,多次分家之后,未婚子代在婚配中实则面临已婚兄弟的多重代内剥削。首先,先成婚子代已花费大量家庭共同积攒的资源,后又通过分家提前转移家庭财产。其次,分家单过的小家庭拥有独立的财产单位与社区性身份,对父代有刚性的赡养义务而对未婚兄弟的帮扶则较为弹性。最后,未婚子代一般排行靠后,在其适婚阶段父代已逐渐丧失劳动力或离世,父代的婚姻支持有限,并因与父代同住而需要承担更多养老义务。在多次分家中,未婚子代面临财产划分、婚姻支持、养老义务方面的多重剥削,代内支持弱化。
(三)家庭目标:传宗接代与强生活面向
蔡村是一个有着六百余年历史的单姓宗族村,村内以同姓男系血缘为主轴不断绵延扩展,蔡村人以生育男孩为根本的人生任务。失婚男性CYF的父亲认为:“有了男孩才能延续香火,生100个女孩顶不上一个男孩,女的无财产无责任,嫁出去就是别人的。我只要生男孩就可以,多子多福。”可见,生育男孩意味着祀奉祖先的“香火”不断,有人继承家庭财产并承担养老义务,既向上回应祖先崇拜的超越性追求,又向下回应自我有限生命的无限绵延。通过生育男孩,每个人都处在“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意义体系中(37)张建雷:《家庭伦理、家庭分工与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进程》,《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6期。,活在“祖先—我—子孙”的绵延链条中(38)孙庆忠:《乡村都市化与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广州城中三村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村里的70后木匠说:“有钱有什么好炫耀的,你没有儿子,钱有什么用?别人和你吵架就会说你没有儿子还拽什么。”与市场中的经济指标相比,蔡村社会仍以生育男孩作为村庄社会评价体系的核心标准,并以此规范个体及家庭行为。
父代们常说:“我只管生男孩,养大就可以了,其他的不管。”在完成传宗接代的目标后,他们对子代教育、婚姻期待不高,大多数失婚男性初中就辍学在家包假烟赚快钱,父母也不再管他们的婚姻大事,整个家庭没有长远发展目标。家庭资源配置也围绕当下生活与社会交往展开。村内血缘与地缘关系高度重叠,在此基础上还叠加了姻亲关系、血亲关系、朋友关系等,社会关系网络复杂且社会交往密度大。父代家庭的烟酒茶叶、人情、请客吃饭等费用较高,以宗族、房头为单位组织的公共性庆典与祭拜仪式花费较多,且村内人地关系紧张,粮食、蔬菜、养殖等农产品仍需要依赖市场,生活成本较高,在村生活的支出较大但农业剩余较少。进城子代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社会交往与城市接轨,日常的烟酒茶叶、人情往来、休闲娱乐等支出比重较大,务工剩余较少。
五、弱家庭发展能力与男性失婚机制
(一)家庭资源弱积累与婚姻支付困境
自改革开放和打工潮兴起以来,受城市化生活方式、现代婚恋文化的影响,男女青年更加注重婚恋中的浪漫情感体验,而这都需要以城市化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为基础,婚恋物质成本不断上涨。男性及其家庭能否支付高额的婚配成本,影响男性子代在婚姻市场竞争中的成败。家庭资源积累能力是婚姻支付的客观基础(39)王跃生:《婚事操办中的代际关系:家庭财产积累与转移——冀东农村的考察》,《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3期。,家庭生计模式影响家庭积累能力。失婚男性所在家庭形成了“半工半耕”双弱主导下的生计模式,农业剩余与务工收入并不多,家庭积累能力不强。一个普通家庭需要为单个子代的婚姻积累数十年以上的时间,子代越多的家庭越有可能出现“光棍成窝”的现象。无论男性子代在城市或本地择偶,都难以应对当下婚姻市场竞争中的婚姻支付压力。
(二)家庭弱代际合力与婚姻支持弱化
费孝通(40)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31-32页。认为中国人的家(族)是一个绵延性的事业社群,内部形成了以父代为主轴、以夫妇为配轴的基本结构,父与子、夫与妻、兄与弟之间有既定的伦理规范及互动模式。为实现家(族)绵延,家庭常需要调整主轴与配轴结构,整合代际支持与代内支持,以代际合力的动员方式应对家庭再生产。子代结婚成家作为家庭生命周期中的关键节点,影响家庭继替与家庭再生产。父代对子代的纵向代际支持与兄弟之间的横向代内支持,共同形塑的代际合力强弱,决定了子代能否在短期内通过家庭动员应对婚姻支付难题。按照当下婚恋成本来看,一个普通核心家庭需要为单个子代的婚恋成本积累十年及以上的时间。代际合力(41)陈讯:《婚姻要价、代际支持与农村青年城镇化——基于晋西北W村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2期。强则能够基于家庭伦理进行家庭策略的功能性调整,整合家庭资源,缩短婚姻资源积累的时间,在短期内帮助子代顺利婚配。
相比于华北农村厚重失衡的代际关系及父代对子代的无限责任,本地呈现为父代责任有限的伦理型代际关系。(42)贺雪峰:《农村代际关系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父代在完成生育男孩的目标之后,对于子代的教育、婚姻支持等持弹性态度(43)张雪霖:《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新三代家庭结构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子代若没有办法结婚成家,父代也能顺其自然地接受,村庄也不会责怪父代而认为这是儿子自己没本事。已婚子代对经济独立的要求将分家行为提前,代内伦理纽带松动(44)麻国庆:《分家:分中有继也有合——中国分家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未婚兄弟在适婚阶段面临已婚兄弟的多重剥削,代内支持弱化。代际支持有限、代内支持弱化共同形塑出弱代际合力,家庭主体动员的伦理基础较弱。面对子代婚配成本上涨的家庭再生产危机,家庭结构很难在短期内作出伸缩性调整,难以进行强主体动员与强资源整合。失婚男性的婚配危机在短期内仍旧无法得到策略性解决。
(三)家庭简单再生产与婚姻预期降低
家庭发展目标实质上是一个现代性概念。传统农业时代,传宗接代、帮助子代结婚成家、抚育孙代是家庭核心目标,在本地通婚圈稳定、经济低度分化的背景下,婚配成本较低且教育期待不高,农民家庭能够在本地实现低成本的家庭简单再生产。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乡村人口进城务工并追求城镇化,农民家庭再生产嵌入到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主义浪潮中。在完成传宗接代的家庭简单再生产目标后,家庭还需要投资子代教育以提升其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并帮助子代在城市买房买车以顺利结婚成家。转型时期农民家庭同时面临家庭简单再生产、家庭发展与社会地位流动的双重任务。李永萍(45)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根据家庭发展的不同定位,将家庭目标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生活型目标、维持型目标、发展型目标。本地家庭以香火延续、传宗接代为核心目标,重视当下生活体验与社会交往,家庭资源主要用于日常消费与人情往来,子代教育投入等发展性支出较少,家庭自身的发展面向较弱。再加之村庄内部低度竞争、低度分化,村民个体及其家庭的外在发展动力不强,当地家庭呈现出一种低度维持的简单再生产状态。失婚男性家庭成员围绕简单再生产目标开展家庭生活,家庭发展需求多元化,家庭资源使用方式弥散化,整个家庭尚未对全国性婚姻竞争等现代性发展任务作出功能性调整。长远来看,失婚男性家庭尚未将“积累子代婚姻资源”作为家庭核心目标,婚姻资源积累周期延长,子代顺利婚配的预期降低。
六、结论与讨论
在快速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我国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婚恋观念等都在发生剧变,婚恋图景下的现实经验也更加复杂多变,如果仅从宏观的人口视角、微观的个体视角、中观的社会视角去分析男性失婚成因,很难呈现出婚恋经验本身的复杂性、多元性。本文通过对蔡村男性失婚现象的考察,发现进城农村男性在自由恋爱后并不能顺利婚配,即转型期的婚恋并非完全是个体主义的逻辑,而是与个人、家庭、社会变迁都有关。在已有三种解释视角的基础上,提出“家庭发展能力”的分析视角,以家庭资源、家庭结构、家庭目标为分析维度,动态分析婚恋图景变迁、家庭再生产、个人选择共同形塑下的男性失婚机制。
在婚姻性别挤压、择偶梯度挤压、婚姻竞争挤压的共同作用下,转型期农村男青年婚配危机,主要表现为婚配成本高涨下的经济压力、城镇化压力,并通过物质转化机制向家庭内部传递(46)陈讯:《婚姻要价、代际支持与农村青年城镇化——基于晋西北W村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2期。,向家庭策略与家庭发展能力提出了转型要求。本地“半工半耕”双弱主导下的家庭资源弱积累状态,难以在当下帮助子代支付高额婚配成本。有限代际支持和逐渐弱化的代内支持使家庭代际合力减弱,家庭难以在短期内进行强主体动员与资源整合,未婚男性在短期内仍旧无法策略性应对婚配危机。本地家庭呈现出低度维持的简单再生产状态和弥散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尚未围绕子代婚姻转变家庭目标和资源配置方式,子代在较长时期内的婚姻预期将会降低。当子代婚配危机通过婚姻成本的经济压力向家庭内部传递时,家庭发展策略并没有对此作出功能性调整,仍旧按照传统农业时代的简单再生产目标去安排家庭生活,家庭资源分配方式的发展面向不强且主体动员能力较弱,最终形塑出的弱家庭发展能力,使子代在当下、短期内、长期内都难以应对婚姻成本上涨的婚配危机,陷入失婚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青年婚恋,的确如阎云翔在东北下岬村考察的那样,有了更多私人化、个体化色彩,男女青年进入城市自由恋爱,择偶与婚姻的自主性增强。但自由恋爱并不意味着顺利婚配,相比于传统农业社会,城乡流变中的子代正逐步退出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大多数时间是在城市务工,并按照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去调适自己的行为,其务工经历、城市生活实践形塑了他们对婚姻家庭生活的城市化期待。在城市定居、抚育后代的生活预期嵌入于青年的婚恋实践中(47)王跃生:《婚事操办中的代际关系:家庭财产积累与转移——冀东农村的考察》,《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3期。,并表现为在城市买房买车、高额彩礼等物质成本方面的婚配条件。婚姻的理性选择、物质主义色彩将恋爱和结婚分离,在城市自由恋爱的农村男青年或许会因结婚成本而陷入“找得到、娶不起”的失婚困境,男青年及其家庭并不能为浪漫爱情提供物质基础。转型期的婚恋就表现为介于浪漫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第三种爱情”,恋爱靠个人,结婚还需依靠家庭支持。正是这种特殊的婚恋形态,对当下的家庭发展、婚恋转型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当子代婚配压力向父代家庭传递时,实则是向父代传递城镇化发展需求的压力,帮助子代结婚成家的人生任务转变为帮助子代进城的功能性目标,父代需要无限扩展代际责任、延长责任周期,不断向子代倾斜资源。其本体性价值被无限扩大,而自身的社会性价值与基础性价值则被无限压缩(48)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最终可能会引发父代的养老危机与人生意义危机。其次,子代婚配危机所带来的城市化压力,实则是向中国农民家庭提出了现代性发展任务,对家庭目标、家庭结构、家庭生计等家庭发展策略提出了转型要求。传统农民家庭的简单再生产目标或许需要转变为发展面向较强的扩大化再生产,子代婚姻、进城等物质成本的提高或许会促使家庭对当下家庭结构、资源整合作出灵活调适。但家庭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以家庭伦理为支点逐步撬动家庭发展动力的渐近过程,这也预示着我国农民家庭的城镇化道路注定循序渐进。最后,转型中的家庭为应对子代婚配危机,也会对婚恋策略作出调适,比如以早婚、娃娃亲的形式提前抢占婚姻市场中的女性资源,以上门女婿、娶二婚的形式获取婚姻补给市场上的女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