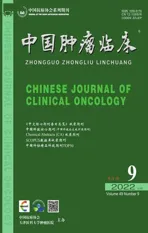肿瘤患者支持治疗的进展
2022-12-08邓婷巴一
邓婷 巴一
肿瘤支持治疗是与手术、化疗和放疗并重的治疗手段。欧美地区国家肿瘤支持治疗起步较早,发展相对成熟,已逐渐成为一门完整的学科。中国的肿瘤支持治疗起步晚,许多医院仍偏重抗肿瘤治疗,轻视肿瘤支持治疗。大部分医务人员对肿瘤患者支持治疗的概念、意义和发展仍不十分明确。同时,患者及家属对于支持治疗的认识度也不够,对疗效的重视需求程度远超于支持治疗。随着社会进步以及人们追求更高的生存质量,我国的肿瘤支持治疗必将面临飞跃式的发展。本文拟就肿瘤患者支持治疗的基本现状及进展进行综述。
1 肿瘤支持治疗的概念
1.1 肿瘤支持治疗的定义
早期的肿瘤支持治疗与姑息治疗的概念是混淆的。随着医学发展和认知的提高,支持治疗与姑息治疗分别有了各自不同的定义。1993年Senn[1]首次对肿瘤支持治疗进行了定义,对肿瘤支持治疗描述为一个“保护伞”,除了抗肿瘤治疗之外,还涵盖患者各方面的需求,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2008年肿瘤支持治疗多国协作组(MASCC)对支持治疗进行定义:支持治疗是预防和管理癌症及其治疗的不良反应,包括从诊断开始到治疗以及治疗结束后的整个过程中对生理、心理症状以及治疗不良反应的管理。加强康复、预防二次肿瘤、生存状态和临终关怀也是支持治疗的组成部分[2]。这一定义至今仍被广泛认可和使用。
1.2 肿瘤支持治疗的内涵
根据MASCC 定义,肿瘤支持治疗包括从肿瘤诊断开始一直到生命结束的全程,支持治疗的对象不但包括正在患病的肿瘤患者本人,还包括抗肿瘤治疗结束后的肿瘤幸存者以及家庭照料者等,其具体内涵包括肿瘤症状和治疗相关并发症的处理,以及心理、精神、社会、家庭、信仰、情感、经济等各个方面全方位的管理[3-4]。因此,肿瘤支持治疗涉及的不只是一个学科,而是多学科的共同协作。参与的人员涉及广泛,不仅包括肿瘤专业的医师,还有相关不良反应涉及的各个专业医师和社区医生,以及营养师、心理治疗师、社工、宗教人士等。从广义的角度而言,肿瘤患者抗肿瘤治疗后返回正常生活,需要的是全社会的接纳和认可。
2 肿瘤支持治疗的意义
上述涉及到肿瘤支持治疗的内涵的深度与广度,其现实意义必然是提高患者治疗的疗效和生存质量,以及家庭照料者的生活质量。早在2010年有研究证实在非小细胞肺癌中,支持治疗可以延长2.7 个月的中位生存期,并能改善患者抑郁症状[5]。研究证实,肿瘤支持治疗可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和延长生存期中的价值[6],因此肿瘤支持治疗不仅是辅助,更是增加疗效的治疗模式。其次,从家庭层面而言,有研究证实支持治疗可以降低家庭照料者在肿瘤患者在确诊后、死亡前6 个月以及死亡前3 个月时的不良情绪[7]。而家庭照料者可以直接影响肿瘤患者治疗的进程。再次,从医疗资源层面考量,加强肿瘤支持治疗能降低20%左右的30 天内再次就诊率、缩短平均住院时间等[8-9]。这对于节约国家有限的医疗资源,整合不同层级的医疗服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3 肿瘤支持治疗的进展
3.1 肿瘤支持的整合治疗模式
肿瘤支持治疗有三种常见的运行模式:独立治疗模式(solo practice model)是肿瘤医师负责处理肿瘤患者出现的所有需要支持治疗的问题,其缺点是由于肿瘤医师专业知识的局限性,患者很多问题可能得不到恰当的处理;联合治疗模式(congress practice model)是肿瘤医师将患者出现的的问题转诊给相关专业的专家处理,其缺点是专业知识的片面化,缺少对多学科协作的理解,各个亚专业医师往往只专长于本专业。目前肿瘤支持更倾向整合治疗模式(integrated care model),即肿瘤医师与支持治疗各亚专业组成支持治疗团队,互相协作。该模式可以使患者得到全面、整体的支持治疗服务,提高医疗效率[4,10]。2018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指南推荐肿瘤支持治疗的多学科诊疗(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形式,指出支持治疗团队应由内科姑息学专家、肿瘤专科护士、全科医师、营养师、心理肿瘤学家、社会工作者、理疗师、药师、家庭照料者、志愿者以及其他等共同组成[11]。2021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教授团队发表其开展的一项前瞻性Ⅲ期临床试验研究,证实营养与心理组成的联合支持治疗在抗肿瘤治疗的基础上可以使晚期食管胃癌患者的生存期从11.9 个月延长至14.8 个月,降低32%的死亡风险[12]。此结果可以媲美部分新药的疗效,且成本低,患者生存质量高,实现了疗效与生存质量的双重收益。但支持治疗的MDT 模式对医院及治疗团队的要求较高,广泛推广尚需时日。
3.2 以患者为中心的支持治疗
3.2.1 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支持 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模式已被广泛认同,但是在临床实践中,患者很难区别肿瘤本身及治疗的不良反应,以及其他疾病引起的不适;在与医护沟通中,表达能力的差异也阻碍了医护人员全面地去处理患者各方面的主诉。同时,由于生存质量本身具有主观性和多维性的特征,肿瘤患者可能具有个体化的症状和体征;且随着疾病的进程发生变化,因此肿瘤患者的支持治疗需要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11,13]。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肿瘤患者自身和医护人员对患者生存质量的评估可能存在差异,比如对疲劳、食欲下降、恶心、呕吐、腹泻和便秘等症状评估可能不一致[14-15]。在一项对44 例参加Ⅱ期临床试验的肺癌患者调查发现,当医师未参考患者主诉症状时,会丢失近50%的症状[16]。重视患者主诉是以患者为中心的支持治疗的基础。2018年ESMO 指南明确指出要开展以患者为中心的支持治疗,并强烈推荐使用患者报告结局(patient-reported outcomes,PROs)[11]。
3.2.2 开展以PROs 为基础的临床研究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将PROs 定义为未经过医师或其他人解释,直接来自患者的有关其健康状况的任何方面的信息。近年来,国际上陆续开展了以PROs 为基础的系列临床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17年一项研究[17]显示入组了766 例实体瘤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和常规治疗联合数字化PRO(ePRO)系统组,患者自报12 种常见症状,结果显示与常规对照组相比,联合ePRO 系统组可以延长5.2 个月的中位生存时间,降低7%的急诊就诊率。说明重视PROs 对整个治疗疗效都产生了重要作用。目前,收集PROs 数据也逐渐成为临床研究中评价疗效和药物安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Checkmate-214 研究公布以PROs 作为探索性终点的阳性结果[18]。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于2021年9月发布了《患者报告结局在药物临床研究中应用的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提示开展以PROs 为基础的临床研究将是未来肿瘤支持治疗中的重要研究方向。
3.3 肿瘤支持治疗的全程化管理
3.3.1 支持治疗与肿瘤的早期整合 肿瘤支持治疗包括从肿瘤诊断至生命结束的全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肿瘤诊断的初始阶段,即应积极进行支持干预。Bubis 等[19]对2007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确诊为癌症且生存至少1年的120 745 例癌症患者中,共诊断出729 861 个症状,而且大多数症状都是在诊断后的第1 个月内出现的。另外,Hirparaa 等[20]在11 075例确诊为Ⅰ~Ⅲ期肺癌的患者中发现,在其确诊后的12 个月内存在69 440 个不同的症状,乏力最常见,其次为呼吸困难、体力状态差等。说明即使是新确诊的非转移性肿瘤,同样应尽早进行支持治疗干预。2012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更新建议对于转移性肿瘤患者应该在诊断初期就将支持治疗整合入标准抗肿瘤治疗决策中。而实际上,该建议对于所有肿瘤患者(包括早期)均适用。
3.3.2 关注肿瘤幸存者阶段 目前广为接受的肿瘤幸存者/幸存者阶段的定义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制定的:指从肿瘤患者完成积极的抗肿瘤治疗后开始,一直至生命结束后的全过程。肿瘤幸存者包括已经治愈的肿瘤患者和姑息治疗后病情稳定并接受维持治疗的患者[21]。肿瘤幸存者数目庞大,到2040年预计美国将达到2 600 万,澳大利亚为190 万[22]。有研究显示肿瘤幸存者的生理、心理、情感、社会功能均低于正常,30%以上的肿瘤幸存者可能存在各种症状[23-24]。一项研究通过PROs 的形式,让肿瘤幸存者从个人的角度反映存在的问题,结果发现20%的幸存者在治疗结束6 个月后仍对未来不确定,60%治疗结束时未被满足的需求在6 个月后并未得到改善[25]。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等多种机构推荐应该根据肿瘤的类型、既往治疗的方法、患者的自身特征以及其他因素等对肿瘤幸存者制定个体化的支持治疗策略[26-27]。由于肿瘤幸存者数目庞大,涉及内容宽泛,仍是未来研究的重点,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3.4 肿瘤支持治疗的数字化发展
癌症发病率的升高和患者生存期的延长,导致现存肿瘤患者数目较前有了明显增加。而相较于有限的医疗资源,患者与医护间沟通不足的矛盾也日益明显。一份调查[28]显示医师每天仅有27%的时间直接用于与患者面对面临床交流,而用于电子病历与文书工作的时间占52.9%;有一部分医师需要每晚加班1~2 h来完成电子病历。中国的医务人员工作可能更为繁忙,与住院患者的沟通交流不够,门诊及院外患者的情况更不乐观。
“数字健康(eHealth)”的发展为肿瘤支持治疗的实施提供便捷途经。数字健康包括远程医疗(telemedicine)、远程监控(remote monitoring)、移动医疗(mHealth)和一般医疗互联网技术(internet technology)等。近年来,数字医疗的应用在肿瘤支持治疗中进行了一系列尝试[29]。Greer 等[30]开展的一项研究随机入组了145 例晚期癌症患者,试验组使用针对焦虑的定制认知行为疗法移动应用程序,对照组使用常规平板的移动健康教育程序,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严重焦虑人群在使用定制认知行为疗法后缓解更为有效,而一般人群无显著性差异。另一项荷兰的随机对照研究[31]入组了462 例完成抗肿瘤治疗后的肿瘤幸存者,409 例完成6 个月的评估,发现数字化干预可以明显降低抑郁和乏力,对情感和社会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等。同时,数字医疗还具有明显降低医疗费用的优势[32]。目前该领域的研发仍在进行中,是极具潜力的辅助手段。
4 结语与展望
肿瘤支持治疗内容广泛,是肿瘤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生存质量、节约医疗成本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学科发展上,肿瘤支持治疗大学科逐渐向精细化发展,如欧美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了肿瘤心脏毒理学、肿瘤神经毒理学、肿瘤心理学等更细的学科分支;同时,应更多探索基础、转化与临床的结合,如恶病质机制、神经毒性的机制甚至唾液减少的机制和治疗等;在管理模式上,肿瘤支持治疗也将逐渐形成“家庭-社区-医院”的三级管理模式,但提升基层医院和家庭的护理水平,维持整体的一致性,依旧任重道远。随着整个社会对肿瘤支持治疗认知的提高,相信我国的肿瘤支持治疗将有飞跃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