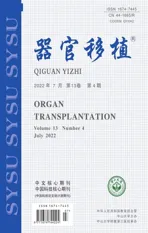HIV阳性肾移植研究进展
2022-11-30韩飞黄正宇
韩飞 黄正宇
据统计,全球约有3 800万人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 ficiency virus,HIV),并且每年新增感染人数约170万[1]。在过去的数十年,随着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combination antiretroviral therapy,cART)的广泛使用,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从一种急性疾病逐渐转变为慢性疾病[2]。且随着cART的应用,HIV感染者的各种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下降,生存时间显著延长[3]。由于AIDS不能被治愈,因此感染者需要终生进行cART以控制病毒的复制,但长期使用cART药物存在药物毒性,导致多个器官功能受损。此外,HIV持续存在于体内会破坏组织器官,以及激活免疫反应导致全身系统性损伤,因此,AIDS发展到后期,大多数患者伴有器官功能障碍。
HIV感染是导致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的一个重要原因,非裔HIV阳性患者ESRD发生率较高[4]。1984年,研究者首次提出HIV感染会导致肾病,并定义HIV相关性肾病(HIV-associated nephropathy,HIVAN)为肾脏来源的蛋白尿并伴随进行性肾功能下降。HIV感染一度被认为是行肾移植手术的绝对禁忌证,因此HIV阳性的ESRD患者只能通过透析来维持生命。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和各种药物的使用,多家移植中心进行了HIV阳性ESRD患者肾移植手术,研究表明这些患者在符合相应的移植条件下行肾移植手术是安全的,且其远期生存率与HIV阴性患者无明显差异[5-6]。由于需要行肾移植手术的ESRD患者很多,为了扩大供者库,部分中心采用HIV阳性供肾进行肾移植,并取得较好的移植效果[7]。如何选择肾移植手术过程中的免疫诱导药及术后免疫抑制药,暂无确切的结论。本文将从多方面对HIVAN以及HIV阳性患者肾移植等进行论述。
1 HIV相关性肾病
大约11%的HIV感染者有微量蛋白尿,研究结果显示,HIV感染是蛋白尿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多种因素可导致AIDS患者肾功能不全,包括患者的自身状态,如年龄、性别、种族、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等。与HIV相关的肾病可以分为很多类,包括HIVAN、HIV引起的免疫复合物肾病(HIV-immune complex disease,HIV-ICD)、HIV相关的血栓性微血管病以及替诺福韦等药物引起的药物性肾病等。
1984年,美国纽约的临床工作者首次报道了HIVAN,定义该病为肾性蛋白尿并肾损伤,病理特点表现为塌陷型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6]。我国ESRD发病率约为237.3/100万人口,1990年的相关研究报道显示,HIV感染者中HIVAN发生率为3.5%~12.0%,但是随着cART的应用,发生率明显下降[8]。据报道,HIVAN在非裔人群的年轻AIDS患者中发生率较高,并且疾病进展较快,患者肾功能迅速衰退至ESRD[9]。与其他人群相比,非裔人群HIVAN的发生率升高18~50倍[10]。研究发现,染色体22q13位点突变与HIVAN有关,其中载脂蛋白L1(apolipoprotein-L1,APOL1)基因的突变与HIVAN之间的关系密切[11],也有部分缺乏APOL1的AIDS患者不会发生HIVAN[12]。在没有感染HIV的情况下,携带2个APOL1风险基因的人群发生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的风险较正常人群升高约4%,该人群感染HIV后,HIVAN的发生率将升高至约50%[13]。
HIV-ICD主要存在于欧洲和亚洲的AIDS患者中,非洲原著患者的发生率也较高。与HIVAN相比,HIV-ICD患者的蛋白尿水平较低,肾损伤进展较缓慢,血浆蛋白水平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有研究通过检查肾功能不足的HIV感染者的肾脏病理标本发现,HIV-ICD的发生率仅次于HIVAN(21%比27%),是导致HIV感染者肾功能不全的第2大病因[10]。HIV-ICD主要是由于免疫复合物沉积在肾小球基底膜和系膜区,呈现出不同的病理表现,包括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膜性肾病等。因为病理类型表现的多样性,其与HIV的关系尚不明确,目前可以解释为感染HIV后的异常免疫反应,或各种感染相关并发症后的肾损伤。
在应用cART之前,HIV感染者肾损伤进展较快,随着cATR问世,AIDS从急性疾病演变为慢性疾病,HIVAN的发生率下降了约60%[8]。虽然cART能控制病毒复制,但长时间应用也会导致线粒体毒性、脂肪代谢障碍综合征、血脂异常、胰岛素抵抗、心血管疾病、肾毒性等[14-15]。指南建议HIV感染者尽早开始进行cART,但是由于需要终生服药,临床医师应该考虑到药物累积的不良反应,对感染者加强管理,以减少药物相关并发症。不同cART药物对肾功能的影响不同,并且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影响肾功能,对于那些已经报道对肾功能有影响的cART药物,患者在服用后应注意定期监测,调整用量。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在选择抗病毒药物治疗时,应避免使用具有肾毒性的药物,如洛匹那韦、替诺福韦、阿扎那韦等。
HIV感染不仅会导致CD4+T细胞逐渐减少,也会影响其他细胞的表型,如通过感染或间接机制逐渐阻碍中枢神经系统、骨骼、心血管系统和肾脏细胞的稳态和功能[16-17]。HIV感染后会诱导细胞凋亡,这是病毒复制和HIV蛋白与宿主细胞成分相互作用的结果[18]。病毒蛋白R(viral protein R,Vpr)是HIV-1的辅助基因产物,在病毒复制周期和宿主基因表达中具有多效性,Vpr被包装在病毒粒子中,并通过促进病毒粒子核心的核转运在非分裂细胞的感染中发挥早期作用。一项对HK2细胞(人肾上皮细胞)的研究表明Vpr与凋亡通路的破坏有关[19]。从机制上讲,Vpr被认为是通过激活DNA损伤反应途径诱导细胞凋亡,如在HK2细胞和转基因小鼠模型的肾组织中,随着Vpr过表达的磷酸化组蛋白2A.X变异反应水平的增加,肾损伤越严重[20]。HIV是否能在肾组织中进行复制一直备受争议,有文献结果显示,肾小球和肾小管上皮细胞能够支持HIV进行复制[21]。并且在外周血没有检测到HIV RNA的情况下,在肾细胞中检测到HIV RNA、DNA和染色体外环状DNA[22]。研究显示,通过药物严格控制病毒复制的情况下,移植肾的足细胞和上皮细胞也可以检测到HIV DNA、RNA,提示肾脏可以成为HIV储存的场所[23]。
2 HIV阳性患者接受肾移植的条件
由于HIV感染者免疫力低下,有可能同时合并多种感染,并且在肾移植术后需要终生口服免疫抑制药,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HIV阳性被列为肾移植的绝对禁忌证,AIDS患者进入尿毒症期后只能通过腹膜透析或血液透析维持生命。随着医疗技术的改善,新cART药物的研发,HIV阳性患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接受肾移植。接受肾移植手术的HIV阳性患者首先要满足普通人群行肾移植的手术标准,比如心脏功能耐受手术、无肿瘤并发症等。北美和欧洲的一些临床工作者试图建立HIV阳性患者行肾移植的标准[24-26],但标准仍未完全统一。目前普遍认为需要符合以下几点:(1)CD4+T细胞计数>200/μL;(2)肾移植术前接受cART至少6个月,血浆HIV-1 RNA<50 copies/mL;(3)不合并活动性感染。
不同地区的研究者对于合并感染的定义各不相同,英国和意大利的学者认为在移植手术前出现过曲霉或其他侵袭性真菌感染、活动性巨细胞病毒感染、近期严重的细菌感染和未治愈的分枝杆菌感染的HIV阳性患者都应该禁止行肾移植手术,因为在术后服用免疫抑制药的情况下,这些感染的复发率很高[24-25]。但美国和西班牙的研究者并没有把这些感染均纳入排除标准中,包括既往的结核分枝杆菌、卡氏肺孢子菌和食道假丝酵母感染[26]。
3 HIV阳性患者接受肾移植的效果
在符合手术标准的前提下,HIV阳性患者肾移植术后移植肾存活时间与HIV阴性患者相当。在cART药物用于治疗HIV感染之前,HIV阳性患者行肾移植的效果较差。有研究报道,39例在肾移植术前未进行cART的HIV阳性患者中,在随访的2年时间里,21例死亡[27]。在cART出现后,HIV阳性患者肾移植术后的生存率才得到了提高。针对HIV阳性患者肾移植的第一项前瞻性临床研究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医学院开展的,该研究从2001年至2004年为40例HIV阳性患者进行了肾移植,术后1年和2年受者生存率为85%和82%,移植肾存活率为75%和71%[5]。受者死亡原因包括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心肌梗死、药物不良反应;移植肾丢失的主要原因包括急性排斥反应、移植肾出血、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等,其中急性排斥反应的占比较高,约为22%[5]。200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也开展了一项前瞻性研究,18例HIV阳性患者接受肾移植,中位随访时间为3.4年,术后3年受者生存率为94%,移植肾存活率为83%,与普通人群行肾移植的效果相当[28]。该研究结果显示,HIV阳性患者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依然高于普通人群,术后1、2、3年累积排斥反应发生率分别为52%、64%、73%,肾脏穿刺活组织检查结果显示78%为细胞性排斥反应,6%为体液性排斥反应,11%为混合性排斥反应[28]。
HIV在口服免疫抑制药的情况下是否会大量复制以加重疾病的进展是HIV阳性患者行肾移植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2010年,一项包括19家移植中心的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HIV阳性患者肾移植术后1年和3年的生存率为94.6%和88.2%,移植肾存活率为90.4%和73.7%,受者生存率与HIV阴性患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不会增加HIV感染相关并发症,通过监测HIV RNA复制量,显示联合用药情况下HIV的复制并没有增加,证实HIV阳性患者在特定的条件下行肾移植的手术效果较好,但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依然较高(33%),这可能与各种药物的联合作用导致血药浓度波动较大有关[29]。
肾移植术后HIV也会侵袭移植肾,在移植肾中保存并复制。然而,目前尚未明确HIV为何在肾移植术后能够迅速侵袭新的肾脏,可能原因如下:(1)即使术后进行cART,外周血中没有检测到HIV-1 RNA,也无法避免病毒在局部组织或腔隙内的短暂暴发而引起移植肾感染;(2)病毒有可能通过受者感染的T细胞传染至移植肾组织细胞,体外实验也证实了这个推测[30];(3)肾移植术后免疫抑制药和cART药物之间相互作用,导致血药浓度不稳定,可能会引起短暂的病毒复制。
因此,肾移植术后免疫抑制药和cART药物之间的用药平衡对于移植肾存活以及HIV的控制非常重要,术后应密切监测相关指标的变化。有关HIV阳性患者肾移植术后HIVAN复发率的研究大多为小样本量研究,结论差异较大。法国学者研究报道,接受HIV阴性供肾的患者,术后HIVAN复发率高达68%[23]。部分学者认为接受HIV阳性供肾术后HIVAN的复发率将会高于HIV阴性供肾,但是目前尚无大样本研究报道。
4 HIV阳性供肾的使用
供肾短缺是全球面临的一个难题,很多患者在等待过程中失去生命。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临床医师开始思考HIV阳性供肾能否移植给HIV阳性ESRD患者。2008年,南非格罗特舒尔医院将4个HIV阳性供肾移植给了4例HIV阳性患者,术后1年,4例受者均存活,移植肾功能良好,这是首次报道的HIV阳性供、受者之间的移植[31]。将HIV阳性供者纳入到可捐献的范畴,的确扩大了供肾池,并且极大地满足了HIV阳性患者的移植需求。随后开展的一项多中心研究结果显示,接受HIV阳性供肾的肾移植受者术后1、3、5年的生存率分别为84%、84%、74%,移植肾存活率分别为93%、84%、84%。术后1年和3年急性排斥发生率分别为8%和22%[32]。HIV阳性患者接受HIV阳性供肾,术后受者及移植肾存活时间与接受HIV阴性供肾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虽然现有的研究结果证实接受HIV阳性供肾是安全的,但移植科医师仍担心由于cART的广泛应用,部分HIV会产生耐药性,如果产生耐药性的供肾移植给非耐药性的受者,可能会导致受者出现耐药性。加上术后免疫抑制药的作用,HIV复制增多,有可能会增加受者病死率,或由于HIV侵袭肾细胞,导致肾脏病理改变,影响移植肾功能,增加移植肾丢失率。
2013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将HIV阳性供肾定义为“增加风险”的供肾。按照我们的理解,HIV阳性供肾应该是“传染风险增加”的供肾。在美国,该类供肾能够扩大20%的供肾池。据报道,在首例HIV阳性供肾移植后,32%的外科医师改变了他们对于HIV阳性供肾不能用于HIV阳性患者肾移植的想法[33]。调查显示,大多数等待移植的HIV阳性ESRD患者不希望接受HIV阳性供肾移植,认为这类供肾应该给透析风险高或者生命垂危的患者[34];且42%的患者明确表示拒绝使用该类供肾。事实上,拒绝使用该类供肾对于等待者来说是不利的。有研究结果显示,HIV阳性供肾用于移植,可增加可移植患者的数量,减少等待时间,和继续等待者相比,移植受者术后生存时间显著延长,医疗花费更低,因透析导致的各种感染率也明显下降[35]。在移植术后6个月,接受“增加风险”供肾移植的受者和未行移植的患者相比,死亡风险下降了42%[36]。
5 HIV阳性患者免疫诱导药与免疫抑制药的使用
HIV阳性患者肾移植术后排斥反应发生率较高,如何降低排斥反应发生率及延长移植肾存活时间至关重要。研究结果显示,与不使用免疫诱导药相比,使用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ntithymocyte globulin,ATG)进行免疫诱导治疗可以降低61%的急性排斥反应发生风险[37]。然而,使用ATG进行免疫诱导治疗会使CD4+T细胞计数明显下降,机会性感染的风险增加,受者死亡和移植肾丢失的风险增加[37]。且ATG的治疗窗口窄,风险较高,因此仅推荐排斥反应风险较高的患者使用ATG作为免疫诱导药。贝拉西普作为一种免疫诱导药,也许对于HIV阳性患者的用处较大,因为它与钙调磷酸酶抑制剂和cART药物间不存在相互作用,并且能降低非免疫毒性的风险和严重程度,例如新发糖尿病、移植后高脂血症和高血压等[38]。
免疫抑制药的维持至关重要,需要在HIV复制、机会性感染和排斥反应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的建立非常困难。大多数移植中心推荐使用他克莫司作为一线用药,但是并没有任何研究证明他克莫司的效果优于环孢素。不管是他克莫司还是环孢素,都会对cART药物产生影响。患者在使用蛋白酶抑制剂时,应注意减少钙调磷酸酶抑制剂类药物的剂量;吗替麦考酚酯可能会提高阿巴卡韦、替诺福韦的细胞内水平,增加药物毒性;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具有抗增殖作用,以帮助预防移植相关的恶性肿瘤,如卡波西肉瘤。对于肾移植术后使用何种药物维持免疫抑制的效果更佳,目前尚无确切的结论。
6 小 结
患者感染HIV后ESRD的发生率较正常人群明显增加。HIV阳性ESRD患者接受肾移植后,受者及移植肾的存活时间与正常人群相当,但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较高。HIV阳性供者能显著扩大供者池,缩短HIV阳性ESRD患者的等待时间,并延长其生存时间,目前暂未发现该类供肾移植后的严重不良事件。对于排斥反应风险较大的HIV阳性受者,建议使用ATG作为免疫诱导药。术后建立免疫抑制药和cART药物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