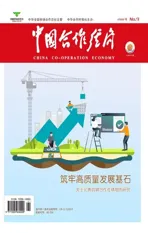从“小农”到“大农”
——简论张謇对农业的贡献
2022-11-21葛志华
文 葛志华
在近代历史人物中,张謇是独树一帜的。他既有全国性的作为,在诸多历史风口留下了或显或隐的身影,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又有区域性的贡献,在家乡江苏省南通市开创了诸多事业,奠定了“中国第一”的历史地位。他既有独特的理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又有丰富的实践,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之一。他既热衷于工业化,成为毛泽东眼中“不能忘记的四人”之一,又致力于推进农业现代化,为现代农业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张謇在致力工业化的同时,又与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不解之缘主要表现为认识层面的先人一拍、实践层面的快人一步、行政层面的胜人一筹等,从而奠定了张謇在中国农业现代化史上的历史地位。
认识层面的先人一拍
农业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但农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农业社会,农业虽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却是“小农”形态,诸如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工具简陋、经营规模狭小、生产力低下,既脆弱又易再生等,其本质特征就是物质与能量的封闭循环。到了工业社会,农业占比日渐缩小,但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农业生产技术、经营规模、经营机制、要素投入、功能作用等多方面呈现出新变化,其本质特征就是物质与能量循环由“封闭”转向“开放”、由“小农”转型为“大农”。因此,“小农”与“大农”虽只是一字之差,却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前者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后者却是现代化的结果。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告别了刀耕火种,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在此后的2000多年,虽然朝代更替不断,但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不快,家庭分散经营形式基本不变,呈现出内卷化特征。资料显示,先秦时期我国小麦亩产已达51公斤,经两汉到隋唐时期仍只有53公斤,1000年左右只提高了两公斤。明清时期,我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又被迫卷入现代化的漩涡,继而又有洋务运动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这些都没有动摇小农经济的根基。与之相适应,统治者仍把以农为本、重农轻商作为基本国策,知识界对农业的认识仍是以不变应万变,信奉传统文化定义的重农抑商、重利轻义的那套说教。
张謇所处的年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犹如一块魔方,由四个不同侧面,或者是四个不同的过程相互交织相互激荡而成。这个过程包括统治集团自身衰败的过程、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革命化的过程、现代化的过程。因此,近代中国既面临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又面临现代化的时代潮流。顺应这一潮流,扛起历史任务,就成为所有仁人志士的共同选择。正如张謇所说,“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意愿,致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为实业致钱新之函》)。因此,“捐弃所持,舍身喂虎”就成为张謇的人生选择。
张謇“家世务农”,在科场蹉跎了几十年,具有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终于“大魁天下”,获得“天子门生”的殊荣。但张謇又不同于一般的士大夫,更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腐儒,而是继承了顾炎武等人经世致用思想,主张“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并告诫世人“雄节不忘田子泰,书生莫笑顾亭林”(《张季子九录·诗录》)。
在与社会各界的接触中,在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在致力于早期现代化实践中,张謇逐渐脱离了传统文化轨道,对农业有了新的认识,扬弃了传统的小农理论,形成了自己的“大农论”。
纵观张謇的文稿,他并没有就大农的概念与内涵作系统的阐述,而是从不同侧面丰富自己的“大农论”。择其要点有:
——农业不再是一个封闭的部门,而是实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实业救国”是张謇的一贯主张与不懈追求,而实业并不是专指工业或商业,也包括农业。工业也不专指传统手工业,也包括机器大生产。张謇认为,所谓“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无工商则农困塞”。可见,张謇并不是就农业说农业,而是把农业作为实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主张。
——农工商三者是有机联系的。张謇非常重视农业,“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农为尤要”(《张謇全集》第二卷第13 页)。但是,张謇重农并不抑商。张謇认为,“本对未而言,犹言原委,文有先后而无轻重”。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重农抑商的说教。他举例说:“棉之始,农之事;棉之终,商之事,其中则工之事。”在张謇眼中,农工商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产业循环链,“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应之势,理所固然”(《请兴农会奏》)。因此,“农工商必兼计而后能相救”(《张謇全集》第二卷第800页)。
——“大农”与“小农”有诸多不同。张謇认为,“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大农”与“小农”有明显区别:在经营形式上,小农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而大农则是“仿泰西公司集资堤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在生产工具上,“小农”是人力加畜力,而“大农”主要是“用机器垦植”;在生产目的上,“小农”是自给自足,“大农”主要进行商品化生产,为工业化提供原料;在经营方式上,“小农”是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只能从事简单再生产,“大农”则是规模化经营,可进行扩大再生产。所谓“扩充棉产,奖励大农,非大农不能有此扩张之能力”“种植棉花,需倚大农”;在要素投入上,发展大农需要金融等社会化支持,“非大农足以收宏效,然行大农法,必有一金融机构为之后援,乃可措手”(《张謇全集》,第二卷第238页)。
当同时代官僚士大夫围绕“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围绕“以农立国”与“以商立国”等争论不休时,张謇已率先把目光转向农业转型,形成了自己的“大农论”,丰富了我国的农业发展思想宝库。
实践层面的快人一步
张謇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提出“大农论”,还在实践层面率先实践“大农论”,为引领农业转型发展树立了典型。
张謇的大农实践始于1901 年。该年5 月,张謇等集资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正式成立。垦区总面积232平方公里,合12.5万亩,其中可垦地11.5万亩。经过十年的艰苦创业,历经“四难”,即与天斗(雨涝)、与地斗(盐碱)、与海斗(风潮)、与人斗(地权),有计划地修筑海堤、兴修水利、招募垦户、建造农舍、改良土壤,引进良种,终于建成。1911年公司开始盈利,当年给股东分红31425两。从1911年到1925年,公司所获纯利高达84 万两,几乎为原始投资的3 倍。张謇在《垦牧乡志》记曰:“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社,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一小世界矣。”(《张謇全集》第三卷第395页)。
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带来了兴办垦牧公司的热潮。资料显示,到1920 年止,张謇先后成立了大有晋、大豫、中孚、通遂、大丰、通兴、华成等公司。上述公司共投入资本2199万元,所占土地面积455万亩,已开垦土地70万亩之多。
在张謇的带领与影响下,江苏东部沿海北起阜宁、南至南通,绵延600多里的冲击带上,迅速崛起了众多盐垦公司,其中属于大生系统的有16家。这些公司进行大规模的废灶兴垦,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引进驯化良种,在荒凉的盐碱地上谱写了垦荒史上雄伟、悲壮的乐章。截至20 世纪20 年代,这些公司已拥有土地2000余万亩、植棉400余万亩,年产棉花60余万担。
虽然垦牧公司投资总额、所占面积、股东构成不同,但有以下共同点:在经营形式上,“份泰西公司集资堤之”,如通海垦牧公司“集股股本的规银二十二万两为准”,每股规银一万两,共二千二万股;在经营机制上,采用“公司+农户”的形式,农户主要负责生产管理,公司主要负责规划、水利等任务;在生产目的上,主要为棉纺工业提供优质棉花,从事商品生产。因此,张謇的农业实践已明显脱离了传统的小农轨道,既开垦了大量荒地,缓和了人地矛盾,增加了政府收入,支持了工业化,又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有益探索,也可以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轫。
从现有史料来看,张謇的大农实践固然保留了不少传统性,但更多地体现了现代性:
从要素投入来看,农业增长的贡献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更明显地转向依靠资本、科技等现代要素。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与劳动力,也就是所谓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小农”如此,“大农”也是如此。两者的区别在于小农只是土地与劳动力的简单结合,一块土地与一个家庭就可进行周而复始的生产。大农也离不开土地与劳动力,更离不开资本与科技等现代要素,张謇通过股份制这一全新的组织形式,把社会闲散资金汇集为巨额资本,滚动开发盐碱荒地,不仅获得了大量土地,缓和了人地矛盾,还有力地支持了早期工业化。在产前环节,垦牧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围垦造田,开展水利工程建设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产中环节,又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土壤改良、设立农校、棉纺试验场、推广新技术、引进驯化新品种,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在产后环节,又用大量资金收购棉花,引导农民进行商品生产,促进了农业的内部分工,扩大了农业多样化联系,加快传统农业与农民的转型发展。可见,资本与科技在张謇的大农实践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从经营机制来看,生产经营的形式由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转向“公司+农户”的产业化经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经营模式。家庭分散经营是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全把式”的小农业,内部没有分工,外部缺失联系。这种小农经济十分脆弱,又极易再生,是传统专制政治的经济基础。张謇的大农实践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公司这一市场主体,形成了“公司+农户”的新模式。就土地权限而言,张謇将垦牧公司的土地划分为“田底权”与“田面权”,公司拥有田面权,负责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向政府缴纳田赋,承诺进行建设时优先雇佣佃户,代建农舍(收费)等。公司将20 亩为一窕出租给农户,佃户拥有“田面权”,只要交付“顶首”(押金)每亩6元,佃户就可获得“田面权”。且佃户一旦获得“田面权”,田主不可收回租佃权,实际上就是“永佃制”,拥有了处置土地的转租、典押、传给后代等权益,还可获得土地改良后部分地价升值收益。这种土地关系与当时南通地区通行的“活佃制”相比,对公司与农户都有利,实现了“双赢”。农户多交了一倍的押金,但获得了永佃权,有了稳定的经济预期,且每年可少交一半田租;而公司通过“伸佃顶”获得了更多资金,缓解资金困难,可以进行滚动开发。
就分配关系而言,在公司的引导下,农户以家庭经营方式进行生产经营,一年两熟,上半年种植谷类、豆类,下半年种植棉花。到收获时,由公司派人估产(议租),收获物按四六分成,公司为四、农户为六,纳税的棉花交给公司,多余的棉花也按市场价格以现金形式兑付给农户。这种议租分成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歉年时,业佃双方共担损失;丰年时,业佃双方共享其成。
就双方权责而言,公司负责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新品种的引进与推广、棉花的收购、代建农舍等工作。公司还承担垦区内堤渠、涵洞、道路、桥梁工程公共设施的维修,所需人工则优先雇佣佃户。农户主要职责是生产经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
由此可见,公司与农户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公司决定农户生产什么,负责将其产品变成工业原料,把农户纳入现代经济轨道;农户则按照公司的要求,组织农业生产,为家庭增加经济收入。农户与公司是一种互利关系,公司增加了现金流,有了稳定的工业原料基地;农户则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产品有了稳定的销路。土地为公司与农户共有,这与地主封建所有制有本质区别。
从功能作用来看,农业产业发展由单一的食品供给转向多功能拓展。在张謇的大农实践中,农业不再是封闭的循环,而是现代实业的一部分,与其他部门的联系越发紧密。就农业与工业的关系而言,大生公司与垦牧公司相互支持,融为一体。大生公司为垦牧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垦牧公司则为大生公司提供价廉质优的工业原料;在大生转盈为亏时,又给大生以可观的经济回报。就生态环境而言,张謇的大农实践改变了垦区的面貌,白茫茫的荒滩变成了良田与相对繁荣的村镇,成为“新世界的雏形”。就功能而言,农业产业的多功能作用日益明显,农业的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外汇贡献等基本功能持续存在并得到加强,旅游观光、江海文化传承等新的功能逐渐显现。就产业发展而言,农业产业横向与纵向联系不断加强,产前、产中、产后紧密衔接,产加销、贸工农环环相扣,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形态与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农业经营的新局面。
与那些负气、空言的官僚士大夫相比,张謇的大农实践无疑是有价值的,不仅开垦了大量荒地。增加了物质财富,支持了工业化,还成为我国早期农业现代化的典型。但张謇的大农实践又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不仅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缺乏现代化的环境与条件,还因为张謇的大农实践是一个“早产儿”。中国工业化处于初始时期,自身力量十分弱小,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改造传统农业的动力。因此,当大生集团进入下行通道后,垦牧公司也就摇摇欲坠了。
行政推动层面的胜人一筹
张謇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有时居庙堂之高,身居“总长”等要职;有时又处江湖之远,致力于“村落主义”;更多是以“通官商之邮”的特殊地位为践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呕心沥血。
张謇当过幕僚、翰林院修撰、实业总长、农林工商总长等职,拥有“天子门生”的光环,与当朝重臣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拥有丰富的行政资源。他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很复杂,有依赖的一面,比如张謇“奉旨总理通海商务”,请两江总督派兵驻守垦区,打击“沙棍”与土匪,维护农业生产秩序等;也有抗争的一面,比如张謇对一些官僚不识时务表示失望,对政府的苛捐杂税进行抵制,对军阀混战进行批评等。
虽然居官的时间不长,但张謇长袖善舞,抓住“窗口期”,综合运用组织、行政、立法、经济等手段扶持大农、改造小农,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效。
——提出设立农会。发展大农离不开农会。为了有效发展大农,张謇多次建议设立农会,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研究、管理与指导。他提出,应在上海设立总会,各地设立分会,农会应开设农学堂,延聘外国农业人才。他还明确农会的三大任务,即辨土壤、考物产、筹资本。张謇还参考英国、美国农会的经验,提出了农会的创办方法、经济来源、功能作用等。
——强化行政推动。张謇在担任实业总长与农林工商总长期间,主持起草了一系列促进实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倡导兴农垦殖、废除苛捐杂税、制订银行条例、发布《商业注册章程》。他还发布了《关于征集植物病虫及害虫给各省民政长官的训令》,颁发《劝农员章程》。张謇还以总长身份对改良土壤、病虫害防治、种子改良、农具改进、金融服务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为大农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推动农业立法。张謇以为,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在总长任职两年中,亲自主持修订颁布了“二十余种农商部法规”(《九录·政闻录》卷七),诸如《森林法》《国有荒地承垦条例》《造林奖励条例》《植棉制糖牧羊条例施行细则》等,为农业发展特别是大农发展创造了法制条件。
——运用经济手段扶持大农。无论是垦荒还是种植,张謇都把大农作为重点,在奖励方面向大农倾斜,支持建立规模化的生产基地。
张謇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扶持大农发展,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有效促成了民国初年垦荒高潮,加速了民国初年农业现代化进程。但因当时的历史条件,有的文件成为了一纸空文。
改进传统小农,发展现代大农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没有也不可能在张謇手中完成。但张謇的先人一拍、快人一步、胜人一筹,无疑奠定了他在农业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因此,研究中国工业发展史,不能不提到张謇;研究中国农业发展史,不能忽略张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