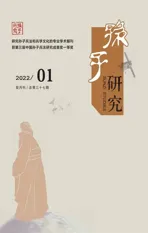试析中国古代战例中以少胜多的关键因素
2022-11-21穆晨璐倪霄汉
穆晨璐 倪霄汉
后周柴荣曾言:“凡兵务精不务多”〔1〕,清代魏源认为“从古兵愈多者力愈弱”〔2〕。“以少胜多”,较之于“以多胜少”和兵力相当的情况下取胜,不仅对于兵力少的一方的军队质量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战前筹划和战场指挥层面也更加困难。纵观古代战争,并不是所有的“少”都能胜“多”。本文结合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分两个方面归纳以少胜多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以少胜多的本质。
一、精兵建设方面
朱元璋曾言:“兵不贵多而贵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阵。”〔3〕通过对以少胜多的战例分析,可发现建设一支精兵是以少胜多得以实现的基础。在精兵建设方面,以少胜多的关键因素有:
(一)集兵方式合理,精选士卒,规模适当
精选士卒是建设一支精兵的开端。不同历史背景下,各支军队的集兵方式不尽相同,不能武断认为某种集兵方式好于其他。北宋时期, 宋军常常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败于辽和西夏,于是宋人在各方面进行反思,集兵方式即是其中之一,稍晚时期还出现了专论集兵方式的著作〔4〕。部分宋人因亲身体验到募兵制的种种缺陷而追忆唐代的“兵农合一”为理想兵制,在熙宁年间(1068-1077)强制推行民兵制以与募兵制并行,而后又因为现实中的失败,重塑募兵制最优的观念,循环往复,但军队战力并未因集兵方式的不断改变而提升〔5〕。唐、宋、明三朝集兵方式均在不断改变,但“前代之兵莫少于开国,亦皆莫强于开国”〔6〕,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唐中后期的募兵制、北宋中期仿府兵制而行的民兵制、明中后期的募兵制就一定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著名精兵戚家军即是招募而成,北府兵亦是广泛招募北方的流民团体,而西魏北周赖以统一北方、频频以少胜多的府兵〔7〕则是“兵农合一”。故集兵方式没有绝对的好坏,需要立足于实际情况来选择。
精锐的军队在集兵方式和规模上均是立足于现实选择最优的方案,不囿于僵化的模式。如西晋马隆奏请司马炎,抛开世兵制组织的军队,另行招募三千人组成新军,终平定鲜卑秃发树机能之乱。谢玄广泛吸纳北方战斗经验丰富的流民团体,曹操吸纳张辽、徐晃等部的边军降军和黄巾军的精锐,这些举措都迅速提升了全军的战斗力。
在集兵规模上,并非多多益善。吴起提出“简募良材”〔8〕,以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的例子说明用一支规模精干的军队即可威震天下。南宋初期威震金国的岳家军虽来源复杂,但却极其重视拣选,只挑精锐编入军中。当初朝廷拨付韩京、吴锡两军时,岳飞拣选编入军中的不足千人〔9〕。反之,前秦军队为了尽快灭晋,临时大规模征召无战斗经验的普通民众,导致军队大而不当,埋下了淝水战败的祸因。
(二)军事训练水平高,有足够的作战经验
孙子用以庙算的“五事七计”中即有“士卒孰练”〔10〕。吴起亦云:“用兵之法,教戒为先。”〔11〕否则便“如驱市人而战,虽有百万,亦无益于事”〔12〕。
军事训练分单兵技能训练和部(分)队合成训练,中国冷兵器时代军队的部(分)队合成训练突出表现为军阵训练。一支军队的战力高低往往与其军事训练水平密切相关。岳家军就极其注重日常训练。在单兵技能上,岳飞训练骑兵高难度骑术科目时仍然要求披重铠〔13〕。通常情况下,南宋骑兵只专习马上箭术或枪术中一种,并且还难以精熟,而岳家军骑兵则是枪术和箭术并重,还经常考核。此外,岳飞对军阵训练也造诣颇深,“授兵指画,约束明简,使人易从”〔14〕。
一支军队的战斗力的提升,不仅需要军事训练的历练,更需要作战实践的历练。官渡之战中的曹军与袁军从建军时间来看相差无几,但曹军中经历实战的老兵比例高,且曹军经历的战斗场次也远高于袁军。从而在两军战力上,双方公认“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15〕。岳家军更是百战精兵,十几年间不断与金军、刘豫、杨幺等作战,作战水平已臻化境。淝水之战中的北府兵的兵员来源——流民团体多年来为了生存,在北方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军后,谢玄率领北府兵在淮泗地区多次击破秦军,充分锻炼了部队的协同配合能力。反观前秦军队临时征召,二十余万的前锋军中有为数不少的新兵。这些兵士自征集至投入战场,军事训练时间极为有限,更遑论军阵训练和实战历练,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协同配合上都难以与北府兵相称,故战场表现极为拙劣。
(三)各级将领能力出众
孙子云:“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16〕一支精锐的军队不仅需要兵精,更需要将能。孙子提出将领要“智、信、仁、勇、严”俱备,吴起要求将领要做到“五慎”,懂“四机”〔17〕。《六韬》中提出“将有五材十过”〔18〕。克劳塞维茨提出了“军事天才”的概念,认为优秀将领需要有完善的勇气、看穿战争迷雾的智力、镇静果断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19〕。总之,古今中外对于良将标准的研究不一而足,但从这些以少胜多战例的作战方面进行分析,将领的战役布势、情况判断、作战筹划和战场指挥能力更为重要,如果还能熟稔武艺、弓马娴熟,则更为加分。
1. 战役布势能力方面。曹操在兵力劣势的情形下,利用内线作战的便利,建立起白马——延津、官渡、许都三道防线,并选择官渡作为主战场,利用地利成功将袁军拖在了官渡一线,并以荀彧、满宠、李通、赵俨等人留守后方。虽然在官渡战事结束前未能完全解决物资运输困难问题,但至少平定了各地叛乱,基本消除了袁氏在豫州的势力。曹操还任用臧霸、刘馥于青徐、扬州方向,保证了次要战略方向的安全。
郾城之战前,由于南宋朝廷昏聩的战略调动,岳家军阵地成为了宋金战线的突出部,两翼无友军掩蔽,实有全军覆没之危。在此危急之时,岳飞果断做出缩短正面战线,分出本军团兵力抢占要地的决策,凭借本军团兵力稳固防线,填补了张俊军留下的防线漏洞。
2. 情况判断能力方面。官渡之战中,荀彧力谏曹操坚守官渡一线,从而能够等到夜袭乌巢的战机。在夜袭乌巢、袁军救援骑兵即将抵达时,曹操毅然否决分兵拒之,坚决集中兵力攻乌巢,终完成转折之战的胜利。这些表现充分体现了曹操、荀彧等人精准的情况判断力。
郾城—颍昌之战,岳飞更是情况判断精确果断,战役布局先敌一步。特别是郾城之战后,立即命岳云驰援颍昌。此役完颜宗弼的反应也非常快,郾城之战后仅四日就遮蔽了郾城和淮宁向颍昌的通路。如果迟上些许时间,颍昌将没有任何援军。郾城战斗的第一阶段岳飞判断完颜宗弼还有战力强大的预备队,故一直未让步兵军阵参战,从而在正确时机对女真“铁浮屠”予以克制。在郾城战斗的后期,城中兵力几乎已全部投入战场,但战斗仍呈相持之势,岳飞判断自己此时在指挥位置发挥作用已不大,果断亲率四十骑投入战斗,一举激励起将士的军心士气。小商桥战斗中,杨再兴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精准判断敌军会对郾城指挥部造成极大威胁,果断下令与数量庞大的敌军缠斗,直至全体阵亡。颍昌之战中,负责守城的董先、胡清看出宋军已成颓势,精准判断态势,果断率领两军生力军投入战场,一举扭转战势。
3. 作战筹划能力方面。谢玄利用苻坚急于速胜的心理,设计出“让秦军少却”的方案,使秦军认为后退有利可图,从而同意“移陈少却”。在秦军移阵过程中,谢玄寻找最佳时机,以精锐一部快速突击秦军前军,致其混乱,而后乘乱击穿秦军,使其溃败,再由主力发动进攻。正是这一成功的战前筹划,使得晋军以少胜多成为现实。反观秦军,由无统兵作战经验的苻融担任主将,更无谢玄式的“执行主将”。针对晋军的“少却”提议,秦军从主将到各级将领都未发现其中蕴含的杀机,作战筹划能力远不及谢玄,主将的能力不足成为此战秦军的最大软肋。
郾城—颍昌之战中,岳飞通过兵力的集结和运动,在确立三角防御的基础上积蓄进攻的作战力量以待战机。这一作战筹划以守为主,并可有效防范金军侧后迂回断大军后勤供应,迫使金军不得不在岳飞集结兵力的战场进行决战。在郾城之战后,岳飞立即令张宪部内收向颍昌方向运动,令岳云率背嵬军一部紧急增援颍昌,岳飞的这一系列通过战前筹划发布的指令成功地弥补了战略上的劣势,使得岳家军具备与金军一战的基础。
4. 战场指挥能力方面。白马之战,曹操根据战场态势采纳谋士荀攸的策略,击破围城的颜良部,并利用敌军收拢部队的时间差,阵斩颜良。延津之战,曹操主动设谋阵斩文丑。官渡相持之时,曹军野战不力,立马转入防御,并且化解了袁军所有能使用的攻坚战法。于禁攻破汲、获嘉袁营数十座并于官渡前线督守土山,乐进先登破乌巢力斩淳于琼,徐晃官渡一役功最多,曹仁、李通后方平叛,任峻提升后勤运输的安全性,曹洪坚守官渡大营,诸将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与决策执行力带来了一次次作战行动的成功,逐步扭转曹军的颓势。反观袁军,颜良白马围城执行不力,文丑延津追击执行不力,刘备去汝南串联首鼠两端,韩荀骑兵部队作为偏师深入敌后作战不力,淳于琼守乌巢不力,张郃、高览攻曹营不力……袁军的战役失败就是由各级将领战场指挥能力不足导致的一次次作战行动失败而积累起来的。
郾城之战中,岳云率领精锐骑兵与数量占绝对优势且战力强大的女真骑兵反复冲杀数十回合。骑兵每一回合的冲锋、交战、重整阵形等都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指挥活动,随着回合数增长,兵员人数、人马体力、战术执行力都在下降,指挥难度更大。故金军号称能战一百多回合,不仅需要顽强的作战意志和娴熟的战斗技能,更需要骑兵主将出色的指挥能力。故从郾城这场战斗已能体现出岳云的骑兵指挥能力胜于金军骑将。颍昌之战中,岳云领马军居中冲锋,王贵领步军两翼列阵。特别是王贵的两翼步军,硬憾比己方兵力更为庞大的金军骑兵,虽然战斗末期,步军已成不支之势,王贵出现“怯战”想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步军能坚持六个小时不败本身已是奇迹,这充分显示出岳飞麾下第一将的战场指挥能力。
此外,还有地形运用能力、掌控士气能力等等。以上的种种能力均属技能经验类能力,须长期在专业领域内学习和实践进行经验积累,并非一朝一夕即可获得,更不可能仅通过书本习得。
(四)内部团结协作
孟子曾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0〕此言道出人和的重要性,而军队内部的团结尤为重要。张居正就言及:“古之论战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锐,尤贵将士辑和。和,则一可当百;不和,虽有众,弗能用也。”〔21〕
本文由于是就作战层次论述,故不涉及主君与前线将帅之间的关系,探讨范围限在前线军队之中。
官渡之战中袁军内部争斗激烈,袁军中分为汝颍系与河北系,凡是关于袁绍势力的重大决策,两大集团内部各自意见都是一致的,但集团间的意见基本相左。在官渡之战中,处于大后方的河北人审配处置了许攸的家人,直接导致许攸投奔曹操,引曹操来攻乌巢。在应对曹军偷袭乌巢的危机时,颍川人郭图反对河北将领张郃的意见,并在乌巢败后进一步诋毁张郃。官渡败后,南阳人逢纪直接导致河北田丰之死。如此激烈的派系之争,使得派系之间的利益诉求胜过了袁军集体的利益追求,再加上袁绍热衷于平衡派系的政治权术,使得内忧甚于外患,成为了袁军官渡之败的主因之一。
派系之争对作战的危害在17世纪朝日之间壬辰之役中体现得更为明显〔22〕。在朝鲜朝堂官员的心目中,东、西派的意气之争的重要性甚至超出了国家存亡。这些官员在作战准备中专以攻讦对方为主要目的,在两军对垒中一味以是否本派官员的意见作为军事决策依据,从而使得朝军在一系列战斗中尽管占据兵力优势,却一再大败于日军,险些亡国。
反观曹操,其势力的组成极为复杂。在官渡之战期间,虽然曹操统治区里内乱不断,但这些动乱大多为袁绍所推动,并非曹操势力内部的争斗。就连投曹操不久的李通,面对刘表和袁绍争相拉拢和曹操统治区内危如累卵的境况,仍然坚定地“斩绍使”,平定汝南郡内动乱。曹操的主要部属〔23〕众志成城,从而保证曹操势力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能够坚守至夜袭乌巢的转折。
体现内部团结更为明显的是临颍战斗中,杨再兴所部三百骑为给大军争取时间,毅然决然地率所部全体阵亡。颍昌之战中,董先等将见城外岳家军逐渐不支,未等到王贵军令,毅然主动率守军支援,从而击溃金军。这一系列正反例证说明内部团结协作是一支军队获胜的必要条件,也是以少胜多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
(五)法令严明,战斗意志顽强
孙子的“五事七计”中即有“法令孰行”“赏罚孰明”,他把法令的完善程度和执行效果作为庙算双方胜负的重要依据。“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24〕尉缭子阐明战斗意志来自于严明的法纪。
官渡之战前,各方对战役结果进行预测,荀彧提出曹军取胜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并且“与有功者无所吝惜”〔25〕。凉州的杨阜也论及曹操“法一而兵精”。郭嘉也有类似言论。这些均可佐证曹军管理制度规范,且能贯彻执行。从留存史料中可见曹操发布的多部作战法令,如《军令》《船战令》《步战令》等。通过这些法令,曹操严格规范了作战行为步骤,内容非常细致,并附有严苛的惩罚措施。这些法令有助于部队迅速习得作战技能,加速形成各部之间的协同默契。这是曹军迅速生成战斗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绍兴四年,胡松年评价岳飞部:“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26〕岳家军中的信使为了执行军令,“宁为水溺死,不敢违相公令”〔27〕。这些都体现了岳家军严明的法纪。在约束将领方面,岳飞有过必罚。岳云因为训练失误,几被斩首,众将求情,才改为一百军杖。秦桧认为王贵数次被重罚必定怨恨,让其诬告岳飞时,王贵尚言:“相公为大将,宁免以尝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28〕这从侧面说明岳飞治军虽严但能服众。
惩罚可使军队整肃,号令严明,但不一定能得部属真心拥护。岳飞不仅仅用严令约束军队,还能以身作则。如岳飞在生活中“待人以恩,常与士卒最下者同食。……出师野次,士卒露宿,虽馆舍甚备,不独入”〔29〕,故能“虽万众而犹一心”〔30〕。正因岳飞身先垂范,赏罚公正,故能使全军信服,从而方能“御众得其死力”〔31〕,“猝遇敌,不为摇动”〔32〕,“凡即戎,皆至寡敌至众”〔33〕。
金军素来以坚忍著称,更是号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 何以谓马军”。但郾城之战中,岳家军骑兵与数量庞大的精锐女真骑兵反复冲杀数十回合;颍昌之战中,岳家军以劣势兵力与金军鏖战六个小时,“人为血人,马为血马,无一人肯回顾者”。这两场战斗都是以金军失去战心落败而结束,显示出岳家军官兵比金军更为坚忍的作战意志和悍不畏死的战斗意志。特别是在小商河战斗中,杨再兴部为了拖住金军,三百骑全体阵亡,以己方的牺牲为大军争取了时间。
戚继光言:“军令以齐之,军法以摄之,使强弱同奋,万人一心,攻坚摧强,无往不胜矣。”〔34〕结合岳家军、戚家军的作战表现,更可见法令对军队战斗力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六)作战编成精当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35〕这里的“分数”即是指平时的军队编组和战时的作战编成〔36〕,尤以作战编成更为重要。曹操论及袁军的缺点时就曾直言其“兵多而分画不明”。
袁军因人数众多,本身指挥管理难度就较大,而袁绍还加大了这种难度,多次扰乱作战编成。如攻灭公孙瓒前夕褫夺战功居首的麴义兵权;官渡之战前,将沮授兵权划分为三,而后又将沮授兵权完全剥夺划分给没有任何统兵经验的汝颍士人郭图。更为离奇的是,袁绍居然在界桥之战大胜公孙瓒后,骤然任命一名为崔巨业的星象士为主将统兵数万攻公孙瓒。如此随意变换将领与部队的统属关系在袁军中并不罕见。
官渡战前袁军中军职最高的是沮授,为奋武将军,其余史料中未见袁军中杂号将军的记载。袁军规模远大于曹军,曹军中都至少有三名杂号将军与数名偏、裨将军,袁军中的高军职将领人数反而与曹军相当,说明袁军从杂号将军至诸校尉的指挥幅度过大。指挥幅度过大带来的后果就是管理效率降低,从而指挥难度加大、命令执行速率降低。
此外,高军职将领人数的不足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组织两千人以上规模的战斗时就不得不以一部的主官——校尉临时统带其余各校尉,与稳定明确的作战编成相比,显然在各部〔37〕之间配合熟练度和各校尉间的指挥协调效率方面都远远不如,易造成指挥体系的末端紊乱。这也是“兵多而分画不明”的主要体现之一。
反观曹军,从杂号将军到中军诸职能校尉和实职领兵校尉,作战编成清晰精当。岳家军亦是如此。绍兴九年,岳家军有“统制二十二,统领五,正副准备将二百五十二”〔38〕。由此可见,军与将比例约为1:3,岳家军从军到将到部到队,指挥幅度适当。岳家军各军主将与其部属关系密切,多是加入岳家军前的原部属。北府兵具体编成已不可考,但其是由各将带领原部曲加入,统属关系应是变化不大。故这三支军队一直保持了较高的指挥效率。
(七)武器装备精良
本文所详述的三个战例,两军的武器装备差别不大。即使是袁曹两军,也只是铁铠与铁质马铠数量的差距,而非质的代差。但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交战双方武器装备还是存在着代差现象,如陈汤所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39〕陈汤认为汉军之所以面对胡军能以少胜多,是因为兵刃和弓弩等武器装备精良,远胜于胡军。
二、精兵运用方面
建设好一支精兵,还需要合理运用,否则亦难以做到以少胜多。在精兵运用方面,以少胜多的关键因素有:
(一)因敌制宜,灵活运用战术,适时创新战法
《孙子兵法》提出了著名的“诡道十二法”,即是“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40〕。孙子还明确提出“兵因敌而制胜”,要不断根据敌情来灵活运用战术。官渡之战时,袁军运用了土山、挖地道等多种战术,曹军均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予以应对。
在郾城和颍昌的战斗中,岳家军巧妙地将“以步制骑”与“以骑制骑”相结合,且对步兵和骑兵的使用方式灵活多变。郾城之战中,岳飞将步兵用作预备队,以小编组的形式较分散地与金军甲骑具装对攻。而在颍昌之战中,王贵将步兵结成严密的军阵位于两翼主守,用于克制金军的“拐子马”战术。两场战斗中,岳家军都将骑兵集中使用,作为拳头力量与金军反复冲杀,最大程度地运用了汉人骑兵的近战优势〔41〕,但郾城之战中,岳家军骑兵对阵的是金军骑兵,而颍昌之战中,其对阵的是金军居中部署的步兵军阵。可见岳家军对骑兵的应用因敌制宜,不拘一格。正是将骑兵和步兵的兵力优长都最大程度地发挥,岳家军才能在巨大的兵力差距下寻求胜机。
这两次战斗还都出现了战法创新。郾城之战中,岳家军的步兵预备队以小型战术组为单位,一组对一骑,一反步兵以严密军阵对战骑兵的通常战法,使“铁浮屠”遭受较大损失。颍昌之战中,王贵排出了以骑兵居中,步兵严密军阵列于两翼的非常规阵形,完全针对金军的“拐子马”战法进行克制。这些战术创新都是根据金军的作战习惯和兵力部署,以及开战前的侦察情报来采用的,最终收到奇效。
(二)合理规划使用兵力,精准把握出击时机
兵力少的一方虽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如合理规划使用兵力,亦能部分弥补这一差距。而兵力多的一方如若不能妥善使用优势兵力,反而会变成对方的可趁之机。淝水之战中,秦军即是因为兵力过于庞大,指挥调度耗时过长,从而被晋军击破军阵,全军溃乱。夜袭乌巢的战斗中,曹操之所以仅带五千步骑,这是他权衡大营防守和攻取乌巢两场战斗而作出的决定。淝水之战中,谢玄以八千北府兵第一批渡河,就是综合考量战场幅度、渡河和列阵时间、军队战力等因素后定下的员额。
为最大限度降低遭受骑兵冲击的威胁,谢玄选择了最佳的渡河发起进攻时机——秦军骑兵军阵刚刚开始移动时。此时秦军骑兵军阵刚由作战阵形调整为行军队形,难以第一时间发动冲击,若由后退队形重新调整为进攻阵形则须经一系列程序,这一时间差刚好为北府兵的战机。趁此时机,八千北府兵组成的突击力量迅速完成渡河、结阵、冲击、接敌的步骤,使得秦军一触即溃。
郾城—颍昌之战中,岳家军更是将合理规划使用兵力和精准把握出击时机发挥到了极致。岳飞在长子岳云率骑兵与数倍于己的女真精锐骑兵反复冲杀数十回合人困马乏之际,仍未派出预备队,直至等到了金军的“铁浮屠”,才派出预备队,从而铲除了这个最大的战场威胁。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岳飞毅然亲率仅四十骑的兵力作为第二梯次的预备队,凭借自身超群的武勇,给予金军巨大的视觉冲击,同时将宋军的军心士气提升至最高点,一举击溃了金军。两次预备队出击都是恰到好处。颍昌之战中,负责守城的董先和胡清发觉己方已成颓势,而金军已全军压上,未等王贵军令,决然地率剩余的兵力出击,迂回金军的侧后薄弱点,瞬间扭转局势。
(三)充分利用地理环境,使之成为战力倍增器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孙子用了《地形》和《九地》两篇专述地理环境的重要和如何利用地形,《九变》中也有六种情况涉及地形。克劳塞维茨把“地理要素”列为决定战斗运用的五个战略要素之一〔42〕。中外两位兵学大家都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从历次以少胜多的战例来看,地理环境确实影响重大。
官渡之战中,曹操选择以官渡一带作为主战场和防御底线,正是因为官渡一带有着利于防守的地理环境。官渡位于平原地带,其北数条东西流向的河流,可以成为袁军南下的层层阻碍,其西南北流向的汴水与北边的河流刚好构成前三角的防御地带,对曹操势力的后方颍川地区是天然的掩蔽。此外,官渡水同阴沟水的汇合处和圃田泽构成官渡东西面的两大障碍地带。官渡一带的地形极大地弥补了曹军兵力不足的劣势,使得曹军能够坚持到乌巢战机的到来。
淝水之战中,晋军由于是在本土作战,因此凭借熟稔地形的优势较大程度地弥补了兵力不足的劣势。据史料,晋军陆军部署在八公山、淝水、淮水之间的三角地带,并向八公山区延伸,水军部署在淮水的“S”形河段的下弧部。考察晋军在淝水东岸建立起的防御阵地发现,其背山临水,左翼是八公山区,右翼是淮水,两翼都为自然地貌所掩蔽,受到威胁较小,防御时可节省大量兵力。而芍陂东侧淝水由正南流向正北,故淝水战场的西岸地形难以在横向上为骑兵提供冲击空间,从而不便于秦军骑兵侧面截击渡河的晋军,只可进行正面冲击。正因这一地形特征,晋军方敢以八千人正面突袭秦军,而不需提防侧翼可能出现的秦军骑兵。
天宝十五年(756)发生的灵宝之战也是利用地形以少胜多的一个典型范例。潼关至函谷关狭长的通道为原崤函古道(今河南洛阳以西至潼关一带)的一段。这一通道北依黄河,南靠秦岭,约120里,十分狭窄,地势险峻。黄河北岸区域北接中条山,亦是十分狭长。此战交战双方为哥舒翰统领的唐军与崔乾佑统领的安禄山军。唐军虽然有二十万之众,但在这狭长的通道里人数优势反而成为劣势,一旦遭到伏击,不但难以指挥全军,而且连战斗队形都无法展开。唐廷决策者不通军务,催促病中的哥舒翰出兵,使得唐军在这样的地理环境里中安军埋伏。崔乾佑又令军士焚烧草木,在封闭的峡谷地形中,烟雾迅速弥漫,造成唐军难以视物,从而引发溃乱,甚至自相残杀〔43〕。最终唐军大败,只剩八千残兵逃归潼关。
因此,兵力少的一方如能巧用地理环境,即可使其成为战力的倍增器,弥补己方的兵力劣势。
(四)重视己方后勤物资补给与防护,并伺机破敌供给
“军无辎重,则举动皆缺。”〔44〕后勤物资的补给线是军队的生命线,“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45〕。《武备辑要》言:“探贼辎重所在,以轻兵袭之,燔其积聚,贼可立败。我师辎重,必严兵防之。”〔46〕这句话明确提出要去侦察敌军辎重所在地,并用轻快部队袭击焚烧,同时注意己方辎重的防护。官渡之战即是通过攻击对方辎重所在地完成战役转折的典型战例。袁军在乌巢之战前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曹军渐渐不支。但许攸叛逃带来当夜袁军运粮队暂驻乌巢的情报,给了曹军战机,从而使得曹军转败为胜,以少胜多。此役曹军虽然严重缺粮,但这是统治区内本身军粮不足,并非运输和防护不当,其对己方粮道的维护,颇有可取之处。负责物资运输的任峻使“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复陈以营为之”〔47〕,防守严密,从而袁军难以成功劫粮。
此外,乾元初(758-759)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是通过绝对方粮道从而以少胜多的范例。该役唐军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号称六十万军队围攻邺城,城中已是“食尽,一鼠直钱四千”〔48〕,危如累卵。安军援军史思明部仅五万人,但由于唐军由宦官鱼朝恩监军,全军无将领统一指挥,给了史思明部战机。由于唐军各部号令不统一,史思明命军士伪装唐军不断袭击运粮船只和民夫,焚烧物资,不仅切断唐军补给,还激起唐军各部的矛盾。“由是诸军乏食,人思自溃。”〔49〕在这样的情形下唐军仓促应战,终致大败,史称“邺城之溃”。
(五)做好防间保密,并竭力获取敌方情报
孙子言:“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50〕他明确提出了“间”的重要性。对于己方来说,一方面要努力以“间”去获取对方情报,另一方面自身要做好防间保密。官渡之战中,正是许攸的情报才使曹军有了战机。袁军没有第一时间发觉许攸叛逃,并且运粮队伍当夜驻扎地点这一绝密情报被无关人员许攸所探知,这些都反映了袁军内部人员管控、防间保密的严重疏忽。淝水之战中苻坚更是大意到派晋人朱序去说降晋军,生生把己方情报透露给晋军,显示出秦军高层对情报保密的严重忽视。晋军正是因为朱序的竭力劝说和其带来的重要情报,才得以形成对秦军的准确判断,从而针对秦军弱点精确制定了作战方案。
除通过“间”的途径外,还可有多种方式去获取敌方情报。其中在战场上直接观察敌情、分析敌情就是最直接的方式。《六韬》言:“登高下望,以观敌之变动。望其垒,则知其虚实。望其士,则知其来去。”〔51〕除去直接观察外,还可利用部队攻击来侦知敌虚实,如: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
郾城之战中,由于完颜宗弼利用宋军破绽,率骑兵奇袭,直至郾城仅二十里才被岳家军发现。此时岳飞难以准确判断金军情况,故令岳云领精锐骑兵通过战斗探敌虚实。在小商桥的战斗中,杨再兴也是通过交战来探知这一部金军实力。颍昌之战中,正是王贵等知晓金军的以往战法,才能创新阵型克制金军,弥补兵力的劣势。
三、以少胜多的本质:精兵精用
以上从精兵建设和作战运用两方面总结了以少胜多的关键因素。要达成以少胜多,不仅要建设一支精兵,还要能够妥善运用这支精兵。这两者缺一不可。
如果仅有良将,而无精兵,则良将也难以作为〔52〕。战国时赵国名将廉颇即是著名的例子。长平之战初期,尽管廉颇的能力强于秦军主将王龁,但赵军的战斗力弱于秦军,故“秦数败赵军”,因而廉颇才坚壁不战,欲老秦师。廉颇暮年因受排挤投楚为将,却因为楚军战力比赵军更弱,从而“无功”,郁郁而终〔53〕。
如果有一支精锐的部队,若没有被妥善使用,也难以取胜。天启元年(1621),沈阳之战中,明军主将贺世贤轻敌冒进阵亡,致使浙兵戚金部和石柱兵秦邦屏部未能与城中明军会合,从而被清军主力合围,全体战殁。戚金部和秦邦屏部即是历史上著名的精锐部队戚家军和白杆兵,但因为沈阳守将贺世贤的失误而未能妥善使用而全军覆没,虽给清军造成较大伤亡,但仍难以改变战役的结局〔54〕。
综上,可以得出以少胜多的本质是精兵精用〔55〕,即高质量的军队加上良好的作战运用。高质量的军队,取决于精兵建设;良好的作战运用,关键在于将帅能力。概而言之,就是:以精兵制胜为基础,以良将克敌为关键。
【注释】
〔1〕[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92《后周纪三》太祖显德元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519页。
〔2〕 [清]魏源:《圣武记》卷11《武事余记·兵制兵饷》,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504页。
〔3〕[清]夏燮:《明通鉴》前编卷3《前纪三》洪武二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页。
〔4〕如[南宋]陈傅良:《历代兵制》,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两宋时期其他论述集兵方式的著作可见于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7-465页。
〔5〕详见方震华:《和战之间的两难》,第79-147页。
〔6〕《圣武纪》卷11《兵制兵饷》,第504页。
〔7〕西魏的府兵曾创造出沙苑之战(537)、河桥之战(538)等著名以少胜多的战例。
〔8〕《吴子》卷上《图国》,见于《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武经七书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431页。
〔9〕《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卷9《遗事》,第835页:“上初以韩京、吴锡两军付先臣,皆不习战斗,且多老弱。先臣择其可用者,不满千人,余皆罢归,数月遂为精卒。”亦可参见卷17《分拣吴锡韩京两军讫申省状》。
〔10〕《十一家注孙子》卷上《计篇》,第11页。
〔11〕《吴子》卷上《治兵》,见于《武经七书注译》,第445页。
〔12〕《宋史》卷324《张亢传》,第10487页。
〔13〕参见《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卷9《遗事》,第835页。
〔14〕《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卷9《遗事》,第836页。
〔15〕《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第166页。
〔16〕《十一家注孙子》卷上《作战篇》,第37页。
〔17〕《吴子》卷下《论将》,见于《武经七书注译》,第449-450页。“五慎”指理、备、果、戒、约,即治众如治寡、出门如见敌、临敌不怀生、虽克如始战、法令省而不烦。“四机”指气、地、事、力,即掌握士气、利用地形、运用计谋、训练精熟。
〔18〕《六韬》卷三《龙韬·论将第十九》,见于《武经七书注译》,第323-324页。
〔19〕[德]克劳塞维茨著,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6-88页。
〔20〕《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21〕[明]张嗣修、张懋修:《张太岳集》书牍12《答总兵戚南塘授己击土蛮之策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22〕详见[加]塞缪尔·霍利著,方宇译:《壬辰战争》,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23〕曹军中亦不乏与袁军暗通款曲之人,但这些并非曹军中的核心人员。
〔24〕《尉缭子》卷1《制谈》,见《武经七书注译》,第154页。
〔25〕《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第260页。
〔2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第1326页。
〔27〕见《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卷9《遗事》,第866页:“在合肥日,遣骑驰奏,至扬子江,风暴禁渡,典者力止之,骑曰:‘宁为水溺死,不敢违相公令!’自整小舟绝江,望者以为神。”
〔28〕《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卷8,第723页。
〔29〕《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卷9《遗事》,第836页。
〔30〕《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续编卷4《第四辞免同前不允诏》,第1299页。
〔31〕《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卷9《遗事》,第866页。
〔32〕《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卷9《遗事》,第867页。
〔33〕《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卷9《遗事》,第866页。
〔34〕《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11《胆气篇》,第220页。
〔35〕《十一家注孙子》卷中《势篇》,第79页。
〔36〕作战编成,指为达到一定的作战目的,将建制内和配属的参战力量组合而形成的有机整体。见《军语》(全本),第65页。
〔37〕此处的“部”是东汉军中的一级编制,军力在千人左右,主官为校尉或都尉。
〔3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6绍兴九年二月,第2138页。
〔39〕《汉书》卷70《陈汤传》,第2613页。
〔40〕《十一家注孙子》卷中《势篇》王皙注,第83页。
〔41〕参见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3-67页。
〔42〕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85页。
〔43〕事见[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35《哥舒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73页。
〔44〕[唐]李筌,刘先廷译注:《太白阴经》卷4《军装篇》,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
〔45〕《十一家注孙子》卷中《军争篇》,第126页。
〔46〕[清]许乃济辑:《武备辑要》卷5《制胜要策》,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古代兵法研究组:《中国古代兵法选辑》,石家庄陆军学校(翻印),1962年,第263页。
〔47〕《三国志》卷16《魏书·任峻传》,第409页。
〔48〕《资治通鉴》卷221《唐纪三十七》肃宗乾元二年,第7068页。
〔49〕《资治通鉴》卷221《唐纪三十七》肃宗乾元二年,第7068页。
〔50〕《十一家注孙子》卷下《用间篇》,第266页。
〔51〕《六韬》卷4《虎韬·垒虚》,见《武经七书注译》,第388页
〔52〕这里的“兵精”指相对的“精”,如井陉之战中的汉军,征召时间不长,难算精锐,但能以劣势兵力与赵军相持良久而不败。虽有韩信指挥的因素,但考虑到兵力相差甚为悬殊,相对赵军而言,汉军可算精锐。
〔53〕详见《史记》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第1876、1878页。
〔54〕详见孙文良等:《明清战争史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4-109页。
〔55〕 需要注意的是,从形式逻辑上来界定,精兵精用是以少胜多的必要不充分的条件,即以少胜多的战例中必然是精兵精用,但精兵精用不一定能够以少胜多,还须结合其他客观条件。故总结为以少胜多的实质是精兵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