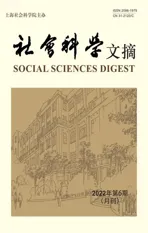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互补替代”效应:理论与实证
2022-10-22穆怀中
文/穆怀中
随着人们生育意愿的降低、少子高龄化社会的到来,家庭养老能力和观念都在渐渐地发生着变化。子女有赡养父母的养老愿望,但由于家庭老人数量增加和自己经济能力不足,难以实现子女养老的合意水平和理想状态。这就使得人们开始想到“养儿防老”的替代方式,其中之一是个人储蓄养老。从理论上说,这就出现了横向代际交叠和纵向生命周期交互重叠的养老保障模式。
随之产生的问题:一是在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少子高龄化趋势下,家庭子女养老保障是否还需要,如果需要子女养老,子女给父母提供的养老保障水平多少为适度;二是个人选择养老储蓄,储蓄多少为适度;三是随着子女养老能力的降低,个人储蓄养老水平应该相应增加多少以达到养老水平不降低,这里的替代水平如何优化。本文试图研究和解读这些问题。
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储蓄养老“互补替代”原理和数量分析
(一)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理论分析
1.家庭子女养老的性质
家庭代际转移养老方式,属于“纵向积累式”代际转移养老。老年人在其青年期通过经济和情感上的付出养育子女,子女在其青年期在经济和情感上赡养父母,这属于在家庭血脉传承基础上的代际经济积累及代际转移,属于人的一生纵向的经济和情感付出积累和回报,在传统习俗里人们称其为“养儿防老”。从经济收入再分配看,“养儿防老”是一种代际收入再分配,老年人在青年期把自己收入一部分分配给养育子女,子女在青年期再把自己收入一部分分配给赡养父母。
2.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的“互补替代”
互补和替代是经济学中两个概念。互补表现为元素之间的同方向变动,替代表现为元素之间的反方向变动。家庭养老和个人养老之间既有替代关系又有互补关系,或者说存在着互补基础上的替代关系,所以本文统称家庭养老与个人养老存在着的“互补替代”效应。
一般而言,家庭子女多的父母,子女赡养总量多,个人养老储蓄可以相对少些;家庭子女少的父母,个人养老储蓄可以相对多些。从理论上说,个人养老储蓄的多少,与家庭子女的多少是负相关。从纵向上看,老年人寿命越长,个人养老储蓄可以相对多些。个人养老储蓄的多少,与老年人寿命延长是正相关。这就是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储蓄养老之间的“互补替代”基本假设。
3.生命周期均衡收入再分配原理与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适度水平概念界定
按个人生命周期均衡收入再分配原理,人的一生总收入,从理性逻辑上可以均衡分配在青年期自己生活工作消费、子女抚养教育消费、未来养老消费等方面。在此,我们以人的寿命总年龄数为时间指标,以一生劳动收入为经济指标,以生命周期少儿期、读书期、劳动期及老年期的年龄系数为人口结构参数,研究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均衡分配逻辑关系,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对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适度水平概念进行理论界定。
在人口生命周期中,青年劳动期的均衡收入分配系数,就是在生命周期的总年数中按劳动期年数比重,均衡获得劳动期的收入份额,也就是青年期年数占总寿命年数的比重系数。老年期的均衡收入分配系数,就是在生命周期的总年数中按老年期年数比重,均衡获得劳动期的收入份额,也就是其老年期年数占总寿命年数的比重系数。青少年期的均衡收入分配系数,就是在生命周期的总年数中按青少年期年数比重,均衡获得劳动期的收入份额,也就是从出生到读书年数占总寿命年数的比重系数。在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互补替代”框架内,青少年期的均衡收入分配系数,实际是父母对子女供养投入系数,也是子女未来赡养父母的给付系数。
从理论上解读,养老人口结构均衡收入分配中的“均衡性”,可以作为养老收入再分配适度性的标准之一。生命周期中家庭子女养老均衡收入分配水平,也就是家庭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适度水平。生命周期中个人养老均衡收入分配水平,也就是个人养老收入再分配适度水平。
(二)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保障收入分配适度水平数量分析
1.家庭子女代际转移养老收入再分配适度水平分析
(1)家庭子女养老适度水平,与家庭子女数量结构相关联,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子女养老保障收入再分配水平系数提升。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展望,是我国近期和远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应该选择的重要时点。据此,本文人口生命周期总年数时点选择在2035年。依据联合国预测,我国2035年人口平均寿命将达到80岁左右(79.13岁),本文在此选择80岁作为人口生命周期总年数参数进行模拟研究。统计发现,在20岁参加工作,60岁退休,80岁寿命条件下,1孩家庭子女抚养投入和未来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水平系数为0.14,约为工资收入的14%;2孩家庭子女抚养投入和未来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水平系数为0.25,约为工资收入的1/4;3孩家庭子女抚养投入和未来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水平系数为0.33,约为工资收入的1/3。家庭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有两种规律。一是子女数量增加,家庭子女抚养投入和未来子女养老水平提升;从1孩到2孩家庭,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从0.14提升到0.25,再到3孩,家庭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提升到0.33。二是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家庭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增长呈现递减趋势,从1孩到2孩,家庭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提升1.78倍;从2孩到3孩,家庭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提升1.32倍。
(2)家庭子女养老给付系数水平,在老年人寿命既定条件下,与劳动人口退休年龄无关联,随着父母劳动年龄的延长,子女养老保障收入再分配水平没有提升。统计发现,在人口寿命既定条件下,个人生命周期范围内,劳动年龄的延长,如60岁退休延长到65岁退休,自己工作时点从40年开始向后延长到45年,从时间上看,向后延长使得退休后的时间从20年缩短到15年(以80岁生命周期总年数为例),而对子女抚养教育年限没有影响,因为生命周期总年数没有变化。与父母工作期的延长相关的是,家庭父母一生总收入水平会提高,对子女的抚养教育收入再分配的基数值会提高,但家庭代际转移收入再分配系数不变。
2.个人生命周期养老收入再分配适度水平分析
(1)家庭个人养老适度水平,与家庭子女数量结构相关联,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父母个人养老保障收入再分配水平系数下降。统计发现,在20岁参加工作,60岁退休,80岁预期寿命条件下,1孩家庭未来个人养老收入再分配水平系数为0.285,约为工资收入的28%左右;2孩家庭个人未来养老收入再分配水平系数为0.25,约为工资收入的1/4;3孩家庭个人未来养老收入再分配水平系数为0.22,约为工资收入的20%左右。家庭父母个人养老收入再分配规律:一是子女数量增加,家庭个人养老水平减低;二是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家庭父母个人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变动呈现递减趋势。
(2)家庭个人养老适度水平,与劳动年龄结构相关联,随着劳动年龄延长,父母个人养老保障收入再分配水平系数下降。统计发现,在20岁参加工作,80岁寿命,工作年限到60岁延长到65岁,1孩家庭未来个人养老收入再分配水平系数从0.285降低到0.214;2孩家庭个人未来养老收入再分配水平系数从0.25降低到0.187;3孩家庭个人未来养老收入再分配水平系数从0.22降低到0.166。
(3)家庭个人养老适度水平,与老年人寿命年数相关联,随着老年人寿命延长,父母个人养老保障收入再分配水平系数提升。统计发现,父母个人寿命从65岁延长到85岁,再延长到100岁,老年人寿命每提高5岁,个人养老保障收入再分配系数提升1.82倍到1.11倍,提升速度呈递减趋势。
3.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收入再分配“互补替代”水平分析
(1)家庭个人养老对子女养老收入分配“互补替代”水平系数,与家庭子女数量结构相关联,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互补替代”系数下降。统计发现,家庭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个,家庭个人养老与子女养老保障收入再分配“互补替代”系数下降2倍到1.5倍,边际替代率从1.7下降到0.37,下降呈现递减趋势。
(2)家庭个人养老对子女养老收入分配的“互补替代”水平,与劳动年龄结构相关联,随着劳动年龄延长,父母个人养老对子女养老保障收入再分配“互补替代”水平系数下降。统计发现,一是劳动年龄延长,“互补替代”系数降低。在20岁参加工作,80岁寿命,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家庭个人养老对子女养老保障收入再分配“互补替代”系数从2.0下降1.53(1孩),从1.0下降到0.75(2孩),从0.66下降到0.50(3孩)。二是随着劳动年龄延长,子女数增加形成的家庭个人养老对子女养老的“边际替代率”降低,从1.70递减到0.25(2孩),从0.37到0.33。这一替代系数变化规律说明,家庭个人养老对子女养老“互补替代”的水平,直接与劳动年龄的长短和劳动收入的持续性相关联,个人劳动期时间越长,创造的财富和收入越多,自己的养老保障实力越强,越不依赖子女养老,家庭个人养老“互补替代”减弱。
(3)家庭个人养老对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互补替代”水平,与老年人口寿命相关联,随着老年人口寿命延长,父母个人养老对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互补替代”水平系数提升。统计发现,20岁工作,60岁退休,老年人寿命到80岁,再延长到90岁和100岁,家庭个人养老对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互补替代”系数提升到1.0,再提升到1.51和2.0;边际替代率波动性增长,从0.1递增到3.0左右。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随着老年人口寿命的延长,个人为自己积累养老保障资金和财产,依靠自己养老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4.“十四五”时期至2035年远景期的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收入再分配水平分析
(1)“十四五”时期和2035年远景期,在两代人代际养老收入再分配框架内,个人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呈现增长趋势,子女养老再分配系数呈现递减趋势。以2孩家庭为例,父母个人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从0.220增长到0.235,增长了1.5个百分点。家庭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从0.259降到0.254,降低了0.4个百分点。从总体看,增长和降低的幅度不大。这说明,“十四五”到2035年远景期,是我国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制度建设的相对稳定的机遇期。
(2)“十四五”时期和2035年远景期,如果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明显,家庭父母养老负担将会降低。以2035年远景期为例,2孩家庭较之1孩家庭,父母个人养老再分配系数将由0.270降到0.235,降低3.5个百分点。因此,全面二孩政策不仅有利于调整劳动力供需结构,也有利于缓解家庭养老压力,减轻未来老年人的自我养老负担。
(3)“十四五”时期和2035年远景期,如果老年人寿命每五年延长1岁,延迟退休政策实施选择先快后慢的策略,每年延长0.2岁也就是每五年延长1岁,老年人口寿命延长的家庭养老再分配增长效应将会被延迟退休政策效应对冲,实现家庭养老收入再分配水平的相对稳定和平衡。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角度看,这种对冲也将会在社会养老收入再分配中产生积极效应,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障资金供需不平衡风险,推进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相对平衡。
基本结论和对策建议
基本结论如下:(1)在家庭子女数量增加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条件下,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收入分配存在“替代”关系;在延长劳动年龄条件下,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收入分配存在“互补”关系。(2)家庭子女数量从3到1,子女养老适度水平系数为0.33到0.14,个人养老适度水平系数为0.22到0.285;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替代均衡时点是家庭2孩,均衡适度水平系数均为0.25;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边际替代效率递减。(3)老年人寿命延长,带来家庭养老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子女养老系数下降,个人养老系数上升且上升速度大于子女养老系数下降速度。老年人80岁寿命,个人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为一生收入的1/4;90岁寿命,个人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为一生收入的1/3,100岁寿命,个人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为一生收入的2/5,接近1/2。(4)劳动年龄延长,子女养老系数不变,个人养老系数降低,边际替代率MRS为零,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存在“互补”关系。劳动年龄延长从60岁到65岁,个人养老系数从0.25降到0.178。(5)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之间存在“互补替代”效应,及其替代均衡时点与人口学生育更替水平2.1存在契合效应,以及倒V曲线右移动效应和左移动效应。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家庭2孩和人口生育更替水平2.1,既有利于社会人口结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家庭养老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家庭2孩,子女养老收入分配系数和个人养老收入分配系数处于均衡状态,这既有利于减轻家庭一孩的养老经济负担,也有利于减轻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个人养老经济压力,有利于养老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
(2)提高个人养老保障意识,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风险。树立个人养老保障占主导地位的养老保障意识,改变全部依靠国家和家庭子女养老的观念,并且在自己一生收入分配安排中,将生命周期养老分配规划列入理性行为选择过程,在青年期就开始理性规划自己老年期经济消费水平。
(3)择时延长劳动年龄,缓解生命周期养老压力。为了保障生命周期养老收入分配的均衡可持续发展,可以择时延长劳动年龄,进而改变生命周期养老供需结构,延迟国家和个人养老保障供需平衡时点,缓解国家和个人生命周期养老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