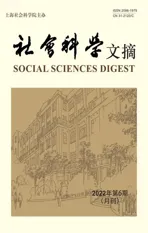“三重摹创”视野下非虚构写作的实践图式探究
2022-10-22王灿
文/王灿
摹创一词既通过丰富的含义指出了非虚构作品中的复杂性,亦是对现实的再现与情节的组织和编构。身处在当下后现代、后真相的情境中,由保罗·利科所划分出的摹创一、摹创二和摹创三,可分别对应于前构型(preˉfiguration)、共构型(conˉfiguration)和重构型(reˉfiguration)。三重摹创指的是从摹创一经由摹创二中介至摹创三的运动过程。在三重摹创理论中,“如其所是”的非虚构写作必须在读者的阅读活动中才得以完成。作为“构型活动”的非虚构写作,仅仅满足了写作者将自身限制在对“历史痕迹的追溯”这一条件,只有等到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相逢时,写作者的伦理意图、与被书写之他者的关系,乃至文本的意义及其对现实的“指涉”,才可能在作为摹创的非虚构写作中凸显出来,并被读者指认。“非虚构写作”本身除了体现写作者与其生产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从前构型至共构型阶段的运动过程,至于写作如何在引入读者的行动后产生其他力的作用与关系,则必须将视野拓宽至三重摹创的运动图式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认识。
前构型:双重的“债务”关系
利科对历史学家以及历史的债务责任之说明,确实为非虚构写作者与其所叙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考的路径。但对这种“债务”所产生的作用,利科显然未能从读者的位置提供有效的理论解释,而仅能说明写作者的意图。当写作者决定实践非虚构写作时,最先涉及的是非虚构作为一种文类的规约作用。写作者之所以能“非虚构地写作”,是因为他已经掌握了“真实的依凭”,并以此为写作的前提。相应地,当读者将一个文本视作“非虚构”作品时,已预先承认写作者以“叙说真实”为写作的前提。因此当一个文本被宣称或认定为非虚构时,认知者便与作者之间签署了一个隐蔽的契约:读者预期文本将指涉自身所处的真实世界,作者则回溯性地被赋予了“叙说真实”的义务;作者一旦决定以非虚构指称文本,实则同意读者可以对文本内容进行真伪的检验和判断。因此,非虚构作为一种文类,事实上是基于主体间性的相互建构,奠基于作者与读者对彼此及文本的期待。将非虚构的“文类规约”移至三重摹创的图式中,借由前构型阶段中所涵括的象征资源(即将文本命名为“非虚构”的意义与指涉),作者与读者在通过文本的中介前便共同承认了“非虚构”的范畴,进而将其作为共构型/重构型活动的条件。
从叙事学的结构来看,作者对读者所背负的次级债务,就是作者需要向读者保证,叙事内容是由真实的“我”所说出的话语。由此,在一些非虚构作品中所揭示出的等式A=N(作者等于叙述者),事实上已然指认出了在非虚构写作中,叙述者为何总能直接连结于作者的原因。因为这是写作者最能“有效”向读者保证真实,从而清偿次级债务的方法。这也是为何一旦非虚构文本的真实性遭到质疑,读者的直接感受是自己被作者背叛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对次级债务的违反,仅限于写作者对相关信息的意图欺瞒。一方面,由于信息掌握不充分或自我诠释的误差所导致的“不真实”,或读者对作者陈述的不接受,并不构成对“债务关系”的伤害,相反,这样的偏差是诠释学的动力来源之一。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次级债务”本身的关系性,对债务的违反无法全然从规范性的角度衡量,而是可能随着作者与读者双方对非虚构规约理解的偏移和变动有不同的认定。这也意味着,非虚构写作的规约可能经由“摹创”在行动世界的中介,在不断的诠释过程中发生改变。
如果进一步将“次级债务”与写作者对叙说对象的“原初债务”这一双重的“债务关系”置放于三重摹创的图式之中,可以看出“债务关系”相当于前构型阶段中施为者对非虚构的原初理解,它决定了非虚构的规约与伦理限制,并构成共构型阶段中作者进行非虚构写作的基础。不仅如此,债务关系作为非虚构与虚构叙事之间最重要的分野,显现了非虚构写作的“意图”和意向的“对象”,并决定了施为者在叙事交流中的身份。通过“次级债务”,写作者必须忠诚于痕迹的原因获得了解释:它既是写作者自愿承担的限制,亦是债务关系所强加的责任。双重的债务关系,共同保证了非虚构写作“不可虚构”的必要性,并使得写作者的非虚构写作实质上是一种对伦理债务的清偿。从这个角度来看,非虚构写作的核心定义是建构在写作者对自身所叙说的内容“负责”的基础上的。
共构型:讲述的自由与中介的平面
写作者拥有完整重建事件和行动语境的伦理意图,但这种意图必然会在情节化的中介下产生偏移。这是因为在文本世界之中,作者的意图仅仅是其中一个可能的面向。不仅如此,作者原先所意图指涉的对象,也在文本中被分裂为两个向度,一个向度指向缺席的某物,一个向度指向文字自身。由此来看,情节化与其说是写作者不得不面对的“限制”,更不如说是作者以象征的方式连接自身与世界的“能力”。在这个层次上,利科对共构型活动的解释,接合了叙事学理论对叙事话语的考究,“情节”既是赋予事件一个可理解的因果关系、将其嵌入更高整体的整合过程,也是作者对“如何”将事件转化为故事的选择。
由此不难看出,非虚构的共构型活动包含了债务关系所附着其上的写作规约以及写作者对如何将经验带入文字的思考。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这是非虚构写作所必须面对的“自由与限制”。其中,自由指的是作者可将所描写的对象塑形为自身的观点,包括人物、行动、事件等;限制指的是对这些描写对象的责任,可等同原初债务。“自由与限制”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一种活性辩证的关系。一方面,从不同角度形塑描写的对象虽然是自由的,但不能悖逆于债务关系的优先性;另一方面,尽管写作者要尽可能地还原所描写的事物,但也必须通过不同的情节构建去赋予事物可追随/理解的线索与结构。意即作者若不尽可能地探索语言和写作本身,则关于人的行动、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经验,便无法被“解蔽”,“真实”也就无法被“如其所是”地展露。在这样的理解下,自由即是对限制的忠诚。“债务本身即作为写作者伦理欲求的对象”的概念,因此得以在非虚构写作“自由与限制”的拉扯中被突出。
从写作者的原初认识出发,通过共构型活动所指涉出的“真实”,显然不是从文本“内部/外部”关系中所划分出的“外部世界”。事实上,利科以摹创取代过往“再现”的概念,正是为了取消文本内外的区分。作为摹创过程中的一环,文本是共构型活动所生产出的产物,是写作与阅读活动的中介。文本因而并不划分出内部的符号世界与外部的生活世界,而从来是“纯粹”内部或外部的“中介空间”,是施为者从前构型迈向重构型阶段的必要途径。中介因而不仅仅是通道、是事物得以发生的条件,而更是文本彼此互涉的交汇处,是人与现实、人与文化、人与时间相互彰显的“公共区域”,是中介让主体的碰触/遭遇得以关系化。“文本世界”因此不在他处,而与我们所居处的世界共在一个“平面”上。
借由中介平面的架构,非虚构写作的自由是不断朝向去疆界化/去系统化的运动,而限制则构成了写作的边界和图式。对原初债务的清偿,便在这一隐喻结构的形成中被展示出来。由此,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就“现实”与“真实”作出一个基本的区分:“现实”是为象征所前构的行动和事件,是我们所接触且能够“共享”的日常生活,然而因其未被挪移至诠释的过程,故尚不具“真实性”(veracity);“真实”是已经由诠释运动“保证”其真实性的行动和事件,是通过叙事和叙说内容间形成的隐喻关系被回溯性指认的内容。从这个认识来看,非虚构写作者对“痕迹”的忠诚,同时是债务的目的也是实现债务的手段。因为它留下了可追索的线索,让读者得以“检验”写作者的宣誓,从而实现“证明”的有效性。痕迹如何被指认,如何嵌入叙事中甚至是如何筛选,就成为非虚构写作必须“构型”的一环,也体现了非虚构写作者在自由与限制两端的动态综合。
重构型:指涉与真实的多重性
从文类规约的角度来看,读者在阅读非虚构文本时,必然带有对“真实”的期待。他们因此不必耗费太多时间,便可以接受文本中所叙说的人物、事件与行动,是“如我们一般”生活、发生在现实世界之中的。此外,由非虚构的指称所成立的次级债务关系,使读者可以在进驻文本世界的同时,对文本所宣称指涉的内容进行检验。只要读者具有“辨识”痕迹的能力,非虚构文本之于现实的隐喻关系,便可能被拆解、还原至尚未被“指涉”所连结的状态。读者也可能由此产生出对作者和文本的不信任,进而反过来质疑文本所包含的美学与伦理建构。
对非虚构文本的阅读因此涉及了一种对命题真伪的判断,这个判断不只是认识上的,也包含伦理的意涵。但读者并不因此被要求必须对文本提出“真实”上的认可,次级债务关系与其连带的真伪判断,是作为非虚构文本的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事实上,判断通常仅在文本缺乏相关证据支持,或情节对材料的整合和诠释与读者的认知产生冲突时,才会被拉至阅读活动的前景。在非虚构的阅读活动中,除了对文本正确性的关注,仍然包含对投入故事的幻觉与“陌生化”的辩证过程。而对非虚构作品的读者来说,“陌生化”所带来的效果,将进一步促使其逼视文本对真实的宣扬,进而回过头来重构自身的理解。
但如果重构型活动的介入使指涉不再是固定的,而是进一步依据施为者所处的不同位置回溯性地确立,那么非虚构写作所宣称的“真实”,就需要重新从实践的层次来理解。利科认为“真实”仅在它意味着“人类行动通过构型的事实以‘有效地’被重构”时,这个概念才具有保留的必要。即“真实”的问题在于人如何感知自己尚未感知的世界、如何认识自己尚未认识的自己。总的来说,“真实”并非始终不变,而是随着施为者的诠释过程无限运动着的界域,其中包含了潜在的中介平面和实在的行动世界。中介平面作为行动世界意义的根本,行动世界作为中介平面结构的支持,共同组成了“真实”的真实性。而指涉便是在中介平面中使要素和要素之间产生连结,构成经纬,从而确立出要素间的指向关系。现实/记忆因此得以重新在平面上被“发现”,进而被认为是“真实的”。
因此,非虚构写作者欲清偿债务关系的伦理意图,在经过文本的中介以后,务必要将写作者原本对其忠诚的痕迹和“真实”,置入“问题与答案”的运作之中:读者对文本所给出的信息提出疑问,并试图对这些疑问提出一个可接受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又可能在重复的阅读中,促发新的疑问和答案,甚至给出新的债务关系,提供另一种写作/摹创过程的动能。从这个观点来看,前构型阶段也具有了积极的能动性,一方面给出新答案,另一方面成为新叙事的基础。非虚构写作因此在一次次的诠释中获得了循环不息的发展动力。虽然必须承担“内容是否真实”的质问,却也因为这些质疑,而可能反复对自我与世界的同一性进行诗性的叩问与回应。这是非虚构写作对自身的“债务清偿”,亦是其对自身概念的证成。
非虚构写作的三重摹创图式
事实上,通过对三重摹创的说明,将非虚构写作与摹创概念连结起来的理由,已经得到了清楚的展示:摹创一的概念有助于指认出非虚构之所以被辨识为一种文类的原因,并彰显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作用。结合上述“叙事”概念,笔者所提出的关于非虚构的实践样态和历史脉络这些问题,便可同时置放在三重摹创的图式中被论述,进而有可能整理为一种相互交织的模型。同时,由于利科并未详细说明,摹创二的“情节化”过程具体应该如何操作,而只是强调其将异质元素综合为“非和谐的和谐”的中介作用,叙事学理论对叙事话语的关注,就可以补充“情节化”的内涵。由此来看,叙事的速度、聚焦和叙述者位置,无一不是使繁杂的事件成为有机的连结体的“情节化”装置。摹创三的引入,则赋予了“叙事”交流模型中作为讯息接收者的读者生产意义的能动性。这不仅与费伦所提出的“作者代理—文本现象—读者反应”这一叙事结构形成了概念上的连结,亦由摹创三回返摹创一的动力进一步让单向的交流成为可循环的“再对话”。对非虚构究竟是事实还是虚构的思辨,成为非虚构永远向新的诠释保持敞开的动力来源。而叙写同一行动、事件的非虚构文本,也因为作者在前构型阶段的差异,和身处不同脉络的读者在阅读时所选择的诠释基础的不同,可能出现多元的实践内容与文化意义。
虽然“非虚构写作”在国内兴起不过十余年,但其所带出的思辨皆指向对社会环境的历史性认知,所以它也延续了报告文学对写作伦理的质问,并在文化转译层面连结了相关学科前人探索的成果与脉络。从非虚构写作中所锤炼出的“实践的智慧”,深化了国内非虚构写作的特殊性,甚至进一步促使论者对这一文类的诠释,从认识论延伸向伦理学的向度。事实上,非虚构写作让我们正视的恰是写作本身责任的可归咎性(imputation)。或许在“后真相”的时代里,如何意识到自我叙说的能力,从而为自身的言论负责,正是非虚构写作所可能揭橥出的伦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