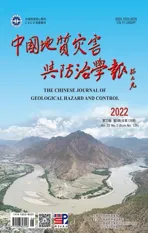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风险“点面双控”体系构建与思考
2022-07-04铁永波向炳霖卢佳燕龚凌枫高延超
铁永波,徐 伟,向炳霖,2,卢佳燕,3,龚凌枫,高延超,田 凯
(1.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四川 成都 610081;2.重庆交通大学河海学院,重庆 400074;3.中国地质大学地质科学院,北京 100083)
0 引言
受特殊地质和气候条件影响,西南地区发育有我国近1/3 的地质灾害点,也是全国地质灾害发育数量最多、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同时,西南地区也是我国重大工程规划建设的重点地区,如何提前预防和降低潜在地质灾害风险,对工程与城镇建设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1−4]。随着全国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较详细调查工作结束和新一轮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的全面推进,全面掌握我国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底数将是未来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一个重要基础。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新防灾减灾形势下,如何保障西南山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需要进一步强化“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的理念。根据最新一轮县市地质灾害较详细调查及风险普查结果,截止到2021年12月底,西南地区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约9.5 万处。从各省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数量上看,四川省约3.0 万处、云南省约2.5 万处、西藏自治区约1.5 万处、重庆市约1.4 万处、贵州省约1.2 万处。从地质灾害类型上看,滑坡约5.0万处、泥石流约1.7 万处、崩塌约1.6 万处、不稳定斜坡约0.2 万处、地面塌陷0.08 万处,其它0.12 万处。从地质灾害威胁对象上看,有约600 余万人、3 000 余亿元财产安全仍有可能遭受潜在地质灾害威胁,地质灾害风险形势仍较严峻。
地质灾害风险管控能力不仅仅只涉及到技术和管理水平,还是社会经济发展和防灾减灾要求的体现[5−8]。在新一轮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全面铺开后,地质灾害防灾减灾重点开始向预防和减轻风险转变,对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全球范围内较早开展地质灾害点风险管控探索和实践的是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早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部门就对全香港的滑坡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并建立了专业的边坡安全数据库,对因不合理工程建设开挖形成的边坡进行了系统管理和维护,并结合提高公众安全防范意识等手段,将地质灾害风险降低近50%,减灾成效明显,相关经验得到广泛推广[9]。自1999年全国高易发县市1∶10万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试点开始以来,对已查明地质灾害点风险的“点控”就已通过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实施。经过二十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基于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相结合的“人防+技防”体系已日趋成熟,特别是在“十三五”期间,普适性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实验工作取得极大进展,在地质灾害防灾减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于地质灾害风险“面控”而言,新一轮基于县域1∶5 万地质灾害风险普查是其重要的基础,从2020年开始的全国新一轮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已在西南各省、市、自治区同步开展,截止到2021年底,西南地区已有400 个县市开展了1∶5 万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包括重庆市41 个、四川省122 个、贵州省88 个、云南省75 个、西藏自治区74 个),但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地质灾害风险“面控”体系。如何构建起有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管控模式,将地质灾害风险“点控”和“面控”有机结合,提高地质灾害风险综合防控能力,是目前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急需突破的难题。
1 地质灾害风险“点面双控”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地质灾害风险“点面双控”是指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地质灾害风险区进行风险管控。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是通过1∶5 万地质灾害较详细调查后查明的灾害隐患点,按照滑坡、崩塌、泥石流等主要地质灾害类型进行划分,这些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数量、分布、规模、威胁对象等都已基本查明,并建立了数据库,可实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数据的动态更新、查询与综合分析等。地质灾害风险区主要根据新一轮县域1∶5 万和重点区1∶1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结果进行区划而得到,按照自然资源部的最新分级标准,地质灾害风险区分为极高风险区、高风险区、中风险区及低风险区四个等级(图1)。

图1 四川省喜德县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图Fig.1 Geological hazard risk assessment map of Xide County,Sichuan Province
新一轮地质灾害风险普查主要以1∶5 万(县域)和1∶1 万(重点区)比例尺为主,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易发性、危险性、易损性及风险四部分。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多采用信息量模型和证据权模型对评价指标进行计算分析,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影响地质灾害发育分布的地形坡度、坡向、断层、工程地质岩组、水系等主控因子,具体评价指标的选取要结合各地地质灾害孕灾条件的差异而有针对性地确定,如西南高寒山区考虑增加冻土因子、红层地区考虑顺向坡因子及权重等。危险性评价是在易发性评价基础上采用栅格法叠加区域多年月平均降雨量(1∶5 万县域)和24 小时平均降雨量(1∶1 万重点区),并参考不同降雨频率进行评价。1∶5 万易损性评价主要应用最新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采用栅格密度、核密度等方法对承灾体类型、数量、分布密度等因子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实现易损性评价,1∶1 万易损性评价主要采用高精度无人机航拍解译与现场调查数据进行评价,并考虑了不同结构建筑、不同年龄结构人群等因素,评价结果更为精细化。在危险性和易损性评价的基础上,将两者评价结果进行空间叠加运算后得到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结果,并按照极高、高、中、低4 个等级进行分区评价。
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影响区范围看,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地质灾害风险区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通常情况下,地质灾害风险区内会包含一个或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对有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而言,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影响区范围则是风险区内最为核心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地质灾害风险“点面双控”的核心就是在已有且较为成熟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体系的基础上,将地质灾害风险区管控一并纳入管控体系建设,形成点和面的双控模式,全方位对地质灾害风险进行预防和管控,但目前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1 地质灾害潜在风险识别精准度问题还有待提升
随着地质灾害调查技术方法的创新,基于光学遥感、InSAR、LiDAR 等综合遥感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地质灾害调查精度和准确度得到明显提升。但是,每年仍有约80%的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不在已知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库中,且每年都会造成一定数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与自然资源部陆昊部长提出的解决“隐患在哪里”、“地质结构是什么”、“灾害何时发生”等要求还有一定差距[10]。这主要与西南山区地形地貌复杂和植被覆盖度差异有关,特别是对发育在高陡斜坡上部且植被覆盖较好地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而言,即使采用最先进的遥感技术也难以对其进行有效识别与调查,故山区许多高陡斜坡的早期变形特征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这也是导致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隐蔽型强的一个主要原因[1,11−13]。
1.2 地质灾害风险区划的科学性有待提升
根据目前各省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结果看,不管是县域1∶5 万还是重点区1∶1 万的评价结果都存在精准度不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风险区面积过大,或风险区内有明显不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平缓地形、区内无明显变形灾害点等情况,地方政府在开展风险管控时难以有针对性得采取管控措施。一方面是由于西南地区不同地形地貌及孕灾背景差异极大,地质灾害控灾条件复杂,现有的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模型不适用复杂地区的实际情况,评价过程中所选择的指标也不完全能反映该地区地质灾害的控灾条件,这就会导致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另一方面,因为参与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的技术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对地质灾害发育规律认识及对风险评价技术要求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导致评价标准及尺度在统一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1.3 地质灾害风险“点面双控”机制尚不完善
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两者在边界上存在许多重叠,需要合理划定两者边界,同时兼顾局部和整体的管控成效。同时,地质灾害风险“点面双控”除了地质灾害隐患点管控机制和风险区管控机制都要建立以外,还需要对两者的管控成效进行有机结合,目前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管控措施较为完善,但风险区的管控实践目前尚无相关的经验和机制。一方面是技术层面的“点面双控”体系研究和实践经验不足,在风险管控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方面还未深入,尚未形成从调查评价到管控的技术支撑体系;另一方面是管理层面的管控机制尚不成熟,缺乏官方法规性的风险防控责任落实与相应的惩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快速和有效的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效率,特别是大众参与的积极性会得不到充分发挥。
1.4 地质灾害风险“区控”模式有待创新与示范
目前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风险预防性管控主要通过监测预警和群测群防体系实现,“人防+技防”的“点控”模式已经形成,但对地质灾害风险“区控”而言,采用“点控”的手段和模式开展风险区管控是否有效,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对风险区的管控除了要对区内的灾害点进行重点管控外,还需要从面上对整个风险区进行总体考虑。由于风险区面积相对隐患点较大,若进行全面的细化管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较大的负担,可操作性不强。若风险管控区不能全面兼顾,有可能会忽略掉有潜在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在灾害发生时不能及时进行处置,从而起不到风险管控的效果。因此,急需形成科学、合理的地质灾害风险“区控”模式,构建适用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区管控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示范,最终实现推广应用。
2 地质灾害风险“点面双控”体系构建思考
结合西南地区地质灾害发育分布规律及成灾特征,笔者认为,地质灾害风险“点面双控”体系的构建应在科学的风险评价与区划基础上进行技术层面的系统性研究和管理层面的制度化建设。在体系保障上,需要形成专业技术支撑体系、多级行政联动体系和大众知识普及体系,实现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的专业化、体系化和全民化,并在 “点面双控”试点相对成熟的示范后再进行推广应用,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图2)。

图2 地质灾害风险管控体系模式图Fig.2 Pattern diagram of geological hazard risk control system
2.1 构建地质灾害风险精细化调查评价与区划技术方法体系
对地质灾害控灾条件复杂的西南地区而言,风险调查评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与区划实现的最关键环节,通过基于县域的1∶5 万比例尺和重点区1∶1 万比例尺精度调查,基本可实现对风险底数的把握,但要实现真正的风险管控还需要更为精细化的调查评价。一方面,要在本底风险掌握的基础上提高调查评价精度,这里所指的精度不应过度关注比例尺的精度,而是要注重对承灾体和潜在风险源的精细化分类,即重点聚焦有承灾体、有潜在危险区的高陡斜坡等区域。同时,还要加强技术与管理之间的关联,地质灾害风险精细化调查评价可考虑以乡镇或村组为评价单元开展,这样成果能更好地为地方提供切实的指导,并得到及时应用,指导地方防灾减灾。此外,还要从技术层面开展地质灾害风险精细化调查评价与区划技术方法研究,特别是针对西南地区多灾害种类、多控灾条件、多成灾模式等特点,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构建,逐步增加控灾地质条件参数,优化评价模型,使得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地质灾害风险评价过程更为灵活,让结果更为科学、合理。因此,地质灾害风险精细化调查评价与区划技术方法体系的构建是风险管控体系的重要前端内容,也是实现从风险调查评价到管控全链条支撑的关键环节。
2.2 构建地质灾害“风险双控”的“双责任人”模式
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风险区管控是 “点面双控”亟待突破的难点,管理层面的创新和探索也是极为重要的环节。根据已有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管控经验,基于“人防”的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模式经受了充分的考验,成效斐然。对于已有变形或活动迹象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而言,现有的防灾减灾体系已能实现对其定期监测与风险防范,但对许多暂无明显变形体的风险区而言,如何对整个区域的潜在风险进行有效预防,需要探索有针对性的措施。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人防+技防”风险防控模式依然是风险区管控需要借鉴的经验,“人防”要充分发动风险区内受影响群众的力量参与,让老百姓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并上报,这需要探索创新一些激励机制,激发非监测员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换取最大风险预防成效。“技防”要充分应用普适性监测预警装备的经济性和便捷性,结合风险区内地质条件及潜在危险源分布特征进行系统把控,达到基于潜在危险源监测的全区风险管控目的。在此基础上,结合地质灾害风险“点控”和“面控”特点,特别是对区内有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质灾害风险区而言,要将两者进行统筹和融合,需要在地质灾害隐患点责任人(监测员)的基础上,构建地质灾害“风险区监测责任人”,即由当地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当地人组成,主要工作是对地质灾害风险区开展定期巡查、险情上报等工作,对于一些面积较大的风险区而言,可以考虑由多个“风险区监测责任人”组成。在这基础上,将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员和地质灾害“风险区监测责任人”形成体系,实现“双责任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模式(图3)。

图3 四川省喜德县地质灾害风险管控模式示意图Fig.3 Geological hazard risk control mode in Xide County,Sichuan Province
2.3 构建全民参与的地质灾害风险管控体系
西南山区高山峡谷地貌发育,许多隐蔽性强的高位地质灾害早期识别仅仅依靠专业队伍调查难度极大,依靠当地百姓对地质灾害发生前的征兆识别在实践中具有很好的成效。一方面是要建立完善的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体系,在对重点区百姓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全覆盖基础上,逐步实现对山区百姓的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全面普及,提升普通大众对地质灾害基本特征的了解。另一方面要以地方政府部门为主,形成“省-市-县(区)-乡(镇)-村-组”联动管理体系,建立完善的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惩奖制度,对在地质灾害发生前进行科学预判和合理避让的,应给予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奖励和表彰,鼓励全民参与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充分发挥老百姓的智慧和力量开展地质灾害风险早期识别。此外,还要构建永久性技术支撑体系,可通过地方政府与专业技术队伍的长期合作机制,形成稳定的技术支撑保障,对地质灾害风险及时进行动态更新,使政府开展地质灾害风险管控措施的科学性得到保障,形成技术与管理融合的风险管控机制。
3 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展望
3.1 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多元化趋势
西南地区地质灾害类型多样,成灾模式也有明显差异,故对其风险管控也需要有较强的针对性措施。西南地区多数地质灾害都由降雨引发,对滑坡而言,通常会经历蠕变、加速变形再到滑动的过程,其时间跨度相对较大,可以从数小时到数天,这也为滑坡灾害风险管控带来有利条件。对泥石流而言,从降雨、启动到冲出沟口需要数分钟到数十分钟,故对泥石流风险管控而言,在时间上的要求相对较高,需要更精准的把控,若考虑泥石流暴发的频率,则低频泥石流和高频泥石流的规模等也会存在差异,风险管控措施也需要更有针对性。对崩塌而言,由于崩塌多发育在陡坡上部,其突发性和隐蔽型极强,其前期征兆不明显,且土质崩塌和岩质崩塌的成灾模式具有差异,崩塌的发生不像滑坡和泥石流那样有较长缓冲时间,故对崩塌风险的有效管控难度极大。随着地方政府对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要求的提高,多元化地质灾害风险管控措施体系构建将是西南地区未来防灾减灾的必然趋势。
3.2 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制度化趋势
风险管控是一个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并重的过程,技术聚焦前端区划,管理注重后端管控,但综合管控体现的构建主要由政府部门主导实施,占有主导地位。随着国家对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标准的提高,作为全国地质灾害易发性最高的地区之一,西南地区必将会在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制度化方面逐渐成熟。一方面是在国家相关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基础上形成“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的地质灾害防治制度,实现纵向的管理制度化;另一方面,还会构建针对风险管控责任主体部门的惩奖机制,逐步实现横向上的管控体系化,目前相关奖励试点已在西南地区进行了较多的探索,如在2021年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棉桠镇“8·27”泥石流应急撤离中有效避免33 名学生伤亡,相关教师和村民受到四川省教育厅等单位的物质奖励和表彰,在带动全民参与防灾减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示范效果。此外,西南山区城镇和村庄建设多受地形限制,其承灾体的分布差异性极大,对不同等级风险区而言,人口密集区的城镇、存在或重要工程区若处在极高风险区内,则在降雨红色预警时要临时紧急撤离避让;高风险区应随时做好撤离准备并加强巡查与研判;对中风险区而言,高危险等级降雨预警要实行加强监测强度和密度的措施。因此,形成省、市、县等具有约束力的多级制度文件,逐渐实现地质灾害风险管控的体系化、规范化和法制化,是西南地区未来地质灾害风险管控体系构建探索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3.3 地质灾害风险管控保险化趋势
从商业保险的角度看,在西南地区投资地质灾害商业保险成本相对较高,且现行的保险补偿机制具有不对等下性,实施起来较为困难[14−16]。一方面是西南地区地质灾害种类齐全且频发,因地质灾害带来的潜在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概率较大,因灾害本身带来的潜在风险相对其它地区会较高。另一方面是受西南山区百姓文化水平影响,人们对地质灾害的基本知识掌握程度还不够,对地质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加之山区农村的“空心化”等现象,也使得他们在面对地质灾害时的抵御风险能力相对较低。随着西南地区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政府部门对山区百姓的地质灾害知识普及力度加大,人们对生活条件的满足感及对生命的重视程度增加,地质灾害保险商业化的各项条件已日渐具备,在相关制度日趋完善的背景下,地质灾害保险商业化也必然会成为未来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的一个趋势。
3.4 地质灾害风险管控智能化趋势
地质灾害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其风险等级、风险区范围也会随着地质灾害数量的增减发生动态变化,因此,地质灾害风险管控体系必然也要面临一个实时的、动态调整的过程。对地质灾害孕灾背景复杂、地质灾害风险动态变化更新快的西南地区而言,对大量灾害点、地质及社会经济数据的统计分析与风险区划更新需要有庞大的人力及物力支撑,且区划结果更新的时效性也会受到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将西南地区地质灾害已知隐患点、已知风险底数及孕灾背景基础数据数字化,在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模型构建的基础上,构建智能化地质灾害风险动态评价与区划系统,尤其是对解决不在已知隐患库内的80%新发生地质灾害隐患点识别而言,实现基于“地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动态更新,在此基础上探索地质灾害风险数字化管理与决策,也是未来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智能化的一个新趋势。
4 结论
(1)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风险家底基本查清,但目前的评价成果与地质灾害风险精准管控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风险评价与区划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评价尺度和评价单元的针对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风险调查、评价及区划的精细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2)西南地区地质灾害类型多样,成因机制复杂,地质灾害风险管控体系的构建难以通过速成达到预期效果,相关的调查技术、评价模型及区划方法构建需要经过充分论证和实践后再推进,从技术层面提升风险管控前端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风险区内承灾体多样,实现不同类型承灾体和不同文化层次社会群体的兼顾难度较大,需要逐步形成完善的体制或制度,从充分发挥风险群测群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管理层面提升风险管控后端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4)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风险“点面双控”体系构建的核心是地质灾害风险区管控的实现,涉及到的技术和管理层面内容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在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同时,还要打通两者之间融合的壁垒,让风险管控体制更为成熟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