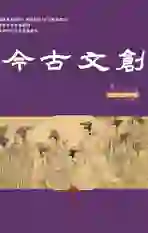论村上春树小说创作中的“ 洞穴 ”原型
2022-06-22祝越
【摘要】 村上春树的多部小说中都有着类似的“洞穴”原型,该文章选取其代表作之一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分析其中两种“洞穴”原型的表现形式、特征与内涵。小说中的“世界尽头”小镇与夜鬼的地下圣域都是“洞穴”原型的变形,二者都具有封闭、黑暗和安静的特点。而在相同的特点背后,其延伸内涵各有侧重,“世界尽头”侧重于表现小镇的封闭性与人类的工具化,地下圣域的刻画则主要强调其原始的神秘感与危险性。但从本质上而言,小镇是继承了地下圣域的神秘与危险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而作为另一条支线的“冷酷仙境”则是在现实世界中继承了独角兽小镇“异化人类”的内核。由此,通过结构上的层层嵌套,作者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牢固的禁锢人“心”的“洞穴”,对现代社会人类生活空间的被挤压,人心的异化进行了奇幻式的呈现与批判。
【关键词】 村上春树;洞穴;原型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0-0031-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0.008
村上春树作为日本当代的重要作家之一,其作品也自然受到各领域学者的青睐。许多学者将其归入日本后现代作家之列,并关注村上作品中体现的后现代色彩,例如消费性,以及对意义和自我的消解等(王向远,1994)。此外,村上小说的寓言性特质也受到较多的关注,其小说的“物语特色”,创作的“物语观”等也得到了许多研究。而对这种寓言式小说的研究,则自然离不开对其中丰富意象的解读与分析,“森林”“水井”及动物等意象就受到了较为集中的关注,其中“井”的意象由于在多部小说中反复出现,因此研究成果颇多,邹波围绕“水井”这一意象分析了村上小说中的“水井”谱系,以及其在《奇鸟行状录》中的隐喻内涵(邹波,2015),对这一意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和分析。
村上春树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并不只是“水井”,还有“通道”“地下洞穴”“狭窄的房间”等意象,例如《1Q84》连接两个世界的高速路上的通道,《刺杀骑士团长》中“我”顺着幽暗的通道去寻找少女,《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通往夜鬼圣域的通道与森林中连接两个世界的湖,《舞!舞!舞!》中海豚宾馆里的羊男为“我”守候着的那个房间……虽然不似“水井”那样明确,但它们在作品中都共享着同样的特征——狭窄、阴暗、幽深、封闭,且有着类似的“连接”作用,作者往往要进入这些“井”或“通道”去寻回一样东西。事实上,“水井”与“地下通道”等意象,都能够归入一个更为原始的意象,即“洞穴”这一原型。
荣格在其分析心理学的研究中提出了“原型”这一概念,它是人类共有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人类在远古时期不断重复累积的原始经验沉淀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形成的心理结构便是“原型”(荣格,1987)。而原型批评则将心理学中的“原型”概念移至文学领域,通过寻找文学现象背后的“神话原型”,对具体个别的文学现象进行更加本源意义上的阐释与解读。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便存在着很多的“原型”,如《寻羊冒险记》就被日本学者大塚英志认为是遵循英雄冒险的“单一神话”的模式,王玥也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从“单一神话”的视角对村上的作品进行解读(王玥,2012)。
而学界对村上春树作品中的“洞穴”原型则还没有太多的研究和论述,这一原型在村上的小说中大多并非表现为现实具象的洞穴,而是在原型基础上的一种变形,随着村上的写作越发成熟,“洞穴”原型也越发清晰、突出地呈现出来。《舞!舞!舞!》(以下简称为《舞》)中的“房间”,《刺杀骑士团长》里的“通道”和“枯井”,《奇鸟行状录》里的“枯井”,以及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下简称为《世》)中,被称为“世界尽头”的小镇,和夜鬼居住的黑暗狭窄的地下通道。意象背后深层的“洞穴”原型使这些具体意象共有着相似的特征与作用。可以看出,村上春树的小说中存在着“洞穴”原型的不断变形,这一原型结构反复在不同作品中出现,因此对其进行研究也就是必要的。本文尝试缩小研究范围,以《世》一书为中心进行细读研究,分析其中的“洞穴”的表现形式及特征,进而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内涵,呈现出《世》一书中两种“洞穴”的区别与联系,使小说的结构更加明晰。在《世》中,通過对“洞穴”原型的反复描绘、采用,村上春树将小说的世界也建构为一个牢不可破的“洞穴”,从而将小说中的人物封锁其中,并借此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批判。
一、“洞穴”原型的表现:封闭、黑暗和寂静
《世》一书中的“洞穴”原型,如前所述,主要有两种最为明显的表现形式。一是作为小说中两条支线之一的“世界尽头”,即生活着独角兽的小镇;二是小说中的“夜鬼”的圣域,即“我”和“胖女郎”为了找到她的“祖父”而前往的那个秘密栖身场所,一个地下洞穴。这两个“洞穴”在小说中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作者在书写的过程中,却或有意或无意地为它们赋予了类似的特征,并在多处加以强调,可见二者实则是由同一种原型变形而来。首先,二者在形态上就都呈现为一种“洞穴”,小镇由围墙紧密包围,而在“冷酷仙境”中图书馆的女孩所提到的“外围山”,可以视作“世界尽头”的小镇形态的一个注脚,可见小镇中的人与兽生活在一个四周封闭的“山丘”之中,只有西门可以出入;而夜鬼的地下洞穴的形态则更为清晰,书中的“我”通过一条狭窄的黑暗通道进入,而最终到达一片更为开阔的封闭场所,即夜鬼祭祀的圣域。可见,小镇与地下洞穴都是一种“洞穴”的表现。而不论是世界尽头的小镇,还是夜鬼的地下洞穴,都有着封闭、黑暗与安静的特征。在具体的语境中,这些特征由不同的描绘方式展现出来。
小说中“世界尽头”作为与“冷酷仙境”相对的另一个世界,表现为一个充满欧洲风情的静谧小镇,在这里人类与独角兽共存,过着远离纷扰的生活。作者在一开始就点出小镇的“静”。生活在小镇中的独角兽是安静的,“安静得近乎冥想,连呼吸都像晨雾一样悄然安然。”(村上春树,2007)小镇中的建筑也是“沉默的”,被一种“淡漠的失落感的氛围”(村上春树,2007)所包围。作者对小镇简约的建筑风格,以及无人烟的氛围反复渲染,使“世界尽头”的小镇如其名称一样笼罩在沉重的寂静之中。9A12BED8-D238-43C5-A21B-7259BF963ED4
除了“静”之外,村上还着重表现了小镇的“封闭”。小镇中的“围墙”是一个重要存在,不论是直接通过“我”的双眼所见,还是借看门人之口,作者都多次强调围墙之高,看门人还骄傲地介绍围墙的严丝合缝,“其缝隙连一根头发丝都别想伸进。”(村上春树,2007)这都是直接从外表描绘了小镇的绝对封闭性。而“围墙”不仅在外围住小镇,它也从内部一点点地使小镇的秩序固化。进入小镇的人必须舍弃自己的影子,此后,人的“心”也会一点点丧失,而围墙则是“任何心的残渣剩片都不放过的”(村上春树,2007),它将心的碎片统统吸光,从内保证了小镇的封闭性。“围墙”使小镇坚不可摧,小镇中的一些“规矩”也是其表现,例如看门人每天按时将独角兽放出小镇,之后又将它们召回;例如“我”作为读梦人每天的读梦工作。这些规矩与工作都已经失去了意义,但人们却始终墨守它们而不做改变,这种对规矩的绝对遵守也是小镇“封闭”的表现。
对于小镇“黑暗”的特点,作者着墨不多,但也并非没有表现。在“世界尽头”的小镇中,村上所着重塑造的是“我”所见的个人空间的“阴暗”。“我”是作为“读梦人”进入小镇的,而为了获得读梦的资格,我的双眼留下了伤痕,因此必须避开阳光,生活在阴暗的环境中。这使得故事叙述者的“我”失去了阳光,而“我”的生活空间,以及透过“我”的双眼所见的小镇的景色也就自然被限制在了阴暗的环境内,阳光反而成了带来伤害的存在。除此之外,村上还时常渲染小镇“暗”的氛围,例如描写图书馆内部的阴暗,或是渲染冬天沉重阴暗的天气等。
小说中对于夜鬼的地下圣域的特点,大多则是直接进行描绘。相比起小镇的静谧安宁,夜鬼的地下洞穴则险象环生。与“世界尽头”不同,夜鬼的地下圣域仅在小说中的一段情节中作为环境出现,因此作者对其的描写篇幅总体而言较少,但也使其特点更加集中突出地呈现出来。地下洞穴的“封闭”更多的是外部直接的封闭,由于深入地下,“头上星月皆无。只有黑暗重叠地压在身上。亦无风,空气沉甸甸地滞留在同一场所。”(村上春树,2007)对于地下洞穴的黑暗,作者则毫不吝惜地进行层层描绘,渲染出“黑暗”之浓与重,描写通道中“一色浓黑,黑得像要把人的手吞噬进去”(村上春树,2007),甚至令人怀疑起自己的身体是否存在。地下洞穴的黑暗仿佛具有了实体,将通道中的人们严密地包围。关于“静”,村上则是巧妙地借“我”听到胖女郎足音之后思绪的一系列延伸、跳跃,侧面衬托洞穴中的安静。其黑暗、寂静和封闭的特点背后都延展出一种原始的危险以及人类本能对未知的恐惧。
综上所述,“洞穴”原型的象征在《世》中表现为两种具体形态,即“世界尽头”的小镇与夜鬼的地下洞穴。二者在外部形态上都呈现为一种只有单一通道的、半封闭的“洞穴”形态,而在作者的笔下,它们共有的封闭性、黑暗与寂静的特点也得到了着重强调与渲染,足可见二者是同一种“洞穴”原型在不同具体语境下的变形。
二、“洞穴”原型的内涵与嵌套结构
世界尽头的小镇与夜鬼的地下圣域同属于“洞穴”原型的变形,但在具体语境中,两种“洞穴”所表达的内涵却有所不同。独角兽小镇表现的是“洞穴”的封闭性以及对意义和“心”的消解,地下圣域则更集中营造了“洞穴”的原始神秘感和危机四伏。两种“洞穴”呈现为一种嵌套关系,并最终构成了《世》这一小说世界整体的“洞穴”。
作为“洞穴”的小镇,其封闭性延伸出的是小镇生气的缺乏,其中的人与兽都失去了生活的意义而沦为维持小镇运转的工具,且人們不再对于离开小镇、摆脱围墙的控制一事抱有希望。从建筑开始,作者笔下的小镇就是没有特色、平淡至极的。而小镇中的人与独角兽,都是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无意义的生活,独角兽每日进出小镇,冬天死去而又春天降生,不断循环往复;镇中的人虽然有各自的职业,但也只是一种不解其内涵的重复劳动。更重要的是,小镇中的人都会逐渐地丧失“心”,而彻底地沦为一种工具。而作为“洞穴”的地下圣域,作者则侧重于表现其作为原始祭祀场地的神秘性与对人类的威胁性。“黑暗”象征着一种世界原初的状态,是还未被人类创造的城市霓虹灯覆盖的状态。因而生活在地下黑暗中的夜鬼与“组织”和“工厂”分立,是有别于现代文明的原始存在,而它们的祭祀场所则由于这一深埋于地下的黑暗环境增添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也由于其神秘和未知的特点,使人加深了对地下圣域这一“洞穴”的恐惧感,作者对其狭窄、封闭、黑暗和寂静的反复刻画,都进一步渲染了其危险性。
但二者在具体语境中延伸出的不同内涵方向,却在深处有着自然而紧密的联系。总的说来,小镇之“洞穴”实际上是夜鬼之“洞穴”在文明社会中的复刻和翻版,而被称作“冷酷仙境”的现实世界,虽然没有“洞穴”的形态,却继承了非现实世界中小镇“洞穴”的内核。作为“夜鬼”这一原始存在的生活环境,地下的世界是神秘且危险的,对于人类而言则是肮脏和具有威胁性的,然而它们也有自己的秩序与原始逻辑,例如对鱼和黑暗之神的崇拜,以及原始的祭祀仪式。同样,有着更为完备文明的小镇中,人们虽然生活安宁,却也摆脱不了小镇中神秘的危险。围墙对人心的吸收,冬天森林的危险性以及水潭的漩涡都是小镇安宁生活背后的潜在威胁,面对这些威胁,小镇中的其他人都只知其有,而不知其为何存在,只是将它们作为一种规约接受下来。
而镇子里的各项规矩也同样,规矩自然存在,而其中的原因则被消解,也无人追问。这就使“世界尽头”的小镇与夜鬼的洞穴有了深层的连接:两种“洞穴”中都有着无法把握的神秘部分,且对于生活于其中的生物而言都是一种威胁,同时“洞穴”中的生物都遵循着约定俗成的规约,有着自己的“仪式”。可见,即使小镇脱离了夜鬼地下世界的肮脏与原始状态,但其本质仍然是夜鬼地下“洞穴”的一种复刻和翻版,而在这一复制基础上,作者更强调“洞穴”生活中“人”的丧失。
小说的另一条主线“冷酷仙境”,则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社会结构理性有序的文明世界,这是“我”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作者虽未塑造其“洞穴”的形态,但却仍然使它继承了小镇这一“洞穴”的内核。在“冷酷仙境”这一科技社会中,人被工具化,成为社会发展进化中的实验品、牺牲品,而失却了本应该有的“人的生活”。“我”在小说中的一连串离奇曲折的经历便是最好的例证,“我”作为一名计算士,在不了解工作缘由及目的的情况下为人工作,但“我”只是博士庞大计划中的一个工具而已,最终这也危及我的生命,使我未来生活的梦想破灭。小说中的博士为了推进人类的进化而研究消除声音的技术,这无疑是在不断地磨去人作为人的生活,仅仅保留其工具的部分。9A12BED8-D238-43C5-A21B-7259BF963ED4
综上所述,小说中塑造的两个“洞穴”在其表象之下隐含的内涵既有不同的侧重,又有深层的联系。夜鬼所在的地下世界暗示着一种原始的神秘性与危险性,而“世界尽头”的小镇在继承了原始洞穴神秘性与危险性的基础上,更突出地表现了“洞穴”中人的异化,人沦为社会运转的工具。即使没有狭窄的地道,没有高耸的围墙,现实的“冷酷仙境”也仍然继承了小镇作为“洞穴”的内核,现实中的“我”同样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成为博士计划的工具,计算士与符号士们同样在不清楚世界真相的情况下为各自的组织卖命。
通过对同一原型的反复套用和对其内核的多次继承、延伸,村上春树在小说的世界中构建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洞穴”,从夜鬼的地下世界到“世界尽头”的静谧小镇,再到拥有现代文明的“冷酷仙境”,虽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内核都是否定人的“心”,而保留其“工具性”的“洞穴”。“洞穴”在村上的笔下成为一个禁锢的象征,且因小说结构的设置而呈现为层层嵌套,密不透风的监牢,主人公似乎无处逃生,无处安放他的“心”。这既是作者对故事中人物生存空间的禁锢,也是作者对现代社会的观察,对高速发展的科技社会挤压了人的生存空间这一现象的担忧与批判。小说中的“我”最后选择了将意识留在世界尽头的森林里,试图寻找一条不至于失去心的出路,而活在现实世界的我们又要去哪里守护我们的“心”呢?
三、“洞穴”原型的发展
除了本文主要探讨的这部小说之外,村上春树的其他几部小说中也有类似“洞穴”原型的运用,较为明显的是《舞》中海豚宾馆里的房间,作者也着重刻画了其幽暗、封闭和安静的特征。作为《寻羊冒险记》的续篇,《舞》承续了“青春三部曲”中的孤独主题,海豚宾馆中羊男守候着的房间成了“我”心灵的归所,其作用是使“我”能与他人、与世界建立连接。作为“心灵的房间”,海豚宾馆中的房间与世界尽头的小镇有些许相通之处,“世界尽头”代表着“我”意识的内核,或者说“是‘我创造出的,是‘我的内心。”(王茜萌,2017)而不论是“世界尽头”还是“冷酷仙境”,主人公都面临着同样的孤独,现实世界中与人没有连接,非现实世界中也无法与失去心的女孩相爱。可以说“孤独”仍然贯穿于两部作品的“洞穴”的内涵之中。
而在《舞》中隐含于字里行间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讽刺意识,显然在《世》中借用“洞穴”原型得到了更强烈的发挥。《舞》作为续篇,在故事、风格和主题上都更靠近“青春三部曲”,而《世》作为一个獨立的长篇,则得以将笔墨集中在刻画现代科技文明对人的异化,对“心”的禁锢和吞噬上,因此将“洞穴”这一原型象征本身的封闭感渲染得淋漓尽致,在这一封闭空间中,人类日复一日地为进化出力,但最终却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车轮下失去了对科技的控制力。这种批判性在村上春树的后期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奇鸟行状录》对战争与暴力的反思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奇鸟行状录》中,“洞穴”成为一个介入暴力的通道,为主人公提供了对抗暴力的途径和指引。
“洞穴”这一原型在柏拉图的隐喻中,是一种封闭、虚假世界的象征,其后在漫长的文学史中也有学者和作者对其进行不断地再解读与再创作。村上春树在许多小说中都或有意或无意地加入了“洞穴”原型,其创作在沿用了“洞穴”这一基本原型内涵的基础上,又添加了很多贴合现代社会的内容,例如《舞》中的房间就是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核心,这正是与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有关的。可以说,村上春树的小说中建立起了以“洞穴”原型为基础的意象体系。除上述作品以外,村上春树其他小说中的“洞穴”原型,以及这些原型在村上的写作历史中的形成过程,其背后的深层文化无意识等问题,也值得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向远.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村上春树[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5).
[2]邹波.村上春树的“水井”谱系及隐喻——以《奇鸟行状录》为中心[J].日语教育与日本学,2015,(02).
[3](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4]王玥. “单一神话”视角下的村上春树作品解读[D].中国海洋大学,2012.
[5](日)村上春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6]王茜萌.论村上春树的物语观[D].南京大学,2017.
作者简介:
祝越,武汉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9A12BED8-D238-43C5-A21B-7259BF963E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