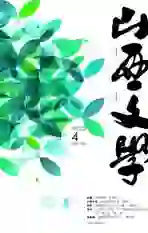托尔斯泰的林中草地
2022-04-04方丽娜
1
时光仿佛停滞在一个多世纪前,素雅的客厅,静穆的书房,凉丝丝的楼梯扶手上还残留着主人的余温,隔窗望去,远山、丛林、田舍,以及河塘对面晴朗而葳蕤的苹果园。这是一块可以从容思考的土地,也是一片可以畅谈理想的处所,置身其间,使得托尔斯泰的写作有着难以抵御的从容和博大。无论是美德还是罪过,是远方风暴一般横扫战场的骑兵,还是近处撕扯纠结的七情六欲,都从这醉人的绿色里汩汩流出。
托尔斯泰有两处可供瞻仰的故居,一是图拉州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另一处是莫斯科列夫·托尔斯泰街上的淡金色别墅。无一例外的青草蔓延、林荫夹道,连同斯拉夫式的翡翠色屋顶。
2015年夏季的莫斯科,祥云低挂,树影婆娑,伴着几声小山雀的鸣叫,恬然静谧,我将目光从窗外的白桦林,移注到托尔斯泰的客厅。沙发、餐桌、挂像,还有妻子索菲亚的风景画,全都定格成主人生前的模样。墙上的托翁须髯飘飘,目光深邃而略带忧伤,好似在问: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与19世纪沙俄时代上流社会盛行的奢华相比,托尔斯泰的居所优雅、大气。50岁之后,他主要栖居在莫斯科这栋小巧精致的别墅里。如今的橱柜里还挂着主人的猎装、睡衣和毛皮外套,偏安一隅的墙角立着沉寂百年的三角钢琴,唯有过道里的英式落地大钟不知疲倦,每逢整点,仍旧为老宅报时。面对托翁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我都有种恍惚般的亲切。仿佛它们的主人并没有走远,而是在回廊下张望、打盹儿,抑或在草径上散步。不由得想起冯骥才先生的一句话:作家作品之外的部分,就在他的故居里。但前提是,他的故居一切照旧。
托尔斯泰一生充满了叛逆:他出身贵族,却痛恨奢侈;他蛰居乡野,但时刻关注欧洲局势;他赞美爱情,却视婚姻为人生的枷锁。他曾说:在俄罗斯,生活是一种永久的折磨。幸亏在艺术、诗歌和友谊的天地里,还能找到避难所。
那一年的六月,列宾和契诃夫来了,屠格涅夫和柴科夫斯基也来了,他们就坐在这间洒满阳光的客厅里,自由自在地饮茶、聊天、争论,静立一旁的书柜钢琴和英式大钟,俨然忠实的听众,淹没在他们的争论与和解之中。午后的托翁与故人下完了棋,饮完了酒,就在契诃夫和柴科夫斯基的注视下,坐在黑色的三角钢琴前,轻抚琴键,随心所欲地弹了一段柔美的和弦。
俄罗斯媒体人苏沃宁曾说:“我们有两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列夫·托尔斯泰。这个无冕之王,令尼古拉二世的王冠和王朝一度摇摇欲坠。”
一个阴霾蔽日的黄昏,70岁的托翁正伏在书桌前,为他最后的杰作《复活》苦思冥想,而后写道:“当聂赫留朵夫到火车站送别玛丝洛娃时,他见到的已不是往日那个精神萎靡、愁眉不展的她,而是一个性格开朗、乐观向上的玛丝洛娃。她汗涔涔,红彤彤的脸蛋上,绽开了爽朗的笑声。”稍后,他走进大女儿托尔斯塔娅的房间,兴奋地问:“你猜,我的聂赫留朵夫和喀秋莎怎么样,他们会结婚吗?嗯,实际上,人物一经塑造出来,便开始了他们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再受我的意志支配了。”
年轻时的托翁,酗酒、赌博、沉迷女色,甚至染上过性病。可他的晚年厌恶贵族们的寄生生活,同情苦难的底层民众,他带着负罪感试图与过去一刀两断,放弃世俗生活,成为彻底的清教徒。托尔斯泰主义最著名的拥戴者,是东方的印度圣雄甘地。
乔叶在她的散文《托尔斯泰的声音》里,如此写道:“相比于四面光八面净完美无瑕的神,我更爱犯过错误走过弯路做过蠢事的神,因为他来自于人,和我一样的人的肉身。”
她说得真是太好了。
2
远行到图拉的庄园去,不是屈服于它的博大,而是为了那方简朴的墓地。
托翁的墓冢,孤零零躺在自己早年栽种的白桦林的浓荫下。不过是一方幽暗的土丘,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没有墓志铭,甚至连托尔斯泰的名字都找不到,然而,它却是茨威格眼中“世间最美的坟墓”。事实上,任谁站在这里,也不会无动于衷的。有谁能够否认——这个人,比任何一个梦想死后永垂不朽的人都更不朽?
一个真正伟大的生命,从来就不会因为其肉体的寂灭而落幕,也不会因其墓碑的大小,而削弱他在人们心中的分量。生前受声名所累的托翁,愿意自己像农夫、士兵或者流浪汉一样,不留姓名地被埋葬,伴着旷野的风儿,全然化为泥土。可他的灵魂,如同七月的阳光,笼罩着林间草地和四季长风,又像是一个凡心未泯的天使,长着强有力的翅膀,永驻人间。
庄园的环境赋予托尔斯泰喷涌的创作灵感,并推动着一个个故事情节的拓展。《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就诞生于此。托尔斯泰本人曾这样描述图拉庄园在他生活中的角色和作用:“如果没有我的亚斯纳亚-博利亚纳庄园,我很难想象俄羅斯,以及我对她的态度。”
窗帘低垂,晚霞斜照,托尔斯泰一声叹息,凝重的空气中安娜与沃伦斯基邂逅于大雪纷飞的月台上,娜塔莎与安德烈的生死诀别,在廊檐下的白色圈椅上点点滴滴地酝酿着,苦苦思索中,被金属笔尖划过的痕迹,不经意间留在了幽暗的书桌上。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在所有的小说家中,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对于《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我们除了这么说,还能说什么呢?
博利亚纳庄园,俄语意为“明亮的林中空地”,是托尔斯泰的母亲——沃尔康斯基公爵小姐的嫁妆。托尔斯泰生来贵族,坐拥伯爵头衔,而这块接近农耕时代原始风貌的土地,却唤起他童话般的遐想:愿全世界的人都脱光了衣裳,匍匐在田野上。庄园之外绿野广袤,红土地,黑土地,连同茂盛的夏庄稼和葱绿掩映中的小教堂,一幅色彩斑斓的斯拉夫油画,在雄浑凝重的天幕下铺展开来。有那么一刻,我站在银墙碧瓦的廊檐下,想象托翁当年骑着高头大马,徜徉于杂草丛生的旷野间,悠扬的钟声划过山顶教堂,瞬间掠过如镜的水面,我周身的血液直往上涌。
我迷恋托翁作品中的俄罗斯乡村风俗,以及西伯利亚的广阔图景,它们与图拉庄园的辽阔、葱翠一脉相承,浑然一体。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那样,托翁乐于回归田园,做一个充满激情的园丁,亲手种下数千棵苹果树。在与大自然的交流对话中,他喷涌的灵感纷至沓来,纵情演绎人世间的交响曲。gzslib202204051439晚年的托翁喜欢早起,他手拿拐杖,疾步行走在笔直的林荫道上。即便是晚上,月光下的林中草地也是托翁的最爱。他边走边思考,困惑、郁闷以及和周遭的疏离与隔膜,一股脑倾泻在草甸子上。
在相距180公里的两处寓所之间,托翁常常步行。他身着普通长袍,肩上搭个口袋,看上去跟沿途的老百姓毫无区别。途中的食宿就在车马店里解决。沿途经过火车站时,托翁就到三等车厢的候车室里歇歇脚。有一次,他在月台上徘徊时,刚好碰到一辆客车,车上的老太太招呼他道:“唉,老头儿,快去盥洗室里把我的手提包取来,我忘在那里了!”托尔斯泰急忙奔过去,幸好,手提包还在。
老太太慌忙掏出五个卢布,递给他说:“多谢你了,给,这是赏钱!”
托尔斯泰不慌不忙地接过赏钱。他一点也不在乎别人把他当做普通人。
2010年的北京黄昏,鲁迅文学院第13届高研班的讲坛上,请来了艺术家陈丹青,不久前他刚从俄罗斯走访归来。那个时期,陈先生写了不少中外文艺评论,自然与人文相互关照,令人耳目一新。我端坐在鲁院的讲坛下,听陈先生深情讲述他的苏俄记忆,和他那永不磨灭的托尔斯泰情结。陈先生14岁开始阅读《战争与和平》,眼下已读到了第五遍。他说,托翁的文字一经触碰,便痴迷其中,像少年一样癫狂。彼时的鲁院窗外,瓜果蔬菜的叫卖声,夹杂着往来人声的鼎沸与喧嚣,隐隐浮荡在鲁院的讲堂里,与陈先生沉稳而谨严的讲述相映成趣。
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会产生托尔斯泰。陈先生瞳仁微突,语调凝重地说。
但我想,在中国的土地上虽没有诞生托尔斯泰,却产生了像他这样不朽的读者。
回到维也纳我再次捧读《战争与和平》。娜塔莎与安德烈的情爱最是牵动我的心,弥留之际的安德烈和娜塔莎相拥而泣的情景,屡屡让我泪流满面。而读《安娜·卡列尼娜》时,我总是止于走投无路的安娜在站台上的纵身一跳。万念俱灰之后,感觉自己随着她的灵魂溘然飘逝,就再也读不下去了。
3
幸运得很,陪伴我们拜谒托翁故居的白嗣宏先生,旅居莫斯科多年,是位集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于一身的学者型作家。他翻译的《托尔斯泰戏剧集》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与此同时,白先生也因其在文学方面的特殊贡献,荣获俄罗斯作家协会颁发的“舒克申奖章”。
古稀之年的白嗣宏先生,银丝满头,谦逊儒雅,言谈间一派中国老式学者的风范,君子之风,绅士之态,同时交织在他身上——一种东西方文化浸润其中的精神与人格,令人肃然起敬。白先生祖籍河南开封,前不久夫妇俩特意回古都开封游历、怀旧。白太太是德俄血统,叶卡捷琳娜后裔,见过的人都说她气质典雅高贵,肤白貌美,当之无愧的皇室后裔。白先生早年毕业于久负盛名的圣彼得堡大学语言文学系,他翻译的前苏联剧作家阿尔布卓夫的经典话剧《老式喜剧》,由北京人艺搬上了舞台。
从托翁故居出来,白先生邀我们坐进了莫斯科一家德式餐馆。酷爱音乐的白先生得知我先生是奧地利人,便谈起早年和太太专程来维也纳听歌剧的往事,眉宇间满是欣喜和恋念。餐馆里洋溢的德语氛围,熟悉的啤酒品牌,以及络绎不绝的德国游客,令我联想起1941年的冬季,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当时的德国“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上将的司令部,就设在托翁故居。多年后,古德里安在他的回忆录中表明,出于对托尔斯泰的敬仰,他和部下丝毫没有破坏托翁故居。
晚年的托尔斯泰,对东方文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尤其推崇老子思想。他感慨于中国人保留的农业社会的原貌和美德,并惊叹于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哲言,称其充满了自我完善与爱的内容。那个时候,还没有俄语版《老子》,托翁便找来法文译本研读。在他的影响下,当地一些贵族和作家也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有时候,命运总以奇特的方式,让遥远的灵魂交汇、碰撞、并擦出火花。
还是在莫斯科的托尔斯泰小庄园里,白先生和我们徜徉于花草蔓延的白桦林里。这里虽不及图拉的博利亚纳庄园那样浩瀚、幽深,但它玲珑精致,处处透着主人的风雅。披着淡阳的白先生,凝神注目回廊下托翁常坐的带花纹的棕色小沙发,一只乌鸦在林子里聒噪,两条黑白相间的比格犬从廊下走过,他都毫无察觉。
1910年托翁的最后时光,与妻子索菲亚严重分歧,从而深陷焦虑、困顿及崩溃的边沿。为了寻求精神的解脱和心灵安宁,82岁高龄的托翁秘密出走,辗转于冬季的俄罗斯,途中不幸患上了肺炎,在一个小火车站病逝。
【作者简介】方丽娜,祖籍河南商丘,现居奥地利维也纳,毕业于商丘师院英语系,奥地利多瑙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发表和转载于《人民文学》 《中国作家》 《北京文学》《十月》《作品》《小说月报》等。著有小说集《夜蝴蝶》《蝴蝶飞过的村庄》,散文集《蓝色乡愁》 《远方有诗意》等。代表作“蝴蝶三部曲”。现任欧洲华文笔会会长,欧华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