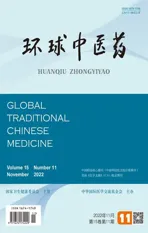高社光从五郁痰凝论治失眠
2022-03-23胡翠平李莉赵慧娟李海英
胡翠平 李莉 赵慧娟 李海英
失眠是影响现代人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中医各家对本病诊疗有丰富的经验,睡眠的机制医学家已经研究多年,仍存在许多未解之谜,诸如神经递质、内分泌激素以及免疫细胞因子等等均参与机体的睡眠—觉醒活动,睡眠—觉醒机制通过科学家们的研究仍未能完整解释,其相关的研究存在相当困难的挑战。失眠是中国成年人的常见睡眠问题,在中国的成年人中符合失眠症的诊断标准者在10%~15%[1]。改善睡眠质量、延长有效睡眠时间、缩短睡眠潜伏期、减少入睡后觉醒等等方面西药仍占据着重要地位,但部分患者服用后的宿醉反应、依赖性、耐药性、停药反跳等不良反应时刻困惑着人类。
高社光为河北省首届名中医、首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优秀学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贴专家。高社光通过多年临床经验并结合古今文献,发现“脏郁”和“痰凝”为失眠的核心病因,五脏郁滞在痰邪的催化下表现出不同症状的失眠;失眠—脏郁—痰凝—失眠常相互搏结共存,致疾病缠绵难愈,故而在治疗上提出分脏调郁,祛痰转机的理论,使机体达到阴阳和合的平衡状态。
1 五郁者发病之机也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2]中“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启发,在张介宾《类经·运气类》中认识到:“天地有五运之郁,人身有五脏之应,郁则结聚不行,乃致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化不化,而郁病作矣。故或郁于气,或郁于血,或郁于表,或郁于里,或因郁而生病,或因病而生郁”。提出了虽然心、肝、脾、肺、肾诸脏与失眠有关,但辨证重点在于郁,责之于痰—五脏皆可发生郁,亦不离痰。孙思邀《千金要方》:“五脏者,魂魄宅舍,精神之依托也。魂魄飞扬者,其五脏空虚也,即邪神居之,神灵所使鬼而下之,脉短而微,其脏不足则魂魄不安。魂属于肝,魄属于肺”从而可见典籍中亦有相关五郁的记载。
1.1 肝郁者,不达也
肝郁表现在临床实践中最常见,而《四圣心源》中曰:“凡病之起,无不因于木气之郁,以肝木主生,而人之生气不足者,十常八九,木气抑郁而不生,是以病也”。肝的生理机制主要是疏泄和藏血。它的疏泄可调节机体之气机,气机条达则情绪安然,脾运健硕,胆汁泌泄合顺。肝有血藏则精神安养,魂有所依,魂可节制眠—醒循律。魂生于心,而从肝受之,魂生活在肝中,依靠肝中精血滋养,而人类在活动时血液移动至经中。魂活跃之时,正是人类躺下休息的时候血液又流回肝脏。其《血证论》中曰:“肝病不寐者,肝藏魂……若浮阳于外,魂不入肝,则不寐”。因此,可通过肝的疏泄条达功能正常,以及肝血的滋养,还有肝阴的濡润,便使人类精神平和,就可以安然入睡。
现代医家多从肝郁入手研究失眠,周建[3]用调肝安神方治疗肝郁型失眠在临床中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并提供了有效的分子生物学指标支持。王婷婷[4]通过对中药药对的研究在基因层面为调控肝郁来治疗失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谢炜[5]运用柴胡桂枝汤治疗肝郁失眠可明显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和日间症状。
综上高社光认为情感的内在伤害会导致肝气郁结,肝舒不畅,气机受阻,气郁火化,火性炎上,扰动神明,使躁动不安的人无法入睡。气机的停滞导致精气血运行不畅通,使人心神失去营养而失眠,临床上常常会有烦躁,口干,口苦,睡中惊醒,或表现为醒来后难以入睡。亦有肝气横逆犯脾,脾不健运,水谷不化,导致神明失养而失眠;并有脾失运化引起的痰湿滋生,痰阻气机,郁阻化火,以致心神异常或痰浊困扰神明引起失眠。还有肝脏过度疏泄时,则很容易损伤肝血,阴血不足,致肝阳亢盛,而失眠频发。
1.2 心郁者,不发也
早在《景岳全书》[6]中就记载有:“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心是人类内脏的主宰,因而有心主神明之说,人类周身血脉亦有心所主,心神需要血脉的滋养同时又存附于血中;当人心脉协调时,心脉中气血充盛,心神有序调控气血运行并营养周身,心神亦可动静协调,可使人动静有序其睡眠平静。
在此方面现代医家更加注重心肾不交而致的失眠,蓝浩[7]总结并完善了交通心肾治疗失眠的重要方法。而高社光认为现代人多熬夜,多欲望,多应酬等等情况的生活习惯,导致身体生理机能发生改变,经常表现为暗耗心血,而临床症状可见难以入睡、心慌、梦多、疲劳、健忘和易醒等;亦有阳亢体质致心火亢盛,临床中可见心烦失眠、胸闷烦热、口舌生疮等等表现。
1.3 脾郁者,不运也
典籍中脾郁,又称“土郁”,《赤水玄珠》[8]曰:“脾郁者,中脘微满,生涎,少食,四肢无力。治宜陈皮、半夏、苍术”。陈士铎《石室秘录-夺治法》曰:“夺治者,乃土气壅滞而不行,不夺则愈加阻滞,故必夺门而出。”“脾胃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已得到共识,只要脾胃正常的运化水谷并且功能协调,才会有充实的物质基础供应给机体,保障神的动静和谐;脾将其化生的水谷精微上输于心肺,在心肺的功能下使其变化为血,而后充养神明,使机体动如脱兔,静以安眠;若中气不足,脾阳不升,则心神、精明失养产生失眠。脾胃不分家,胃功能的强弱同样影响睡眠,若胃气旺盛,其水谷受盛腐熟功能强盛,即可以保障脾运化充足的精微,上奉心肺,以资神明;若胃气不足则脾运匮乏,气血乏源,心失其养,神失其资;若胃阳虚弱,水湿停滞,扰动胸中诸脏;若胃阴不足,阴虚生火,虚火上扰,神明不安,所有这些都会引起睡眠障碍。
现代研究张敏[9]提出了健脾开郁法,强调了脾在失眠中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李鑫重视“和”法,倡导“治未病”思想从中焦脾胃论治失眠取得佳效[10]。
高社光提出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打乱了许多规律,使现代人长期处于过度紧张中,为缓解紧张,人们常常进食高热量和高脂肪的食物,而有效的运动又不能完成,终致疲倦、饮食伤及心脾,脾失健运,脾不升清,则气血生化缺乏,复加心血消耗,阴血不足,心血匮乏,无法收敛阳气,阳不入阴,最终导致心脾两虚,神失所养,即发不寐。临床可见入睡困难,眠而易醒等等。
1.4 肺郁者,不泄也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11]中曰:“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肺在人体内气的产生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可以调节全身的气,并有助于心的血液循环;它的宣发和肃降功能还可以将水谷精微传播到整个身体。《灵枢·本神》曰:“肺藏气,气舍魄。”即肺主气,气生精,再有“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魄为精神之治。喜润恶燥为肺之特点,因此热邪炽盛,损伤肺阴,肺脏受损,无以藏魄可致失眠;肺阴亏虚继之濡润再失则焦躁难耐,而阴虚内热则魄无以养,魄气变换,百脉不和,魂魄扰动不安,卫不入营,魄不归脏,夜不成寐。还见气虚致肺,则肺魄不制肝魂,致魂摇魄乱而发不寐。
现代亦有从虚研究者赵婧[12]从肺气亏虚入手,应用中医理论调节肺肝平衡来治疗失眠获以良效。高社光认为在肺的调节中需补、散共用,即补中有散、散中寄补,以达到肺气充盛,肺脏的宣发与肃降平衡,以及外邪的有效抵御。
1.5 肾郁者,不张也
张介宾在《类经》中提出:“折,调制也。凡水郁之病,为寒为水之属也,水之本在肾,水之标在肺,其伤在阳分,其反克在脾胃。水性善流,宜防泛滥,凡折之之法,如养气可以化水,治在肺也,实土可以制水,治在脾也,壮火可以胜水,治在命门也,自强可以帅水,治在肾也,分利可以泄水,治在膀胱也”。肾中精微充盛,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保障,而睡眠是人体不可缺失的生命活动之一;肾为先天之本,“本”中包括肾阳和肾阴,肾阳亦是人体阳气的起源,肾阳有温养脏腑的作用,其肾气的推动功能亦是生命活动的动力,人体水液代谢有赖于肾气的气化蒸腾,同时调节着肺和脾的水液代谢,如果肾气不足,导致蒸腾和气化乏源,从而影响肺脾对水液的代谢,致积水湿化,水湿侵心,扰动神明,引起睡眠障碍。脏腑之阴本在肾阴,肾阳之火受肾阴制约,助脏腑之阴以制脏腑之阳,使人达到“阴平阳秘”的协调状态。若肾阴不足,一则相火妄动,心神受扰发为不寐;二则肝木无肾水滋养,则魂失所养,游逸于外发为梦游,甚则肝阳无制,上扰神明发为不寐、多梦,再有肝阳无制化风而见手足拘挛;三则心阴不得肾水之济,心肾不交,心阳独亢,火扰神室,令人睡卧不安。
现代亦有杨瑞涵[13]把老年失眠的病位定在肾,认为其病机是肾虚血瘀,临床多用益肾祛瘀法治疗每效果显著。彭志鹏[14]的研究从试验层面给出了中医五脏通过不同机制来影响睡眠,并明确了肾和脾对失眠影响的差异。
五脏之间在临床中往往相关影响,如肺与心即气血关系。气运血,血载气,气血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气血不协调会影响睡眠活动。而肺和肝对于调节人体的气机同样重要,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意思是说肺位于隔上,其气以降为顺;肝在隔下,将气上提为升气之源,形成肝将气从左侧上升,而肺将气从右侧下降,如果肝和肺对气血的调节正常,则肝藏血、肺主气、肝升气、肺降气的作用相互制约,产生气血调和,寐寤正常。其中脾控制气血的运输,它是精气和血液生化的来源,它将水谷化生的精微物质输送到肺,依赖于肺气输布到整个身体,其中肺所需要的气津液也是通过脾的运输和转化而丰富的。因此,有“肺为主气之枢,脾为生气之源”之说,即肺主气,脾益气,气血充盛,上充心神,心神得养,心神沉静。而肾阴是人体阴中精髓的根源,肾阴的丢失会导致肺阴不足并影响肺功能,肺宣降的功能有助于肾脏水的上升和心火的下降,当心和肾相交并且水和火互润时,睡眠将是正常的,这体现了五脏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为用。高社光强调五脏失调非独失眠的原因,六腑、经络、气血津液失调等等在失眠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 痰凝者,失眠之枢纽也
痰是人体水液的代谢产物,《丹溪心法》中曰:“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可见痰液分为有形和无形。相互依赖的无形之痰和有形之痰之间相互影响。人体之气和液的流动与否决定着痰的存亡,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影响着机体内水液的运输和转化功能,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出现任何问题即可见气机郁滞,津液不布,聚湿生痰,因而朱丹溪[15]提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的观点。赵欣然[16]等医者认真分析《中华医典》中有关从痰论治失眠的组方用药规律,为临床从痰论治失眠提供参考依据。痰虽然说是水液代谢的产物但当其影响机体气机运行时即为病理产物,也可以称其为一种致病因素随气而流窜体内,无处不到,并可加重脏腑表里内外的气、血、津和液的郁滞,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痰结”与“气郁”即可单独作为致病因素也可相互为用共同导致失眠的发作。
另一方面,气郁为功能表现属阳,痰结为有形之邪属阴;临床上以痰证为主的失眠其表现多为入睡困难、寐浅易醒,多梦,醒后难以入睡、舌苔腻、脉滑等等现象,缺乏其显著的具代表性的外显信息,而通常在临证时应用传统辨证思维辨痰证失眠时势必有所局限甚至错漏的风险存在,通过多年的临床高社光在系统回顾总结从痰论治失眠古今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失眠病理因素往往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的特点,挖掘痰证失眠的发病机理与病理演变转化。通过五脏郁滞的病情特点总结痰证失眠的临床表现,尤其捕捉隐性症状,并用疗效反证等途径,证实五郁与痰结是密不可分、又紧密相连的情况。
3 五郁、痰凝之果,当辨其主次
痰由形成到人体内的运转与自身津液的运行转化息息相关,五脏功能直接影响到津液的运化和输布,名老专家总结有“肾为生痰之本,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心为驱痰之力,肝为动痰之机”之说,其机理为:肾阳为人体阳气之源,是人体津液代谢的原动力,并兼调节水液代谢,在肾阳亏损的情况下,影响膀胱开阖功能,则水液转化失度,进一步波及脾肺,而痰邪滋生,因此肾生之痰,多表现为虚痰,故有肾为生痰之本学说;故在治疗中肾虚痰凝者应开肾祛痰。
水谷摄入人体后是变化为气血还是转化为痰浊,起决定作用的是脾的运化功能情况,典籍《医宗必读》中载有:“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何痰之有”“脾土虚弱,清者难升,浊者难降,留中滞膈,凝聚为痰”此及脾为生痰之源的由来,脾为痰之源泉已经得到古今中外诸多中医大家的共识,但多以补脾为先,可见临床中有诸多以脾郁为主,治疗中需畅脾祛痰,使痰无以生。
痰的输布又有赖于肺的宣发肃降功能的强大,肺在治节无权时,其宣降功能失调,致津液所生之痰居于肺内,而有肺为贮痰之器之说,痰邪以生储于肺内,阻碍肺的宣发肃降,致肺郁宣降失常,因而治疗中需先祛痰而后调肺。
心主血脉,推动气血津液的正常运行,此功能也表现在对痰的转运上,在《灵枢》[17]中载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正所谓心之所养者血,心血虚,神去则舍空,舍空则郁而停痰,即心脉瘀阻,则聚而为痰,所以是心为驱痰之力,痰瘀互促互进,使心郁更著,如心气舒畅则瘀不生、痰不凝,可见舒心可祛痰防瘀。
肝为体阴用阳之脏,它的疏泄功能直接影响到人体全身气机的调畅,影响到痰的运化和输布,《内经》曰:在气为柔,其性为喧,其德为和,其用为动。朱丹溪指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先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由此可见肝为动痰之机,此处之气以肝气为主兼心气、肺气、脾气及肾气,可见调肝则痰消眠安。综上诸多观点情况,治疗失眠时需综合多方面考虑,并凸显主次,协同配合,方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4 治疗失眠处方用药特色
在治疗方面,高社光采用多法处方,力求将药与证相结合。多法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治法的联合应用,是治疗证候兼夹和复杂发病机制疾病的有效手段。高社光认为,在临床实践中,不仅有单一的发病机制的病证,而且有更多的情况是证候兼夹、证象错杂等等现象。如有些患者表现为失眠多梦,急躁易怒,同时伴有心烦嗳气,胸闷脘痞等;还有些患者失眠腹胀,便溏,同时伴有腰酸膝软,健忘多汗等。
高社光的药方大多是根据古代药方制定的,尤其擅长小方药的复方。所谓的小处方通常指的是1~4味药,但组合非常恰当,其小方都是数千年的中药实践和临床实践证明了疗效的经方。如心郁以发郁汤为主,肝郁以达郁汤为主,脾郁以夺郁汤为主,肺郁以泄郁汤为主,肾郁以折郁汤为主,痰凝以痰郁汤为主,方方之间又常常因患者具体情况而相互配合应用。
对于失眠状况复杂的患者,特别是老年慢性病患者或长期失眠的人,常常虚实错杂、多脏同病或表里同病,治疗上常出现治实则虚甚,治虚则实滞,简单的多种治疗方法堆积,有明显的药力不专的缺陷。如在发郁汤为主的情况下多配以中药香囊;而在达郁汤的情况时则多配合针刺、刮痧;夺郁汤为主时多配以灸类方法;泄郁汤为主时则配以罐类疗法;折郁汤为主时则埋线、穴位注射比较常用;痰郁汤常常配用之以上多种情况。
高社光将小方分主次联合,协同应用,药理证理结合选方,以理为基,以方证理相结合。高社光基于对五郁和痰滞的发病机理的认识,提出解郁祛痰的治疗原则,还结合了外洗、针刺、耳针(耳穴豆)、埋线、艾灸、拔罐、穴位推拿、穴位敷贴、脐疗等等必要的方法。
5 小结
“痰”与“郁”为失眠的重要致病因素,久病多痰在其他致病因素下又易触发失眠,郁阻经络脏腑为现代诸多疾病的致病因素,郁可生痰、痰可助郁,两者相互搏结共存,引起机体和精神不同层面的多重症状。痰凝郁结为失眠主证,故解郁化痰法是为主要治法,在临床治疗中,不仅适用于“痰凝郁滞”证型,且对于其它证型,治疗时基础方中加用解郁化痰药往往能收到更好效果。在现代诸多研究中发现失眠与气郁痰凝密切相关。但在中医认识失眠方面临床症状辨析较细,而诊断标准在定性和定量上比较缺乏,导致目前现存的研究和临床纳入标准不一,结果差异较大。古代典籍中不寐的治法、方药繁多,但均缺少理论和实验等方面的系统论证,致使现代中医人在阅读中面对众多证侯、治法、方药难以理清思路,导致临床实践无从下手。使得中医失眠病的认识、治疗等方面仍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