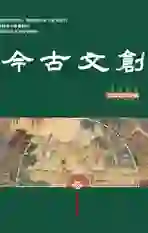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2022-03-22魏琳
【摘要】 美国作家赛珍珠双重文化背景不仅赋予了她双重民族情感,也让她将异质文化互通融合的理念投射在女性角色创作中。她的诸多中国题材小说中以其独特的跨文化视角描写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中国女性形象。在这一系列女性形象塑造中传达了赛珍珠独特的女性主义思想。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赛珍珠跨文化书写渊源和多元文化视角,进而指出赛珍珠的女性主义意识历经了童年时期的萌芽发展、美国教育经历的洗礼、婚姻中的觉醒及后期女性运动的成熟。
【关键词】 赛珍珠;女性主义;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2096-8264(2022)10-0043-03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5wx24)。
赛珍珠的人生经历横跨东方和西方,她将美国称为她的母国,中国为她的父国。这一特殊的经历使她有机会接受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双重熏陶,这种双重世界的生活不仅赋予了她两种民族情感,两种思维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让她获得了包容开放的文化理念,并将这一理念投射在她的诸多作品中,特别是她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塑造中。虽从未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赛珍珠对作品对于中国各阶层女性的关注和同情是全方位的。《大地》中如地母般沉默辛劳的阿兰,《群芳亭》中智慧勇敢的吴太太。《母亲》忍辱负重坚韧勇敢的母亲。还有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女性角色都在她的小说得以再现。赛珍珠独特的东方女性视角与其特殊的成长经历分隔不开。她的女性主义意识历经了童年时期的萌芽发展,到美国教育经历的洗礼,再到婚姻中的觉醒,及后期女性运动的成熟。
赛珍珠于1892年出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在三个月大的时候便随父母漂洋过海到了中国, 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是一名狂热的传教士,他娶了赛珍珠的母亲凯丽也仅仅是为了便于传教。在前往中国传教时,他甚至忘记为自己的妻子准备船票。赛珍珠曾在《战斗的天使》中这样表述他父亲的观点“女人从不认真听布道,女人什么也不懂,不必要在她们身上浪费时间”[1]。赛珍珠的母亲不仅要忍受背井离乡和病痛缠身的痛苦,同时还默默承受着四个孩子的相继夭折。而在他父亲的眼里,妻子和女儿与自己的传教事业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样女性饱受歧视的家庭氛围中,赛珍珠的母亲的曾发起过抗争,如:提出家庭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妇女应该和男人一样有随意支取的权力。然而,她的挑战往往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她把目光转向了女儿的培养上。她将女儿视为同一战壕的盟友,赛珍珠在自传中曾经写道:“尽管母亲从不服输……所以把我完全当作男孩子培养的想法,她十分入迷。”[2]
同样像母亲一样影响赛珍珠的女性还有家里请的中国保姆,赛珍珠称她为阿妈。阿妈虽然不识字,但她经常给赛珍珠讲故事,鼓励赛珍珠学习。阿妈深刻地影响了赛珍珠。她在自传中写道:“她的一部分化入我们身上,像母亲之一部分化入儿女身上一般,所以现在以及永远,她的国家如同我的祖国,使我起敬起爱,而她的民族就同我的同胞一样。”[3]
从小目睹母亲的压抑抗争,赛珍珠心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在悄悄地萌芽之中,而促使这一萌芽迅速成长的是在赛珍珠十六岁时,母亲凯丽送她前往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接受大学教育,弗吉尼亚州林其堡市的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是赛珍珠女性主义观念的温床。这个学校有别于当时传统的女校。并不开设家政,烹饪,服饰等流行的课程。反而是把数学、科学和拉丁语作为重点。同时,它受女性主义新思潮的影响,宣扬男女平等,鼓励女性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财产权和工作权利。许多知名政界女性活动家被邀请到学院演讲,这让少年时期的赛珍珠了解到了和中国女性完全不同的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生存状态。并意识到女性可以不需要依附于男性,女性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参加社会工作,拥有话语权和设计自己的人生。
在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赛珍珠重新认识了作为一名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认识了机会、成就与性别的关系,从而激励她以积极的方式摆脱男权文化对女性的限制”[4]。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为赛珍珠打开了一扇女性主义之窗,让她看到了与中国女性现状和自身家庭环境迥然不同的女性体验。也为她其后的女性主义创作奠定了基础。
1914年,为照顾生病的母亲,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的赛珍珠回到了中国。她践行了母校倡导了女性要积极争取工作的权利。她先后在润州中学和崇实女中和宿州教会学校任教。1917年,赛珍珠与第一任丈夫巴克结婚,随丈夫居住在安徽北面的南徐州城内。在这期间,她并没有和白人为邻,而是选择和中国人居住在一起,这让她有了更多机会了解中国妇女。她常常和普通女性一起闲聊,或者去当地的探访名门望族,并常常发现“在我居住的那一带的女人既有德行又能干,我认为这是因为男人们小时候被宠惯了的缘故,而女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自己不会被娇生惯养,所以必须很能干。不管是何种原因,中国妇女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着比男人更坚强的意志。”[5]
这段日子里,她对中国女性的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与当时的美国妇女这段时期也是她创作积累的重要时期。她其后发表的重要代表着《大地》《母亲》《群芳亭》等都取材于这一时期的见闻。深宅大院里重男轻女,包办婚姻,童养媳,裹脚等见闻让赛珍珠对中国女性所遭受的苦难和中美两国女性问题的差异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她意识到中国女性不仅和西方女性一样承受着父权制度的压迫,并且她们还同时承受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她们的苦难更深重,寻求自由和平等的道路比起美国女性来更曲折更艰巨。
1921年,赛珍珠的母亲逝世,赛珍珠伤感之余,整理母亲笔记佚稿,开始传记《流亡》的写作,并使其成为生平第一部书。而此时她在婚姻生活中遭受的不公和忽略也让她重新审视女性的家庭地位问题。婚后的赛珍珠过得并不幸福,她发现,丈夫巴克和父亲一样完全沉醉于自己的事业,而忽略自己的家庭。“像父亲一样,布克对女人在男女关系中可能成为平等伙伴的观念不以为然,仅把妻子作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和附属物;像父亲一样布克完全被学术研究所占据,完全醉心于自己的事业。几乎抽不出时间来陪伴妻女,更不可能关注家中的事务”[6]
残障女儿卡洛尔的降生更是让这段关系雪上加霜,赛珍珠不得不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年幼的女儿。同时经济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痛苦彷徨也激发她拿起笔书写女性在家庭和社会遭受的不公。1926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东风西风》发表于《亚洲》杂志。1931年长篇小说《大地》在美国出版,引起轰动,成为畅销书。
1934年,由于和丈夫感情不和,赛珍珠离婚并回到美国定居。第一段婚姻的失败让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同时中西方世界的两个维度带给了她女性思想更广阔的视野。她深刻的意识到不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东方世界,女性都受到阶级和父权的压迫,她们的处境悲惨,但却被社会默认为理所应当。只有将这种不公和压榨书写揭示出来,女性的悲惨处境才有可能改变。因此在《大地》获得巨大成功后,她相继写下了一系列以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她塑造了诸多坚强忍耐的中国女性形象,并将自己对女性自由和独立的渴望投射在在其中。
彼時的美国正在历经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妇女在争取教育的平等权利以及选举权方面热情高涨。随着全美妇女选举权运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终于在1920年8月18日,美国国会批准了《宪法》第19条修正案,明确规定“美国或任何州地区不得因性别而拒绝或剥夺美国公民的投票权”。至此,历时百年的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迎来最终的胜利。与此同时,美国中产阶级妇女面临着身份重构问题。女性所受的教育使得她们有能力并且渴望获得和男性平等的工作权利,但是她们的工作机会却少之又少。女权主义者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提出女性不应该被限制在家庭内,而有权利进入社会参与工作中。
赛珍珠也加入了这场论争之中。通过她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她的女性主义观念有了更为成熟的蜕变。在文中她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务,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她分别于1938年和1939年在《哈泼》杂志上发表了《中世纪的美国妇女》和《火药式美国妇女》。1940年,赛珍珠在美国妇女争取自身权利一百周年时发表《妇女:一个少数群体》,在文中,她进一步指出美国妇女应该继续为了获取和男人平等的权利而斗争。其后她于1941年发表了论文集《论男人和女人》,该书针对当时的美国性别之间的问题进行了透彻而全面的分析。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应享有和男性同样的工作机会,承担同样的责任。如果让妇女受教育,却不让她们用其所学,那只是一场更加痛苦的骗局。
在以上著作中,赛珍珠揭示了美国社会上流行的仍然是从中世纪传下来的观念,中产阶级妇女虽然有机会接受教育,但是女性的才华,智慧,能力却被社会拒绝,难以和男人一样在工作中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她将美国妇女分为三类:第一类妇女专注于职业和自己兴趣的天才女性,第二类专注于家庭的家庭女性,她们乐于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家庭和孩子。而第三类妇女介之与这两者之间,也是大多数妇女的状态,她们没有特别的才能,对家庭事务的兴趣也不高。她们有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整天无所事事,不知如何释放和利用多余的能量。也就是赛珍珠所说的火药式妇女。她主张这些妇女去参与社会事业的发展,认为只要这些‘火药式妇女’走出家庭,她们就会使自己的生活更充实,其所居住的社区乃至整个国家都将受益。赛珍珠建议这类女性可以去从事教育或其他人道主义事业,将自身的精力投入社会事业之中,她们的生活状态将会有很大改观。此后,赛珍珠先后发表了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龙种》(1941)、《同胞》(1949)等,借此表明妇女同样具有旋风般的威势和无穷的力量。
纵观赛珍珠女性主义书写历程不难发现,其独特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是历经了童年时期的萌芽,美国教育经历的洗礼,再到婚姻中的觉醒,及后期女性运动的成熟。独特的成长经历使赛珍珠一生中既经历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旧思想碰撞,也体会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冲突。赛珍珠复杂的人生经历塑造了赛珍珠独特的女性主义观念。她的女性观融合了母亲和她两代女性的沉痛体验,融合了东方西方两个世界的生存状态,融合了家庭内部固有模式和社会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这些特殊的女性体验和经历让她的创作呈现出既往作家从未有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也使得她的女性主义作品没有仅从西方女性主义角度或者仅从第三世界女性视角出发去批判和否定哪一方,也没有从男女两性对峙的视角去驳斥和抨击对方,而是在两者之间,用更客观中立的视角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异同,更为温和建议在尊重男女的性别差异以及双方的互相沟通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两性平等。
在20世纪初,大部分的女性主义学说都是以西方白人女性为中心。大量深受美国女性主义学说影响的学者在看待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时都有主观臆断之嫌,她们忽略了国家之间阶级、种族以及文化的差异,导致文化误读甚至是歪曲的产生。而赛珍珠是一个典型的关注国别差异的跨国女性主义者。在其他作家凭借想象看待中国妇女问题时,赛珍珠切身体会使她可以真实地看待、理解这中西方女性问题。因此,她的女性主义观念中呈现跨阶级、跨种族、跨文化的特征。对于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的重要贡献,展现的勤劳忍耐,她在作品中都如实呈现并倾注了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赞扬。
在作品《大地》中,女主人公阿兰一生任劳任怨,如大地一般将一生默默奉献了自己的家庭。她辛勤地耕作在田间地头,在生孩子的当天还在毫不停歇的劳作。她勤俭持家、隐忍坚强。在危难关头,表现出超强的冷静和魄力。在遭遇饥荒,家中断粮,丈夫王龙还在犹豫不决之时,是她果敢地将家中的牛杀了,暂缓了家中断粮的绝境。饥饿的村民们在王龙叔叔的怂恿之下涌进家门搜刮粮食,是阿兰勇敢地挡在前面。有理有据,镇定地解决了危机。赛珍珠的女性主义思想中有着对东方女性伟大力量和奉献精神的深切认同,她并没有站在西方白人女权主义者的角度对她们在家庭忘我的付出和奉献进行批判,而是肯定了东方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赞美了她们勤劳节俭无私的美德。
除了肯定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和力量,赛珍珠在作品中还将女性追求平等自由的理念投射在人物塑造中,如《群芳亭》(1946)中的女性角色吴太太身上。吴太太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美德,她持家有道,孝顺长辈,爱护子女,在她的打理下吴府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同时,吴太太身上也有着西方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在她四十岁生日时,她宣布搬到兰花院,并发出了她的女性独立宣言“我要在剩下的岁月里,集合我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我将细心保护我的身体,不是为了再去让男人喜欢,而是因为我住在里面,我要依靠它”[7]。同样在1949年出版的《同胞》中。梁玛丽放弃协和医院的优厚待遇,到乡下参与国家的战后重建。她很快获得了男性知识分子的认同,并通过办识字班以及农村医疗推动乡村的现代化。
综上所述,大家可以看出赛珍珠女性价值观中肯定女性力量、倡导女性在可行范围内追求自由平等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的特点。真实的东西方体验赋予了赛珍珠女性书写更宽广的维度和视角,也成就了赛珍珠独特的女性主义思想发展。
参考文献:
[1]Buck, Pearl S. Fighting Angel. New York: Day.1939.93.
[2]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M].尚营林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98.
[3]林如斯.赛珍珠传[A].郭英剑主编.赛珍珠评论集[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604.
[4]Conn, Peter. 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51
[5](美)赛珍珠.异邦客[M].林三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62.
[6]怡青.一个真实的赛珍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78.
[7]赛珍珠.群芳亭[M].张子清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349.
作者简介:
魏琳,女,江西赣州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3171501908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