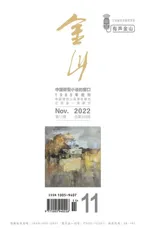微珠世界 耀眼争辉
——第二十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获奖作品述评
2022-03-07江苏徐习军
江苏/徐习军
任何评奖都是一种在“规则”下进行的“比较”“筛选”的过程,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也概莫能外。第二十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在公布评奖规则后,通过作品申报、初评、复评、公示、终审等环节,最终于2022年8月份揭晓评奖结果。由于评奖是比较的结果,而且是在一定规则下进行的比较,加之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是一个主观因素极为强烈的审美活动,经过多个评委多轮评审,呈现出“见仁见智”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必然的,是在“见仁见智+规则约束+妥协平衡”中“筛选”出“结果”的。因此,我可以武断地说:没有评上奖的未必不是好作品,只是由于“比较”因素而没有被“筛选”出来;评上奖的作品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能评上奖的一定是“比较”好的。这次揭晓的九篇获奖作品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下面就这九篇获奖作品谈谈自己的阅读感悟,有言在先——这是本人的“主观”阅读审美活动,与广大读者的阅读理解乃至获奖作者的创作意旨有差异,甚至完全不一致,也属于“见仁见智”的正常现象,因为真正意义上,一篇文学作品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便是这个道理——这样也就没有必要为产生“误解”而担心了,解脱了“害怕”读者“误解”的心理障碍,我便可以就自己的感受“胡说八道”了。
一
先说说总体印象。九位获奖作家出生年份分布于20世纪40年代到近80年代,可谓覆盖“老中青”三代,获奖作家均为省以上作协会员,或具有高级职称,大部分是中国作协会员,虽然“会员”之类的身份不能等同于“水平”,但至少说明获奖作者都是长期耕耘于文学田园,掌握“写作”这门技艺的“手艺人”,且都是写出了诸多优秀作品的地道的作家,这一点是无须置疑的。最年长的获奖者是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原副主席聂鑫森先生,已经七十有五,不仅自身耕耘不止、佳作叠出,还是微型小说界“导师级”的大咖,在先生主持《株洲日报》等文学阵地的时候,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微型小说作家。而生于1979年的获奖者吴嫡,虽然与“90后”“00后”相比已经不算年轻,但他已经有相当丰厚的积累,在国内各大报刊、网站发表大量作品,并且有作品已经成为当今中小学生的阅读教材。长期的文学创作实践加之丰富的文学积淀,使他们能够成就好作品,也成为他们在本次年度评选中获奖的厚实基础。
综观九篇获奖作品,有的以小见大,道出了人和人之间不离不弃的真情,如聂鑫森的《花草之眼》;有的书写对“合理想象也是必要的”这类过往“经验”的反思,如王德新的《跳闸》;有的展示人世间多少悲惨也能有惊人的重现,如杨静龙的《前夫》;有的表达身居污浊却保持良心不灭,如张建春的《叶明之的遗书》;有的赞美生活的磨难挡不住文学结缘的魅力,如陈振林的《小叔木江》;有的通过皇家的汤与百姓的命的描写,揭露时代的腐朽,如蒙福森的《紫禁城的鲥鱼汤》;有的描绘了一个高明画家在玩物失志时代的众生相里,以画作揭示出这种没落生活不过是一纸空虚,如周东明的《画蟋蟀》;有的阐述“子孝母”与“母爱子”的天差地别,如徐全庆的《母亲走失》;有的以哲理般的逻辑述说着“眼见”与“心见”的不同,如吴嫡的《啥都没看见》。
九篇获奖作品,取材跨越古今,题旨丰富多样,表达篇篇出新,然广泛题材也好,花样表达也罢,却无一例外聚焦人与社会,获奖作品作者的“善心”所致正是这次获奖作品的一大共同特色。
二
随时可能出现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跳闸”“停电”,在生活中就是一种正常现象,然在作家眼里它就是个“事件”,于是就有了“小说”,于是就有了王德新的获奖小说《跳闸》。
寻找“跳闸”原因成为电力工作者的常态化工作。几拨人巡查没有发现原因后,认为“是大鸟,是大鸟……”,以前发生过多次跳闸,就是大鸟引起的短路。“处理故障这事儿,有时合理想象也是必要的,这是一条经验。”然再次强行送电依然“跳闸”,这是第一次对“经验”的嘲讽,于是小说主人公老毕亲自出马巡线,“3号”楼子的出现,让老毕眼窝一热,老毕不会忘记,正是他主持了3号楼子的报废。15年前报废的时候,剪了楼子的内线,剪掉内线,那变电器就断了奶,外线有时剪有时不剪,就算完活,这也是传统的“经验”。当导致“跳闸”的真正原因出现——一个盗线的孩子“挂在电线在室内的短短茬头上”,那个骇人的场景,对传统的“经验”、对老毕,无疑是撼人心魄、刻骨铭心的一记震天响的耳光!小说中两次对“合理想象”这类“经验”的否定,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经验主义是最大的障碍”。对于介入处理案件的公安来说:“断这种案子,有时合理想象比事实更靠谱,这也是公安们的经验。”作者讽喻和否定的笔触,由此可见。
如果作品写到这里,不妨可以说也算是一篇不错的小说,但也就缺乏了思想的高度。于是小说进行了“提升”——老毕的事故报告,对“两个方向”的取舍——一是“盗窃触电引发的跳闸故障”,非责任事故;二是电业公司报废变电站时残留了外线,导致一名未成年人触电,属责任事故。老毕考虑了两天,按照责任事故提交了报告,两眼熬得血红的老毕,形象瞬间丰满高大起来。
张建春的《叶明之的遗书》,写了身处不同境地的两个人:落入魔掌、经受折磨而英勇不屈的正义之士叶明之和为牢狱打杂送牢饭的黄三。两个人物没有任何对比的描写,甚至没有多少情节:一是某天夜里,叶明之听到了来自黄三的低低的哭声,这“哭声”显示出黄三心底的“良”和“善”;二是黄三听叶明之自言自语,赶紧捂住他的嘴,防止叶明之无意识的泄密;三是逃出来的黄三,找叶明之自言自语呼唤过的人,冒死传递消息,“我就是遗书”,这是何等的良心语言!
在徐全庆的《母亲走失》里,做儿子的翻遍了所有储存,居然没有找到一张母亲的照片,“徐家大院”群里那么多亲人,居然也没能寻到一张母亲的照片,而在关键时刻,母亲却凭着儿子的照片,被人送回了家。小说情节结构之简单、行文叙述之简约,折射出了一个很大的、很严肃的社会问题——如何对待老人的问题。如今,在代沟乃至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包括母子关系在内的亲情关系大不如前,虽然我们看到的“孝子”依然是社会的主流,但是如今子女“尽孝”多体现在物质层面和生活表象化层面,像《母亲走失》小说中的儿子,其实在心里已经“丢”了母亲,而母亲却始终如一地将儿子的照片带在身上……“子孝母”与“母爱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以上三位作家在作品中,对“合理想象也是必要的”这类过往“经验”的反思,才有“老毕们”的行为取向;黄三身处污浊而良心尚存;看似“孝子”,却连老母亲的一张照片都不存,何以能把老母亲真正放在心里,而老母亲却将子女放在心底里……这不仅是作品主人公,更是作者“向善”的积极表达。
三
本次获奖作品中的《前夫》《紫禁城的鲥鱼汤》《啥都没看见》以及前文述及的《跳闸》《叶明之的遗书》,都有关于人物死亡的描写,文学艺术通过悲剧的形式描写死亡或恐惧,不仅是要引起读者的恐惧和怜悯之情,更是要通过卡塔西斯的作用使怜悯与恐惧成为“适度”的感情,诚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同情和恐惧都是一种痛苦的情绪,而悲剧引起的怜悯与恐惧之情,却是读者体验到的一种特别的感受。而前文说过的《跳闸》《叶明之的遗书》中死亡的悲剧情怀并不足以让读者产生强烈的震撼感,因而不再进行探讨。
杨静龙的《前夫》,描写了一个乡村“哭灵师”阿奇嫂,在一单“生意”中面对丧主,得知死者是“打稻机漏电,他碰了电线……”,阿奇嫂的哭灵“仿佛一道火焰在身子里燃烧起来,要穿透她的胸膛,要从她喉咙里窜出来”,如此凄惨、如此悲诉,如丧至亲。如此描写,丧主及读者对阿奇嫂的“职业”产生了高度的认同,但如果仅仅从“哭灵师”职业角度理解阿奇嫂的“哭灵”,显然达不到震撼读者的功效。到了小说的结尾,阿奇“那一年夏收,阿奇的邻居在水稻田里碰了电线,他看到了蓝色的目光……后来,他娶了这位邻居男人的女人”,这个“邻居男人的女人”成了阿奇嫂!行文至此,给读者的震撼已经无可比拟。阿奇嫂岂止是为“雇主”“哭灵”啊,人世间多少悲惨居然有惊人的重合呈现,阿奇嫂哭的不正是自己前夫的在天之灵吗!
蒙福森的《紫禁城的鲥鱼汤》则将死亡的悲剧意识及其对读者的怜悯之情和恐惧感发挥到了极致。渔民打捞到鲥鱼的“连声惊叫,手脚无措”,官差“八百里加急”、快马撞倒男孩踩中他的头部仍不停息、驿途快马加鞭换马不换人送往京城,御厨张和的高超烹制手艺,洇入鼻翼、沁人心脾的鲥鱼豆腐汤让皇上“百吃不厌”,读这些顺时序的小说叙事,尚不能调动读者的怜悯之情,也无法形成“悲剧意识”。然而,蒙福森毕竟是位微型小说高手,当作品中张和“梦见儿子哭着向他跑来”,“堂弟来京城”将张和的儿子“被送鲥鱼官差的快马踏破头颅不治身亡”这一消息告诉张和的时候,无论是作品主人公张和还是读者,都一样的悲从天来、悲痛欲绝,至此,小说的死亡恐惧感和震撼力发挥到了极致。张和幼子死于非命,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皇家的奢侈建立在百姓死亡的基础上,而精心烹制皇家汤的张和,还不知道为这个汤调味的正是自己儿子的血和命!巨大的张力彰显了那个时代的没落腐朽。
另一篇涉及人物死亡的作品是吴嫡的《啥都没看见》,这篇小说与《紫禁城的鲥鱼汤》《前夫》的表达是不同的,它是将“死亡”作为小说的背景而设置的。清洁工老张目睹了司机撞死人的全过程,也与肇事逃逸司机有一个反复斗智斗勇的过程,肇事者声称只要老张“没看见”就可以给他一笔钱,老张“三番五次”收肇事司机的钱,这是读者所能“眼见”的,“眼睛不好”的老张确实“看不见”肇事人的模样和车的牌照,然不能“眼见”并不代表老张对此“熟视无睹”,即便在高额金钱面前,老张依然是“心见”了这场撞死人的事故,心之所见决不能昧着良心而“不见”,于是就有了“三番五次”斗智斗勇、引蛇入洞的“操作”。
关于小说作品中的人,一方面是人的自然性本质决定了人在物质贫困中要遭受痛苦,另一方面是人的精神引导对物质贫困造成的苦痛的超越,两种张力共同作用制造读者的审美境界,成为衡量现实生活中人的道德情操高下的分水岭。
四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批评家卡斯特尔维屈罗说过:“当看到别人不公正地陷入逆境因而感到不快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认识到自己是善良的,因为我们厌恶不公正的事。我们天生都爱自己,这种认识自然引起很大的快感。”
本次年度奖一等奖得主聂鑫森的《花草之眼》,叙写校园修车师傅车百里和他的盲人妻子蓝姑,与一个贫困女大学生杨帆之间发生的故事。贫穷的女生杨帆“真的需要一辆车,可以节约出许多时间”,可是她穷得连二手车也买不起,徘徊在修车铺前,修车师傅车百里似乎读懂了杨帆,要为她“组装”一辆自行车。我们这个社会,善良的人总是会在看到别人遭受不合理的苦难时,能够认识到这种苦难或许会降到自己或者与自己一样的人的头上。于是默默然中不知不觉地就“明白了世途艰险和人世无常的道理”,修车师傅对于杨帆的困境,杨帆对于盲人蓝姑以及修车师傅,大约就是这样的。小说借助修车师傅和盲人妻子那花瓶里每日一换的花和草这一道具或者说载体,“看多了,心上会长出明亮的眼睛,什么都看得见”,以小见大,道出了人和人之间不离不弃的真情,这个真情也感动了女大学生杨帆,对杨帆的人生成长和道路选择产生持续的影响。
陈振林的《小叔木江》是一个“文学结缘”的主题写作,作为一个正高级职称的语文特级教师,“寓教于作”是他的强势所在。小说以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代表作品《源氏物语》切入,却并不纠结于《源氏物语》所描写的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而是通过《源氏物语》这一“道具”,将辍学打工的小叔木江和同为打工妹的小婶梅子,在当年因为《源氏物语》开始了一段美好的爱情,如今借助阅读《源氏物语》而将所结下的良缘不断延续这一美好故事呈现出来。中文系大三学生的“我”在小叔木江的推荐下也读起《源氏物语》,并且有了和小叔、小婶“探讨”《源氏物语》的契机。大约是作为一个教师的职业习惯,《小叔木江》中多有“掉书袋”式的对《源氏物语》以及对文学的普及,但这并没有妨碍作品结构的紧密和故事情节的推进,反而使得故事内容更具知识性和丰富性,所以,作者发出了“一个初中生正教着一个大学生读一部长篇小说”的慨叹。
九篇获奖作品中,意旨最为突出且文化意蕴极富的要数到周东明的《画蟋蟀》,作品以斗蟋蟀这一古代常见的兼具娱乐、赌博性质的项目为背景,描绘了那个玩物失志时代的众生相。“蟋蟀”斗场上,富七爷手捧放在前清官窑陶罐里的“八将军”,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让富七爷能横行斗场。然一个专画蟋蟀的画匠的出现,让富七爷、斗场观众对“纸画蟋蟀”产生了不可思议的被动“体验”,相信读者也同样产生了不可思议之感,因为在众生的不可思议中,“赤手空拳”的画匠用纸画的“铁铡刀”蟋蟀打败了“斗场无敌手”的“八将军”,一片纸画蟋蟀,让“八将军”跃上罐沿“仓皇逃命”。这个故事情节就有着深邃而又醇厚的文化内涵,可以用动物心理学来解释“八将军”的败北;也可以用社会学来开解——揭示出再厉害的蟋蟀、再好玩的“斗蟋蟀”,也逃脱不了它的宿命——这种没落生活不过是一纸空虚;还可以有多种解读,有赖读者诸君见仁见智了。面对一个故事能解读出多重主题,正是一个小说家的高明之处!
不仅如此,作品还作了进一步反转和提升,画匠“蟋蟀画”受到追捧,价格飙升到画上“每一只蟋蟀八块大洋”,且吝啬到不可讲价、不多画一只的地步。小说结尾,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人,来找画匠买画。“一只蟋蟀趴在罐沿儿上,只露出上半身,低头卷须,两眼无光,落荒而逃的样子。”这幅画则无疑是对读者阅读审美力的一个考验。半只蟋蟀收四块大洋,穿长衫、戴眼镜的买画人在衣袋里掏出十六块大洋要递给画匠。画匠仅仅按照画面收了“半只蟋蟀”的价格四块大洋。其实,“长衫”一眼就看出了画上的“两只蟋蟀”——半身趴在罐沿上的蟋蟀是败者,另一只更威猛的蟋蟀王者稳坐罐子里。所以才有了那幅半只蟋蟀画,展出时题款《两只蟋蟀》,并且拍卖了八百万元!
五
第二十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的九篇获奖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作为文学创造的主体,无论艺术世界如何虚幻与完美,都必须依靠人类感性的本体来负载与摆渡。因此,宽泛地说,九篇获奖作品都以其独特的方式,以人的活动,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人”作为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这就导致了人的存在是在两个基本层面上展开的,一个是自然性(物理性)的维度,另一个是精神性(历史性)维度。正是因为两个维度存在的张力与平衡才构成了人的存在的丰富性,把握好这两个维度,一篇优秀的微型小说也就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