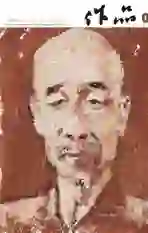她们的诗
2022-03-04林珊周瓒安琪林馥娜于燕青范丹花夜鱼
林珊 周瓒 安琪 林馥娜 于燕青 范丹花 夜鱼
林珊的诗
冬至日,重访天坛
我们真的来过这里吗?
庙宇与宫殿之间
落日与群山之间
我现在站立的,远眺的
这片土地,这道宫墙,这块花岗大理石
究竟是散落在哪一个梦里?
也许回忆,从来都是一个人的事
深冬的鸟啼,和初夏时
已然不同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是否
还能隔着一千多公里
遥望同一个落日
回音壁前,我听见一个人
大声呼唤
另一个人的名字
雪为什么总是落在别处
漫长的黑夜里,那些渺不可及的
山川,河流,草原,荒漠
自古就没有一夜白头的心愿
只有四面八方的风,迎面而来
不断吹拂浮世里,万千个
日渐消瘦的你和我
我知道,在一首诗里是等不来一场雪的
我需要一个人,顶着满头白雪
从远方迢迢赶来,拥抱我
这悲欣交集的人间
这漫长的短暂的温暖的清冷的
离别之意渐起的盘山公路上
他开始为她唱歌
他的侧脸,那么清朗
他的歌声,那么动人
可是她的眼泪,是止不住的
泪眼婆娑中,村庄和荒野
树林和麦田
一退再退
晨曦中的所有事物
都是模糊不清的
世界的尽头
亘古的六盘山山脉起伏延绵
群山之巅,唯有那白雪
那一夜之间突然降落的白雪
暂且忘记这悲欣交集的
人间
山河万里
从一条熟悉的河流
折回。我几欲失声痛哭
每一个深秋的傍晚
在岸边徘徊过的,一定不止
我一个人
可是所有的孤独都是相似的
此刻秋山尚浅,流水过深
熟悉的你,陌生的你
是不是
也徘徊在
空空如也的黄昏
众鸟飞尽
清晨我在桌前看书
湿漉漉的衣服在阳台上滴水
“滴答,滴答”的声音
碎了一地
有那么一瞬
我仿佛回到江南四月的雨中
只是此刻,众鸟飞尽
高空没有鸟鸣
我知道远在天亮之前
那些飘零的叶子
已如遗骸
在寒风中耗尽自己
而人世间所有的离别
也从来都是缓慢的
站台上,伸出过的无数只手
至今仍停留在那里(即便这只是幻影)
这多么令人惆怅
我们都回不到过去
我只好重新铺开一张白纸
陷入回忆的灰烬
竖琴
一场音乐会上
一把竖琴,让我出神
这世界上最古老的拨弦乐器之一
这起源于古波斯的,有弦之弓
我曾在詩里写下它
是源自于我的一个梦吗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会离它这样近,这样近
一场音乐会上
一把竖琴,让我出神
你们相信吗,这就是曾在我的梦里
出现过的,那把竖琴
弦月,给陈罕
当我和她坐在餐桌前。一切
都安静下来
这安静下来的一切
让我暂且忘了,这人世的忧愁
“多拿些酒来,因为生命只是乌有。”
我惊讶于佩索阿的诗句
借她之口,对我说出
事实上,痛饮过葡萄酒的玻璃杯
此刻盛满的,是清茶
猝不及防地,一些深藏多年的阴霾
还是顺着异乡的灯光
溢出来
流淌的暮色越来越浓
无数盏街灯渐次亮了
白杨树和鸟巢一如既往
在寒风中摇晃
一切都安静下来
一轮弦月高悬在
我的窗外
弦月之下,突如其来的
悲伤
击中我
周瓒的诗
语言的背叛
1
曾经,九个太阳被一个人射落
剩下的唯一一颗才能成神为王
全世界公共的玫瑰,永恒的光源
而标举太阳之旗的种族和被供奉的
那个人,在修辞的强光下
站成了这个词的反面:一呵死亡
这“一呵”如同神的冷笑
刍狗般省思人的悖论
高科技造福这个世界,而语言
却紧接着背叛了它的记忆
当人们紧张地关注受苦的他人
通过互联网传送的恐惧混乱
一飙远方之难,存在之困
那贫瘠荒漠的暴风如此接近我们
让我们共同沐浴了词语的哗变
为了一腔滚热的生活,一死自由
机场上逃亡的民众,屏幕里大声
呼救的女人,以及恣肆的病毒
虚伪的谎言,在沉默里
悄悄结起绵密的理解,如原始森林
2
一叠树迫切于静止,须多强的风才能吹皱
枝叶织就的波面,时光的森林,恍惚如一飞逝海
这是世界万万倍的延时摄影与快进播放
你的瞳孔能装下宇宙级的变化,却对不变
拉上了眼帘。那是人痴迷的定律,先验存在
不确定感使我们堕入及时欢愉和相对生死
需要拭擦多少回,才能还回人民的清晰面孔
要把他们和我放进去,要对你们反复追问
一支队伍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
而组织它的机制,值得你用真理来测试
斜挎在肩上的枪没有性别和种族之分
有谁期待它们发言,一响心愿,两身粉碎
暴行和它的旁观者们分享弥散的虚弱
而冥想的正午消耗着造物主残忍的耐心
3
词语如何使事物具备心意的色泽
譬如你给了我“荷”“晕”“苍”
于是中国画的淡墨与晕染,带我们去到
一个写意但精确的心灵世界
当我们说“一荷女人”,便可用阿富汗
天青石调制的颜料勾勒荷叶的筋茎
她的轮廓,墨色里有“一晕罩袍”
但那洇开的浅墨在现实里却是血痕与泪迹
也连带了并不遥远的那“一苍历史”
那些害怕女人拥有自我,那些恐惧歌声
那些信仰教条,用暴行寻求存在感的人
我们要如何与之共有一个世界、一颗地球与一
片天
而语言背叛着我们,橄榄枝发出呼救
回环之诗(给小翟)
小时候夜读聊斋,爱与怕交织
醒在夏日南方的蚊帐中
文字故事幻绘出眼前图景
从窗棂探进来风的大手
轻轻搅动帐幔,而晨光改变着
它上面的阴影与气息:几个人物
服饰随便,一匹小兽出没不定
一骨灯笼起火,便烧毁画中娇娘
小儿附体小虫,妖怪以人为衣
一大早依旧梦魇压床,洗脸时
麻木里不敢一瞥一秒镜子
瓷面盆内,晃动的一捧月亮
也提示:长夜未尽,故事待续
而下回分解恰巧落进你的一首诗
那里有人以菊为灯,照向起雾的大河
看见与内观(给徐冰)
从《山海经》到奥维德,果然
古人最擅长的,就是讲述背后的故事
又如你的一黄远山,转到玻璃的内面
其实是灯光下橘色的麦秸与散漫的枯枝
令人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果然
看见,是需要我们反思的一个词儿
不被一面的美欺骗,倒是其次
你或许是在考问我们:观看
从来都不客观,正如倾听需要倾心
角度不同,音乐略胜于舞蹈
化腐朽为神奇者,须为一公(认之)
异人,复眼般看出材料的二重(性征)
而比起蜻蜓,人的眼睛布满了死角
人不能裸眼望向太阳,虽然可以
一望太空,那也无异于回身观自在
一望太空,人立刻意识到何为渺小
太空也有它背后的故事吗?果然
“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若非有心
在蜻蜓之眼中,人永远都是复数
是无,也是一。一望太空,会有天书
搭乘火箭,等我们译写文明的新多元吗?
而太阳底下有尘埃,物质不灭
沉重的废料再生为一对凤凰鸟,飞出千山
而内观的人,变出了轻盈与充溢
在元典美术馆(给朱金石)
咖啡馆开在美术馆里了
但来看展的人没找到吧台、桌椅和服务员
只有两扇概念的店门真实地开合
在元典美术馆唯一的长条形窗扇上
这条窗前,曾挂过秦玉芬的铁蒺藜窗帘
试图穿过它的人不免会被扎痛
那是名为珊瑚的一簇簇暗礁
把美术馆改装成了大海汹涌的一角
这片珊瑚岛下也盛产海鲜吗?
上周,鳌虾咖啡馆开张啦
——你好,来一杯美术馆咖啡如何?
但我们找不到吧台、桌椅和服务员
也许是一家外卖咖啡店吧
你没有闻到咖啡的香味吗
从一两声窗口的招呼中
当你打开微信,弹出圈友对话窗
——因为疫情,来看展的人少了
没关系,我们能直播看展,能叫外卖
在元典美术馆的鳌虾咖啡馆
两扇木格子门像是错位的时空
转换了维度的言语,就像我说
一株大坝,几座小树,两首房子……
我没有用错量词,詩人的工作不过
是改变我们内在的眼睛:咖啡馆,珊瑚,鳌虾
都市中的海洋生物,生存的技能和愤怒
词语装置,句子行为,声音肖像
这一切使得世界经历了一回微妙的改变
微妙到你以为是在脱壳,但其实
是现实把另一个自己——真实,诞生了出来
安琪的诗
哗
肖邦的钢琴曲
和百丈漈的瀑布声哪样
好听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对着百丈漈的瀑布弹奏肖邦
肖邦
会被淹没得,无声无息。再努力
的肖邦也比不过百丈漈的一滴水
它混合在一群水中
前赴后继
跳下悬崖,粉身碎骨前大喊一声
哗
便足以将肖邦打败。再伟大
的作曲家也敵不过百丈漈的一滴水
哗,一滴水叫喊着!
哗哗哗,一群水叫喊着!
无需技巧
无需升C或降E
无需大调
或小调只需亘古恒久一个音
哗
便足以打败肖邦,打败肖邦
莫扎特、贝多芬组成的强力军团
便足以打败
人类想象力创造的极致——
一曲难忘啊百丈漈
你只用一个音
便演奏出了最伟大的,山水交响!
一支笔在铜铃山
小腿肚
不再酸疼的时候铜铃山就远了
但一支笔有信心把铜铃山唤回
先是在漫长的山道转啊转
山道一圈又一圈,一支笔探身车窗外
呀银钟花
连香树福建柏天竺桂花榈木鹅掌楸
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把一座山站满了
山
一座接一座一座叠一座越接
越密越叠
越高但一支笔不发怵——
某些人已经扛不住了他们
面色苍白胸中翻滚起阵阵难受
铜铃山
你在哪里?一支笔微笑着它心知铜铃山
就在那里!它已嗅到清澈又清澈、神秘
又神秘的深潭气息——
十二口深潭建造的山,铜铃山!
十二口深潭已等候在一支笔
和我们的
必经之道上并且摆出了各种造型——
心形潭、太极潭、大葫芦
牵引小葫芦潭壮年潭老年潭阴性潭
阳性潭月亮休憩潭吴成藏金潭……
为美景所惑
一支笔东瞧瞧西望望险些跌入鳄鱼潭!
一支笔在铜铃山吸足了天地之灵气它
有责任
有义务记录下它所看到的一切,现在
正是时候!
燕子把宫殿建在哪里
谁能想到
燕子居然把它们的宫殿
建在格凸河上
格凸河当然知道
它抿着深绿色的嘴,死命地保守着
天大的秘密
那看见数十万只燕子飞入宫殿的人
在向我讲述时依然大睁着惊叹的眼
太壮观
也太恐怖了,它们猛烈地扑过来
扑过来,我连忙趴在栈道上,它们
把唾沫把燕子屎
把尖叫声甩到我身上时我感觉
我要被淹没了
黄昏时切记
不要走进大穿洞,她说
那是神给燕子建的宫殿
宫殿旁有一个大坑,燕子年老体衰时
就会飞到坑里等死她继续说
真有这么一个“她”对我说?
我在写作此诗时也迷糊了但我确曾
闯入燕子的宫殿在公元2021年7月
24日的格凸河上——
那宫殿有一个名字叫大穿洞!
赵已然
弹断了吉他
就弹雨,雨水如麻,如纷乱生活
弹不断这纷乱生活
弹断了雨
就弹肋骨,这一把消瘦老肋骨今天就断给你
凤凰,雨水中翻滚起呐喊的泪水是凤凰飞升
的翅膀。你是不是死神最疼爱的人死神说
不。你是你自己最疼爱的人你只为自己活
这一生
你只为自己活。于是你做到了!
诗与诗
诗的距离
太远固然不好,太近
也不行。必须在恰到好处时停下
微微闻得见喘息,和体香,好比
爱情
止于初见一刹那,心动于毫无防备
一本书刚刚翻开便跳出刺你心扉的
一个字
突然不舍读下去,更不舍读完
诗
与诗的距离,不可落笔,只止于
灵魂出窍的瞬刻
在绝望的内心也许有一点希望
路过希望
看到它的内心有一点绝望
路过语言的好感觉
制造出的夜晚,噩梦很完整正奔赴前来
路过
水声哗哗的这里惊异沉默的那里
亲人们都不曾从那里回来,那里
究竟有什么好?
路过绝望
看到它的内心还有一点希望……
漳州之夜:给余畅
直接唱,开场白不要太长
生命太短,来不及铺垫,来不及相爱
当我
在陌生中回到故乡,故乡已是你乡,你
从新疆来,那片我向往的土地
已被你放弃就像我放弃漳州
我们互换一具躯体,转个身相逢在酒中
兄弟,祝你在异乡夜夜
笙歌但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我的不可能
今夜我们欢聚于一首诗
一首永远写不出也写不完的诗……
林馥娜的诗
爱上的
节日把所爱送到你面前
像飞凤歇落山中
天地的怀抱中有拥我入枕的臂弯
将一茎清荷轻呵为珍宝
往事青涩,复到眼前已是熟透
天色暗下来,意绪也随之苍茫
路上灯火次第亮起,又隐匿
一切在到来,又在远去
而时光的盒子中有我们
爱上的四合山色
科莫湖
從米兰中心火车站
跌进阿尔卑斯山南麓
洁净的幽静
如青绿山川揽拥靛蓝湖水
白船与野鸭流荡于碧波中
仿佛梦境浮出地平,筑成
积聚念想的洼地
那些长长的石子路
我与家人一同走过
冰川湖的清凉水氤浸透体表
我们在湖山之间走走停停
手中的冰淇淋
滋味不止于我们所获取的三种
香甜,入口即化于此后悠长的时光
走过了漫长的世道
过往与未来聚焦于一个字
爱,就是去爱本身
应和
带广角镜的黑瞳藏着亲近万物的复眼
森林之路向内弯曲
树叶的歌声有清泉唱和
一只丹凤眼打开无界之境
复眼幽深处,一束黑火焰燃起
照见另一处被镀金的丛林
丛中有生物制光,集光,发光
并被强光所灼伤,承受早至的坍缩
如果打开茧房与洞穴
赤裸全息的细胞
你便懂得高蹈的与承载的
如何在脉搏的频率与光影的微粒中
同频共振,同体慈悲
当你仍会被打动,仍能微笑或哭泣
在城市里听见风呼与虫鸣
闻到新浴的体香,便可为自己恭喜
时间不能带走一切
雨在窗玻璃上独唱
它选择在深夜,以打击乐敲响
全世界的沉默
幸存的人圈地为界
在玻璃罩中睡眠
一个抓住微小梦想的人
把一枝带洁白花蕾的茉莉
扦插于五月——
时间不能带走一切
梅花落梅花开
在高楼的窗页上,写一枝青竹梅
古典里的清冽梅馥便溢出时空
远道而至梅林的女子
不为仿效梅妻鹤子的处士
亦不做,提灯照梅的怜香者
只为借亘古风、傲霜骨
影塑立世的腰身。梅花落处梅花开
逼仄人间宜心存旷野
尽管天空时常笼罩灰霾
仍有不缺席的一枝白、一段香
用以对应你胸怀中的山岳
而青梅煮酒,豪情岂分雌雄
叫不出名字的关怀
装满生老病死的住院楼
不断复制、粘贴着类似的情节
每个人的羁留只是
长篇剧本的一个标点
就像机器中某个被更新的小螺丝
我们都不曾深究
水泥楼层上的纯白芦花
如何在半空中柔韧绽放
以躬身的重负
直面生命的诀别与迎候
并把白持守为永恒
当我携着亲人离开,我要为
那些叫得出名字
叫不出名字的关怀而深深
感恩,那些朴素的善意
草木本心,慈悲在怀
于燕青的诗
无限
我翻开一本书,恰好
这事就发生了
点横竖撇捺像被胡乱堆着的弃木
落日正慢腾腾地抛出黑夜
枯荣正在加紧交班
我必须矮下身子,再低下头
深入下去,是我
从未见过的另一番景致
我一直都在努力
清瘦的十指刨出整整一座荒原
它们是那么地庞大,也只是
洪荒里的一点零碎
我的手越来越干净
就要摸到那隐藏的至圣的
无边无际
我老了
走斑马线过红绿灯去自助餐厅
从这头到那头,放眼望去
行人们食客们,大都二三十岁的模样
我夹在其中,忽然不知该干什么
这差距让我有些荒寒,仿佛
刚经历过一场失败
我深知,根与花朵的差异
就是谎言与真理的差异
我是那个找不到接头地点的特工
暗号照旧却无人回应
我的同龄人越来越少
活着活着,一不小心
就成了某个场景里最老的那个人
我曾在午后的某个时刻愣怔
最后的晚餐还未备好,黄昏就要来临
越老越不喜欢那些斑斓的蝴蝶标本
和,童话里皑皑的白雪
浪花
你也开花
开白色的花,只为祭奠
祭奠逝去的所有美好,和
所有的不美好
你开在俗世的岸边,一开就谢了
一朵一朵一片一片,瞬息即逝
像来不及展开的青春
像那些一去不复还的人们
像疏狂的隐喻与虚构
你以消灭轮廓的决绝
对抗世俗的束缚
我来不及说一声,珍重
你这般烈,想表达什么
这红尘俗世,除了我你开给谁看
只有我能看见你厚厚的落叶
我至今不看白雪,不看
一夜之后,被关在窗外的早霜
逝去的就让它逝去吧
这是我的梅
不是王安石那开在墙角的数枝梅
不是陆游驿外断桥边的梅
也不是林逋梅妻鹤子的梅
这是我的梅,青梅
与我的名字有着同样的羽毛
同样的忧郁与决绝
至小至轻的梅
一不小心,让整个山野白了头
一朵很小很小的梅
让落日、流水、长廊、短亭
有了更浪漫的面目
这是一个神迹
耗去了我所有岁月里的盐
一朵很轻很轻的梅
让我想起灵魂的事
想起翅膀
想起诗歌不是可有可无的
这里更像一片麦场
这里更像一片麦场
这里的一些人,或脸上画着红色的十字
或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步履蹒跚
病房里,住着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暂时或永久地丧失了人的某些功能
他们本来在某些地方走动
他们在太阳下走着走着
就被风带到了这里
像连连落地的麦穗,风是命运的镰刀
风能搅起一地黄叶
这天地间的急管慢弦,你细听
就能听出,生与死的相撞
或是死者给生者让路
或是落叶和那个人踩着同一韵脚
做伴去了活人没去过的地方
是悲是喜,落叶不说
那人也不说
范丹花的诗
爬山
我们约好了爬一座山。半年未见
当你告诉我最近游离在你身上的那些
艰深的闪痛被指认为是一种病症
如太阳黑子,时而隐匿时而又
出没于我们的交谈之地,你继续
向我描述黑夜,重叠的雨声像松针
我们头顶忽然就飘着厚厚的云团
大雨不偏不倚,淋湿了衣裙
正如这山形草色下奇异的割据
走过一段陡坡之后,竟全是下台阶
这和我进山前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然后你说:估计要与不适共存了
幸运的是,有一条瀑布也在弯曲向下
直达山底,那奔腾的声响让身体舒展
也许我们也似这段溪水
不知不觉已翻过了那座虚拟的山头
约翰·巴勒斯的森林
用深山来藏下,如果这一生的石头
还不够多
落日会把余晖葬在故乡的山顶
我可能回不去了——当
踏寻的耳朵已藏进树的暮色
在那些无人问津的地方,诞下
语言之痂
无须申辩哪一种挖掘更无意义
我也会永不回头,在梦中
一次次步入丛林
不速之客
夏天,山里蚊子是那么凶狠
不知不觉就带走了我身体的血
三天了,手臂与脚踝处还红肿着
瘙痒不止,以至我不停地伸手去挠
鼓起的包块不断提示着我,那
毒性之大,我的抵抗力又如此薄弱
那无情扎向我的六根螫针必定
又长又细,像被植入一种
特殊又漫长的疾患?我想象它扎入
我毛细血管的样子,是那样毫不留情
三天过去了,那嗡嗡之声,不绝于耳
这使得我不能一直从容地站着
不能枉然侧身也不能沉静平躺
否则,就能感到有什么在周身蔓延
在起伏不定的呼吸和动脉运行中
让我隐隐作疼
秘境
一個人悬在半空
一个人饿着,在云中找到
纯白的装置
他越偏执身体就越轻,几乎
就要飘走了
我看见他在暴雨中把水接住
我看见他用脚猛踩着雨滴
后来的事都有了语境的差异
他始终是一个人
无人为他送去食物,无人
爬高
像他那样全心全意地
参与着黑夜的认领
赫拉克利特的河流
漆黑并非是一种静止,它吞噬了
大量细缝和沙石
夜半忽然醒来,有一条河正在穿过
像细长的白雾从朦胧的彼岸卷尾
在我身上升起布帆和锋芒
升过废墟上那日夜囤积的高山
再漫流到旷野
我始终知道:渡河是一个人的事
上帝从来就没有踏入更何况第二次
中秋节片段
她忽然握着我的右手腕,像握住了
所有流失的韶华,她缓慢转过脸来
对着我笑,那笑容穿过了苍茫
的岁月之海,有幽深的曲折与波浪
她把口水吐在右边地上,嘴角上扬
开始唱起了戏曲,她仿佛回到台上
那时多美呀,她曾是名满乡镇的花旦
她唱了几句停了,声音还回荡在屋内
我简直要喜极而泣了,为她鼓掌
赞美她,她又转身对我笑了一次
双眼冒出喜悦的星星,仿佛听懂了
所有的话,我几乎也要忘记了
一周前,在同一张沙发上,我紧紧
握着她的手,她木然地看着远处
我端详,思绪重复在那张嘴
却没有成型的言语中塌陷又枯竭
那时她女儿刚为她剃短了头发
她弟弟和两个儿子正站在厨房
为如何安置她这个大脑已退化
大小便都失禁的老人而起了争执
最后都在无声的雷鸣中匆匆离去
夜鱼的诗
致意
初冬阳光短暂,刚过午
已倾斜软塌下去,离消隐
也就两三盏茶的工夫
闲坐于亭,被密密匝匝的绿
环绕,高楼缝隙间射来的阳光
使得周身的一切
浓淡相宜,明暗有序
也使得虚搭的树林花园
呈现出的光阴
干净、真实,又来去无迹
上周那枝蓝色绣球花
就是在你左肩后摇曳的那枝
仿佛不是萎谢了,只是向我们
致意后转身暂离
我将记下这座山这座亭
记下每一瞬,活着的
挚爱与悲欣
夏末
她在蝉鸣带来的寂静里
在一所看不到风景的房子里
想着她的风景
初春甜,暮春浓,眼下有些说不清
也许正在冷却,装满爱情的房子
租期将近
两小时前,烈日炎炎下她路过的小区
正在做核酸检测,长长的队列
人们垂着头颅,一种认命的安静
聒噪蝉鸣都打不破的静
她无力关心人类,低着头默默走过
院子里落下许多枯黄的叶子
脚下沙沙响,有一种远胜口号的慰藉
是的,世界迟早归于寂静
寂静里也许什么都没有,也许什么都有
但无论如何
她都不愿再卷入
红枫树下
那棵紅枫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
百年老树,该有多少故事
我很想和你探讨,诸如
黄荆山、磁湖
以及这里的张姓原住民
据说他们就是从红枫树下的渡口
船行磁湖,再渡长江
然后在集市里出清鱼货
可惜这一切连同村名已被人从地图上抹去
你也所知不多
有些含糊其词,但你很清楚
此处地产房价高的来龙去脉
比如炒作、糊弄,租半个公园来
画的饼,都是这几年的事
浓厚的古红枫翠荫下
你指着隔栏外的一片低矮拥挤
“瞧,张姓人家搭盖的违建。”
也就是说曾被古红枫
目睹过的繁衍生息,从天经地义
到违章搭建,也就近几年的事
厮守
晚餐后,煎黄鱼的香味还未散尽
你熄灯,泡普洱,又端来一碟荔枝
这加深了黄昏的幽暗与甜美
我们彼此倚靠,身心放松
仿佛身子底下不是一张沙发
而是一片沙粒细润的海滩
时间可有可无,又浓厚稠密
一波波涣散,又一波波凝聚
你偶尔揽紧我,像神情严肃的船长
偶尔紧握一下桅杆
这赋予了我勇气,去审视与瞭望
另一个我:她的缥缈、执迷与昏聩
如同曲折而又漫长的海岸
椰林的阴影下,纠缠无数阔叶与藤蔓
礁石在海浪的冲刷下,不动声色地变形
哦,那么多的随风而逝
但只有你,只有你的眼里闪烁我的梦境
只有你才能改变我暂居者的命运
低处
卧榻小窗边的香樟
不受季节影响,叶子茂密
持续送来风声,以及雀鸟儿
细碎的咕咕声
离香樟几步远,一棵硕大的乌桕
挂满喀拉拉响的乌桕子
正对阳台的则是一棵鹅掌楸
立冬后,半树黄叶,越来越稀疏
不停飘坠,风大些,就会飘过红砖路
飞向对面的树丛
那里有更多树种,最外围是一排
高低错落的李子树
初夏时,紫色的果实曾满地滚落
磅礴的浪费,气势直逼
四周僵硬的高楼
我终于意识到低层的好处
当晨曦或夕阳穿过无数叶片
抵达我闲握的书册
当深夜簌簌,当我垂下眼帘聆听
雨叶和奏。一种领受
如众神的脚步穿过茫茫宇宙
我的痛苦不是一间黑房子
法师,此刻我正看着办公室窗外的阳光
那些晒过的叶片
绿意比山上的浅了许多
而山下的我,也似乎比山上浅
刚才一件工作上的事,我半小时完成了
接下来,我将继续按部就班
下班买菜,煮饭熬汤
除了不得不为了孩子,尽量避开血腥
但却没办法不爱葱姜蒜
我不想刻意改变什么
我也没有因此感到难堪
心不安,山上山下就都一样了吧
法师,我想不起那天在庙前,低头望着脚下阶
梯时
到底想了些什么?让您生出怜悯
阿弥陀佛,俗世之人其实都可怜
我也不例外,挣得脱挣不脱
此消彼长,并无圆满
那就这样吧,我饮下的是茶还是酒,都不重要了
明日的醉意可能更不可解
我的痛苦不是一间黑房子,是一架云做的梯子
月光洒在上面
风使它轻轻地晃动,我的
生之趣
也不分黑暗光明,只是随风晃动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