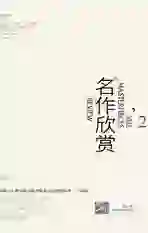读书问学四十年
2022-02-10谢思炜杨阿敏
谢思炜 杨阿敏
谢思炜,1954年生,北京人。唐宋文学及文献研究专家。1996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2001年起,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宋诗学论集》《唐诗与唐史论集》等;整理点校出版《杜甫集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等。
杨阿敏:请谈谈您中小学的教育经历?
谢思炜:我小学到五年级就赶上“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就都停课不上学了,进入中学应该是在1967年,小学等于没毕业。进入中学之后,那个时候又不能正常教学,文化课就上得很少,经常搞运动和学工学农各种活动。到1970年我们就应该初中毕业了,但实际上中学两年多,真正在学习上的时间是不多的。比如说我们的数学,学到哪里呢?就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外语呢,就是英语,是开过几次,大概就是学了最简单的一些问候语。
那时候也没有高中,我们这一届初中毕业后还没有恢复高中,一直到我们下面的一届两届才开始恢复,有一部分学生可以升入高中。我们中学毕业以后,都是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像我哥哥当时去的就是东北的建设兵团,他比我早一届,是1969届的。我们这一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大部分没有上山下乡,因为当时北京市缺工人,前面的好多毕业生都到外地到农村去了,我们那一届基本上就都留在北京了,被分配到各个单位,我们中间大概有好几百人都被分配到一个建筑公司。我做了将近八年的建筑工人,一直到恢复高考,这期间一直是在建筑公司。
我们那个工种叫抹灰工,跟瓦工差不多,它可以归到瓦工里面,要细分的话叫抹灰工,这是建筑的一个很重要的工种。后来就恢复高考了,但是这之前呢,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差不多都有一个经历,你没有一个完整的好好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当时没有后来的应试教育的一些压力,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找书来读。
杨阿敏:当时您看书的途径都有哪些呢?
谢思炜:书当时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的,从图书馆也能借到,“文革”刚开始的那一段时间可能借不了,但是到后来也就慢慢恢復了。我父亲在中学,他从学校的图书馆能够借出一些书来,当时社会上也流传一些书,各种各样的书都会有一些的。那时候我们读的比较多的,提倡读的;就是马列原著,包括比较难懂的像《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读这些书至少让你对马克思之前的整个西方思想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些书也训练你的思维。后来我和我的研究生同学聊,他说他当时把马恩全集全读了一遍。我没有读那么多,但是也看过一些,包括三卷《资本论》都读下来了。
也读过很多像历史、文学一类的书,《鲁迅全集》我基本上都看过。北师大的郭预衡先生有一段时间是做现代文学,就是研究鲁迅,他对鲁迅是下过好大功夫的。现代文学中比较著名的像茅盾、巴金,能找到的当时都看过,外国的也看过不少。另外,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有好多内部书,那时候是由高层组织的一些人专门去翻译的,那些书翻译的质量都很好。
杨阿敏:您还记得当时参加高考的情况吗?
谢思炜:1977年恢复高考,我还算比较幸运,当时大概就几个月的准备时间,这几个月我主要就是学数学。以前只学过一点,我就把从初中到高中的数学全学下来了,基本上是自学,包括到高中的解析几何。那年高考也比较有意思,北京市出的题是各个年级水平的都有一部分,比如说你只会初一的,他可能有一道题就是初一的,你能够得十分,他照顾到不同层面。我是数学最难的题都做出来了,但是中间也有两道题是做错了的,因为审题错误。
当时就是考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好像没有考外语。高考作文北京市出的题叫《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个题是北师大郭预衡先生出的。另外还有一些阅读理解题,出的是鲁迅的一段话,让你谈怎么去分析它,大概就是这样。
当时是考前填志愿,但是那个时候只能填三个志愿,就是你只能报三个学校。我第一志愿填的北大,第二志愿填的北师大,学校也很少,当时三个学校报的都是中文专业。
杨阿敏:请讲一下您的大学生活?
谢思炜:当时是春季入学,春季毕业,1978年春季入学,所以我们后面那届1978级只和我们差半年。大学还是很好的,当时上很多课。像韩兆琦先生、辛志贤老师、杨敏如老师、启功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启功先生是讲中间一段,给我们讲杜甫。聂石樵先生、邓魁英先生那时候都给我们上过课。那时候北师大古代文学的这些老师,力量也很强,本科阶段基本上都能听他们的课。
那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老先生教的,他们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还有一批基本上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50年代毕业的老师。当时不够开放,大家的视野还不够开阔,能够了解的学术、思想还是有一定局限的。
杨阿敏:在大学期间,您是如何读书的,自己买书多吗?
谢思炜:这个应该是跟我们以前的经历有关。以前自己已经有读书习惯,自学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跟我经历差不多的这些人都是这样。原来就是主动找书来读的,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进了大学之后,条件更好了,也更方便了,好多书都能看到,而且有比较完整的时间。我在本科的时候把《左传》和《史记》读下来了,这样文献阅读的基础就比较好了。另外还读过古代文学比较重要的一些典籍。
我自己也买一些书,当时我不像有些同学非常执着。当时有些同学只要是出新书他都要买,我没有这样。现在来看的话,当时大学买的书后来基本上都没有用。那个时候因为课比较多,自己的兴趣也比较广,所以可能各种书都会买一些,以后你研究范围越来越窄,其他专业的书可能就用不到了。
杨阿敏:有人提倡读作家要读全集,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谢思炜:读全集也是要分阶段,本科刚开始进入的时候恐怕读全集是读不进去的,还是要有一个基础。像我们当时是跟着文学史的课,它有一个作品选,首先要把这些先读下来,然后有余力,再选择一些作家来读。可以先读专业课要求你读的作品选,另外再读一些重要作家选本,像李白、杜甫可以读一些选本,以后再进一步。我们是到研究生阶段老师才要求完整地读作家,读全集。当然像李白、杜甫这种大家,他们的集子的量也非常大,读一个差不多就要半年,如果在本科阶段这样读的话时间也不够用。
杨阿敏:毕业之后为什么选择考研究生呢?研究生阶段导师是如何指导您学习的?
谢思炜:考研究生就是为了深造,也是学了这么多课程之后发现还是对这个专业比较感兴趣的。以前也曾经考虑是不是考其他专业,而选择这个专业一个是因为我们专业古代文学前后几位老师都讲得非常好,能吸引你喜欢这个学科。另外我也是在这上面投入了比较多的精力。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我们那年的研究生招生不是所有专业都招,有些专业不能保证每年都招生,有些专业是今年招,有些专业是明年招,招生是逐渐恢复的过程,而我们那一年正好古代文学专业招生的计划名额是最多的,所以从考试的角度来讲,考这个更有把握一点。原来的计划是招五个,后来好像是录取了七个。没有保研,那时候都是统考,全国来考,所以竞争也还是很激烈的。我们那时候考研的比例也是很低的。
我们是春季入学,就是1982年年初入学,如果完整的话应该是到1985年年初毕业,我们当时就稍微提前一点,到1984年年底答辩都进行完了。然后就入职了,按年来算的话其实也还是三年。
当时是启功先生、邓魁英先生指导我的。当时就是按段分,从先秦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是一段,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是一段,启先生和邓先生是负责指导唐宋这一段,然后元明清是一段。主要是启先生和邓先生合作,当时毕竟启先生年龄比较大了,有些具体事情可能都需要邓魁英先生帮着来处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合作指导。
研究生阶段老师指导还是很具体的。是唐宋方向,邓先生就大概分配了一下,一年是读唐代,一年是读宋代。老师是有资深经验的,就说你要选重要作家来读,要完整地读,一个学期读一个作家。所以我们第一学期读李白,第二学期读杜甫。李白就是读瞿蜕园、朱金城先生的《李白集校注》,杜甫还是读仇注,这是一年。第二年读宋代,第一个学期读了苏轼,当然苏轼的量很大,读起来也是很紧张的,诗词文都读,后来读得就不那么细致了。到第二年第二学期就要考虑毕业论文了,再读一个大作家可能就讀不下去了,所以当时我自己又读了一些江西诗派,黄庭坚这些。
我们那个时候上课是不太多的,也不像后来规定你必须要修多少学分,必须得开多少课。这种要求当时都不是很死。老师就是布置一些这学期要读什么,最后每学期都要提交一些读书报告、小论文。
另外,启先生也给我们上课,启先生特别给我们准备了一门他开玩笑称之为“猪跑学”的课,就是说,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他是从俗语来说的,就是说要提供有关古代文史的各个方面的一些知识性内容,很多是在一般的课程或书本上不一定能查到的。
那个时候老师指导我们更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和我们讨论问题,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也随时都可以问老师。像启先生,他有什么想法都会跟我们讲。这种方式对于学生来讲是很有帮助很有收获的。你会经常接触老师,去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老师也经常会想要听听我们的看法,听听我们对问题的了解,也会让我们介绍一些学术上新的观点。没有什么固定的讨论,都是一些日常性的交流,老师也没有要求你必须什么时间要来参加讨论。而且这种交流也不限于读学位的这几年,后来我留校工作的十几年时间还经常会去找老师,当然平常这种交流很随意,听老师谈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是帮助很大的。
老师教你一些东西,解答一些问题,直接传授一些知识包括治学方法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见识了一种做人和做学问的境界。
杨阿敏:硕士毕业论文为什么选择研究宋代江西诗派的诗人吕本中?
谢思炜:当时唐宋诗读下来之后,前面读杜甫花了很大的精力,就想到和杜甫有很大关系,受杜甫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江西诗派。我把江西诗派像黄庭坚、陈师道就基本都看了一下,黄庭坚花的时间比较多,因为他的诗不太好读。具体到硕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当然要和导师交流,要选黄庭坚这样的诗人可能难度比较大,不一定做得下来,硕士论文时间比较紧,我就选择了相对而言当时讨论还比较少,但还是有一定重要性的诗人吕本中。
吕本中的集子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的,作品数量也比较多,大概有一千多首诗吧。而且当时我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了他的一个外集,叫《东莱外集》,收藏在北京图书馆,以前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包括钱锺书先生,他在《宋诗选注》里面选了吕本中的一些作品,提到吕本中有一组诗只从《瀛奎律髓》里面选了几首,这组诗现在见不到了,他很遗憾,说这组诗应该是很重要的。那是靖康事变之后吕本中写的一组诗,这组诗实际上是保存在《东莱外集》里面的。当时发现这个资料,是大家曾经知道,但是都没有调查到的,也算是我的运气比较好。所以当时我还给钱锺书先生写信,告诉他我这个发现,钱锺书先生也给我回信了,他说他们所里面也有一个学者发现了这些作品,告诉了他这个消息。
我当时做论文还给吕本中编了一个年谱,基本把吕氏家族的材料,从北宋后期到南宋的历史文献、各种文集我基本上都翻了一遍,有关的材料都找出来了。论文答辩的时候是傅璇琮先生做答辩委员会主席,傅先生编过《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的资料汇编》,所以他看这个论文的时候,说我里面有一个材料是他没有用过的,就是关于吕本中家族的一些材料。通过这些家族材料能够说明吕本中跟黄庭坚、江西诗派的一些关系。
吕本中在宋代文学中的地位,我觉得是过渡性的,他位于南北宋之间,但毕竟不是第一流的大诗人。我硕士论文后面有一部分讲他的创作,后来发表了。他在南北宋之交经历了很大的社会变动。像当时也和江西诗派有一定关系的陈与义的创作,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变,他的诗讲他事变之后的逃难等经历。吕本中也是,在这一个阶段,有很集中的一些作品记述这个时代。而且当时他就在东京的围城之内,还参与了一些活动,这都在他的诗里面有记录。他这种集中的书写应该是与杜甫有关,包括他写很长篇的像杜甫《咏怀五百字》的作品。宋代诗人里只有少数人选用这种形式来创作。可能与他的创作经历有关系,所以他也写这样的长诗,另外还写一些组诗。这些诗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钱先生在《宋诗选注》里对他的有些作品也是评价很高的。
杨阿敏:您硕士毕业以后留在北师大任教,为什么要考虑继续读博士呢?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什么课题?
谢思炜:我们读博士是在职的。在高校工作,学历上当时是没有什么要求,后来还是有要求的。另外读博的话收获会比较大,你可以集中一段时间做一个专题。那个时候正是学术积累阶段,有这样一个压力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博士论文做的是白居易,后来就以《白居易集综论》出版了,这是启先生帮我定的题目。有一部分是讨论文献,就是白居易文集的中国刻本、日本的抄本,还有其他一些文献的调查,另外一部分是有关白居易的生平、思想、文学创作的讨论。
选白居易当然也是考虑到他还是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的,有开拓的空间。另外也受启先生的影响,启先生对白居易的诗非常喜欢,也非常熟悉。他有时候讲其他诗人还有一些批评,会挑一些毛病,但是讲起白居易的诗他很少这样。启先生的看法和他的诗学观念是有关联的。他书房里挂了一副对联,是他收藏的清代学者的,上联是“元白文章新乐府”,下联是“霓黄画法旧诗传”,可以看出启先生对白居易的诗是非常推崇的。
也是受启先生的影响,当时我想把白居易好好读一读。我在读硕士的阶段其实没有读白居易,那时候老师也说白居易确实不好读,因为那时候白居易是没有注的。到大概1988年,朱金城先生的笺注出来了,但是他的笺注基本上不注典故和词语,主要注人物和事迹。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就没有推荐我们去读白居易,我是工作以后才开始花时间把白居易完整地读下来的。
做博士论文要考虑选择什么题目,我有一段时间还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选择杜甫,因为在这之前我做他的研究还是比较多。但是后来又看到一篇文章讲日本白居易文集抄本研究情况介绍,这也是一个因素,就是我了解到有关白居易的相关文献,还有很多我们不太了解的日本学者在做的一些工作。
日本抄本的源流都是唐抄本,跟中国的刻本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是当时由各种途径传入日本的。其中有一个是日本僧人到苏州南禅院,苏州南禅院保留有一套白居易的集子,这个叫惠鄂的和尚就把苏州南禅院的集子整个抄了一遍带回日本,后来日本的那些抄本就是对这些抄本反复转抄,所以跟中国的刻本的系统就不太一样。
杨阿敏:您研究生阶段师从启功先生和邓魁英先生,启功先生可能大家比较了解,您刚刚也讲了一些,您可以谈谈邓魁英先生等其他先生吗?
谢思炜:邓魁英先生和聂石樵先生是夫妻,所以我们实际上跟两位先生都接触,他们会跟我们谈各种问题。我觉得邓先生和聂先生做研究很有经验,所以对我们学习、做研究的指导很具体,可以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比如说我选择一个研究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可以做一篇学位论文,邓先生、聂先生听一听你的想法,就能帮你判断这个题目做得成还是做不成。
这个对学生来讲确实是很重要的,我们没有经验,可能觉得自己有一点想法,就把它做下去吧。但是这时候如果有一位有经验的人帮助你评价一下这个题目是不是有价值,就现有的研究、材料来看,你有没有必要继续做下去,这很有益处。
这两位先生都是那种非常谦和,从来也不张扬的知识分子,对学生也都非常关心,有什么事情他们都会帮助你。
我当时从这些老师身上学了不少东西。比如像郭预衡先生,他也给我们上过课。有一次我调查杜甫的集子,发现杜集原来有好多小注,我判断它应该是杜甫的自注,但是过去有一个说法,自己写的诗不能给它作注。所以杜甫诗里面的这些注怎么来判断是不是自注,也有好多怀疑。后来有一次课间我就问郭先生:中国古代文人有没有给自己做自注的情况?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郭先生马上就告诉我像谢灵运的《山居赋》里面就有大段的自注。就使我比较有底了,知道诗文自注实际上是有这种习惯的。
在本科阶段,郭先生有给我们的讲座辅导。他讲了怎么学习,说学习要学三方面,一个是要学一点记问之学,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说你必须要记一些东西;第二个叫学一点章句之学,这个主要是指要理解它的篇章大意;还有是要学一点通人之学,这个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还有聂石樵先生,本科的时候要写毕业论文,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写论文,我们就请老师辅导一下。我记得当时聂先生给我们开一个讲座,就是讲怎么写论文。他讲“首先你的论文题目是从哪来的?”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题目很重要,希望老师告诉我们一个秘诀,怎么去找论文题目。聂先生说论文题目是从长期的研究工作积累中得来的。这个大家听了就有点失望,觉得这个还用老师说吗,但是我感觉聂先生这个话都是甘苦之言。就是说你不要急于求成,忽然间就能发现一个题目了,这不太现实,需要靠你学习研究的积累。
聂先生当时还特别强调一点做学问包括写论文,不要发怪论。聂先生这些讲法其实都是有针对性的,是多年来他自己做研究看到一些现象之后的认识。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人研究杜甫,讲杜甫是“农民诗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这种观点的,这个就是怪论。就是故意找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说法,看起来好像很新颖,但是其实这种提法并不能说明问题,也站不住脚。聂先生的这些告诫对于当时还是学生的我们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杨阿敏:您在数十年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您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读书经验和方法吧?
谢思炜:经验倒是谈不上。我自己读书后认为,一个是要有比较好的基础。刚才说过本科的时候和我之前是有一个转变的。之前读过哲学、经济学之类的书,所以高考的时候我特别想选择这样的专业,但因为刚恢复高考,好多专业都没有,而我们家庭又不太支持我选择哲学专业,我就选择了中文专业。我一开始对中文专业的文艺学比较感兴趣,后来逐渐地转到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上。想在这一方面多花一点时间,就去读《史记》《左传》,这些其实都不是老师要求的,是自己觉得需要这么去做。把这些书读下来,我就有了比较好的阅读基础。做古代文史研究,小学的训练非常重要,像文字、训诂、音韵,我自己也确实讀过一些,有些专业课也听过,但是我这些方面学得不好,我的记忆力比较差,像《说文》我也看,但是没有非常系统地学一遍。这可能是我自己读书的一个差距。
另外一个是要读作家。我做唐宋这一段,就从李白、杜甫这些大家开始读,毕业以后也是接着选这些作家继续读。宋代的作家也读了一些。另外各种史料都要读,在读硕士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你一边读作家(比如你读唐代作家),一边要把唐代历史总体读下来。
比如唐代这段,老师说一开始读《资治通鉴》中唐代这一部分就行。这是帮你了解整个唐史的情况,而且《资治通鉴》相对比较好读,是叙事的,看前面就很想了解接下来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光读《资治通鉴》显然不行,其他的唐代史料要根据研究需要进一步去了解。
一边要读文学作品读这些作家,另一方面要尽量多读一些材料,多读一些史料。大概要有一个计划,像有的学者说的,你要做哪一段的研究,有一些基本材料你花五年十年应该把它都读下来,这是一种做法。但有时候因為材料太多,时间不够,就只能先读一部分。另外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要有目的地去调查。比如我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白居易的时候,真的是必须把唐代的这些相关材料都读一下,我花了一段时间首先把《全唐文》整个查了一下,并想到可能会有哪些是我研究白居易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我带着这些问题去查这些材料,用比较快的速度把《全唐文》整个看了一遍,可能会有对我很有用的一些材料,我就把它搜集出来。
唐以前的史书我就读得不够,只是在调查的时候会看一些,因为后来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我也做过一些专题研究,当然也会看一些,但是我知道看得很不够。
先秦两汉的典籍,是一些基础知识,必须得读。但是有一些确实是很不好读的,像《十三经》,像三礼(《仪礼》《周礼》《礼记》)。而且它们还有注疏,而这些注疏量也非常大,要花很多时间去读。所以这些要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有目的地去调查,会更好一点。
杨阿敏:读研究生阶段,您认识到材料考证、版本校勘是研究的出发点,当时选做的一些课题大都与此相关,您如何看待这一阶段的朴学训练?
谢思炜:这个也不好说是朴学吧,朴学有些东西我也没有很好地掌握,这个实际上就是文献学,文献学是一个基础。另外从治学角度讲,应该尽量全面一点,有一些做研究的,对文献方面基本上不涉及,就用别人整理好的文献,这个就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我自己的体会是,你只有从文献做起,才能心中有数。
比如说我做杜甫,做白居易,文献方面我掌握得相对比较充分一点,所以讨论它的作品问题,就心里有数。其他一些我没有直接做过文献调查,或者做得比较少的,我也可以谈一谈,但是就不敢像讨论杜甫、白居易这样,不敢全面地进行讨论,只能限定在一定的范围里。
从文献的调查里面确实能发现好多问题,即便是做杜甫,前人不知道已经做过多少研究了,但是从文献入手的话,还是会发现一些问题,甚至文献的基本理解上都有一些问题。这就能弥补前人的一些不足,纠正一些不准确的说法,才能够更深入地讨论一些问题。
杨阿敏:前人有一个说法叫读书先校书,您怎么看呢?
谢思炜:有时候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说所有的书你读之前都要校,作为你的研究对象,这个是应该有的一个基础。
文献学其实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不是说上一个文献学的课,读两本文献学的书就能解决问题的。比如说有一个文集,那就从校勘入手,启先生说文献学里面什么最重要,就是校勘,这就是一个基础工作,只不过是愿意不愿意做的问题。因为校勘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花很多时间,校得头昏眼花的,但是最后校出来的问题可能很少,所以好多人就不愿意去做。但不采用这种方式,又没法进入文献的工作中,去研究版本等。如果没有经过校对,校勘,你根本没法判断一个版本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杨阿敏:毕业任教后,您开始接触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各种哲学思潮、文艺学思想,为什么会有这个认识上的变化?这样做给您带来了什么影响?
谢思炜:以前其实也知道一些,但不是特别的关注。80年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西方的各种学术观点、学术流派包括一些研究方法介绍进来的比较多,一开始觉得目不暇接,东西太多了,消化不了。但也是大势所趋,你必须得知道一点,眼界狭隘是不行的。
外文原著如果读不了很多的话,可以读一点,包括读原文。现在也有一些专门选给研究生,包括本科生也可以用的经典导读著作,它就是一个范例,原文不一定每一篇选很多,把一些很重要的,至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选一些。这样的话就可以花相对比较少的时间,读的面比较广一点。
另外,我自己的体会是,假如做某一方面的研究,就需要适当了解国际上的相关研究成果,就必须读它的原著。因为什么呢?光看中文有时候确实是不够,现在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个引进其实是滞后的。如果仅看翻译,肯定会丢失一些东西。这个当然得有一定的针对性。
杨阿敏:您最初留在北师大工作,期间曾到日本名古屋大学讲学,之后怎么到了清华大学中文系工作呢?
谢思炜:我们这个专业在高校工作最合适,当时留在北师大是最好的选择。那个时候硕士就留校工作了,我们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博士。我们之前的那一届研究生也是硕士就留校了,我们这一届这个专业就有三个人留校。那个时候机会比较好,现在可能博士也不一定能进高校工作了。
从1984年一直到2000年在北师大,有十五六年吧。当时主要是开文学史课,唐代、宋代、元代还有魏晋南北朝这几段我好像都讲过,另外选修讲过杜甫、禅宗等,研究生也讲过一些课,也是唐宋文学研究。
到日本名古屋大学讲学是学校间的合作,当时北师大派我去那边当外国人讲师,中文专业教一年的中文。从一年级开始就有这样的课,各个年级都有。这种课我其实在好多地方都上过,在韩国上过,在国内也上过,也给留学生教汉语。这个课也挺有意思的。
在这之前我跟日本的有些学者有过联系,因为做白居易研究,我给太田次男先生写信,他后来就让他的一个学生跟我联系,给我带一些资料过来。所以我和他们在这之前就有联系,后来利用这一年的时间,我在日本参加了学术界的一些年会、读书会之类的,接触了更多学者,在他们那边查文献资料也更方便一些。后来我在2007年、2011年、2014年又去过几次日本,有一次就到东京的各个书库去调查,当时时间很仓促,就像看展览似的要看一下日本这些抄卷保存的情况。
在日本生活还是挺好的。比较遗憾的是尽管在日本待了一年,我的日语却没有学好,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我交流的那些学者大部分都会讲汉语,有一些通过翻译的帮助,也能交流。除了这次到日本,我还去过韩国一年,也是校际交流,担任教中文的任务,是2006年在清华的时候。
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工作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就是一个正常的工作调动,在北师大待了很长时间,后来清华这边正好有一个机会,他们想让我过来,就调过来了。后来傅璇琮先生过来,成立了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傅先生是主任,就给我派了一个副主任。在傅先生领导下,我们做一些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工作。
这个提要工作主要是傅先生在做,他策划组织。做这个提要是要很多学者参与的,难度是很大的。现在这种情况需要组织集体来做,不像过去,现在大家都很忙,做這个工作需要很大的投入。但这是一个集体项目,从效益上来讲,大家觉得不是那么划算。所以,组织起来是比较费劲的。约稿都是傅先生在做的。集部的这一部分傅先生让我做主编,做一下统稿工作。大概有上百位学者的稿子,我把它们看一遍,做一下加工。
这个工作做了好几年,现在还有两卷没有出版,最早出的是集部和史部,经部和子部后出。
杨阿敏:您现在清华开一门《左传》课程,为什么会想开这门课呢?
谢思炜:这是给本科生开的,而且从一年级就开。我们设计了一个课叫经典研读,是一个系列的课程,要上四个学期,就是选一些最基本的典籍来研读。原来这个班是一个试验班,文史专业是不分的,所以这个课就是帮助他们打好基础。文献阅读基础,这是很重要的。除了学古代汉语这些专业课,还要有文献阅读做保证,那么就逼着学生读原著,通过读原著培养他们的文献阅读能力,同时也能了解了历史、文化的一些基本知识,这些训练对他们还是有好处的。
我这个课就是读,给学生规定好每个星期读一百页,你自己回去读,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在课上一块儿读,我让每个同学当场读当场翻译,就是检查他们阅读的情况。学生翻译一遍后再讲评,看看他们是不是读懂了,其实就是起这样一个作用。同时,读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课上交流。一个学期基本上能读完。我上课用的是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我对他们的要求就是把它通读下来,但是现在我们一个学期只有十六周的课,课时是紧一点,所以有时候后面留一点就是到课程结束后再去读。我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一周读一百页,那个书大概有一千多页不到两千页,一个学期把它读下来还是可以的。
刚才说的经典研读,叫中国经典研读,另外他们还有一个西方经典研读,正好是配合的,我主要是开中国经典研读。
杨阿敏:作为博士生导师,您是如何指导研究生的?
谢思炜:指导学生,这个谈不上有什么经验。因人而异或者因材施教吧。学生情况千差万别,中国学生和外国留学生肯定是不一样的,要求也不能一样。主要还是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比如说你做什么样的研究题目,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杨阿敏:请您谈谈自己阅读和研究杜诗的一些经历?
谢思炜: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是第一次完整地读杜诗,当时我自己就做了一个工作,因为那个时候跟老师学习,就是在文献方面进行训练,老师也给我们一些指导,我自己也想去尝试,于是我就做了一下杜诗的校勘。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读杜诗基本上还是读清代的注本。清代注本的校勘受当时学术条件的限制,他们好多材料是没有见到的,比如看仇注的校勘,仇注以前像钱笺的校勘,还是很不够的。有些资料我们后来能够见到的,像《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本杜工部集》,它基本上能够反映北宋二王本的面貌,这些材料清代注家基本上没有利用。
所以当时我想可以自己做一个训练,也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可以做一个更好一点的杜诗的校勘工作,我就找当时比较能够容易找到的杜诗的宋代刊本,当然都是影印本,像《四部丛刊》里面的,还有像《九家注》的影印本,就是最有代表性、最重要的这些本子,我挑了这么几种,然后做了一下校勘。这个校勘工作对我就是一个学习,一个初步训练。当然,整个工作做下来之后,我对杜集版本的情况、文本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把握。
后来到硕士论文做宋代江西诗派,杜诗这个就放了一段时间。工作以后,想研究哪些课题,我就想还是回过头去再做杜甫,就开始写了一些有关杜甫的论文,后来都收到《唐宋诗学论集》里面了。当时我投的一篇关于杜诗自传性的论文,特别得到《文学遗产》陶文鹏老师的鼓励,他说这篇还是写得不错的,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我得到鼓励,接下来继续写了几篇,前前后后有十年的时间,就是讨论杜甫的思想、创作等。
同时,那个时候我也给北师大本科开选修课,讲杜诗,主要是讲作品。选了大概是三四十篇。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周绚隆先生约我做一个杜诗的选本,开选修课时的那些底稿,就用在《杜甫诗选》里面。这个选本出了以后反响还是比较好的。
再后来就是决定做《杜甫集校注》。我并不是很早就有这个计划,大概是2007—2008年,那个时候我的《白居易文集校注》已经交稿了,就有一点空闲,当时也在考虑接下来做什么。有一次在出版社开一个讨论会,讨论古典文学的选题计划。当时大家就在议论,就讲到这一点。那个时候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还没有出来,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大家就说有一些很重要的大作家的新的校注,从1950年代到现在,还没有人做。
那个时候我忽然有一个想法,我是不是也能做这个选题。当然我知道,萧涤非先生他们正在做,但是我觉得我们做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我就试着做一做,看自己能不能做。之前我有版本调查、校勘的基础,我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校注工作。我就这样做了几卷。正好第二年,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赵昌平先生到北京来开会,当时我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赵先生就是来开这个工作会议。在底下聊天的时候,我就把我正在做的跟他说了。后来我就把完成的前五卷寄给了他。他可能比较满意,也接受了这个稿子。大概从2008年做到2012年,2012年5月我就给出版社交稿了。
作者:杨阿敏,《中华瑰宝》杂志编辑。“尔雅国学”公众号创始人。
编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