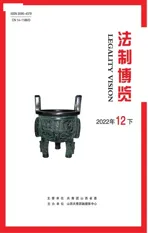县域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研究
——以常山县“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体系改革为例
2022-02-10李黄骏宋淑溶
李黄骏 宋淑溶
1.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 杭州 310012;2.中共绍兴市越城区委党校,浙江 绍兴 312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期间提出建设“法治浙江”,其中,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成为法治建设过程中的治本之策。从城市管理相对集中处罚权到综合行政执法,再到“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集成改革,浙江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探索成效显著。2022年1月,《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制度框架基本确立。作为浙江省“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省级试点之一,衢州市常山县统筹推进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为我国县域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县域综合执法体制的内涵
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正式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1]这也是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开始的标志。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创新探索,目前学界对于“综合行政执法”这一概念尚未形成权威、统一的定义。大部分学者认为“综合行政执法”是指“将部分政府机关中原有的执法权力进行整合,交由新的独立的行政执法机关统一行使执法权力,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原机关不再行使权力”。[2]在《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中,“综合行政执法”的内涵释义为:按照整体政府理念,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通过优化配置执法职责、整合精简执法队伍、下沉执法权限和力量、创新执法方式,开展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行政执法活动。[3]从特征层面来讲,综合行政执法与分散执法是互相对立的关系,其旨在从根源上消除由于各执法部门分工过细、职能分散、权力交叉、多头执法等带来的执法越位、缺位、错位等系列问题。从现有的实践效果来看,将各项行政处罚权集中于一个政府机关,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政府执法资源浪费,也有助于政府权力的优化和制约,加强法治中国建设。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则是指构建而成的行政执法机构和制度规范的统一体,为实际执法的机关赋予“执法资格”,确保“有法可依”,即某一个行政机关(包括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在法律法规范围之内,合法拥有原本多个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权,行使各项行政执法权力。[4]从国家治理角度出发,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是对原有行政权的一次系统性调整,是政府为积极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治理环境所采取的一种适应性措施,[5]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抓手。
县域治理承载了我国大部分治理内容,从实践层面看,县域作为全面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关键节点,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探索中,不仅要贯彻落实中央顶层设计中对行政执法职能以及机构整合的整体部署精神,[5]亦需将改革的落脚点落至地方治理的现实需要。从理论研究层面来看,目前我国对于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探究改革的顶层设计及总结经验领域,从县域层面出发研究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具体实践,不仅拓宽了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是从微观角度对综合行政执法现有的相关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完善。
二、现行县域综合执法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矛盾也日趋复杂,这对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项重大考验。总体而言,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进展和社会新需求仍存在一定差距。部门间多头执法、执法主体权责不清、执法队伍力量薄弱、执法行为监督缺位等共性问题仍然存在,县域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正面临挑战。
(一)执法主体不明确
行政执法是一项多层级、多领域的管理工作,往往需要多部门联合执法,但在多头管理的情况下,执法主体不清现象时有发生。基层事务的多样性、复杂性导致很多事务的处理仍分属于多个部门管辖,而不同部门的内部审批、监管流程、行政处罚、监督程序等却在各自体系内封闭循环,[6]这导致执法部门管理职能无法实现完全整合,部分执法资源也无法实现完全共享,“看得见、摸不着”的问题仍然存在。同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相关机构合并调整难以一蹴而就,使得部门间权责模糊、各自为政、跨部门联动协调机制运行缓慢的现象时有发生,其根源在于难以完全协调各部门间的利益平衡。此外,政府执法缺位也会导致执法主体不明确,许多事项的执法权在县级以上,但在具体工作中往往委派下级政府代替执法,[7]由于下级政府不完全具备执法资源与职能,进而导致执法缺失,形成执法真空地带。
(二)执法权责不对等
目前,我国对于可以划转至综合执法机构的行政执法权的种类与具体内容尚未在省、市级作出统一规定,对于如何清晰划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与原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也未经严格论证,两者之间的权力界限尚未厘清。在实际执行中,基层往往根据区域实际情况沟通协商自行划分,这容易导致不同地区主体职责范围不一,受部分职能分工和行政级别影响,部分职责划转不合理。个别职能机构基于本位主义,通常将难度大、获利小的棘手事务划给综合行政执法机构,[8]或者只负责审批,而把监管、执法等日常事务性工作交给行政执法部门。同时,部分行政执法事项需要一定技术资源支撑,对划转的完整性和及时性要求较高。如相关技术支撑并未同步及时转移,容易影响执法效率与效果。此外,一些部门仍保留了部分事项的行政处罚权,导致划转出的处罚权与保留的处罚权相互混淆,形成新的职责交叉和多头执法,造成执法过度。
(三)执法队伍较薄弱
在新形势下,执法工作日益繁重复杂,且跨度大、难度高、专业性强,对执法队伍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但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基层执法人员不足仍是一大制约因素,编制内的执法人员数量与职责任务强度不相匹配,这就需要大量编外人员来协助执法。但是聘用制人员不具备执法资格,且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县域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中的执法人员来自不同部门,专业知识学习和培训虽有开展,但局限性较强,执法人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普遍不高,且实践中部分执法人员法治观念仍待提升、执法理念和执法方式也与当前的执法形势不相适应,对于一些复杂疑难案件和群体性违法行为,执法方式单一,导致很难高效解决行政执法案件。
(四)执法监督不到位
在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仍缺乏有效完善的执法监督机制,致使改革陷入监督困境。例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缺乏程序制约,部分执法部门的同一个办案人员兼任案件的调查取证、处罚决定等多项重要工作,监督制约、问责机制流于形式,从而无法保证案件处理的合法性、公正性。此外,执法监督主体单一,缺乏社会监督也是使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陷入困境的因素之一。当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发挥监督作用的依然以内部监督为主,社会监督机制虽然早已构建,但公众监督渠道的不顺畅致使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依然缺位,导致监督主体的“单一性”,不能真正发挥多元主体的监督合力。
三、县域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的常山实践
2022年1月,《浙江省加快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获中央改革办批复同意,浙江省成为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作为“大综合一体化”的省级试点,常山县坚持“县乡一体、条抓块统”的协同治理新格局,做实做优“综合执法+专业执法+联合执法”,探索出一条符合县域特色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常山范本”。
(一)聚焦权责重构,推动执法事项集中优化
针对部门之间、部门和乡镇(街道)之间执法主体不明确、权责不对等、“三不管”“多头管”等问题,按照整体政府理念重新调整执法权限,减少交叉重复、填补执法空白,推动“多部门执法”向“一个政府行政”。第一,坚持清单化管理。加快梳理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编制形成全县行政执法事项库。在省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基础上,对散落在24个部门的4100项行政执法事项梳理归类,将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执法频率高、多头重复执法突出、专业要求不高的1367项执法事项,统一划转至重新组建后的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集中行使。第二,坚持分类赋权赋能。结合乡镇(街道)权力清单和“属地管理”事项清单,将综合行政执法事项中镇街“易发现、接得住、管得好”的46件事403项行政执法事项,赋予规模能力匹配的七个中心镇街集中行使。对其他不宜整合或下放的行政执法事项,根据不同应用场景,建立健全“一件事”协同办理、联合执法机制,形成“综合执法+专业执法+联合执法”多层次立体化行政执法模式。
(二)聚焦队伍重组,推动执法力量集聚下沉
针对各方面执法队伍单兵作战、缺乏合力等问题,坚持抓人促事、人随事走,根据行政执法事项划转情况,在机构、编制、人员总量不增的前提下,同步开展事项划转与机构编制调整,对全县行政执法队伍进行优化重组,减少执法队伍种类,加快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首先,加大县级行政执法队伍整合力度。把原先的14支执法队伍重新整合形成“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管、生态环保、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卫生健康”的“1+4+1”县级执法架构,合理划转相应执法人员。其次,推动执法力量向乡镇倾斜。全县60%的行政执法人员下沉,强化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力量配备,统筹考虑执法资源分布和镇街执法需求,将全县14个乡镇(街道)划分为七个区域,由县综合执法局成立7支派驻执法中队,加强规范化中队建设。
(三)聚焦机制重塑,推动执法体系集成完善
针对当前信息孤立、执法资源集约程度较低等问题,坚持数据赋能、打造功能平台、优化联动体系,统筹协调“综合执法+专业执法+联合执法”执法体系高效运转。首先,打造综合一体运行平台。对标“整体智治、布局科学、高效集成、便民利民”原则,在县社会治理中心打造全省首家共建共享共用的县级行政执法集成应用平台,集统筹指挥、执法办案、综合会商、法制审核、检测受理、便民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进驻司法、市场监管等其他专业执法力量,整合集聚资源,高效协同,开创县域行政执法与基层治理“一站式、一体化、全链条”模式。其次,推动线上一网智治。通过全面接入“基层治理四平台”、12345、智慧城管等系统,与天眼、雪亮工程等监控互联互通,实现乡呼县应、协同联动执法事项线上流转。运行执法监管部门“常驻+轮驻”制度,统一调度、分流交办、联勤联动。
四、小结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措施,县域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担负着实现社会善治的重责大任。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常山案例为县域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第一,推进县域综合执法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县乡统筹。全县域“大综合一体化”和乡镇街道“一支队伍管执法”两个模式同频共振,才能不断发挥乘数效应、释放改革红利。第二,推进县域综合执法体制改革需要多部门多维度协同推进、一体指挥。在县域范围内建立建强指挥平台,在改革过程中压紧压实执法监管,把县乡作为一个“战斗单元”,各条线齐头并进才能真正发挥改革的聚合效应。第三,推进县域综合执法体制改革需要更加依赖最末端基层的治理能力,做到重心下沉、服务前移。增强乡镇范围内各街道“块”的功能、统的功效,充分发挥基层组织“毛细血管”的作用,助推基层治理,才能有效放大改革的综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