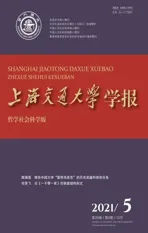康德自我概念中的循环问题
——一种表象主义批判的视角
2021-11-30肖根牛
肖根牛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暨哲学系,长沙 410081)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重要特征就是对主体性的强调,因为整个认识事业的根基放在了主体身上,作为近代哲学基础的理性已经不是近代之前的宇宙理性或天启理性,而是变成了人的理性,所以自我概念对近代哲学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但是由于经验论和唯理论对自我概念的理解都出现了偏颇,所以不是走向了对自我的怀疑就是走向了对自我的独断,这会有损认识论的根基。康德对近代哲学的批判的重要方面是对自我概念的重新理解,他认为近代哲学之所以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知识大厦,原因之一就是对自我概念的理解不够全面。康德依然把自我概念作为先验哲学体系的基础,他在自我概念中看到了自我具有在一切经验之先的纯粹层面,即先验自我意识。先验自我支撑起了人类普遍的认知结构,所以它能够提供普遍的认知形式,基于此之上的认识才能够是普遍必然的。但是,康德发现把自我理解为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的两种维度之后,出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循环论问题,即对自我的认识永远已经预设了事先对自我的认识,这在康德先验哲学立场上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也说明了表象主义的困境。
一、 自我作为智性表象
康德对自我概念的思考受到了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的影响,尤其是休谟和笛卡尔的观点。休谟把彻底的经验论原则贯彻到自我问题之上,认为我们对所有的经验对象都只是一些印象而已,对自我的认识也是如此,他说:“当我转而反思自我时,我永远也不能感知到这个自我没有某一个或某一些的感知,而且除了感知以外,我也永不能感知到任何东西。因此,形成自我的就是这些感知的组合。”(1)休谟.人性论: 下册[M].关文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672.可以说,如果按照经验论的逻辑,休谟彻底的怀疑论是最忠实的经验论者的表现,仅仅依靠被给予的感官材料,自我只能是一连串的感觉。休谟对必然性的怀疑给了康德很大的震撼,康德意识到如果坚持经验论立场的话就不可能有任何必然性知识,包括对自我的认识,所以康德认为必然性依据不能来自经验本身,而必须源于先于经验的人类共同的心灵结构,它是先验的。但是这种先验自我只有在思维活动和表象活动时才首先被意识到,这时还不是对自我的认识,认识必须是知性对直观材料的综合,康德说我意识到我自己只是“我在”,这个表象是一个思维而不是一个直观。(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104.不难看出,康德认为对自我最初始的把握仅仅是意识到自己,即我思,而不是休谟的印象。
从这个角度来说,笛卡尔比休谟更接近揭示自我概念的实质,笛卡尔也看到了关于自我的感觉都是可以怀疑的,但是他并没有止步于休谟的怀疑论阶段,而是通过普遍怀疑找到不可怀疑的东西,笛卡尔认为就是我思,我思乃是整个知识大厦的起点。从某个角度来说笛卡尔的思考方向与康德非常接近,而且笛卡尔无意中揭示了自我的先验维度,当笛卡尔说“我思维多长时间,就存在多长时间;因为假如我停止思维,也许很可能我就同时停止了存在”(3)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26.的时候,他已经揭示出了自我是依赖于思维而存在,思维是规定自我的动作,不过这个自我并不是认识到的,而只是预设的逻辑主词,因为能意识到的只是思维活动,而不是自我。当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的时候,其中的那个“我”应该是逻辑主词的先验自我,而不是经验主体,从笛卡尔用的拉丁文“Cogito, ergo sum”表达式中看得更清楚,作为思维活动的“Cogito”中并没有“ego”,但笛卡尔却说“我在(ergo sum)”,那是因为笛卡尔对“Cogito”预设了一个主体“ego”,这个预设的主体没有任何认识,只能是逻辑主词,所以“我在(ergo sum)”中的“ergo”也必然是逻辑主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康德认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只是一个分析命题了。(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314.所以,“从逻辑上看,‘思考’并不蕴涵‘存在’,至少没有一种像生物和动物之间的蕴涵关系”。(5)陈勇.“我思”与“我在”何者优先?: 对笛卡尔哲学第一原则的再认识[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4(6): 39-54.但是,笛卡尔并没有把“我思”中的“我”当成逻辑主词,而是在主观上把它理解成了精神实体,并且具有各种属性。也就是把本来作为一切思维活动的逻辑主词经验化为精神实体,当面对与精神实体相对的物质实体即身体的时候,笛卡尔面临如何沟通身心关系的问题,独断论或怀疑论是必然的结果。
康德发现近代哲学都没有完整呈现自我概念的全部内涵,所以造成未能为知识奠定稳固的基础。自我包含经验和先验两个层面,我们能够不断地意识到自我的诸种表象,而且这些表象在时间中表现出差异,这就是经验自我的展现。而自我还有另一维度,即先验自我。先验自我表达的是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它能够表现出自发的联结能力,能够把自我在不同时间中的表象综合为同一个自我的表象,这就是人格的同一性。康德也把先验自我的自发性行动称为纯粹统觉,它是一切综合统一性的来源,表象之所以会成为我的表象,就是因为纯粹统觉把不同的表象集中在同一个自我意识中,先验自我的这种行动并不一定被我们直接意识到,我们能意识到的是一个一个联结活动,但是这些单个的联结活动之所以可能也是因为基于纯粹统觉之上的经验性统觉,否则对当下自我的任何认识也是不可能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休谟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他无法建立起自我联结和统一的来源,虽然他已经无意识地在展现纯粹统觉的作用,否则他就不会说出当下的感知是自我的感知。因为先验自我只表现为自发性的联结活动,所以康德借用笛卡尔的概念“我思”来表述先验自我,既然先验自我出现在一切表象活动中,所以它会产生出“我思”表象来伴随一切表象活动,让每一个表象都变成我的表象,因为否则的话就不可能有任何表象被思考。(6)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89.不过,这种伴随行动并不能被认识到,也不一定能被意识到,它是一种逻辑上的分析结果,“伴随者隐在幕后: 进行判断的主体在判断中并没有真的意识到它的‘伴随着的’统一功能,但是它能够使统一功能得到意识”。(7)赫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现代哲学的基石[M]. 郭大为,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 135.
虽然先验自我能够产生出“我思”表象,但是这表象并不能被认识,它不处于感性直观中,所以它是智性表象,说明先验自我也不是认识的对象。它是认识的先验条件,也是表象活动的前提条件。我们之所以能说出“我”,就是因为自我提供的先天条件能够把当下感知到的杂多综合为一个表象,否则感知到的只是一些斑驳不一的杂多材料。而这只是单个人说出的“我”,表示的是他能够建立起在时间中的人格统一性,但是当所有人都能说出“我”的时候,就说明先验自我不是某个人的自我,而是主体都具有的普遍形式,先验自我呈现出的是人类共同的心灵结构。在此,康德的自我概念隐含着一种主体间性,每个人能说出“我”是因为处于主体之间。而且,康德把认知的客观性奠基于自我概念之上,其实奠基于主体间性之上,这种客观性是人类普遍承认的也对人类普遍有效的客观性,脱离人类的客观性是什么,这无从得知。
二、 自我的循环问题
康德用“我思”来表达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时,并没有用笛卡尔的“Cogito”一词,而是用德文“Ich denke”来表述,表示他认为“我(Ich)”与“思(denke)”同等重要,而且说明这里的“我(Ich)”只是“思(denke)”的逻辑主体,不是“思”的产物,我们对它没有任何的直观材料,也就不能有任何的认识,所以康德说:“我,关于这个表象我们甚至不能说它是一个概念,它只不过是一个伴随一切概念的意识。”(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291.“我”之所以能够伴随一切概念,是因为“我”与“思”是连在一起的,“思”的表象所具有的意识统一性把概念的综合活动集中在一个对象中, “思”是对“我”的规定动作,而不是“我”的谓词,因为它不是表象的对象,而是表象的活动,是“我”的自发性机能,是知性范畴的综合能力的来源,所以“在思维中自我意识的一切样态自身还不是有关客体的知性概念,而只是一些根本不把任何对象、因而也不把自我作为对象提供给思维来认识的机能”。(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293.不难发现,这里的“我”和“思”都是先验的,都不是认识的对象,所以它们作为表象也只是智性的表象,如果一定要追问表象的对象,康德把“我”所表象的对象称为先验主体=X,正是这个X才保证了我们作为一个在时空中同一的主体。
既然先验自我是能思的自我,那么被思的自我就是经验自我了,能思的自我就是进行规定动作的主体,而被思的自我是被认识的客体,它是先验自我把通过内直观获得的自我意识规定为同一个主体的结果,所以我们能够描述自我的任何状态都是因为先验自我的先天规定作用,否则就会出现休谟的问题,自我变成一系列意识状态。所以,决定自我人格同一性的基础不在于经验自我,而是先验自我,即自我意识的先天统一,它保证了自我在号数上的同一性,由此,大家追问的“何为自我”的对象是先验自我,这实际上也是休谟追问的问题,只是他没有明确意识到自我的先验层面。康德发现,追问先验自我将面临一个循环问题,“我们围绕它(先验主体=X)在一个不断的循环中打转,因为我们如要对它做出任何一个判断,总是不得不已经使用了它的表象”。(1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291.也就是说,我们对先验主体的追问、表象或者思维,都已经事先使用了先验主体的自发性表象“我思”,因为“我思”伴随一切表象活动,否则连追问行动本身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循环问题就出现了,对先验主体的追问已经事先预设了对自我的认知或熟悉。在此,这个循环问题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对先验主体的追问已经事先利用了先验主体的作用;其次,追问先验主体已经预设了在追问之前已经对它有所认识,否则如何确定追问的结果就是追问的对象,这样追问就变成了兜圈子。
对于康德的自我概念中的这一循环论问题,当代哲学家的解读路径主要分三种立场: 迪特·亨利希为代表的意识哲学,图根哈特为代表的语义学和扎哈维为代表的现象学。亨利希在他的《费希特的原初洞见》一文中首次提出近代哲学对自身意识的描述都采用反思模式,但是反思模式会带来循环论的问题,因为自身意识意味着主体的自我返回自身。如果不是预设了事先存在的自我对自身的意识,那又如何能够在反思中将自身确立为自我,所以反思预设了自身意识。在亨利希看来,自我意识的循环问题首先源于主客的模式,因为面临作为主体的自我与作为客体的自我的同一化问题,他说:“为了实现与自我的同一,主体必须已经知道在何种条件下能将所遇之物或熟知之物归于自身。它决不能首先通过自我指涉的方式来达到这一认识。”(11)Henrich D.Selbstbewußtsein: Kritische Einleitung in eine Theorie[C]//Rüdiger B,Cramer K,Wiehl R.Hermenutik und Dialektik: Band I. Tübingen: JBC Mohr, 1970: 266.对于如何避免这一问题,亨利希坚持自我意识的立场,认为应该在自我内部进行调整,把自我意识理解为一种非关系的关系,由此来避免主客关系的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以一种反面的方式来描述自我意识,只是把自我意识作为前提换成了无自我的自我意识作为前提,循环论的困难并没有消除,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图根哈特认为自我意识的理论可归为三类: 实体属性的模式;主客关系的模式和反思的认知模式。实体属性的自我意识模式和传统存在论连在一起,心灵实体通过属性来认知自身,而近代哲学由心灵实体走向了自我意识,所以实体属性的模式不被接受了,而是采取主客关系的模式和反思的认知模式。图根哈特认为主客关系的模式和反思的认知模式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循环问题,在主客关系模式中只有预设事先对主体的熟知才能确认主客体之间的同一,这一点已为亨利希所揭示。图根哈特认为反思模式只是主客关系模式的演化结果,反思的模式意味着往里面看,但实际上什么也看不到,这实际上是传统“视觉隐喻”的结果,他说“我们倾向于隐喻性地根据看的模式来阐释对某物的意识的路径,从巴门尼德到胡塞尔的整个欧洲哲学传统都是这一倾向的牺牲品”。(12)Tugendhat E. Selbstbewußtsein und Selbstbestimmung: Sprachanalytische Interpretationen[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9: 16.图根哈特认为必须跳出传统的立场来克服自我意识的循环问题,这一新路径就是语义学的方法。图根哈特认为“我”是索引词或指示词,大写的我(Ich)需要还原为日常中的小写的我(ich),作为索引词的“我”处于“我—你—他”的体系中,当谁说出“我”时,同时另一个人可以用“你”来指称同一个人,如果不存在这一关联体系的话“我”不会标示任何一个人,所以谁在使用“我”时他就知道别人可以用“他”来指称“我”所代表的同一个人,“我”是在这样一种关联体系中确认自身的。(13)Tugendhat E. Selbstbewußtsein und Selbstbestimmung: Sprachanalytische Interpretationen[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9: 74.不过图根哈特对自我概念的语义学分析同样面临循环论,因为说“我”时必须知道他人说“他”是和“我”指称的同一个人,而不是指称别人或别物,而且双方自己要事先知道“我”和“他”的可转换性,同时要知道对方也知道这一点,同时也要对方知道我知道这一点,由此无限循环。
扎哈维认为对自我的反思必然会造成把自我变成认知对象的理论态度,它中断了自我的体验之流,体验变成了孤立的对象。反思过程中包含着某种变更,或者说反思导致了自我的分裂,前反思之我和反思之我之间存在异质性,两者之间是不同一的。反思过程本身就处于体验之流中,所以任何对自我的反思都已经产生了新的东西,所以对自我的反思并不能够把握到起作用的主体性,我所是者并不能够成为我的对象,而只有体验之流本身才展现自我,这就说明了对自我的认识和对自我的体验之间是存在距离的。(14)Zahavi D. Subjectivity and Selfhood: Investigating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5: 92.所以,在扎哈维看来,对自我的反思并不能达到对自我的认识,反而造成了对自我的变更,把主体性的体验自我转变为专题性的对象自我,但是扎哈维又认为这种变更是主体性内在性的要求,因为主体需要一种异己的方式来关涉到自我。不难看出,扎哈维的现象学立场同样面临循环论的困难,反思把主体性的体验之流转变为专题性的认知对象,如果没有对主体性体验之流的事先熟知或者理解,又如何知道这一变更的实现。
以上分析了当代哲学批判自我循环问题的三种路径,笔者发现虽然它们都能敏锐地从某一角度发现问题的症结,但是面对如何避免或者消除这一循环问题时,它们都同样地陷入了困境。他们都能发现反思或者认知的方式必然会带来循环的问题,但是都没有跳脱出认知的作为揭示自我的主要方式的立场,也就没有脱离主体性的思维,或者没有跳脱出主体与世界二分的结构,而这种表象结构正是康德先验哲学的基础,唯有彻底批判这一表象结构才能发现自我循环问题的最终根源。
三、 表象主义的困境
康德之所以无法解决自我概念中的循环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囿于其表象主义的哲学立场。至于什么是表象主义,“所有形式的表象主义都主张世界是独立于概念、判读、语言和精神而存在的,同时又可以完全地被词语、判断、指称、语句、观念、图式和概念所想象、表象和建构”。(15)Egginton W, Sandbothe M. The Pragmatic Turn in Philosophy: Contemporary Engagements Between Analytic and Continental Thought[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50.简单来说,表象主义就是认为主体和世界互相独立,主体凭借对世界的表象来获得对世界的认识和规定,由此可以看出,表象主义预设世界是实在的。另外,既然主体与世界是互相独立的,关于世界的规定性和确定性就不能从世界中获得,主体只能由内在世界的确定性来保证外在世界的确定性,获得关于自我的认识成为获得关于世界的认识的前提,确定性建立在自我的自明性之上。从笛卡尔、休谟到康德无不坚持表象主义的立场,但是康德的表象主义又不同于前两者的表象主义,无论笛卡尔的观念还是休谟的印象,其实质还是图画论的表象主义。康德认为这种图画式的表象是不存在的,既然对象本身是无法得知的,表象就不是对象本身的呈现,表象的对象也不是对象本身,表象及其对象都是主体建构起来的,所以康德采取的是建构论的表象主义路径。
无论采取何种表象主义的立场,都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这是由表象主义本身决定的。首先,表象主义是建立在实在论的立场之上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世界预设,无论坚持实在论还是非实在论的态度,世界已经先于并且独立于主体而存在,主体通过表象来通向世界,而且这会引申出所予论的立场。虽然康德的建构主义能够发挥主体积极性,但是表象对象的材料却不是自己产生的,而必须由世界本身给予。其次,表象主义面临符合论的难题,既然世界是独立于主体而存在,那如何保证对世界的表象与世界本身是符合的,康德建构式的表象主义依然面临这个问题,他无法证明建构起来的对象与对象本身的符合问题,所以康德所建立的是一种主观意义上的实在论。但是他又坚持客观实在论的立场,两者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最后,表象主义实质是一种静观主义的立场,表象主义力图获得世界的确定性,并通过主体内在世界的自明性来保证这种确定性,但是这都有赖于把世界和主体都当作是静态的,唯有世界和主体都是静止不变的才能揭示他们的结构和内容,这无异于把行动和变化排除在外。即使是康德建构式的表象主义也是这种静观主义的展现,他把被给予的世界当作是既定的,主体的认知结构是先天的,所以通过揭示主体的先天认知条件来建构起世界呈现出来的现象,但是认识与行动的矛盾立马就会显示出来。
当康德把这种建构主义的表象主义立场运用在自我概念问题之上时,已经预示了自我的循环问题。康德认为“我思”中的“我”是先验主体,它是先于一切表象活动的,也是一切表象活动的主体,不过这个主体不是经验意义上的主体,而是逻辑主词,是没有任何内容和概念的先验主体,且它的存在是既定事实,只要我们自我意识到自我时就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康德直接称它为“我在”。“我”是独立的本源的存在,所以,“我”对于表象活动来说是被给予的,这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先验自我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自发性,自发性的行动让所有的表象集中在一个自我意识之中,所以自我的被给予性和自发性存在冲突。其次,作为先验主体的“我”通过产生“我思”表象来伴随一切表象活动,当把“我”作为反思对象的时候,已经被“我思”表象所伴随,否则反思活动就不可能进行。而且,既然“我”乃是空洞的智性表象,关于它的认识就不能直接获得,而只能通过回溯的表象方式进行反思,当把“我”当作客体进行认识时,如何证明获得的关于“我”的表象与作为先验主体的“我”相符合,要么事先已经获得了关于“我”的认识,要么需要寻找两者之间的标准,但这又需要标准的标准,无疑引申出无限倒退的问题。最后,把先验主体“我”作为认识的对象,预设了它是不变的,否则认识无从进行。但实际上“我”的自发性决定了自由是自我的本质,自我无时无刻都处于变化之中,不可能出现静止不动的“我”。所以,康德的表象主义立场已经决定了以这种方式来追问自我概念会引发出很多问题,循环论问题只是其中之一。
表象主义的立场并不是彻底的哲学方法,它建立在诸多前提的预设之上,而没有对哲学前提进行追问或悬置,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对世界和自我的预设,把世界和自我的客观存在当成既定事实,但是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自我意识。当表象主义把世界和自我的确定性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时,它既无法证明世界存在也无法对自我进行指称,这面临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指责。康德的表象主义立场比前康德哲学的表象主义立场更为彻底,因为他把自我和世界的确定性建立在先验的认知结构之上,同时把表象的对象限制在现象领域,以此避免怀疑论的侵袭。所以康德的表象主义的核心在于论证主体自身的先天认知结构,只要能先天地证明主体的认知条件是先验的,那就能保证自我和世界的确定性。但是这又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即把表象的条件建立在先验领域如何能确保它必然地运用于经验领域,康德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阐释清楚。黑格尔批评康德试图在认知活动之前来考察认知条件的合法性,犹如要求在学会游泳之前切勿下水,黑格尔的批评击中了康德表象主义路径的要害。
四、 反表象主义的解决路径
康德已经意识到了把表象主义立场贯彻到自我问题上时会产生循环论的问题,但是康德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一问题,所以表象主义路线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作为康德的追随者,莱因霍尔德把康德的表象主义立场发挥到极致,他认为表象才是最基本的事实,表象既把主体与客体相关联,又把它们相区别开来,按此立场,表象结构应该是最原始的。但是莱因霍尔德又把表象归因于主体自身,是主体才使表象成为可能,主体成为原初的,由此矛盾不可避免。而且,莱因霍尔德无法解释表象是如何与主体相联系的,又是如何与客体相联系的,可以说他的表象理论困难重重。
费希特看到了表象主义的立场是无法达到对自我的指涉,他说:“为了每一个意识,我们将无限地需要一个新的意识,而这个意识的对象就是前一意识,因此,我们永远不会到达能够承认一个现实的意识的地步。简而言之,用这种方式无疑不能解释意识。”(16)梁志学.费希特著作选集: 第二卷[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758.在费希特看来,坚持表象主义的立场就会必然把思维或意识看作是表象结构的一个条件,同时又会把思维或意识当作表象的对象。但是思维或意识总是预设一个主体,如笛卡尔和康德那样,而这个被预设的主体不能通过直接认识来把握,而只能通过反思的表象方式,反思又会预设对主体的认识,所以“任何使用反思作为心灵的基本结构的自我意识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以循环论证告终。因为反思预设自我认识是现存的,我们必须假定自我的原初的自我意识先于所有的反思活动”。(17)迪特·亨利希.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 德国观念论讲座[M].乐小军,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387.
费希特认为康德对先验自我的理解不够彻底,康德把先验主体当成逻辑主词,但它的存在即“我在”又是理性事实,导致自我在康德那里成为无法达到的彼岸。在费希特看来,最原初意义上的绝对自我首先是事实行动,而且是绝对本原的事实行动,它不以任何条件为前提,它是自为的和自由的,是一切思维和存在的前提,所以整个哲学探究的前提即自我,不是康德的理性事实而是本原性的行动,在此基础上才形成其他领域和活动,这便是费希特知识学的第一原则,“这个第一原则就是‘本原行动’。事实和行动是同一的”。(18)张荣.康德对传统抽象论的批判及其意义[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2(4): 54-65.所以,绝对自我的本原行动“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意识的诸经验规定之一,而毋宁是一切意识的基础,是一切意识所赖以成为可能的那种东西”。(19)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M].王玖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6.作为绝对的本原行动,自我对自己的意识同时就是对自己的设定,自我的行动同时形成自我的认识,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不需要通过回溯性的反思来寻求这种认识。绝对自我设定自我就是把不属于自我的东西排斥在外,同时也就是设定了非我,绝对自我把自我设定为受非我规定。可以看出,费希特把主体和客体都看作是绝对自我的本原行动设定的,设定意味着去构造某物,某物随着这种设定动作而产生,所以设定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性,自我设定自我就是同时产生出自我;二是规定性,自我对自我进行设定就意味着对自我有所规定,也就是对自我有所认识。所以,自我意识必须拥有一种自我认识,否则谈论自我意识都是不可能的,只要自我一旦被设定,它既是对自我的意识,也是对自我的认识,因为自我既是主体也是客体。
自我原初就是自我指称的,而无须通过回溯的方式来对自我进行指称。既然绝对自我是本原的行动,对自我的设定就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所以自我本身是活动的,对自我的指称也是一种心智生命的发展,从中衍生出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20)迪特·亨利希.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 德国观念论讲座[M].乐小军,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400.由此看出,康德囿于表象主义的立场把自我看作独立固定的本源性存在,使自我桎梏在表象主义的结构中,这无疑是对自我的片面性认识。而且,康德为了认识到主体的先天认知结构而把它与活动对立起来,从而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这不但不可能形成对自我的指称,反而造成自我的内在分裂。而费希特基于行动主义的立场,把概念结构和活动要素都当作自我指称不可缺少的要素,这说明理论和实践在源出意义上是同一的,不存在两者之间的对立。而且,理论与实践的区分都是为了自我心智生命的发展,以朝向自我完善的目标前进。可以看出,费希特的行动主义路线实际上是把对自我的指称置于历史的维度中,在动态的过程中来形成对自我的指称。
费希特在自我指涉问题上的行动主义路径,可以说是真正地开始了反表象主义,作为反表象主义的先河,他直接影响了观念论者谢林和黑格尔,也间接影响了存在主义的相关论述。受费希特的设定理论影响,谢林直接把自我看成行动的产物,认为自我的概念是通过自我意识的行为而产生的。黑格尔接受费希特对绝对自我活动过程的揭示,把绝对自我替换成精神,精神对自我的认识只有精神完成了整个发展历程才能达到,这种历史主义的路线直接颠覆了强调静止固化的表象主义模式,这对黑格尔之后的反表象主义者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包括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
五、 结 语
康德揭示自我概念的循环问题,表明了表象主义的哲学路径只会让自我产生更多的问题,尤其理论与实践的分裂。而且,表象主义的方法抑制了主体的积极性,没有把自我看作原初性的行动,正是基于这种行动而产生其他一切知识。费希特和黑格尔都是反表象主义的践行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康德到费希特的关键转变。表象主义立场实质上把世界固化了,也就把运动和变化排除在外,它首先追求的是对世界本身的揭示,此种对认识的强调最后不仅导致片面性的认识,也使认识与实践脱离,此种立场使主体既无法获得真正的自我认识,也无法实现自由。所以,各种反表象主义路径的出现既是对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也是对恢复实践优先性的努力,只有把认识基于实践基础之上,自我才能达到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