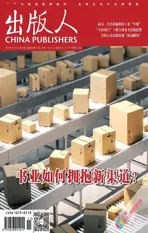我们要如何迎接未来的出版?
2021-11-25缪宏才
文|缪宏才
这两年,出现了几本有分量的“出版图书”(出版人写的关于出版的书)。比如聂震宁的《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陈昕的《理想在潮头》,近日,又有佘江涛的《走向未来的出版》。
佘著篇幅不大,但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出版实务、出版管理的方方面面,行文实在无冗言,直指核心;观点往往前瞻领先;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能抓住要害。
该书最后一组文章冠名为“走向未来的出版”,又用作书名,我理解应该是作者本书最核心的部分。
我近期也偶尔思考这个问题。我一直有个看法:事情是由具体的人做的,而又是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做的。我以为,中国出版的当下、未来走向,主要取决于“政策”和“科技”两个维度。
近两年,中国出版的大环境即所谓背景,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比如出版社划归宣传部管理,比如“双减”政策等等,都意味着出版面临一个革命性的转折关头,出版社如何应对?
我觉得佘江涛比较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引入“未来出版”的概念来讨论这样的问题。
未来,相对于现实,是始终存在的,但只有在转折时期,讨论未来,才是有历史价值的。从汉到清中期近二千年,历史是重复的,不值得讨论未来,只有晚清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必须研究未来,并且参与未来、设计未来。
当下,正值“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出版人同样必须主动拥抱未来。这未来是三五年、一二十年还是更长远?则要看各人、各社了。
根据佘著,出版业的未来是数字出版,当下出版界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可这一点。以科技维度来观察出版业的走向,似乎全世界都是这个未来。
我有一个看法:出版业的未来,不取决于出版业自身。
自上世纪90 年代“e-book”概念兴起以来,出版业这二三十年的纸电博弈,多次数字(电子)出版的小高潮,都有相关数字技术阶段性突破的背景。
即说,如果我们认为出版的未来呈现形态是数字化的话,那么,何时未来变成现实,主要不取决于现在出版界的一批人,而主要取决于现在数字(网络、电子)科技界。可以预计,纸-电博弈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总的趋势会是电进纸退。也许真有一天,纸书会进博物馆成为收藏品。这段时间会有多长呢?除了上述技术上的背景条件,还有社会的一面,其钥匙、其决定权,同样不在出版人手中。
业内人士都知道,中国出版的经济基础、业务主体是教育出版。教育出版的核心是教材。而且,双减政策以后,对教辅的规范、质量监控也可能成为现实。那么,教材的数字化,出版社能说了算吗?而且,即使是教辅,如果数字化,仅限于ToC,那么巨大的成本,很难靠纯市场消化,其行也不远。必须进入ToB模式,但要进入ToB 模式,进不进得了学校?进不进得了市县区教育领域,出版社有发言权吗?
当然,这样说,绝不是说,在走向未来出版上,出版社就可以无所事事、随波逐流,恰恰相反,应该有所作为。这就是佘江涛这本书的价值。他提出“未来出版社的实验室”的概念特别有价值。他假设:“在内生驱动力不强的环境下,融合出版实验室可以通过具体项目,对内容生产和经营方式的创新进行探索与推进,这是一个流程可控、结果可精确评估、可不断优化-复制的实验”。这应该已不是假设,“凤凰融合实验室”应该已是付诸实施了。
总之,佘江涛告诉现在的出版人两种可能性、两种选择:要么主动拥抱未来出版,不断尝试不断创新,适应不断壮大的数字出版;要么被动观望,终于出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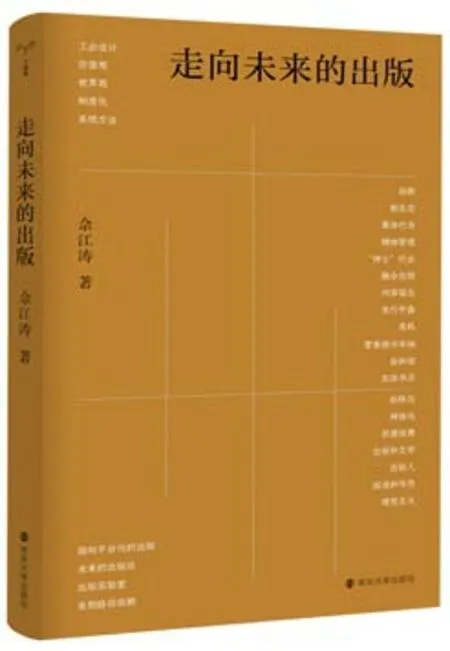
佘江涛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2021年8月
定价:50.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