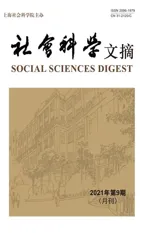部门法宪法具体化的正当性及类型
——与陈景辉教授商榷
2021-11-14李海平
文/李海平
2021年3月,陈景辉教授发表《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一文(以下简称“陈文”),对张翔教授在2019年提出的宪法和部门法“三重关系说”提出批评。其从部门法理论的初步反省,再到法理学层面的釜底抽薪,最终彻底否定了宪法具体化理论。然而,陈文在概念界定、理论预设、论证逻辑等方面疑义甚多,亟待澄明。
概念界定的偏颇与“初步反省”的悖谬
(一)三对关系范畴界定的偏颇
1.宪法和部门法
陈文将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对立起来。这似乎是对张翔提出的在宪法和形式法律的关系意义上理解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回应。可是,这种回应并不成功。首先,“宪法是法律”与“宪法和法律”的表述并不矛盾。其次,宪法和法律的区分具有规范依据。只有明确区分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关系意义上探讨宪法和部门法关系,才能正确理解这一关系的本质。最后,在宪法和法律关系意义上表述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有利于对宪法和部门法关系认知的全面完整。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就是指宪法文本或者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和“宪法相关法”根本上不属于宪法,需要被归入宪法以外的其他部门法,或者将其设置为独立的组织法部门。陈文在排除“宪法和法律”表述结构的基础上界定宪法和部门法,从开始就出现了偏差。
2.最高法和法律总则
宪法作为法律总则,是陈文宪法具体化否定论的基础预设。然而,宪法学者并未提出过这样的理论。同时,陈文的预设即使成立,也不必然得出宪法是法律总则的结论。第一,宪法和部门法既非同一部法律,更非同一个法律部门,用法律总则和分则来对应宪法和部门法根本上是错误的。第二,无论是宪法具体化,还是合宪性解释和合宪性审查,从宪法作为最高法的命题推导便可自足,又何须作出“宪法作为法律总则”的预设而徒增论证负担?这一预设既牵强附会,又显得有些强加于人。
3.具体化和实施细则
陈文对其批评的事项——宪法具体化——给出了明确界定,即部门法“发挥实施细则的功能”。这种界定与“宪法作为法律总则”的预设存在同样的问题。宪法学界有学者提出过部门法作为宪法实施法,但还未有人提出过部门法是宪法的实施细则之论。实施法可以以实施细则的形式呈现,也可以以划定框架边界、赋予形成自由的方式实现。张翔提及的宪法框架秩序说更被宪法学界所普遍接受,代表着宪法学界的普遍共识。陈文一厢情愿地将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与部门法作为宪法实施细则等同,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学术批评树立了一个“稻草人”。
(二)三重关系视角的可证立
陈文把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划分为内容和效力两个层面不能说有问题。然而,这两个层面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而非毫不相干式的相互独立。一旦把二者截然二分,内容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效力也沦为空中楼阁、虚幻泡影。由于法律的规范性和实践性,从公权力机关及其实施宪法的类型来认识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方能揭示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本质。立法、法律适用和法律合宪争议处理,是体现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三个基础环节。宪法具体化、合宪性解释和合宪性审查恰恰与立法、法律适用和法律合宪争议处理三个层面形成对应关系。合宪性解释不能被其他两种中的任何一种形式所吸收或者代替。陈文否定合宪性解释作为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独立形态有些行不通。
(三)并非冗余的部门法
陈文的推理实质上基于一种错误的逻辑。一是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混同。陈文得出宪法具体化会导致部门法冗余的结论,其原因之一是,承认宪法具体化必然承认“存在着直接将宪法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可能”。可是,宪法和实践直接结合只是一种可能性,并非必然性。通过部门法实施宪法是宪法和实践对接的重要步骤,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宪法规范均需要具体化,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宪法规范未经具体化便不能实施和适用。二是实然和应然的不分。在陈文看来,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会为部门法抗拒合宪性审查提供理由。然而,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只是表达了一种应然的立场,与部门法是否在事实上实现了宪法具体化,完全是两回事。以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为理由抗拒合宪性审查,逻辑上不成立,实践中不可能。
实在法命题与部门法的宪法具体化
(一)背离常识的结论
“无论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是否成立,它都与实在法命题无关”,这是陈文关于实在法命题的分析结论。然而,部门法是否是宪法的具体化,本身是一个实在法命题。而实在法命题首先需要在实在法层面解决,而且,实在法能够为实在法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应该是一个常识。对于实在法问题的讨论,由实在法转向法理学或者政治哲学,根本上不是因为实在法问题与实在法命题无关,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实在法解决方案,或者给出更充分的理由。实在法问题不仅不可能与实在法命题无关,且在实在法层面都会有相对明确的结论。
(二)对拉兹宪法概念的不当化约
第一,陈文将拉兹宪法概念的第1项特征——“宪法定义了政府不同分支的主要机关之组成与权力”——排除出实在法命题,超出对宪法概念的一般共识。第1项特征描述了宪法作为组织法的含义。而宪法作为组织法是宪法最为原初和持久的特征。如果将拉兹宪法概念第1项特征中的组织规范纳入实在法命题,恰恰能够部分支持宪法具体化。组织法部门或者部门法中的组织规范,是宪法的具体化,应该不会有太大疑义。
第二,将拉兹宪法概念中的法律不得适用归入法律无效、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同于合宪性审查,属于概念误读。陈文认为:“仅就实在法命题而言,合宪性审查应无疑问,因为它完美匹配实在法命题的第一组。”第一组的确包含了合宪性审查,但其内涵并不限于此。在实体内容中,“无效”和“不得适用”具有并列关系的因素。“无效”主要侧重于对其效力形态的评判,一般体现在合宪性审查之中;而“不得适用”则侧重于描述其纠纷解决功能,一般体现在普通司法程序之中。宪法的司法适用,至少包含合宪性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适用和法律适用层面的宪法司法适用。陈文所说的宪法的实在法命题不支持宪法具体化的结论,是在排除了宪法的第二种司法化基础上作出的,遗漏了拉兹宪法概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三)双子命题与双重内容的不当搭配
陈文认为,实在法命题包含的两个子命题与宪法的双重内容可以形成完美的匹配关系。问题在于:宪法包括的内容仅限于国家权力和基本权利这双重内容吗?伴随社会的剧烈变迁,现代宪法已经形成了基本权利、国家机构、国家目标的三元规范组成结构。两个子命题与宪法双重内容的匹配并不完美。陈文将宪法是最高法和最稳固的法两个子命题,分别和宪法中的国家权力规范和基本权利规范对应,颇值疑问。宪法作为最高法绝非仅因为宪法规定了国家权力,也因为宪法规定了基本权利。宪法作为最稳固的法,也不仅仅因为宪法规定了基本权利,更因为宪法规定了国家权力。以形式方面的宪法特征论证宪法内容方面的命题,似乎有些南辕北辙。
(四)实在法命题对宪法具体化的支持
通过对拉兹宪法概念的修正,我们大致得出宪法是最高法和公法的实在法命题。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讨论,需要在此前提下展开。首先,需要在最高法和公法一体两面的关系视角下认识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如果把这两个面向割裂开来,仅从最高法的属性出发,可以推出所有的部门法均是宪法具体化;如果仅从公法属性出发,其与其他公法部门均处同一位序,自然不存在宪法具体化的问题。这两种分析都是错误的。其次,公法部门是宪法的具体化可成立。宪法是公法且是最高法,这决定了其他公法将宪法的规定加以具体化是其重要使命。其中,组织法部门和行政法部门是最典型的公法部门,其对宪法的具体化体现得尤为显著。最后,私法部门只是部分的宪法具体化。宪法确立的不仅是框架秩序,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公共框架秩序;凡是涉及公共性的立法,立法机关便具有在宪法确立的公共秩序框架内具体化宪法的义务。对于涉及国家公权力、社会公权力和公共利益的私主体关系,单纯由私法调整难免会因形式上的平等、自由遮蔽私主体之间实力上的巨大悬殊,导致实质不平等、不自由的后果,此时便需要包括宪法在内的公法介入。对于私法而言,只有涉及公权力或者公共利益、具有公共性的规范,才是宪法的具体化。
概念命题与部门法的宪法具体化
(一)概念命题和实在法命题的适度分离
毫无疑问,法理学分析是认识实在法问题的重要维度。但是,对于实在法问题法理学分析的效用限度需要具有充分认知。对于实在法问题,法理学分析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补强论证和理论批判方面。补强论证一般发生在法理学分析结论和教义学分析结论高度一致的情形。理论批判,分为直接理论批判和间接理论批判,一般发生于法理学分析和教义学分析不一致的情形。理论批判功能并不能取代法教义学的分析结论,也并不当然实现对法教义学结论的否定。这两个结论完全可以相互并存,除非法理学的分析转化为教义学的一部分,或者其结论最终通过法教义学的自我反思而实现了更新。或许陈文对凯尔森的理论批判可以成立,也或许哈特的理论真如陈文所说不支持宪法具体化,但这并不影响从实在法层面得出的宪法具体化的结论。
(二)概念命题推理中的两个缺陷
缺陷一:对宪法是何种二阶规则的模糊不清。
在概念命题讨论中,陈文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宪法是授权规范,部门法是被授权规范。然而,陈文推理的整体逻辑存在严重问题。在哈特的理论中,二阶规则包括承认规则、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如果所有的二阶规则都是宪法,以二阶规则和一阶规则的关系来分析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尚可;如果宪法只是二阶规则中的一种,那么,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分析还必须包括二阶规则的内部关系。陈文在进行宪法作为授权规范的推理中,回避了宪法作为二阶规则的种类问题,这便使其推理过程出现了明显的漏洞。
缺陷二:把部门法限于一阶规则的可能错误。
陈文仅在一阶规则的意义上界定部门法,不仅与后续提出的宪法是承认规则自相矛盾,并且以此为基础推导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也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具有片面性。
(三)哈特理论对宪法具体化的支持
陈文得出哈特理论不支持宪法具体化的结论,是由推理过程中的上述两个缺陷造成的。如果弥补这两个缺陷,则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宪法是承认规则,而部门法则由变更规则、裁判规则组成。宪法是授权规范,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也包含授权规范,且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这从哈特关于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的论述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承认规则和变更规则的关系如此,承认规则和裁判规则的关系也是这样。哈特并非意在否定裁判规则作为一种规则类型的独立性,而是强调裁判规则本身亦具有承认规则的属性。作为授权规范,承认规则是终极的,裁判规则则是初步的和不完全的,二者的关系只能用裁判规则是承认规则的具体化来加以解释。
价值命题与部门法的宪法具体化
(一)价值命题与宪法具体化的非直接相关性
陈文所说的价值命题从根本上属于政治哲学领域。政治哲学的分析可以抽象地证明宪法是什么。但是,关于宪法的政治哲学分析与宪法实际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由宪法统领法秩序根本上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陈文关于价值命题这部分论述的标题——“作为法律环境的宪法”——已对此给予清晰地展示。陈文将“宪法是对法律环境的恰当反应”化约为“作为法律环境的宪法”,难免有偷换命题之嫌疑。宪法作为法律环境或者宪法是法律环境恰当反应的命题,与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问题没有直接关系。
(二)两种价值共识与宪法和部门法的非对应关系
尽管价值命题与宪法和部门法关系距离遥远,但陈文仍努力将价值命题与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进行直接联系。陈文将价值共识再次按照一阶和二阶的逻辑加以分类。宪法代表二阶价值共识,部门法代表一阶价值共识。宪法代表二阶价值共识尚可理解,部门法代表一阶价值共识就有些不可思议。
首先,在拉兹的宪法概念中,其第7项特征仅强调公共价值共识,并没有一阶和二阶之分。在拉兹那里,只要是共同的价值信仰或者意识形态均可以由宪法来表达,与其是关于具体事情的价值共识还是处理价值分歧的价值共识没有必然联系。陈文将一阶价值共识和二阶价值共识冠以拉兹的名义并不合适,至少需要展开更加充分的论证。
其次,以一阶价值共识和二阶价值共识来对应宪法和部门法本身不能成立。以一阶价值共识和二阶价值共识对应宪法和部门法,实际上是对一阶价值共识和二阶价值共识的根本性和重要性作出区分。二阶价值共识似乎更加重要和根本,因而其和宪法相对应。事实上,一阶价值共识并不一定弱于二阶价值共识,只不过没有产生分歧而已。根据陈文的分析,解决价值分歧的价值共识主要是指民主。民主价值固然重要,但在所谓的一阶价值共识中,还可能包含自由、平等、尊严等价值,其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民主,甚至其价值位阶高于民主,当然也需要由宪法来表达。陈文的区分曲解了拉兹宪法概念第7项特征的原义。
(三)被刻意放大的多数决
在陈文确定的价值共识中,自由、平等、尊严等实体性价值都一概找不到踪迹,剩下的只有程序意义上的多数决。陈文或许是通过“法律环境”中的民主价值,彰显程序主义的宪法观的重要意义,然而,这种程序主义宪法观有些走向极端的嫌疑,即使如哈贝马斯这样的程序主义宪法观的代表人物也难以望其项背。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宪法观并未无视自由、尊严等基本价值,而是将其从自由主义式的先验结构转换为共和主义式的作为共同体的维持条件。
结论:类型化的部门法宪法具体化
宪法兼具最高法和公法是理解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基本前提。对于公法规范和具有公共性的私法规范,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可以成立;对于不具有公共性的私法规范,则不存在宪法具体化的问题。宪法具体化是宪法框架秩序意义上的宪法具体化,立法机关享有具体化宪法的形成自由权。而立法形成自由权则决定了,各个部门法在一体化的法秩序之下具有相对独立性,遵循自身独特的运作逻辑。除了张翔提及的框架秩序意义上的宪法具体化含义外,类型化也是理解宪法具体化的关键词。我们可以称为框架秩序与类型化的宪法具体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