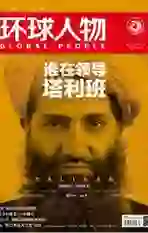“科技是理解世界的绝佳角度”
2021-09-08陈霖
陈霖

吴军
吴军的每一本书几乎都能掀起人们对该领域的大讨论,一些观点与视角甚至成为该领域的参考。2007年,正在谷歌工作的吴军开始在谷歌黑板报(博客日志)上连载文章,分析互联网和通信界各大企业,之后整理成《浪潮之巅》《数学之美》。前者畅销数年,4次再版,豆瓣9分,后者获“文津图书奖”,广受热议。至今,他已出版10多本畅销书。
眼下,各地正迎来疫情下新的开学季。8月,吴军出版《给孩子的科技史》,读者是适龄儿童和学生。这是他首次出版童书,许多人好奇这是本什么样的科技书?这就要提到该书蓝本《全球科技通史》。
科技是一种可重复、可叠加的力量
上世紀90年代,吴军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计算机博士。当时,他天天推公式,成功改进一个算法,把计算速度提高了万倍,这后来成为机器学习领域的一个通行算法。在吴军心里,与艺术等领域不同,科技有一套方法,只要遵循方法就能在前人基础上实现进步。“科技的进步是可重复、可叠加的。”自那时起,吴军萌生想法:结合不同领域,呈现科技的重要性。这才有了2019年出版的《全球科技通史》。
这是吴军首次从科技视角串联历史,以“能量”和“信息”两条主线阐述人类文明的演进。可以这样理解:前者涉及能量和资源的处理,事物的运作几乎都需要能量,比如人的平均基础代谢率相当于一只白炽灯泡的能量;后者涉及信息的产生、解码、传输等。
吴军认为:“所有物质本质上都是能量。而能量如何组织、变化,留下什么痕迹,则是信息。”他如此概括科技的演进过程:一是能量利用效率越来越高,二是信息代替能量。例如,街上摄像头具有信息处理能力,能很快识别罪犯;如果不用摄像头,找数万人遍布角落也能办到,但要耗费巨大能量。“不同文明的竞争比的是哪个更擅长使用能量和信息;此外,文明越发达,信息的重要性会比能量更显著。”
这本书荣获“吴大猷科普著作奖”,入围“中国好书”,入选“文津图书奖”,一度引起人们对“能量”“信息”的解读与讨论。有几次,家长问吴军:“我也想让孩子读读这本书,可他读小学,能看得懂吗?”被问得多了,吴军决定,挑选书中重要事件与人物进行加工,出版一本专门给学生、小孩的科普书。
吴军告诉记者,《给孩子的科技史》最大特点是科普插画。一开始,插画师按书中内容画配图,吴军一看,人物长得很像,“插图目的是让小孩一看就知道在讲什么”,便和插画师讨论,得画出主要贡献:编排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时,在旁边画几何学图案;编排爱因斯坦时,搭配相对论方程……
蓝本《全球科技通史》带入了吴军的个人史观,也就是“能量”和“信息”,而《给孩子的科技史》更强调独立性。“给小孩子看的,更重要的是趣味性,就是能吸引他们阅读。而对于不同科技内容,不同孩子感兴趣的程度不一样,所以书的章节基本是独立的,家长想给孩子讲故事,随便翻开一章都可以。”
在吴军看来,通识教育目的之一是让孩子更了解世界如何运作,“而人类历史最精彩的部分是科技史,科技是理解世界的绝佳角度”。于是,我们的对谈延伸到两个方向:科技理念与科普教育。

《给孩子的科技史》通过插图和文字,能让人清晰了解到人类为了和野兽抗争,如何发明出武器;为了分享传递经验,如何发明语言和文字等知识。
如何避免“娱乐至死”
如今市面上以小孩子、学生为书写对象的图书大多是故事书,科技类童书很少。对吴军来说,《给孩子的科技史》是提升科学素养,进行通识教育的尝试。
《环球人物》:为孩子们挑选知识点时,标准是什么?为何这些精选人物/事件对他们很重要?
吴军:有两个层次。首先是挑知识点和重要发明和发现。比如,农药化肥。如今没有它,人类可能吃不饱肚子,但同时它也带来了污染,需要警惕和反思。其次,要选和小朋友上课相关的知识。现在上课时,老师很少提到某个定理是怎么提出的,就告诉你“是这么回事儿,你也别问了”。我想在书里多写写这些背景,让孩子们便于理解科技。
《环球人物》:您在《全球科技通史》提到:“近年来,全世界出现了一种科技虚无主义和反智的倾向,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娱乐至死的思潮,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给孩子的科技史》可否视为您反对“娱乐至死”、推崇科学的努力与尝试?
吴军:没错。举个例子,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买保健品。中学的生物课上都会讲“蛋白质吃到肚子里分解成氨基酸后才能被人体吸收”,但很多广告直接说“里面含有某种蛋白质,对孩子很有好处”。这很不合理。如果你掌握生物常识,就不那么容易上当。
还有,明星的一举一动很容易就有上亿观看量,而科普视频的观看量有上百万就算很好了。而且,时不时出现质疑或挑战相对论、能量守恒、哥德巴赫猜想的声音,很有噱头。媒体也乐此不疲地报道。其实,媒体不该报道哗众取宠的论点,越报道,他们越来劲。当全民科学素养都提高了,自然就会忽视这些观点了。

毕达哥拉斯。
《环球人物》:关于“娱乐至死”,也有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传播媒介越便捷,就加速了“娱乐至死”。比如,以前是电报、电台,现在有了短视频、播客等,对泛娱乐的传播就更快了。
吴军:其实早些年我也和你有相似的想法,直到我看了奈飞去年出品的一部反映社交网络产品危害的纪录片《社交困境》(The Social Dilemma),今年获得7项艾美奖提名。制片人和导演杰夫?奥尔洛夫斯基采访脸书“点赞”按钮的发明人、全球最大的图片共享公司Pinterest的前总裁等人,他们觉得社交软件就像是“毒品”,近年来纷纷离职。这些工程师是半个产品经理加半个心理学家,设计出让你欲罢不能的功能:脸书的点赞是用户最喜欢的功能之一,短视频的“往下滑”让你沉迷于“刷”视频……
片中有句话我印象很深,“当一个产品免费,你就成了产品”。这些设计把你“训练”成机器,为产品创造流量,增加广告收入。社交产品本质是让你上瘾。根据研究,太频繁使用手机会干扰人的生活节奏,导致睡眠紊乱,更容易情绪低落、沮丧。
《环球人物》:照这么说,我们似乎很难抵抗“娱乐至死”或科技虚无主义。或者我们换个角度,如何抵御这种趋势?
吴军:我承认,很难。我曾对一群自制力较强的人做了小调查,他们手机里只有微信,用来通信,几乎没有其他APP,以减少干扰。
但总体上,只有某个现象给人们的生活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大多数人活不下去时,才会意识到严重性。三四十年前我刚进入职场,很多人抽烟,你不抽烟,人家就劝你‘没事儿,来一根。后来,全社会意识到抽烟的危害,有了共识,就开始禁烟了。如今,你想要抽烟还得找个角落躲起来。
大多数情况下,觉悟的总是少部分人。

上图:《全球科技通史》。下图:《浪潮之巅》第四版。
“鸡娃”不如先“鸡”自己
2015年,吴军的大女儿吴梦华申上了麻省理工学院,开学前问吴军对她有什么期望。经过思考后,吴军给女儿写了一封信,里面提到“态度决定人生格局”。
《环球人物》:在教育这个议题上,您经常提到“格局”“境界”“见识”。在您眼中,有见识、有格局的父母是什么样的?
吴军:首先,他们相信教育是一辈子的事,“赢在起跑线”没有什么用。其次,不盲目跟从。我认为“缺乏远见”的一种表现是人家干嘛你就干嘛。前阵子《小舍得》热播,一位妈妈让小孩去上辅导班是因为孩子同学去补课了。其实,别人家孩子学得好,不等于你家孩子行,家长应该知道自己小孩适合什么。
我认为,中国教育对“完美分数”的追求限制了许多尖子生往上沖的高度和向外拓展的广度。比如,一个孩子花50%的力气考到95分,家长却要他多花50%的力气考到96分,仅为了一两分,目光就有点短浅了。最后,家长应该尝试成为“教育者”,进行引导,而不是让孩子成为试验品。
所以,与其“鸡娃,”不如“鸡”自己,把自己“鸡”得很厉害再去鞭策孩子。不能自己躺倒了,把压力都加在孩子身上。这不合适,也不公平。
《环球人物》:如果说教育是一辈子的事,那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吴军:我想提一下英国社会学家、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他把进化论、“适者生存”的理念应用在社会学上,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大约150年前,他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里提到教育应该为“完美生活”做准备。“完美生活”是什么样?这包括5类活动:直接有助于自我保全;获得生活必需品并间接有助于自我保全;抚养和教育子女;维持正常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满足兴趣、爱好和感情。完成这些活动分别需要5种知识,我把它们概括为:必要的知识(如直接谋生的技能)、间接的知识、为人父母的知识、作为社会公民的知识、锦上添花的知识。
现实情况是,几种知识常被忽略。比如一些父母只看重直接谋生、赚钱的技能,而忽略科学涵养、文学素养等间接知识。这就太急功近利了。养宠物不拴链子,给邻居造成危害,就不具备社会公民意识。但对不同知识的培养也要适当。比如锦上添花的兴趣爱好。现在出现了兴趣班“鄙视链”,一些父母会把特殊才艺视作“时尚”来攀比,比如学马术的鄙视学高尔夫的,学高尔夫的鄙视学击剑的……这就没必要了。
《环球人物》:您觉得理想的学习过程是什么样的?
吴军:我一直认为,学习肯定是辛苦的,但不应该是痛苦的。我有两个女儿,我为她们创造条件,但也相信学习只能靠她们自己。老大一开始在公立小学读书,管理比较放松,我给她转学到一家比较好的私立学校后,她学得有点费劲,但同学非常好学,她耳濡目染,有了学习动力,不懂就问,老师也非常nice地鼓励她。老二是学校球队的成员,每天打完球回到家都晚上8点了,还要做作业,但是她并不痛苦,学得很happy。如果太纠结于一两分或者名次,不断施压,孩子会觉得学习很痛苦,进而失去兴趣。
前阵子有个女孩子因为不堪父母的压力自杀了,当然这是极端个案,但也反映了一些东西。按理说父母爱孩子,但如果他们爱的是孩子前几名的成绩,这不是本末倒置吗?而且家长总说:“我这是为了你好。”我觉得,这在将来究竟对孩子好不好是一回事,但你毁掉了孩子的快乐童年,这已成事实。我觉得这个孩子就学得很痛苦。
《环球人物》:最近颁布“双减”,让教育回归校园,说明社会也意识到孩子负担过重的严重性。
吴军:“双减”确实很有必要,但需要想好把时间减下来以后要干什么。光减负,不太行。我读小学时,学校几乎不组织考试。但到了五年级,一考试,有人考零分,好几个同学的语文数学加起来只有十几分。所以考试少了,家长心里得有数。如果孩子拿这些时间无目的地玩耍,那还不如不减。

吴军曾受邀参加文化综艺《锵锵行天下》,在节目中为主持人等解说西方文明。
《环球人物》:所以还需要做适量的“加法”?您觉得可以从哪些方面努力?
吴军:首先是培养基础技能,就是注重通识教育,提升科学素养,过早的分流(比如分高中和职业高中、文理分科)不利于通识教育。在美国,学生的分流比较晚,小学中学按学区来划分,不用考试,没有太多升学压力。如果小孩对科学感兴趣,基本上就真的很感兴趣,不是被逼出来的。现在在国内,面向全社会的科学教育总体上还比较少。其实,在这个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科普经验。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会给小孩子、学生写科普书,比如宇宙基本模型提出者之一、物理学界泰斗史蒂文?温伯格,还有著名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乔治?伽莫夫,都写过科普书。
其次是培养核心素养,就是发现新知的理性方法。简单来说,要发现新知,首先要触碰世界,看到实际问题,然后理性地质疑它,再用一套科学方法验证它。
最后是分层培养。“分流”是直接不让你学A,“分层”是学A时根据你的兴趣程度让你学A1、A2、A3。有点像国外科普书的“分流”,一本科普书会出几个难度不同的版本,读者分别是没有任何科学背景的人、有点学科积累的人、内行人。
教育是一辈子的事,而科学教育越早越好。
吴军
人工智能专家,风险投资人,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董事,曾在谷歌和腾讯担任高管,著有《浪潮之巅》《全球科技通史》《文明之光》等,曾获“文津图书奖”“中国好书”“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图书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