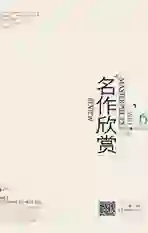鲁迅儿时教育叙写延伸的教育命题
2021-08-03陈彩林
摘 要:鲁迅以自叙传性质的切身体验叙写儿时教育情状,由此延伸出传统而时新的教育命题。教师该如何施教?应具备怎样的品与学?施教效果该如何检验?这一系列教育命题都得以文学直感的方式做出或逆向或正向的回答,进而引发社会对于读书、教书、写书等时代问题的深切思考。
关键词:儿时教育 鲁迅叙写 教育与文学
鲁迅对儿时教育多有叙写。中国孩子认识鲁迅多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始。这篇写于1926年9月18日的散文是四十五岁的鲁迅在中年对儿时欢乐的深情忆念,那是他生命最温慰柔软的部位。这对于五十五岁便因病而逝的他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本来就是怀旧。有意思的是,早在1911年冬他便用文言写了一篇《怀旧》,这也是他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文虽小说,但自叙色彩显明,开篇便叙写了儿时受教情景。但与十五年后所写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相比,所寄儿时受教之情迥异,前者忆苦,后者思甜。正是在这“苦”与“甜”之中,鲁迅以自叙传性质的切身体验引导出教师、教学与教育乃至读书、教书与写书这一传统而时新的教育命题。
学生对先生的情感很大程度上源自先生的施教。秃先生是如何施教的呢?《怀旧》特写了对课场景:
彼辈纳晚凉时,秃先生正教予属对,题曰:“红花。”予对:“青桐。”则挥曰:“平仄弗调。”令退。时予已九龄,不识平仄为何物,而秃先生亦不言,则姑退。思久弗属,渐展掌拍吾股使发大声如拍蚊,冀秃先生知吾苦,而先生仍弗理;久之久之,始作摇曳声曰:“来。”余健进。便书绿草二字曰:“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去矣。”余弗遑听,跃而出。秃先生复作摇曳声曰:“勿跳。”余则弗跳而出。
秃先生上对课不讲解平仄,就让“予”属对。“予”根本“不识平仄为何物”,那种“思久弗属”而“渐展掌拍吾股使发大声如拍蚊”的着急与痛苦宛在目前。先生将学生晾在那里,很久很久才以“摇曳声”的尊荣与高慢讲解。而讲解也只是就题讲题,给个答案,也不对属对平仄问题进行系统讲解,更没有结合九龄孩童接受特点进行深入浅出的循循善诱。而且,草草讲完之后,也不管学生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便来一句冷冷冰冰的“去矣”。从“余弗遑听,跃而出”可见,余逃之唯恐不及的生理与心理压迫。
更有甚者,秃先生还对学生施以体罚与人格羞辱。“予”让王翁讲山家故事,秃先生必继至斥责,而且次日还要“以界尺击吾首”,并责骂“汝作剧何恶,读书何笨哉”。因此,他带给学生的感受是“以书斋为报仇地”。“予又何乐”,度日如年。在这种情形下,学生只能生出两种扭曲的向往:一是“设清晨能得小恙,映午而愈者”,这样“可借此作半日休息”。学生装病逃学的初情,可怜可悯。二是“秃先生病耳,死尤善”。秃先生简直成了学生的梦魇。学生恨先生至死,可悲可叹。
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施教情形,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也进行了叙写: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寿镜吾先生先严后宽,先管后教。学生在先生那里既感受到“严厉”,也感受到“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将律与爱渗透到管理与教学之中。在具体教学方式上,他注重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增加了阅读量。与此同时,鲁迅连续用了两个“渐渐”,强调寿镜吾先生施教对学生接受能力的重视与培养,学习任务慢慢增加,学习难度慢慢提升,注重知识传授的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结果是,学生对他不是怕,更不是恨,而是“很恭敬”。
事实上,鲁迅对寿镜吾先生敬之终身。1915年12月3日鲁迅“得寿师母讣,以呢幛子一送洙邻(寿洙邻为寿镜吾次子)寓”,5日又往三圣庵奠堂吊祭。1923年1月29日,四十二岁的鲁迅还收到七十四岁的寿镜吾先生的来信,并于2月9日作复。二人的师生情谊持之终身。
秃先生的原型已很难考,不过从自叙性看,应该是鲁迅亲历。对于秃先生,“予”不独有怕,有恨,还有讽刺。对于秃先生的讽刺画像,鲁迅速描了一个细节:秃先生“归必持《八铭塾抄》数卷”。
《八铭塾抄》何许书?原来是清代科举课本。一位来往于学校与家之间、时常夹着本应试教材的教师形象,跃然而出。他除了照教材讲讲应试考题,就是在关乎身家安危利益时施展临时应变的投机伎俩。秃先生在学生面前端起架子,以摇曳之声呼之“来”,挥之“去矣”,斥之“何笨哉”,一副道貌岸然的博学模样。他真的像寿镜吾先生那样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对于秃先生这样的教师,早在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谐鬼》中就有精妙描画。
聞有老学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学究素刚直,亦不怖畏,问:“君何往?”曰:“吾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摄,适同路耳。”因并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庐也。”问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昼营营,性灵汩没。惟睡时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缈缤纷,烂如锦绣。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者,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荧荧如一灯,照映户牖。人不能见,惟鬼神见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学究问:“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鬼嗫嚅良久曰:“昨过君塾,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不敢妄语。”学究怒叱之。 鬼大笑而去。
老学究胸中的讲章、墨卷、经文、策略,大约就是秃先生时常夹着的《八铭塾抄》之类。原来教师胸中只有这些应考资料,看似教书之人,其实是不读书之人。他们日日“营营”,可以蒙蔽世人俗眼,混口饭吃。他们读书一生,教书一生,所读与所教之书不过是求取功名与营生的讲章墨卷,而这些在鬼神眼中竟然“字字化为黑烟”。他们施教就像墨鱼喷墨,而学生整日苦读,从早到晚,甚至连节假日都不得休息,不过是“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秃先生、老学究之类也。
对于秃先生、老学究之类教师的施教效果,李汝珍在《镜花缘》中以传奇手法形象再现。
唐敖道:“小弟吃了朱草,此时只觉腹痛,不知何故。”话言未了,只听腹中响了一阵,登时浊气下降,微微有声。林之洋用手掩鼻道:“好了!这草把妹夫浊气赶出,身上想必畅快?不知腹中可觉空疏?旧日所作诗文可还依旧在腹么?”唐敖低头想了一想,口中只说:“奇怪。”因向多九公道:“小弟起初吃了朱草,细想幼年所作诗文,明明全都记得。不意此刻腹痛之后,再想旧作,十分中不过记得一分,其余九分再也想不出。不解何意?”多九公道:“却也奇怪。”林之洋道:“这事有甚奇怪!据俺看来,妹夫想不出的那九分,就是刚才那股浊气,朱草嫌他有些气味,把他赶出。他已露出本相,钻入俺的鼻内,你却哪里寻他?其余一分,并无气味,朱草容他在内,如今好好在你腹中,自然一想就有了。俺只记挂妹夫中探花那本卷子,不知朱草可肯留点情儿?……”多九公笑道:“老夫虽有窗稿要刻,但恐赶出浊气,只怕连一分还想不出哩。林兄为何不吃两枝,赶赶浊气?”林之洋道:“俺又不刻‘酒经,又不刻‘食谱,吃他做甚?”唐敖道:“此话怎讲?”林之洋道:“俺这肚腹不过是酒囊饭袋,若要刻书,无非酒经食谱,何能比得二位。怪不得妹夫最好游山玩水,今日俺见这些奇禽怪兽,异草仙花,果然解闷。”
唐敖中探花那本卷子朱草有没有留点情儿,书中没有明写,根据语境想必也化作浊气排了出去。这样看来,教书若仅为营生,教学仅为应考,胸中只有数卷讲章,施教便不过是喷黑烟。相应地,读书若仅为功名,便不过是吸浊气。教育如果成为“喷黑烟”与“吸浊气”的过程,学校岂不成了林之洋所说“酒經”与“食谱”的加工厂?如此,不管是教书人、读书人,还是写书人,穷其一生,不过是林之洋的肚腹——“酒囊饭袋”,哪怕是像多九公那样年过八旬,除了浊气,所剩便一分没有了。
细思极恐,现实中夹着讲章、讲着墨卷、喷着黑烟的秃先生何其多也,整日苦读、假日补课、吸着浊气的学子何其众也,所作诗文、所出窗稿类同黑烟、浊气者何其滥也。面对朱草,唐敖尚有自愕,多九公尚有自明,林之洋尚有自嘲,而我们是否还在堂皇装睡,继续干着自欺误人的营生呢?
这样看来,教师、教学、教育最起码要有一点老学究“素刚直,亦不怖畏”的胆量,借那位“谐鬼”之目,看看我们的头顶到底有几许光芒,看看教室屋顶与学校上空有无黑烟笼罩;读书、教书、写书更要吃两枝朱草,“赶赶浊气”。
基金项目: 本文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新时期以来广西乡土作家群创作实践多维研究”(17BZW001)阶段性成果
作 者: 陈彩林,文学博士,博士后,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