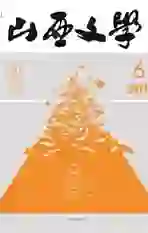冷漠而温柔的夜晚
2021-06-02玄武
1
坐待日落,昼光收而天地冥。就仿佛是我赶着那枚红丸,关入群山之圈中。说赶,其实一前一后,彼此有默契和惯常的步速。尾随而已。一个知道该往哪里跑,在哪里停下,等待着,但不催促。一个相应跟着多少年下来的节奏。
我想起少时,村里一个几岁的小孩。他只有一只羊,拴在自己左胳膊上。他没有母亲,饿了就趴到羊身下,咂巴羊奶頭。我见过这样的场景。后来他害羞了,吃羊奶避开人,但是我还是能够见到。他因此恨我。
许多次黄昏,他和他的羊,在天光里的轮廓从小到大,从远到近,从模糊到清晰,缓缓靠近了村口。
现在我是那个小孩。日头是我唯一的羊。
2
夜游看到一对夫妻鸟,在树杈间交颈而眠。总担心鸟儿睡梦中掉下去,我小时候在柿子树上睡觉,发生过这样的事。睡前我还有意用双脚勾住树枝又交叉呢。但不管用,人这个种类,入睡是四肢舒展开来的。不能像鸟儿。
鸟儿怎会掉落。它的小爪子扣得很紧,翅膀也挨住旁边的枝叶。树是它的软床,怎么睡也不会滚下床去。
这对夫妻鸟梦见了我的灯光,但是看不到我这个人。我隐在暗里,灯光是我的隐身衣。有一只鸟不安地扭动头,却没有飞的意思。
现在鸟儿梦见灯光隐去。我离开,万物如常。鸟的梦断续不连贯,明天醒来,曾经的梦更加模糊,像是前世事了。
这个人闯入鸟梦,究竟意义何在,于鸟,于他,于树,于他冲荡开的那片暗?
3
无月,无一颗星,夜晚的旷野,不知何故是微亮的,像天擦黑时的天光。万物依稀都在,站着的站着,晃动的晃动,藏猫猫的藏猫猫,比如那只成精一般狡猾的兔子。
路上如此,旷野如此,在山间也是如此,仿佛黑暗被弄丢了。夜晚被掉包,成了一个弄虚作假的黑夜。
前几日极寒时还不是这样,即便有月,弯月或者半月,也基本十米外不可见物,大物唯显轮廓。
我还没有弄明白原因,似乎不大有人关心,也不大有人见到。人们忙着赚钱,算计职位升迁,或者此时做着艳梦。他们会发出尖厉的讥笑声,说吃饱了撑的关心这样的事,说关心这个有用吗?他们玩着抖音转着段子嘴里塞着东西口齿不清地说,这个人好无聊啊。他瞎转无聊,他读书也好无聊啊。
夜晚如此,目前能想到的是雾霾所致。雾霾像一个锅盖扣在上空,霾粒反射了城市光线,而且似乎还起了保暖作用。
想不到霾的影响有这么大,夜晚的黑都被它强暴篡改。但真的是这样吗?
4
夜晚不属于人类,他们为睡眠、恐惧所控制,在睡梦里躲避黑暗和寒冷。夜晚的旷野,仿佛另一星球。一只兔子在树林里独自玩耍,不见别的,就它一个。它看不到我,在一棵松树下蹲着,可能正吃松子,两只耳朵耷拉下去,半晌不动。很长时间,大约一刻钟维持那样的姿态,以致我怀疑看走眼了,以为是一个动物蹲状的石头。这时它惬意地伸了个懒腰,蹦跶了一下,又退回去继续吃。它甚至还打了个滚。它孤独而自在,就像造物之初的一个小神灵。它追逐我打过去的一豆点红光,玩得开心。手电亮起的时候,它的眼睛亮了红光。它向下一矬,一动不动,仿佛瞬间石化。忽然一跃,就在一跃之间消失了。
对它,对我,这偶遇都是不真实的事。我和它原本毫无干系,也不可能有干系。彼此的距离,比人群中相识却永不交往的两个人之间更为遥远。
我可能跨过了谁的坟头。出声念了句抱歉打扰,黑暗里打个躬。前面又是坟头,再后来也懒得说了。人类是敬畏与死亡相关的事物的,这传统几乎成为基因遗传。我一样,过此,心中多少起瘆意,后来就没有了。
坟旁边是垃圾,城市不断运来的垃圾就要把一个山谷填满了,我猜也有些无主之坟深压在垃圾之下。新开的道路旁随处都是坟,逼仄地挤在行道树之间,像随时想逃开,却又受拘,逃不掉的样子。死亡与垃圾同在。死者的尊严已成为不可能之事。连生者都无尊严,遑论死者呢。
一只什么动物,发出一种人类的惨叫声,一声又一声,在山谷里回荡。我知道发情野兔的叫声很吓人,是肾上腺憋到大脑沟回里一般的痛苦大喊,是的,是大喊,很大声,接近于婴儿不舒服憋足吃奶气力的哭喊。你简直不能相信,那是一只胆怯的几乎躲开万物的小小的兔子发出的声音。但这个惨叫声我听了很久,后来确定不是兔子。也不是猫狗,不是鸟类。应该出自我不知道其声的某种动物,那一种像被囚禁虐待的女人大声哭泣一般的声音啊,仿佛带了身体的伤痛。
起了风,树林开始摇晃,像一座黑魆魆的船。是黑暗使地上万物有了整体感。拨开树枝,一只很小的鹌鹑,躲在枝叶深处。我头钻进去,它在灯光里几乎透明,茫然地抓着树枝,不知发生什么。它睡得正熟,好像梦中见到了一个恶魔似的人类。我伸手就可以轻轻捏住它。我和它脸对脸,对着端详了一会儿。它几乎没脸,脸上只有一只尖喙。我离开,它没有动。我只是丰富了它的梦。但是一只鸟的记忆留不住一个梦。
黑暗淹没时间,让人对时间失去概念。天快亮了。
草丛窸窸窣窣,隔了冷硬而茫然的风声,也辨得出来。强光手电照着,枯草连片不见头,高过膝盖。深一脚浅一脚过去,忽然有物扑棱棱飞起,骇我一跳。自拍动翅膀的声音可知,它的肉很大,是肥壮丰满如唐朝女人一般的鸟。
它咯咯叫着,原来是野鸡。只瞬间,不知落向哪里,声音停息,不见了。抬头见漫天星辰,刚才羽毛也似的细细的月亮,沉得不见了。
打着灯光再向前走,拔脚吃力,有的草窝子近大腿深。灯光边缘觉得有物——是直觉,并未见到动。手电聚了光照过去,没有东西。想往前走,不甘心,再照,哇塞,是一只雄雉!离我只两三米远,它埋了头在草深处,一动不动,以为能骗过我,却暴露出漂亮的羽毛和尾巴。
捡了块石头扔过去。雄雉吃了痛,一言不发飞起来。它飞得好高!不像以前见过的野鸡斜飞,而是一飞冲天。灯光照见它在苍蓝的天空下飞翔的姿态,像一朵暗红的大花盛开。赞叹!
5
午夜零时的短松林,苍黄的半月低悬,微微有光,但树影里是黑暗的。一棵稍高的树杈间,宛若有一只大鸟——很少有大型鸟。偶有一次,一只大鸟还是两只,从我头顶砉然起飞。我没有看见,没有预料到,浑身都抖了一下。那声音像把黑暗和其他什么东西撕裂了一般。从拍击翅膀的声音判断,是非常有气力的鸟,大而机警,体型使得它不能钻入枝叶,停留在树巅。它应当只是过路鸟,歇一晚上再赶路,像古代风尘仆仆的旅人。它要去哪里,是一对夫妻吗?应该没有带孩子。很抱歉打扰了它们。在它们,也许带了惊惧而去,以为误投了一家十字坡或者龙门那样的黑店。
现在我走近了那只大鸟,绕树三匝,仰头细细寻找。有些角度完全望不到,以为眼花看错,再转又出现了。打开头灯,鸟微微动一下,鸟头很小。它跳出来在一边枝上,我看到它仰起的尾巴。
是黄雀,小小的黄雀。原来是一大群黄雀,因为寒冷,钻枝栊里抱在一起,依靠彼此身体的温度取暖,抵御寒夜。至少有二十只,拢作一团,如同圆球一般,以致昏暗里看去,竟成一体。
我没有再打扰它们,举步离开。眼睛适应了黑,月光仿佛明亮起来。一棵小松树与我视线平行处,似乎也有东西。我已经站在树边了,就像路遇熟人,站着寒暄时那样的距离。树上有鸟,在我眼边,而且感觉到有两只。
我犹豫着,但还是好奇占上风,开了头灯。天哪,又是黄雀!眼前一尺远!
静静端详它,小东西很小,羽毛几乎透明。应是当年的新雀,涉世不深的样子,茫然不动。灯光晃着,它什么也看不到。罩在灯光里,它像被关进嵌入黑夜的一只光笼。
据说黄雀很好养。我忽然有念想捉一只回去,给小臭玩一下。就一下,教小臭认识一下老谋深算的鸟,让僵硬的成语成活。但是不放它,明天晚上再带它回来林子放飞,免得在家里放飞,它不能识得回来的路、找不到种群。它一个人,夹在大群的麻雀、乌鸦、喜鹊里,是无法生存的。它们都欺生。连斑鸠也不会放过它。更何况还有污秽的夜鸟,比如杀人夺命的强盗一般的枭。
我摘下一只手套,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担心惊动它,又急,不能摘另一只了,在黄雀两边双手做捂合状。鸟不动。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在动。手捂过去。
动作还是慢了。我害怕用力过猛弄坏了它,这么纤弱的鸟儿啊。也不敢捂太紧,它从我指头缝里扑棱着飞走了。
不止它一只。整棵小树在尖叫,在扑棱。原来竟有这么多黄雀在同一棵树上!刹那间全部飞起来。就仿佛一棵树在起风时用力一甩,飞出了自己所有的小果子。有几只鸟在光里不知何往,拍动翅膀原地空中維持平衡,忽然俯身,朝光源——我的头顶飞了下来。
这是一群不知所措的黄雀,和一个不知所措的人的相遇。它们撞了我一下,然后不见了。明明是我冒犯了它们,结果却像是它们欺负了我。许多年后,我会想起半月昏暗悬在头顶,头灯微亮,一群黄雀四面八方劈头盖脸落在我身上的情景。这真是一场奇妙到有些诡异的邂逅。
这只是家附近一个园林公司的几千亩地的荒野。仅仅是荒野,不用人管,它就复活了,并且能够复活你身上死去很久、以为此生不再能重生的东西。
人人需要一片荒野,自然,放纵,甚至野蛮。在荒野中,你能够成为一颗种子。但也唯有少数人是种子,许多假的东西与荒野排斥,甚至像塑料一般,是荒野的敌人。
只一月时间,我扭曲的颈椎,感觉不到疼痛了。
6
冬夜遇到过一条蛇。我忘记是为了找一种植物的根须,还是查询一只兔子的洞穴。镐插进冻土,带起它。起初以为是根棍子,伸手从镐上拿开时心念一动,忽然住手。
它好像动了一下,又好像没有。有无之间,就像我与英文的关系,好像懂一点,又好像根本不懂。也好像我与人间的关系,好像懂一点,又好像根本不懂。
此时更可能,只是头灯在晃。它盘曲着,并不呈环状。它身体的某个部位,似乎被镐擦破了,但没有看到出血,或者只是土遮住了伤口。
夏天时我遇过它。我认为还是它,一条灰白色的大蛇,在草丛里几乎不见。我见过它吐蛇信子,仿佛有嘶嘶声,但更像是我的幻听。此时我一边记下它,一边又听到了嘶嘶声。
我注意到它并非因为它游走或吐信的声音,而是它怪异的形态。它刚吞了食物,一只蛙还是什么鸟,粗绳索一般的身体僵硬着,中间鼓起堪称巨大一块。目睹这样的场景让人恶心,但仿佛目光被吸住一般,竟是目不转睛。小时候大人告诉我,蛇能远距离吸住枝头的鸟,比如麻雀,如果它在空中原地扑腾翅膀却飞不走,基本可以断定是被蛇吸住了。
我有打死蛇的片刻冲动。但仅仅因为觉得丑陋,因为斩蛇的古来英雄之梦,因为觉得危险?
我还是放弃了。我也救不得它腹中的蛙或者鸟,救也无意义,蛇终要觅食,那是无人能够破解的古老循环,人也陷身其中。我不是因为不愿杀生,而是觉得杀它是没有意义的事,和我在冬夜挖见它一样没有意义。近年,意义一词,始终困扰我,不离须臾。
它腹中那物又下移了一点时,我离开。下移的那物,明显比一开始缩小了一点。蛇依然几乎不动。
此时的僵蛇,正在夏天我遇到时的附近。我用镐挑着它,放进挖开的壕沟,推开土,埋进去。再上面,堆了些雪。雪是有保温作用的。
惊蛰,想到它。那条蛇今天应该醒了。它要开始一年一度的蜕皮。
蜕皮是神奇而艰难之事。据说受过外伤的蛇,蜕皮更难。但如若不蜕,它可能会憋死在自己的皮里。
此时这蛇正受煎熬。我觉得它可以办到。那么大的蛇,长了多年。从前它也可能有过类似经历。蜕皮犹如脱胎换骨,推翻自己获重生。我拜服这样一种生命呢。是赴死而生的勇气,这勇气更接近天生本能。人类中许多都办不到,没有蜕皮的动力,宁愿骨头缩一点,在皮里待着,憋着,并竭力调整出一副舒服的姿态。他憋不死的,只是憋死了一年又一年的心念。
那么夏天时我还会遇到它,像是老朋友了。我一边渴望,一边心里提防被它咬一口,这也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蛇不主动进攻人的,攻击源于误判被侵犯。有时人自己便是那蛇。
7
野兔跳来跳去,两座果园里拴着的两条狗、不拴的一条狗并不吠叫。不拴的狗也不追赶,它知道自己捉不住兔子,早就气馁了。它们和兔子成了老熟人,是朋友关系。兔子有时为了安全,还有意靠拢狗在的场所。比如狐狸,比如黄鼠狼,它们来了狗就拼命吠叫。它们不敢靠近狗。
但是有几只兔子不见了。早晨在果园的鸡窝边发现一只,提起来看,被吃得剩了一张皮,头、肚子都没了,背上的细骨头都被啃得干净,只剩一条完整的大腿。
起初怀疑是黄鼠狼干的,直到当晚遇见狐狸。没有开头灯,只有仪器的一点闪光,和我的脚步声。它的目力和听觉真好,距我一百多米撒腿就跑,钻进果园深处,一边跑一边回头,那样子就像做了理亏事的小孩。它是又来找昨天没吃完的那只兔子。
我从果园上方绕过去,藏在一面高的篱笆后面。前方是麦田。那厮卧在麦田中央!很近!我用仪器看得见它的尖嘴,它还伸出前爪像人那样抹抹嘴,一副吃了美味的满足模样。麦田那边是路,有车晃着灯光而过,它根本不理会。它太知道车与它毫无关系,构不成威胁。
可以确定,兔子们的失踪事件是狐狸所为。黄鼠狼吃不了那么多。况且亲见了狐狸在犯罪现场。我动了杀心。
母亲却说,打它干什么啊。又不能吃。人们都觉得狐狸漂亮,母亲说的是狐狸“焦毛咯乍”,拖个长尾巴。她说那东西不要招惹,人都得拿它打比方,说谁谁精得像个狐狸。
母亲对黄鼠狼不反感,家乡称作黄鼠狼子。加一个“子”,发音却非zi。我总想古代的称谓,子是尊称啊。庄称子,荀称子,了不起呢。母亲说以前喂鸡的时候,鸡在果园里吃蟋蟀,吃得油光发亮。有只黄鼠狼时常出没,它不咬鸡。一直没有咬过。或许是因为不缺吃的,或许是因为它的家在附近,它需要维持家附近的安宁。它也不愿意因为咬鸡惹着人类。
万物各尊其道,各行其道。
痴迷观察夜间的动植物,它们在夜里熠熠生辉。树仿佛都忽然长了一截,像人一挺胸高了一点的神气模样。无风的时候静静站在黑暗里,万物中止,耳边有抽烟时的嗞嗞声。你几乎听得见树干里树液的流淌声。天暖了,那流淌声变得欢快起来。
8
天黑进入一个山谷,以前见过山民赶牛进入。山口狭小,里面却是阔大,诸物在暗里狰狞,连石头都似作势欲扑的猛兽。我未带弓,连防身的短刀都未带。原想沿一条谷爬到头,只好作罢,缓缓退出。这里是果真有猛兽的,比如狼,比如豹。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金钱大豹,全中国华北豹最多的区域,正在此地。看来若无向導,是无法夜间行山了。改日再来。
路边见火光熊熊,心中一紧,停车来看。已有一车停下,我问是什么,干吗在山里点火。那人说他也是看着不放心下来问。
是农民在烧自己田里的玉米秆。我说,怎么在山里点火啊,这么大火,有风,得当心啊。
你是无法拦人家的,你又不是什么长。只能好意笑着相劝,哪怕黑暗里人家看不见你难看的笑脸。
农民说,就这么点,烧一下,马上就完了。我哪敢把山点了啊,那我不是做下孽了。
这话听得人心里还舒帖一点。我说,你烧完用土盖一下火啊,别夜里又漫开了,那就麻烦大了。
他大声答应着。应付火的办法,他应该比我多。
冷。我不好站在火边守着,回路边跳到车上,开暖风等。看车窗外火光暗下去。写完这段,火光一点没有了。我再下去瞅一眼有没有火星迸开。
9
上古刘累在此豢龙,民间有对权力敬畏的仿佛遗传基因一般的东西,凡异人珍兽古木,一概称王。于是有了刘王沟的地名。以累为名,累的本意是层层堆积,看繁体字型也吓人,犹如见到群龙相互缠绕之状。
然而龙是何物?从前人们乱考证,有说是大杂烩,把各种图腾拼到了一起。有说龙是鳄鱼比如凶猛的湾鳄,称蛟龙,就是周处斩杀过的蛟龙。有时候又说到猪鼻龙,鼍龙。
我认为真实存在过龙这样一种兽。而且古代各个时段,所提到的龙并非一个物种。按照物种灭绝的速度,它们纷纷然彻底消失了,直到只剩下歧义不断的传说,剩下晚清轰然倒地的旗子上飞不起来的装腔作势的草龙,剩下混混们胸口的刺青。我们哪里是龙的传人。可以神农的牛,可以商的玄鸟,但龙从来是邪恶的。
我来此不为寻龙,我对此物毫无兴趣,来的是此处别地,我梦到龙女。我梦游了一个叫龙女沟的地方。在梦中,龙女与教人交合之道的素女、巫山的神女、填海的精卫、被马皮裹走的蚕女、山中乘赤豹的裸女重叠在一起,幻为一人。她的面容,我此生有时候觉得见过,有时候觉得从未遇到。
这个丰饶的小小山谷,足以承载我的梦想。无边无际的花朵等待着我的手,种植和摘下。在梦中我感到自己对这种无限产生的厌烦。
我知道我的梦从此被改变。我将时常听到野鸡扇动翅膀发出的有力的声音,像一个壮硕的女人拍动自己的肥屁股。我听到野兔发情叫春,像婴儿憋足气力的哭喊。我看到刚刚学会走路的小狐狸,看到黄昏的天空飞满了野鸡褐色的蛋卵。有的蛋卵里已经有了小小的野鸡,它在蛋清里好奇地转动脖子,像盘古等待开天辟地那样。
后来我梦见一头豹子,它站起来,长出胡须,胡须变白,它变成了我,我不见了。它在龙女沟口高处的山石上站立打望,并不进去。人间计时还需两月,它才可能进入,杀戮以及繁衍。我清晰地看到了诸物一边挣扎,大者如牛如猪小者如兔如卵,一边变成欲望,变成豹的翻滚和喘息声,变成小豹子。。
我等着豹进去,并不焦急。我平静得不像是等待。
10
午夜苍茫。一人置身漆黑的荒野,有这颗星球上只有自己一人之感。
我是谁?为何在此世?
为何在此时,此地?
为何忽然想起,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与头顶的星辰有何不同?
我是否拥有树上一颗正在积聚力量的嫩芽的品质?
我与黑暗里奔跑的兔子有何不同?
我是谁?那只刚刚消失的狐狸,是否有同样的疑问,或者已有答案?
我绝非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些无意义。我脱离那些经纬而获独立,而得自在。
在接近动物本能,完成循环链接的尊老、爱恨婚配、养育繁衍之外,一定有更隐秘的原因,促使我来到此世。那么它是什么?
什么样的力量使我背离人群?
旷野什么样的性质吸引我,使我觉得亲近?
11
夜里遇到黄大仙,趴在快接近顶部的对面山崖上不动,不知在等待伏击什么。也可能是因为距离太远,看不出移动。用测距仪来看,距我大约二百到二百五十米。中间它明显换了一下位置又不动了。
最近连续遇到黄鼠狼。这厮太快了,技能全面,跳跃、奔跑、攀爬、游泳、钻洞,样样俱全。奔跑起来像一道迅疾而去的波浪,感觉在它眼里,地面和垂直的墙算一个平面,它一下也不停顿已在墙上奔走,速度不减。
小家伙当真不好惹。我压根没想过抓它,只是惊叹。迷上这小东西了,想尽可能研究一下。看一个视频资料,它杀死兔子之前为啥还跳个舞?兔子怎么连逃跑的本能都没了,难道中了屁毒?
但据说它怕鹅。是真的鹅,不是谐音我。鹅夜间视力极好,而且遇险主动攻击。没有见过两者相遇的场景。
12
月芒在屋顶之后而出,射得空中满是。赤裸的枣树微亮,每一棵刺都清晰。
前行几步,满月猛然跳出,如发一声吼!
13
野兔居然也食肉。在极寒地区,已经发现有野兔吞噬同类尸体的现象。它还会攻击鸟类,连毛吃掉。它的胃能够消化鸟的羽毛。它甚至去吃天敌猞猁的尸体。
野兔耳朵不及家兔长,前端椭圆形。前肢比家兔长。野兔与家兔染色体相差甚大,比驴马之间都大,也就是说,家兔与野兔是无法交配成功的。家兔幼崽没有毛,光溜溜的。野兔出生下就有毛,三天后就能奔走。
野兔交配时间只有三秒,当真是一二三。交配成功的标志是:雄兔一个跟斗后翻,暈倒在地。
野兔奔跑可达每小时五十公里,欧洲野兔达到七十公里。狗是不能够捉住野兔的,两只狗一起也不能。狗靠舌头散热,张着嘴能累到无法合上,野兔被枪击受伤不动了,狗累得都无法叼,只能用嘴拱。狗主要起到把野兔轰出来的功效。我亲见过一只野兔,在三条狗的生活圈里活动,几乎每天夜里都如此。狗只是无奈地偶尔汪汪而已。
野兔也是与家兔几乎不同种类的一种野兽。与家兔的驯顺羞怯不同,野兔几乎是傲骄的。它的栖息地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在草丛,树叶茂密的丛林,而是在木叶脱尽的不太高的小树林里。高草使它奔跑不便,密叶影响它奔跑的视野。它自得于奔跑之能,那是它的求生法术,也是它引以自矜的技能。它在高速奔跑时能不可思议地折弯来避开危险。
有天夜里遇到一只野兔,独自在一块坟地玩,它像一个旷野里的小神,怡然自得,伸懒腰,舔前腿,翻跟斗,跃起在半空中。忽然就不见了。我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它出现在一个多半人高的树上,在树洞里探出头来!不知它怎么上去的。
我怀疑那是它的家。这只狡猾的野兔,竟然住在树上。过几天有空,我要去找一找,看一下,证实自己的判断。
14
月亮出来的时候,整座山都冰凉了。只有一只一指长的黄雀,存有稀薄的温度。天擦黑时,我伸手在灌木丛里捞住它。我只是玩一下,无恶意,也不带它走。
现在它从我手上起飞了,它惊慌的气息不是来自于我,与我两隔。它带着我的气息片刻在空中散尽。它进入山体的冰凉之中。
月亮美得不像在人间。像一块反重力的巨石,冉冉升起在空中。它美得让人感觉到压力,及危险。它像一只远古的巨鸟复活重现,振翅停在空中。它是不死的冰凉之鸟。
15
山野遇到孤零零一户人家(其实不能算一户,是一人),住在一个五六平米大的铁皮房子里。在一个正被拆迁的厂子外边,树林边,人迹罕至的土路边。他可能从厂子里拉了电线,因此是有电的。那是他能够享用城市生活的唯一物品。他紧闭的小铁皮门口,常停着一辆电动车。
这几日总在想这个事。他应该不是本地人。他从农村来到城市,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无论他是谁,似乎都不应该这么……可怜,和周围的草木一起枯荣由天的样子。他是个人啊,一个和我们同类的人,却像一块被扔在郊区路边的,垃圾。任其飘荡,风吹土扬,没人去理会。
他还喂着三条狗,狗都瘦,就在旷野的寒风中住,在他小小的铁皮门口,似乎是守门,更像是守电动车。那辆电动车大概是他在城市最大的财产。正常人怕是很难理解它对主人的重要性。前天看到一个外卖小哥因为电动车被扣绝望自杀,幸好被救,我是明白的。这世上苦苦煎熬的人们啊,有在生存中,有在欲望中,有在为屎尿体捧场中,有在权力场不能自拔中,有在囹圄中。有大难身无恙的,我的朋友。
也有在山野游荡中,比如此刻的我。
三条狗也在人间煎熬。狗对我一向友善,但夜间遇到便不同。它们发出声贝不一、频率不一的吠叫,边叫边退缩,胆怯而尽力的样子。有一条狗似乎专门负责快频率的尖吠,像是通知主人快点来啊。有一条应该是大些的狗,它负责发出凶狠的威胁声。第三条狗特点不明显。我没法通过,只好从低矮茂密的落叶杂木林里钻过去,鼻孔里全是土腥味,一直担心枯枝扎了眼睛。
我提到过的那只骄矜的野兔,它便是在这三条狗的地盘上生活。看硕大的体型,那老练不慌的气质,应该也是老狡兔了,有七八岁了吧。与人们想当然的认知不同,野兔完全不同于家兔,它不止骄矜,而且暴烈。它自得于奔走的敏捷犹如田径运动员心醉神迷于自己的速度。它善于躲匿,光天化日之下,你眼皮子底下,最多不过三米,你就是看不到。它在地上用前蹄刨几下卧在里面,脊背与地面平行,或隐身在斑驳的草丛里。它是一位深谙隐身术的草泽隐士。当被天敌捕捉,譬如鹰,譬如黄鼠狼,譬如狐狸,确定无法脱身,它会不顾一切地奔向最近的井,拽着敌人一头栽进去,同归于尽。
16
皇帝盛宴,不敌故乡一钵浆水面。要开花念荠所酿,要昼夜不熄的炉火边煨许多日慢慢发酵,要土榨新油炒,要新蒜,要美女大腿一样的葱白,要门前树上摘的花椒,要入冬时带着泥拔出来冬藏的萝卜,要一棵结了数百小灯笼编起来挂在庭院晒干了的红辣椒,要自种的粗于筷子却嫩如春芽的好韭菜,要当年麦子磨就的面粉,要揉得筋道,要煮得刚刚好一点不能多一点不能少,要今天中午才下的土鸡蛋打在碗里搅拌时还有温度。要立刻干掉盛上。咥!再咥!
梦中的麦田,田埂上土块变成兔子,成群跳跃而过。青草一棵棵飞起来,一边飞一边长出羽毛,长出翅膀,长出嘎嘎的叫声,在麦田上空飞舞。是野鸡,而且是长尾巴的华美的雄雉,像一只只小凤凰。
麦子在夕光下泛出辉煌的金色,其实还没长起来。有些叶片,是在极寒的凛冬枯掉了。麦田刚浇过地,伸脚就陷过脚面。鞋越走越重,像绑了七八斤的沙袋。农民说,浇一亩地是一百多块。这里是水地,是好田。但麦子是旱地产的麦子好吃,筋道韧性有力。
锦衣如豹,夜行于黑暗而布满星辰的故乡天空之下。今晚要穿行三两百公里,正好是一头虎的活动范围。其中徒步二十公里。过:彰坡,甘泉,浍河,二曲,大河。要遇到:夜间的树林,沙沙响的枯叶,长满荒草的田埂与斜坡,细细的月亮,一指长的小老鼠,七八只五六只的野鸡,正在交配的兔子,壮硕的黄鼠狼,沟里游走的狐狸,夜里角仍在生长的野羊,狍子,咻咻的大野猪小野猪。不会遇到豹子,它在丛林深处忽闪着眼睛望我。某个瞬间我感到树枝的闪光,很可能正是它。
【作者简介】 玄武,作家,诗人。1972年生于翼城。1989年开始写作。著述多种,有诗作刊于《人民文学》《十月》《诗刊》 等。有诗集《更多事物沉默》出版。著名纯文学公号“小众”(xiaozhong_xuanwu)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