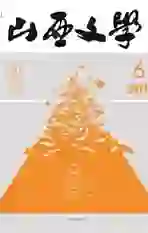四季粥店
2021-06-02邓洪卫
四季粥店当然不是只有粥,很多人在这喝酒。因为这里有很多特色小菜,一碟一碟的,有水煮花生、雪菜毛豆、麻油猪耳、红烧刀子鱼、凉拌干丝、麻婆豆腐等等,可以是喝粥的“咸”,也可以是下酒的菜。想吃什么,拿就是了。喝酒当然适合三五个人,特别相熟的朋友,不那么讲究的,几个小菜摊在桌上,一瓶白酒分到杯里,边喝边聊,一结账,一百块钱上下,经济实惠,童叟无欺,心不疼皮不痒。讲究起来,那就没的数了,得上大饭店,九碗八碟,千把块钱拿不下来,嘴里不在乎,心还是疼的。
也适合一个人独酌,比如今天晚上的胡明亮。他进来时,正好最里边有个空座位。他面朝外坐下。这个位置好,他喜欢坐这个位置,一览众山小。
他拿了三个小菜,坐下后,又回身叫道,拿个酒来。
什么酒?你自己来看呢。老板娘的脸红扑扑的,看来前前后后忙得不轻,响快快地说。
胡明亮说,牛二吧,就牛二。
老板娘拿过一瓶牛二来。胡明亮说,这个有半斤吧。
嗯,半斤装的。老板娘看酒瓶上的商标。
喝不了,拿那个二两的吧。胡明亮犹豫了一下,说。
老板娘过去,拿了个小牛二过来,又拿个玻璃杯子过来。胡明亮旋开盖子,把酒倒在杯子里,先喝了一口,热辣辣的液体通过喉管流下胃子,如一团火。他忍不住咂了一下嘴,拿起筷子吃肉。
这一天,胡明亮上午开会,下午开会,下班了,坐在办公室给自己开会。妻子跟他视频了一下,问他回不回来吃饭——这几乎成了习惯——他说不。说不的理由有很多,比如加班,比如应酬,但今晚既不加班,也不应酬,只是不想那么早回家。他给自己开会,他头脑里有一堆会,他要回顾,总结,分析,研究,讨论,展望。他侧耳细听,外面没什么动静,好像这层楼的人都走了。他觉得没什么意思,今天这会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暂且散会,明天得空再开吧。
现在回去显然为时过早,因为没人喊他喝酒。下班前,隔壁的老刘过来倒了一杯水,老刘五十出头,讲究养生,每天要喝八杯水,一暖瓶水不够,再烧也没必要,最后一杯水都得到他这蹭。还有这么多,你没喝呀?老刘问。他想说今天大都喝会议室的水了,但他张了张嘴,没出声。噢,今天早上冒一下,就没怎么见你啊,哪去的?老刘问。他想说,给领导代会去了。但仍然没说出口。噢,肯定又给领导代会去了,代着代着就成领导了。老刘自言自语。他仍没说话的兴致。怎么了,闷闷不乐的,是不是哪个小婆娘黏着你,甩不掉了。老刘端着水杯过来问。他心里一紧,仍然不说话。老刘说,这个岁数,可千万别找小婆娘,太他妈累人。他的心又紧了紧,还不说话。老刘说,别装深沉了,我知道你是为了竞聘的事,别太放在心上,估计结果明天就能出来。胡明亮问,你怎么知道明天出来?老刘说,别小看我,我也有内线,要不要今晚上哥哥陪你喝杯酒。胡明亮摇了摇头。
老刘说这话挺不容易,单位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过了五十岁就不会再有提拔,老刘五十一了,工作热情蔫了,每天在班上喝喝茶,得混就混,生活热情却高涨,以前都要加班到七八点,现在一到下班点立即走人,一分钟也不多待,据说回去后少吃点晚饭,跟老婆到公园散散步,再到哪边广场跳跳舞唱唱戏,悠闲得很,如提前退休。现在他后悔没给老刘面子,弄得现在孤家寡人,无人诉说。他出来,果然一层楼都黑了,只有卫生间有光亮打在门口墙上。他上了趟卫生间,倒掉杯子里的茶葉,有气无力地尿了下,洗了洗手,抹了抹头发,顺手关了灯,到办公室发现茶杯忘拿了,又回到卫生间,半明半暗中,看着杯子在黑色大理石洗手台上,一伸手,却没拿住,玻璃杯倒在台上,滚到白色的水池里,哗啦碎了。奶奶的,这么脆弱。他不管它。明天一早保洁员自会来打扫。回到办公室关灯,关门,下了楼,到了路边,回头看去,大楼陷于黑暗,唯有楼顶闪着暗沉沉的光,冷笑着目送他远去。
昨天,单位搞了一场竞聘,提拔几名部门副总,五十岁以下,符合其他条件的,可以报名。他参加了。像他这样还参加竞聘的,已经没几个了,大都在四十岁左右。他忽然想起古代的科举考试,有不少七老八十的,还参加考试,自己不就是那样的人吗?他不想考,可是又不甘心,硬着头皮参加了,算是最后一搏,垂死挣扎,连妻子和小鑫都没说。他感觉自己答得不错,挺流利的,心里还是有希望的。
如果上不了,那不是自取其辱吗?他叹息。
可是,不争取下,怎么知道上不上得了,这个岁数,还在乎这一辱吗?他转念又想。
他本想坐公交车回去,公交站台就在门口,过路就上。忽有一股清香袭来,一个女子从面前飘然走过,他情不自禁跟了过去。女子身材并不曼妙,但穿着很节省,白色的吊带衫,露出了几乎半个背,肥肥的,还有一些痘,斜挎着小包,金色链子包带使她后背呈现出浅浅的压痕。还没老嘛,目力还不错。他自嘲。走到一个路口,有一个小摊子,摊子上喇叭循环播放:锅贴锅贴,鲜肉锅贴,刚出炉的,鲜肉锅贴。前面都是方言,最后一个“鲜肉锅贴”是普通话,听上去很是滑稽。女子停下来,看上去要买锅贴。他看清楚女子的脸,没有跟踪的欲望,径自向南走。上了一座桥,一个穿着白衬衫、黑西裤的高个子中年男人站在桥上撒网打鱼。男人一个转身,网已经从桥上旋下去,一个不规则的形状落在水中,桥下路灯映照,水面波光闪闪。一会儿,网收了上来。这男子他碰见过几次,他从没见过穿得这么正式的渔夫。没鱼啊,胡明亮说。不旋一网,怎么知道有鱼没鱼呢,男子说。他觉得男子说得很有哲理。我的快乐不在于是否能打到鱼,而是撒网时的快乐。男子将网整好,放在桶里,冲他笑了一下,骑上路边的摩托车,绝影而去,留下路边一摊水迹闪亮。
这条街靠近他所住小区,虽然陈旧,但很热闹。两边都是店铺,小吃居多,有的还是中华名小吃,比如向东五十米,有个红嫂鸭血粉丝,名声不小,十几张桌,天天爆满;往西五十米,对面有个红半天麻辣烫,只有三四张桌,生意也火得不行。四季粥店不大不小,六七张桌,粥、菜、点心都是现成的,摆在里面墙边桌子上,再往里就是厨房了。
他在这吃的早餐,跟贾小鑫一起来的。他戴着棒球帽,围着口罩,贾小鑫瞪着他,裹这么严实干什么,跟做贼似的。他心里说,可不就是贼嘛。当然不能说出口,不然肯定又会遭到小鑫的白眼加痛骂。他不愿意小鑫出现在他的小区周围,可她偏要出现,还要跟他一起吃饭,亲密无间的样子。
你想干什么?虽是质问,但由于声音小,听起来软绵绵没有力道。
你想干什么!倒是小鑫的反问更有力量,有点不怒自威的意思。他立即不吱声了。
早餐跟中餐、晚餐其实不是一个老板,两对夫妇合租的房子,各干各的,互不干涉。一对弄早餐,十点钟收摊,收拾好第二天早早来弄早餐;一对弄午餐和晚餐,弄到午夜十二点,收拾好,关门,只待第二天十点多到。早餐也比较简单,烧饼、油条、豆浆、稀饭、面条,小菜只有两样,咸菜毛豆,咸菜豆腐。特色是烧饼和油条。烧饼香薄脆,上面芝麻多,油条口感也好,无矾。来的人主要是奔着烧饼油条,虽说是有这样那样不好,但好的就是这一口。
他们点了两根油条,一块烧饼,一碟咸菜豆腐,还有一碗豆浆,一碗稀饭。别人喜欢烧饼裹着油条吃,胡明亮不喜欢,他喜欢分开吃,先吃了一半油条,再吃烧饼,烧饼扒开来,里面涂上薄薄的一层辣椒,这样吃着有味,烧饼吃完了,再吃那半根油条,烧饼油条吃完了,豆浆也喝得差不多了,拿卷纸抹了抹嘴,很舒服。小鑫只吃一根油条、一碗稀饭,几块咸菜豆腐。
从外面进来两个女的,都在二十来岁,一个女的戴着白色棒球帽子,进来后把帽子拿下,栗色的长发,很时尚。她坐在里面,面朝外,另一个女子黑色短发,坐在对面。两个人各撕下一块卷纸擦桌子。忽然,里面那个女子说了一声“真倒霉”,扔了纸,迅速拿起帽子,戴在头上,帽檐压得很低,又戴上口罩。黑色短发女子问,怎么了?戴帽子的女子却站起来,说了一声“走”,黑色短发女子也站起来,掩护着戴帽子女子走了出去。紧跟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走了进来,坐在她们刚才坐的位置上。胡明亮看到那两个女子往里边看了一眼,匆匆消失在门外。
妈妈,我要吃油条。小男孩叫。
一周只准吃一次。妈妈拿卷纸擦桌子。
刚才是怎么回事?小鑫低声问。
你追过去问问。胡明亮戴起了棒球帽。
神经病,什么时候不这么跟做贼一样。小鑫生气了。
我爸那么多女人,也没像你这软样。小鑫不屑地瞪着他。
你妈不管?胡明亮说。
管他干什么,管钱。小鑫说。
跟混蛋较什么真。小鑫又说。
他们走出来,小鑫又回头看了那对母子一眼。
别这样,好不好?
我哪样了?
胡明亮旁边桌上坐着一男一女,在争执着什么。
他们看起来都五十大几了。女的显得瘦,身穿一套白色运动服,头发整齐地向后梳,黑头绳扎成马尾巴高悬在脑后,脑门光洁明亮,看上去干净利落,但细密的皱纹,像小蚯蚓爬行在油亮亮的脸上,无情地暴露了她的年龄。男的一头黑发,梳得整整齐齐,光光亮亮,看上去像染的一样,又显得油腻,一条红绳挂在脖子上,隐入黑T恤内,估计是块什么玉,胸前印着一只什么鸟的图案,看上去也很精神,但脸上几块紫斑把他的档次一下子拉了下来,混浊、脏兮兮的。
胡明亮看了那个男人一眼,又看了那个男人一眼。
你凭什么管我?那个女人跟胡明亮坐一排,她端着杯子,晃了晃,杯里应该是白酒,也晃了晃,她盯着酒花说。
男人酒杯端了起来。来,他说。把酒杯往前一伸,是想和女人碰下杯,但女人端着酒杯没有动,男人只好跟空气碰了一下,喝了一口。
不是在乎你嘛,不是管你,是喜欢你。男人的喉结夸张地动了一下,酒咽下去了。
不是在乎,是有控制欲,我是你什么人,你控制我。女人仍在晃着酒杯,这个动作,让她显得孤傲,有一种无形的气势压着对方。胡明亮也听出来,他们不是夫妻关系。
你不能跟他们混在一起,他们都不是好人。男人语重心长。
你是好人,你是好人给了我什么?我为什么要你管?女人的语气仍然不紧不慢,虽是质问,但并不以声高压人,贵在气势。
我这几个月有点困难,但会缓过来的。男人则显得气势不足,仍然在找自己的感觉。
跟我有关系吗?女人将酒杯靠近嘴唇,吮了一口。
我想有钱了,我们会好些。男人嘟囔道。
那是你好些,真的跟我无关。
我也想我们能好好的,长久的,你应该能理解我。
我理解你什么,理解你能管我。
不是管你。
不是管是什么?是爱?我不需要这种爱,我需要自由,自由无价,你懂吗?
我不懂。
不懂就少说。
不是,我就是不想你跟他们在一块,还那么迟,谁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又管了,我没必要向你解释。
我不放心。
不放心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我们有证吗?你一个月跟我在一起不到十天,其余的去哪,我管你了吗?你跟你老婆亲热,剩下的劲儿来找我,你自己不感到可笑吗?
可是我真的喜欢你。
胡明亮几乎要笑出声来。他确实觉得可笑了,两个都年近六十的老男人和老女人,鬼混也就罢了,还这么矫情,满嘴爱呀喜欢呀自由呀,怎么说得出口啊,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他忽然感觉悲哀。
手机响了,男人的,男人看了一眼,没动。女人说,接啊,别找事。男人这才拿起手机向外走去。
女人瞪了一眼男人的后背,低頭吃菜。
门一开,进来两个人,像父子。父亲看样子四十大几,剃着板寸头,中间的头发根根直立,乌黑一片,两边的头发已经剃到发根,只剩下发茬,基本上都白了,像裹了一层霜。儿子二十出头的样子,跟在后面。他们站在过道上来回看,各个座位上都有人。儿子走到胡明亮的桌子前,看着父亲,这儿?父亲点点头,儿子便将书包放在外面凳子上,又在里面凳子上坐下。
父亲去看菜。
哎,这不东生吗?是老板娘的声音。
哎,熟人啊,这是你们开的?那个叫东生的人问。
胡明亮回头看了东生一眼。
就是我们开的啊,从厂子一出来,就开的饭店。老板娘说。
一直在这吗?东生问。
也不是,换了好几个地方了,开始站路边摆摊,后来是大排档,到这地方也有十年了。老板娘说着,朝后面喊,建军,建军,你看哪个来了。
那个叫建军的老板身上蒙着围裙出来了,手在围裙上蹭了蹭,抓住东生的手叫,东生啊,有二十年没见了吧。
只多不少。东生说。
你是小可蒙吧。老板娘走过来问那个男生。男生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了下,一时没反应过来,愣在那儿。
哎呀,你记得我不,你哪里记得呀,那时你才三岁,我们可没少抱你呢。老板娘说。
阿姨好。男生犹豫着,终于反应过来。
你妈呢,怎么没来,她好吗?老板娘问。
她挺好的。东生接话说。
以前你到哪,她到哪,跟一个人似的,现在不粘着你啦。老板娘说。
多大岁数了。东生有些不自然。
行了,你们吃什么,赶紧拿菜。老板娘回过头来对东生说。
对对对,别饿着孩子,想吃什么拿什么,算我请了。老板放下东生的手。
他们拿了三样菜放在胡明亮对面。又盛了一碗蛋炒饭放在男生面前。
要不我陪你喝两杯。老板说。
他不能喝酒。男生忽然说。
哟嗬,管着你爸爸了,真长大了呀,小可蒙今年大学毕业了吧。老板问。
嗯,刚毕业,这不正在考工作,明天有一场,所以今晚上过来,住这边。东生说。
东生四处看着,问,建军,这哪有卫生间。
老板说,里边就有,穿过厨房往里面,有个小卫生间。
东生就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回来坐下。
老板又端来个猪头肉,说,吃吃这个,我自己卤的,当年值夜班,我们一盘猪头肉,一碟花生米,能喝一宿的酒。
那时也挺好的。东生说。
现在也挺好的。老板说。
那时年轻气盛,总憋着一股气,喝酒打架,才能把气放出来,现在气都放在做事上,也挺好。老板解释说。
东生把猪头肉挪到了儿子面前。
这时,那个打电话的男人回来了,脸上都是汗,拿起桌上的卷纸擦脸,狠狠地扔进垃圾桶里。他坐下来,拿起酒杯,空的,又拿酒瓶,晃了晃,也是空的,已经有两个空酒瓶了,便冲里边喊,老板,再拿一个过来。
女人拦住说,别喝了,都喝两瓶了。
男人说,没事,再喝一个。
贾大鹏,真不能喝了,你看你那脸,都紫了。女人坚决地说。
胡明亮又抬头,看贾大鹏,贾大鹏的脸,果然紫了,那几个紫色的斑块倒映得看不清了。
老板娘已经把一瓶小牛二拿过来了,男人伸手要接,女人挡了回去,说,我们不要了,喝好了。
老板娘便拿着酒往回走,胡明亮说,给我吧,我再喝一个。
老板娘笑了,我刚开始拿半斤的,你说喝不了,现在不够了吧。
是啊,现在感觉才上来。胡明亮也笑着说,旋开盖子,倒了半瓶到杯里。
老板说,大哥,就这个,我跟他一晚上喝十来个。
老板又说,那时,哪天不喝几个,就浑身不自在。
胡明亮笑了,年轻嘛。
老板说,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人不轻狂枉少年,年轻不狂没出息,年老还狂也没出息。
要不来瓶啤酒。男人看着显然不尽兴。
你的尿酸能喝啤酒?女人双手抱胸。
一瓶没事,当年我可能喝一扎啤酒。
好日子那时过到头了,现在痛风痛死你。
你看,你管我。
我才不管你,我是不想让你死在我面前。女人咬着牙说。
就一瓶。男人还在磨。
就一块行吗?东生看着儿子。
医生都说了,你不能喝酒,不能吃肥肉。儿子说。
就吃一块,我好久没吃肉了。东生看着那盘猪头肉。
儿子搛了块瘦肉放在父亲碗里。父亲吃下去,说,真香。吃了一口面,又说,要不我再吃一块,肥的,猪头肉肥的才香。
真不能吃了。儿子说。
就一块。
兒子搛了一块连肥带瘦的,说,说好就这一块呀。
必须的。父亲直接把头伸过去,张嘴接过儿子筷子上的肉,吞进去,他吃得很慢,嚼了半天,才慢慢咽下,过了一会儿,说,真香呀,建军的手艺还这么好。他闭上眼睛,好像在回味什么。
好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站起来,往里边走。
一瓶,就一瓶。男人还在磨。胡明亮吮了一口酒,看他们。男人也看他,喉结动了一下。
胡明亮放下筷子,向后面走。穿过油烟腾腾的厨房,有个小卫生间,他推门进去,看到东生在里面,扶着墙,好像在用劲,看到有人进来,东生站直了。胡明亮在另一个便池哗啦啦尿完了,走出去。东生还站在那里,回头看他。他看到东生的眼里汪着泪。
你要喝你就喝,我走了。女人猛地站起来,拎起包,往外走。男人愣在那里,显然不愿意走。
胡明亮刚坐下,便拿起酒瓶向他扬了一下。男人立即拿着空杯伸过来,胡明亮把剩下的酒全倒到他杯里,男人喝了一口,说,杭州失踪的女人找到了,在化粪池里,是她丈夫杀的。
那男的看上去就不是好人。胡明亮说。
这种坏人,狠人,枪毙一百回都不算多。东生上完厕所回来,说。胡明亮看东生的眼睛,虽然没有泪,但红红的。
狠什么呀,被发现了就不算狠,只能是傻逼。说着,男人一仰脖,把杯中酒喝了。
也不是男的傻,是那女的傻,女人只能装傻,不能真傻,真傻就要了命了。男人把手里酒杯颠了颠,猪肝一样的脸上浮上古怪的笑。
贾大鹏,你走不走。不知什么时候,女人又出现在门口,喊。
东生抬头看那男人。
好,就走,我结下账。男人放下了酒杯。
我已经结了。女人喊。
好的。男人冲着胡明亮招了招手,说,谢谢啊,兄弟。夹着小包,颠颠地跑出去了。
明中午我们到哪吃?男生问。
找个饭店吃吧。东生说。
不想去饭店。男生说。
那到爷爷家吧。东生说。
不想去。男生说。
去你妈妈家吃?东生愣了一下,问。
嗯。男生点头。
好,那你去。东生说。
你也去。男生说。
我?东生说。
我帶你去。男生说。
呼噜,东生喝了一口面汤。
别怪我妈,一个人好多年,你又……
东生咳嗽一声,站了起来,拿起手机,扫二维码。老板娘过来,拦着东生,这就没意思了,我们请客了。
老板也过来,说,没请你喝酒已经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要你掏钱。
东生只好放下手机,说,那就下回吧。
老板说,加个微信吧,以后多联系。
东生犹豫了一下,说,好吧,你扫我。
胡明亮也吃好了,结了账,拿个塑料袋,把没吃完的刀子鱼、鸡爪装上。
老板和老板娘把东生父子送出门外,老板说,你明天来吃早饭吧,兴旺两口子弄早饭,烧饼油条不错。
这不是你们店吗?
本来是我们租的,他一直在城东摆摊,后来不让摆了,就来找我,早饭给他们弄,我象征性收点租金,我们只弄中饭跟晚饭,全弄忙不过来。老板说。
现在摸着门了,让你老婆来玩啊。老板娘在后面说。
好的。东生答应着,却又低声问建军,我旁边桌上那男的,刚才听那女的喊他贾大鹏,是不是我们厂的贾大鹏。
是啊,是他,我们厂厂长嘛,经常来,我们装作不认识他。建军说。
我真想再揍一回这个逼养的,当年他贪了多少钱,干了多少坏事。东生说。
是啊,要不是这些混蛋,那么大的厂子也不会那么快就垮了。建军说。
怎么混了一个老大妈。东生说。
越混越下相了。建军说。
狗改不了吃屎。东生说。
建军笑了,东生没笑。
胡明亮笑了。
这两天,我盯着他,少不了给他一砖头。他听到东生狠狠地说。
算了,不惹事!建军劝。
有仇报仇,有怨报怨,饶不了他。东生回到了座位上。
胡明亮提着塑料袋往小巷里走,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摩托车上下来,把挂在后座上的桶提起。胡明亮看到桶里光亮亮的,跳起一片水花,肯定是网了不少鱼。那男人也看到了他,冲他笑了笑,健步向路边一个小饭店走去。
肖科长,这回可不少啊。一个女人站在门口,招呼着。
你自己称去吧。肖科长说。
两人进了饭店。
他竟然没有觉得惊讶,一个打渔的竟然原来是科长。他本来可以从北门进,这样要近些,但他绕过去,往南门走,不紧不慢,悠然自在。手机不适时宜地响了,他掏出来看了下,是老刘的,他没有接,伴随着手机铃声继续往前走。路上,有人跟他打招呼,是小区里的邻居,一个高个子老头,一个矮个子老太太,每天早晚都要出来锻炼,见人总是笑眯眯的,看上去很有喜感。胡明亮的妻子很喜欢这对老人,说,咱们到老了,也像他们这样,多好啊。老人每次见到他们,总是热情招呼,有时见到胡明亮一个人,老太太总是问,你家娘子呢,你家娘子真不错,看着就招人喜欢,性格温柔。胡明亮笑道,她是装的。老太太也笑了,那哪装得出来,好就是好嘛。
老头说,你们感情真好,像我们一样。
老太太说,你夸别人没忘了表白下自己。
胡明亮绕到南门。有几只野猫正好从南门出来。为首的是只母猫,脸大,看起来很漂亮,几只小野猫也就几个月大,跟在后面。胡明亮咳嗽一声,几只野猫一愣,看着胡明亮。胡明亮喵了一声,往里走,回头看时,那几个野猫都跟了过来。一时间,胡明亮觉得很有成就感。
他妻子喜欢猫,晚上经常带点猫粮下来喂这些猫。他有时也跟着下来,一来二去,跟这些野猫就熟悉了。这些野猫只要听到他们的声音,就跑过来,在他们周围跑来跑去,撒欢打滚,好像老朋友似的。
他们喂野猫的行为,也遭到一些邻居的非议,认为小区里的野猫太脏了,有的还爬到电瓶车座上去,不知有多少细菌呢。他们不理,自顾做自己的事。
小区路旁有两个石凳,本来是园子里边的,被几个老太太弄了过来,每天早晚坐在那里聊天,有的老太太还端着饭碗坐在那里边吃边聊,或者把毛豆什么的拿过来剥。胡明亮想起小时候村里,他的父母们就喜欢这样。这里是拆迁安置房,有不少回迁户,这些老太太本来就是农村人。
老刘的电话又打过来,他还是没接,把裤角往上提了了提,在一个石凳上坐下来。几个野猫在他面前打滚,嬉戏。胡明亮把塑料袋打开,摊在地上,几只小猫立即跑过来,把头埋在塑料袋里。母猫趴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看。
手机铃声终于停了下来。
胡明亮发个微信给贾小鑫,是偷拍的四季粥店喝酒时那个男子的照片。
贾小鑫回,什么情况?
胡明亮问,是你的混蛋爸不?
贾小鑫回,不是这个混蛋是哪个!
胡明亮呲牙乐了,语音说,我今天敬这个混蛋酒了,那个混蛋称我兄弟。
他是不是带着一个女人?贾小鑫也语音。
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说着,胡明亮又笑了,笑得更凶了,笑得那些野猫都从塑料袋里抬头看他。
他要是找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倒不稀奇了,他这两年迷上一个老太太,迷得丢了魂一样,我靠,真把我脸丢尽了。贾小鑫说。
胡明亮止住笑,那些猫们又开始低头吃食。胡明亮感到奇怪,为什么母猫是橘猫,生下的孩子颜色各不相同?他查了下百度:一方面是基因重组,隔代遗传什么的生物学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母猫如果在发情期与不同公猫交配,可能会有窝同母不同父的情况出现。
你跟我好,是不是因为我年轻。贾小鑫问。
你会不会喜欢上一个比你还大的女人。贾小鑫追问。
胡明亮没有回答,他想说,我其实很早就认识你爸,不过厂子那么大,他不认识我,厂子倒了,我考到了现在这个单位。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他还想说,感谢你爸,把厂子搞倒了,要不然我还到不了现在这单位,也就不会跟你有业务关系,更不会有深层关系。
但胡明亮什么也没有说。
胡明亮,你要是喜欢上一个老女人,当心我撕碎了你。贾小鑫叫道。
别闹了,你让你爸注点意,有人这两天要用砖头拍他。胡明亮说。
拍死他才好。贾小鑫愣了一下,又恨道,这个混蛋!说完又笑了。
一个短信跳上来,是老刘的:怎么不接电话?结果出来了。
忽然,那些猫们从塑料袋里抬起头来,转过身来往前面跑。胡明亮看到妻子端着个塑料盒子,站在自家的楼道下面,往这边看。
喵——
【作者简介】 邓洪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在《小说选刊》《北京文学》《天津文学》《江南》《芙蓉》《清明》《飞天》《雨花》等发表各类作品100余万字,出版作品集9部。曾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