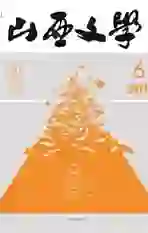老牛啊老牛
2021-06-02成向阳
我是带着三大纸箱的旧鞋抵达单位职工宿舍的。负责后勤的老萧像个猴子,侧着身子一跳一跳把我引到单身宿舍最后一间的门口,说:“这屋里已经有一个人了,你和他两个好好一起住着哇。”
老萧一走,我就把自己装着被褥、书、鞋的蛇皮袋和纸箱一一搬进房去,等搬完才发现,刚刚只顾着哈腰搬东西,都没看清屋里究竟有没有人。那时正是夏日的傍晚,窗子已暗,屋里也没开灯。直到找见门口墙上的开关按了一下,天花板上的一个灯泡突然亮起,我才发现这间泛着一股霉味儿的宿舍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人。
进门靠墙位置是一张显得有些古怪的床,床上的铺盖层层叠叠堆得很高,床头靠窗的一角还码着不知什么东西,鼓鼓囊囊用一块不透明的塑料布裹着。我过去细看了一下,那张床之所以古怪,是因为它不是宿舍里常见的铁架子行军床,而似乎是手工打制的,床脚很高,床面离地至少一米以上,床下黑黢黢的像个洞穴,也同样塞得满满当当,朝外可以见光的地方胡乱放着锅碗瓢盆以及一下看不太清楚的各式物件儿。总之是又脏又杂又乱——显而易见,我的这位室友百分百是个邋遢汉。虽然还不知道他究竟是何尊容,多大年纪,性格如何,但光看他一床灰扑扑的被褥和一大堆破烂儿家当,就足以担心我这个刚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不一定能和他处得惯呢。
这时已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但东西没收拾完,我无心出去觅食,再说对这个刚来的地方也不熟,就索性蹲在地上,把纸箱里装的旧鞋一只只取出来,再配成对儿一双双在行军床下排成两行。这些鞋,大多数都不是我的,而是我的大学同学在打包离校前扔在床下不要了的。我看了大多数其实还可以穿,就把它们都收了起来,心想既然我去的是个土里刨食的建筑施工单位,工地是少不了要常跑的,灰里泥里的,不多备几双旧鞋穿可不行,于是就把这些能带不能带的一并带过来了。
我这边正蹲着收拾,门外就有了自行车的响动。一个人随即上了门口台阶,闷声不响就走了进来。进门前,他似乎缩了一下肩膀,脑袋一收,人就进来了。他很高大,宽肩膀有点往下扣,但腰身很直,戴着个灰色的工作帽,身上背着很大的一个帆布工具包,进门也不看我,先把挎包从身上取下,很沉地往床边桌子上一放,然后摘了帽子,露出一颗光头,才扭身回来,居高临下看着蹲在地上的我。
他说:“你是谁?”
口音很重,分不清楚是哪里的人。但不等我回答,他又说:“你就是新来的吧?姓成?听说你是分在了机关党委?”
我说是。他就问:“你叫个啥呀?”不等我回答,他马上又说,“我姓牛,牛福仁!我现在工地上干工长,这屋呢,本来,是我一个人住着,好几年了都。你呢,既然来了,咱们就一起先住着吧。”
说完这几句,他便不再理我,默默从地上的红色塑料水桶里舀水,洗手洗脸。然后从床头那只工具包里摸出两根黄瓜和几个西红柿。西红柿他放到了窗台上,黄瓜却很快洗净,在一块不知从哪里拽出来的不锈钢板上拍碎,装碗里拌了调料晾着。再然后,他伸长胳膊从床下拖出一只硕大的电炉,那炉子拖着又长又粗的一根电线,插头一插,天花板上的灯泡顿时就像被放血一样失了颜色,一股胶皮烧煳味儿随之窜起来。他却不管不顾,等水开,下小米。
那电炉子真是强大得很,二十分钟不到,这个牛工长已经安坐小板凳,就着黄瓜喝着稀饭吃起大馒头来了。他把脸埋在碗里吃到一半儿,才猛然想起什么似的抬头问我:“一起吃点不?”我赶紧说不用不用,已经吃过了。他就不再客气,呼噜呼噜吃完,又稀里哗啦洗了碗。然后又坐下来,重新热水洗手洗脸。
这一洗却又与刚进门时大不同,刚才只是冷洗,很是敷衍潦草。这次却用了刚烧的热水,还用香皂涂了一脸白沫沫,无微不至地搓啊洗啊。洗完擦干,又摸出一个小刮脸盒子,熟练地拧好刀片,对着小镜子咯吱咯吱细细刮了脸,然后又坐回床前小凳子,给一双从鞋盒里取出来的旧皮鞋打油。
在我惊奇的注视下,这个刚进门时看起来有六十多岁,而现在一下至少年轻了十岁的牛工长,已经套上了一身灰色西服,蹬起了那双刚刚刷出几分光泽的黑皮鞋,然后在地板上硬硬地踩了几踩,扭身说:“我出去一下啊,你睡觉不用锁门。”
当晚他几点回来的我不清楚。只知道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他已赤着上身沐浴在穿窗而入的一柱阳光中,满身的腱子肉,举着一个画着领袖与红旗的搪瓷缸在刷牙。一放下牙刷,他就挎起工具包骑上自行车到工地干活儿去了。
等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老牛是个五台人,时年五十三岁。一张上下几乎同宽的黑脸皱巴巴的,带着一个朝前凸起来的大下巴,显得倔强而自带愤怒。他很少笑,对我表示和善的时候,稀疏的眉毛会垂下来,小眼睛就会眯成一道缝,陷进满脸的褶子里。
老牛是六十年代末借招工政策从农村进入单位的。他们那个地方是个老区,一些出身特别好的人,都借着招工政策来了太原,进了厂矿。这对于老牛而言,乃是人生绝大殊荣。他和我说:“我要不是招工来了太原,我老婆是万万不会嫁给我的。你知道吧,我老婆,年轻时那可是方圆邻近有名的美人儿啊,要不是后来看上了我,她家就要把他嫁给一个县长了。我老婆那时的长辫子啊,你是真不知道有多好……”
老牛虽然占着一间单身宿舍,但他其实几年前就已经退休了。我遇见他的时候,他的身份属于退休又返聘回单位的务工人员。他们这一类退休返聘的人,要不是有特别关系,要不就是有特别的本事,另外,还可能是特别难缠的刺头。而老牛似乎不太像这三种人,他之所以早早退休,是为了他的儿子能从老家过来接班。他自己后来又找了几回领导,才把自己重新送回工地去挣工资。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还留在单位,是因为“咱工地上少不了懂技术的人啊,我这几十年的技术,他们都巴不得我能回来呢。”可住了許久,我一直也没弄清楚他到底有些什么过人的技术,只知道他似乎有点爱占工地上的小便宜——几乎每天晚上下班回来,他那个总是沉甸甸的随身挎包里,总是能摸出几个西红柿、几个土豆、几根黄瓜,或者几棵绿菜,以及一包馒头花卷之类。他也毫不避讳,告我说这些都是工地食堂里拿的,大师傅和他是老弟兄,让他拿回来做晚饭的。但他一般不独享,至少表面上不吃独食。他做好饭,就邀我一起吃,还告我在他不在的时候也可以用他的电炉。不过,“你稀饭里最好不要放绿豆,绿豆难熬,时间一长,这一排宿舍都他娘的得黑灯。”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我一反常态,夜未归宿,第二天一大早才鼻青脸肿从外面回来。进了门,老牛正在刷牙,见我满脸裹着纱布,就惊得把一口刷牙水都咽下去了。他说:“小成,你这是和谁打了,怎么成个这?”我当时嘴里牙齿破碎,说话不清不楚,只能含含糊糊告诉他,和谁也没打,我这是出车祸了,刚从医院回来。他就哎呀哎呀的,说这你可咋办,要不我给你煮点稀饭?紧接着又说不行不行,今天工地事情太多,我得赶紧走,于是一溜烟跑了。等到了晚上,他却回来得早,煮了稀饭,盛了给我。我勉力喝了半碗。他就和我聊,问我是怎么摔的。我说是喝了酒,自行车给撞了。
老牛就说:“酒啊,不是东西,不喝为好。烟也不是东西,我就不喝酒不吸烟。喝酒喝出事的人,我在工地上见得太多了,你这……其实根本不算什么,养着很快就好。”
喝了老牛半个多月稀饭,我脸上的伤算是定痂了。每天晚上,我还正慢慢吸溜着喝稀饭呢,老牛就已经换好西服皮鞋,对我神秘一笑说:“你慢慢吃,我先出去玩啦。”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北大街上的一个露天音乐茶座。他似乎迷上了里面一个会唱晋剧的年轻女演员。
那正是新世纪轰轰烈烈拉开帷幕的年头,省会城市的空中弥散着努力奋进与率先发展的豪迈气息。每个人的耳朵眼儿里,似乎都吹着前进的号角与飒飒的风声,对看不清楚的未来,还有模模糊糊的一份期盼。我是这样,老牛虽然老几十岁,且饱经人生风雨,却也是这样。而对我们单位来说,两项分别投资过亿的“一桥一街世纪工程”正干得轰轰烈烈,工地一线人员的工资奖金月月丰厚。在这种情势下,退休返聘工长老牛的日子自然是过得风调雨顺。他时不时就搓着两只兴奋的手,同时把嘴唇吸得咄咄有声。他几乎都有点骄傲了,有时候连晚饭都吃得得意忘形。
他问我:“小成,你有对象没?”见我不说话,他就说:“你还小,不急。不过呢,你也得抓紧时间了,咱单位女娃娃可是金贵!”又说,“你知道不,音乐茶座里那个小宋,就是会唱歌,尤其晋剧唱得好的小宋,她似乎对我有点意思。”说完老牛的小眼睛就眯起来了,嘿嘿嘿笑着出门玩去了。
需要提一下的是,我们这个单位里的女娃娃确实金贵。有时候一个工地几百号人,却只有一个女的。女娃娃去工地不准穿裙子,但工地却要为女娃娃单独建厕所。这都是硬规定。有时候,我们在荒郊野外修路,一整条线上独独一个厕所,就是专属这一个女娃娃用的。每天早晚,都有人来打水的地方远远站着,看这个女娃娃一过来,就抢上去替她打水。老牛说到这里,常常还莫名其妙地说一句似乎无关的话:“知道我身体为啥这么棒吗?因为我一年到头也见不上我老婆呀。”
需要再提一下的是,老牛几次提过要带我去音乐茶桌看看这个小宋,但我都拒绝了。我听隔壁宿舍里的小张说,那种露天茶座,一次去得十块钱。如果被缠住要小费,那就更不得了。所以我当然不能去,我也很纳闷这个老牛,他是哪来的胆子,隔三差五就去茶座潇洒?
那年,一进十月,工地上要向元旦献礼,项目上下必须赶进度,老牛就总回来得很迟,有时候甚至彻夜加班不归。每次一回来,都是吃了就蒙头睡,一睡即呼噜打得地动山摇。本来,同室三个多月,我都以为早已习惯他的呼噜声了,但累极了的老牛打呼噜真的是异于平常。夜半,我躺着不能睡,只听得墙角处一声忽如大漠孤烟起,一声如飞鸿漫天游,再一声则飞流直下落深潭,起起伏伏,落差极大,且节奏混乱,根本把握拿捏不住。他有时候因为上夜班,就白天里也睡,呼噜打得隔壁的胖女人几次过来捣门。那是单位小车班里一个司机的老婆,不上班,就爱看个电视剧。她骂上门来,是嫌弃老牛的呼噜声影响了她家的电视信号——那时的太原城,有线电视才刚刚铺开,大多数居民区和单身宿舍,自制的易拉罐小天线还杵在窗口前。说老牛的呼噜声影响电视信号,是完全可能的。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老牛蒙头睡着还没起。门外就响起了一阵刺耳的摩托车声,旋即又响起持续不绝的迪斯科音乐声。紧接着一个人提着瓶啤酒就进了我屋里。我一看原来是棍子刘,他满嘴酒气,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讪笑。这家伙,是个早我两年来单位的青工,工地搞施工的,但是不爱干活,只爱玩机车,也爱打架喝酒,更爱盯紧单位新来的女学生不放手。最近我们这排宿舍新来个城建学院毕业的搞造价的姑娘,他很快就盯上了,一连两三次开着大摩托过来,要约人家一起出去吃饭,一起去跳舞。姑娘如果关门不理他,他就会随便拖上我们哪个人,和他一起过去敲门。这回他拖住了我,说要请我一起出去喝酒。我和他根本不熟,再说有前车之鉴,有摔牙之忧,我正在闭门思戒酒呢,就连连推说不去。但他力大,胳膊箍住我脖子就往外拖。就在和他拖拖拉拉的时候,就听身后一身喊:“滚!”
回头一看,是老牛掀掉被子在床上坐着,两只小眼睛瞪着,浑如凶神恶煞。棍子刘一看见老牛的黑脸,赶紧把我松开,说:“牛师傅,你原来住这啊,我这就走,这就走。”
听到外面摩托声响,我问已经穿衣下地的老牛:“这个棍子刘,他认识你啊?感觉他有点怕你呢!”老牛哼了一声,半天才说了一句:“不好好干活,我他妈揍过他。”
后来我才知道,工地如战场,战天斗地嘛,当然也斗懒人和二流子。在这个环境里,退休返聘回来的老牛其实是个不声不响的老霸王。他揍过的人,何止棍子刘这样不务正业的青工。据说现在的老总,大学毕业刚分到工地搞技术的时候,也吃过他劈面一个耳光。而他眼下干活的那个工程标段的项目经理,以前跟他学徒弟时可没少挨打。另外,这个老牛,他还真是一個管道施工方面的专家呢。据说,他年轻时候,跟着几个从上海过来援建的专家学过好几年。
我那会儿在单位机关专门负责编厂报,每天都看许多工地通讯员写的施工简讯,里面常有“退休老工长献妙计解决施工难题”“老工长加班彻夜,顶管施工一夜过街”等消息。虽然每次都不特别点名是谁,但我知道,八九不离十,都是老牛。有一回,我拿着一张厂报回宿舍,指着一条消息问他,这个老工长是不是说你啊?
老牛吸溜着稀饭说,怎么不是?顶管方面,难道别人还有这个能力?
我说,那你得让他们把你名字给写上啊,这不清不楚的算什么?
老牛一摆头,丧着脸说:“那不用,给我多发点儿钱就行。”
入了冬,又狠忙了一阵儿,工程就该扫尾了,老牛和我都闲了下来。一连好几天,每吃过晚饭,我都看着老牛,等他像夏天秋天时那样洗脸刷鞋换衣服出门去玩,但很奇怪,老牛却不再出去玩了。每天吃过饭就找出一副老花镜戴上,趴到床头,在一个红旗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我说:“老牛,你吃在工地,住在宿舍,粮菜水电,一分钱不掏,还记账啊!”老牛说:“不不不,我不记账。我写点东西。”
我说:“老牛,你怎么不出去看小宋唱戏了啊?夏天秋天时不是有空就要去吗?”
一说完这句,我就后悔了。因为老牛的脸唰一下就变红了,又猛然间变白了。他放下手里的圆珠笔,半天才说:“这个……我不想去了。那个小宋,她不是个东西。”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就装看书。老牛却坐不住了,扭回来和我说:“小成,我告诉你啊,以后找对象,一定不能找嫌贫爱富的啊,要看她心里好不好,干净不干净,要不你一准后悔呢。”我赶紧点头,心想,这点头认可,也算是对老牛的一些安慰吧。看他的意思,好像是那个小宋哪里伤害他了。但谁又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呢。
忽然有天傍晚,我下班一进宿舍,就感屋里气氛不同。定睛一看,老牛的床上坐着一个人,是个胖乎乎的老太太,齐耳短发还黑着,就是脸上的皱纹很多,和老牛也差不多。老牛坐在床前的脚凳上,见我回来,就赶忙站起来介绍说:“这是我老婆,她过来看看我。”
我一听是老牛老婆,一下想起的,竟然是老牛曾經夸过的那两条长辫子!但眼前的老太太头上当然不会有辫子,更看不出丝毫当年美人的模样。她从床上下来,脸色很冷,却是笑着说话:“你就是小成呀,听老牛说过你的。我下来,就是来给他收拾收拾。你看,这都脏的。”说着,就去扫她刚刚坐过的床褥子。
老牛赶紧使个眼色,把我叫到宿舍外。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就问他有啥需要帮忙的吗?老牛喃喃着,说:“其实也没啥,没啥!就是小成,你看,我老婆今天下来了,晚上,你能不能出去找个地方住住?就一晚上啊。”
我笑了,说这怎么不能啊,这太能了。
老牛就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摇晃着说那就太感谢你了,说着就把一个塑料袋子塞到我手里。那黑塑料袋子分量轻飘飘的,不像是她老婆带来的什么土特产啊……我正想入非非,就听老牛又说:“小成,你再帮我一个忙好不?这袋子里头,都是我这些年写的一些个东西。有的吧,不能让我老婆看见,我怕她看了多心。你先替我拿一下。那个……这些你都是可以看看的啊。”说着,用手把那些袋子拍了几拍。
当晚,我就窝在办公室里两只对接起来的单人旧沙发上,读了半夜老牛写在红旗本上的东西。这些东西让我大吃一惊——完全没想到这个老牛,一年到头忙得脚不沾地,竟然还有写东西的心思,更关键的是,他似乎还真有这个写东西的能力。比如,里面有一首长篇叙事诗《七上古交》,洋洋五六百行,一句七字,押韵合辙,戏词一样,原原本本叙述了老牛这几十年里七次到古交参与施工建设的经历和心情。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一个路桥建筑工人的骄傲和自豪。但是有些词,他用得很大,与一个劳力工人每天面对的沙子水泥离得太远。我吃不准他这是在虚张声势呢,还是心里真的信这些词里的意思。其实,我早听说老牛他们这一茬招来的农村工人,起初都是单位里称为“壮工”的一个工种。这个工种,工地上俗称毛驴,根本没啥技术含量,就靠铁锹镢头土里刨活儿。老牛能“七上古交”,和工友们修出那个山城一多半以上的道路桥梁,是因为他真的吃苦能干,而且绝对超出了一个工地毛驴的心智程度,一五一十把技术活儿学到了自己手里。
但我随即看到了老牛对一些单位上层人士下的判语,一个人一篇,夹叙夹议,琳琅满目,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依据。作为一个躲在红旗本后面的批判者,老牛时而唇枪舌剑,大打出手,时而推心置腹循循善诱,比如作为一个男人,你不能怎样怎样,又必须怎样怎样云云。这些被他点名批判的,大多数我都不认识,应该都是以前管事的,但也有几个仍然在位。老牛对他们的缺席审判,让我一个新来的人真是看得乐不可支。
最后,我就在红旗本里看到音乐茶座里的小宋了。
写小宋的也是一首长篇叙事诗,但是与《七上古交》不同,它不分行,写成了一大篇,而风格上类似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如泣如诉,一唱三叹,把与小宋相遇、相知、相怨、相离的这个过程写得清清楚楚。
原来啊,这个在文字里开始变得越来越朦胧越来越不像他自己的老牛,以前在五台老家的时候,竟还学过几年唱戏。他一开始去北大街的音乐茶座,也纯粹是让人拉着,一起上街去解个长夜之闷。他发现那个音乐茶座里既有唱歌的,也有唱戏的,就先是路人一般离得远远的看个热闹,却并不到里面坐下喝酒点歌。他是很清楚知道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的。直到有一天,他听见小宋在里面唱戏,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梳洗更衣,在茶座里坐下来听小宋唱了一曲,并把第一张十块钱的小费拍到了小宋手心里。
那十块钱,在给出去的当夜就让他后悔死了。那一夜,他想起了老家的老婆,想起了在运城天桥工地上同样干壮工的儿子,想起儿子在太原还没有房子,想起孙子和儿媳妇还缩在农村老家。他决定,北大街上的那家音乐茶座,说什么也不能再去了。
他也果真没有再去。直到有一天,他骑车从汾河西岸回来,在迎泽大桥上迎面碰到了孤身一人走着的小宋。那时是春天的黄昏,小宋吹着河风,淋着毛毛小雨,也不打伞,一张白脸上神情忧郁,脚下步履恍惚,很像一只饥肠辘辘又满腹心事的小兔子。擦肩而过时,竟然是挨着桥栏走着的小宋先把他给叫住了,为此他很是惊讶,这个姑娘家,怎么就能记住只有一面之缘的他呢?更何况,他还是灰头土脸一个刚从工地下班回来的老汉!但小宋热热情情,“扯住衣袖叫大叔,问我为何不再来。”
小宋那天在微风细雨里说,她还一直记得老牛大叔当晚给她作的点评,一听就是行家里手,是梨园知音呀!老牛闻听不由得心花怒放,自此贾起余勇,有闲即往,渐渐就欲罢而不能了。
至于他与小宋除唱戏听戏之外究竟还有没有别的事情,他的诗里并没有写。但奇怪的是,诗里头很快就画风陡转,由款款深情唱和而生出许多的嫌隙与抱怨来。又由抱怨而批判,大骂小宋人面兽心,见利忘义等等。又怨恨自己识人不明,误信奸计。但小宋究竟是做了何等事,竟让老牛如此狠下断语,他没有写,我也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日,我回宿舍,见老牛一个人坐在窗前发呆。他看我进来,就一伸手,说你都看了?那就还给我吧。我就把装红旗本的黑塑料袋还给他,又问大妈已经走了?他说走了,不走还想咋呀。我不知道该继续说什么,却随即冒出一句:“小宋的事……你也别再往心里去了。有些人,可能就是这样。过去的,你就让它过去算了。”
老牛叹息一声,说:“你不知情,她其实……还借着我1500块钱呢。我老婆这次下来,就是听我儿子说了几句嘴,就下来骂我的。好在她还不知道钱的事……”
我说:“那得赶紧找她要钱去啊!”
老牛颓然:“那个音乐茶座早就都不在了,人还哪能找得见!”
这大概是我和老牛最后的一次深谈交心了。转眼就是年假,年假回来后我们这些大学生就集体搬进了单位位于北大街东口新修好的单元楼顶层宿舍。而老牛则随项目部去了天津。在搬家之前,我把当初从大学宿舍里搜罗来的旧皮鞋全部送给了老牛。这些本来计划下工地时穿的旧鞋,我其实一次都没穿过。因为作为一个编厂报兼写材料的人,我并不怎么需要下工地,即使迫不得已下一半回工地,也只是项目部里坐一坐,或坐上项目部的蛋蛋车,隔着车窗转一转,看一看。那些鞋,不管大小合不合适,留给老牛,或许还有点用处。
到了第三年的秋天,我在单位大院里偶遇老牛,他还是那个我刚见他时的样子——高大,腰直,光头,依然并不显老,只是宽下巴更朝前突。他似乎真的在和谁发怒,看见我,就一把拉住,说小成,你给我评评理,后勤老萧他怎么就能把我从单身宿舍里赶出来呢?
我大吃一惊,问他怎么了。他说,你跟我来。
我跟着老牛来到后院单身宿舍的入口,老牛指着一个塑料布遮顶的小棚子,怒气冲冲说,他妈的,把我给安排这里来了——我一看,只见一堆被褥和锅碗瓢盆满满当当塞在里面,一根又黑又粗的电线从被褥卷里拖出来,隐约可以看见那个藏着掖着的大号破电炉。
老牛说:“这不,我刚回来,就发现进不去宿舍门了。锁换了,我的被褥和东西全给塞到了这里。”说着他一揭锅盖,露出锅里的一只旧皮鞋来。
我说,你没找找老萧问问情况啊!
老牛说:“王八蛋,他们说这排房子马上要拆迁,让我自己去外面租房住,要不就住到项目部里!我工作了半辈子,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都不给我?”
我说,你要不暂且先找找你儿子吧,看能不能和他住一块去。
老牛说,他?他也没地方住了,前一段儿还跑到你们大学生宿舍里挤,已经让人家赶出来了。说他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大学生,名声还不好,不能住!
我立即想起前两天被我们合伙赶出去的那个讨厌人。他原来竟是老牛的儿子啊……
老牛说:“小成,你在机关,又在党委,你替我找找领导?”
我愕然,但一看老牛深陷在褶皱里的两只红眼睛,只能说:“好,我给问一问。”
但我其实也并没有问出什么来。单位那时候正面临着大改制,像老牛和老牛儿子这样的人,正是谁也不便多管的包袱。
而老牛,竟也没有再来找我打问结果。
这期间,单位正在国企改制的大潮里浮沉着,沉渣泛起,波澜不静,发生了许多说不清楚的大事小事。其中有两件被人一时说道却又很快忘到了后脑勺上的事,都对老牛有一点点影响。
一件是渠河路工地盗卖国家电缆的工程项目经理是老牛当年的二徒弟。这事和老牛本没有丝毫关系,但是这个二徒弟孝顺师傅,老牛以前在工地上之所以跋扈,和这个二徒弟关系很大。徒弟这回一出事,老牛顿时就没了靠山。
另一件事,是单位预制品加工厂员工盗窃公章私自招工的事。这事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但情节却简直让人啼笑皆非。单位加工厂材料科的一个人,他爹曾經是个省劳模,但这个儿子不学好,而且脑子好像也不太够用。他利用中午吃饭时间,撬开人家办公室的门,又撬开抽屉,就偷出了厂里的公章,加盖在自拟的一份招工单上。然后他把招工单卖给了绿柳巷口棋牌店老板的儿子,说是只要凭借此单,即可到单位人事报道上班了。棋牌店老板也真信,让儿子拿着三万块钱买来的“招工单”就昂然来了。单位人事先是莫名其妙,但一查,就查到了这个偷公章的人身上。这事闹得一时间沸沸扬扬,但说起来和老牛没半点关系。但是又很不幸,在那个偷公章的傻子和棋牌店老板之间拉纤儿的,正是老牛那个在工地上已不太混得下去的儿子。
而我们这些住在大学生宿舍里的人之所以会合伙驱逐老牛的儿子,完全是因为这家伙实在是有点过于恶劣。别的先不说,单说行径这一桩——因为他并没有宿舍钥匙,于是几乎从来都不走门,而是习惯于在几个单元的阳台窗户之间行走。他随便找一个能尾随进去的宿舍,就从人家的阳台窗户翻出来,扒着窗户沿儿就到我们宿舍阳台外头了。那可是七楼顶层啊,他在外面蜘蛛人一样挂着敲窗户,我们也不敢不把窗户打开,不情不愿地让他进来。到了后来,我们都不敢关阳台窗户,万一他敲不开,一头扎下去呢!这且不说了,他还经常夜半带人回来过夜,他赖着住的是客厅啊,夜半弄得声音很大,让一宿舍人都忍无可忍……
后来,我就听人说老牛带着他被开除的儿子,跟着一个外埠工程项目部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的浑善达克沙漠,要在沙化区里修出一条红柳公路。几年后工程完工,他自己又去了山东枣庄修一座特大桥。再后来,就轮到我自己了——我终于离开了这个消磨掉我部分青春同时也把许多教训刻进我骨子里的单位。慢慢的,也就把老牛和老牛一样的许多人都慢慢忘记了。
直到有一天快吃晚饭的时候,我的手机忽然就接到了一个座机电话。我犹豫着接起来,里面是一个口音很重的老人在说话:
“小成吗?这回我不干了,真是干不动了,我真回老家去呀。听人说,你早不在单位干了,你现在混得还可以吗?”
我说:“你好,你好……那个,你是哪位呀?”
电话里似乎一愣,许久才说:“我,我是牛福仁……”
【作者简介】 成向阳,1979年生,山西泽州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山西省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历史圈:我是达人》《青春诗经》《夜夜神》。诗文见于《诗刊》《诗选刊》《星星》《天涯》《散文》《青年文学》《黄河》《山西文学》《青海湖》《青年作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