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界楷模和斗士
2021-02-24武志
武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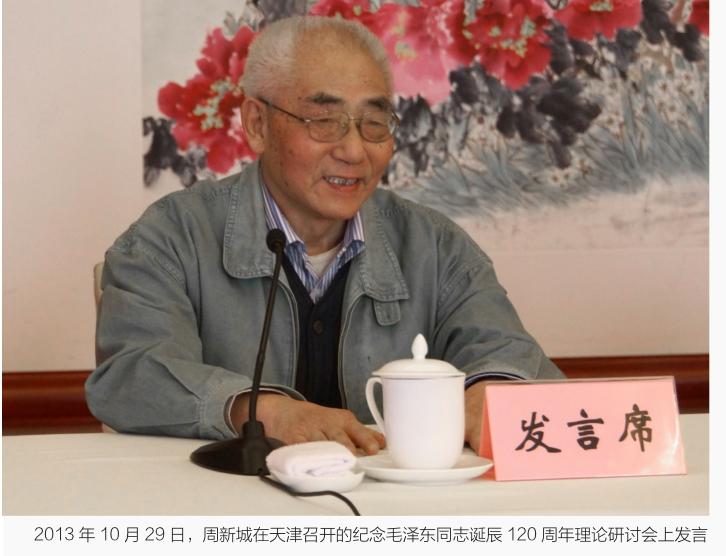
2020年10月20日晚惊闻周新城教授去世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非常震惊和深感悲痛。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泰斗和坚强不屈的马克思主义斗士。印象中他身体一向很好,而且80多岁讲起课来情绪高昂,走起路来精神抖擞,课外还经常带学生爬山,觉得他活到90多岁完全没有问题。10月5日他刚在网上发表了达36000余字、引起很大反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容忘却——纪念建党100周年》长文章,但开头就讲“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近乎临终交待的话,完全不符合他那种不服输的斗士性格,估计他当时心中已有预感,现在再回看这篇文章更是让人唏嘘不已。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期间专门上过周新城教授的课,加上近距离和他交流过多次,并且当面请教过他许多问题,周老师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而一直想写篇文章来纪念他。
第一次认识周新城教授,是我上世纪90年代在兰州商学院读大学时。1997年初周新城教授来学校作学术报告,他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也是学校聘请的兼职教授,地处偏远地区又渴望知识的师生们非常珍惜聆听名校名教授作报告的机会,因此容纳数百人的学术礼堂座无虚席。现在仍记得周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时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是理论界的新课题,不仅报告的内容丰富精彩、学理逻辑严密,而且讲课声如洪钟、激情洋溢,全场的气氛被周老师彻底点燃,让人充分感受到经济学大家的风采,以致毕业很多年后这种场景仍然历历在目。
2015-2018年我有幸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旗帜,大师云集。我当时就想,如果不利用千载难逢的机会,认真听大师们的课和请教问题,那就如进宝山而空返。因而读博时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去听很多名教授的课。周老师这时已经是人民大学的一级教授,在一次课堂上正好遇见了他的博士生高露,表达了想听周老师的课,她告诉我周老师每周四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开授课,且非常欢迎其他学生参加。时隔多年,当再见到周老师的时候真是有点认不出来了,当年满头黑发、腰杆笔挺的中年人,变成了满头白发、略显驼背的老头,但丝毫没有改变的是他精神饱满,讲话洪亮,充满激情,讲到兴致处开怀大笑,当然学术造诣上是更加炉火纯青。通过近距离的上课感受到周老师的学术风范和个人魅力,整个课程学下来,我受益匪浅。还要特别说明的是,周老师是大家,但他为人非常随和、谦逊,丝毫没有架子。无论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向他请教问题还是节日问候,他总是很快且认真回复,而且最后总是署名“周新城”三个字,令后辈感动和敬佩。
周老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之所以被大家深深的敬重和怀念,不仅因为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而且因为他退休到马克思主义学院,本已到了颐养天年的年龄,本该过着和家人其乐融融的日子,但他依然站在教学和科研的岗位上勤奋地忘我工作。一方面作为高校人民教师,他继续兢兢业业授课和带博士生、硕士生,赢得了人民大学师生的爱戴。他退而不休,继续以高校做理论宣传阵地,站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国家和学校培养栋梁之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给社科院的网络课精心备课。另一方面作为高产学者,他不断刊发高质量的文章,赢得学术界同仁的敬重。周老师不仅学术水平高,而且非常高产,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坚决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做斗争。他深厚的学术功底,独到的见解,不屈的斗争精神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学者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之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家更多地参与到国家改革、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制订中。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所主张的政策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利益,因而经济学界不可避免地存在左、中、右的各种观点和激烈交锋。老实说,周老师如果选择明哲保身,置身事外,不参与争论,那么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的地位,以他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研究生院院长的身份,门生遍天下,自然会备受经济学界的尊崇,安享幸福的晚年。然而这恰恰是周老师不“圆滑”、不“聪明”甚至“顽固不化”的地方。经济学是道术结合,术者,技也;道者,信仰也。周老师是以信仰来做学问的典范。周老师在国家大义和人民利益面前,从来都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他更加令人敬佩的原因。
经济学理论上的争鸣、商榷甚至交锋,不仅有利于学术本身的交流进步和健康发展,真理越辩越明,而且对于指导实践极为重要,事关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学者们通过学术争论,方能相互借鉴,不“左”不右,做到既能解放思想,也能实事求是,为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和深化提出创新性观点和建设性意见。因此,经济学界不同理论观点的争论甚至争吵,不仅是积极、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然而这种相互商榷的良好的学风,一段时间变得各说各话,甚至出现一种极端,压制争论,不许对方说话,用扣帽子和贴标签的简单粗暴做法代替了激烈但有益的学术争论。周老师因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不断的发文章对错误的理论和思潮进行批判,也被学术界一些人贴上了“极左”的标签。实际上,周老师根本不“左”,更和“极左”沾不上边。
周新城教授是国内最先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学者之一,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法,提出要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理论,并且把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进行大力宣传。他1997年初就在兰州商学院等高校的讲座,邓小平理论1997年9月被写入党章,1998年正式出版《邓小平理论概论》高校教材。因此,周老师做学问不仅不保守,而是与时俱进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周老师被贴上“极左”的标签,主要是因为他坚决同理论界极右的观点做斗争。攻击周新成“极左”,正好说明他正确。马克思主义历来既反“左”,也反右。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工人运动实践中,一直是既反对“左”倾冒进主义,也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做法自始至终贯穿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各个时期和指导德国、法国等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建设中,有力地帮助工人阶级在理论和思想上走向成熟。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历来讲有“左”防“左”,有右反右。他强调经济领域要防左,要解放思想,克服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束缚,迈开改革的步伐;思想领域要反右,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决定行为,如果思想上偏右的成分过多,经济行为上必然走向右,导致改革偏离正确的方向。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方向仍是首要问题,习总书记强调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他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周老师是著名的苏东问题专家,针对极右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和试图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方向的主张进行理论上批判,這是旗帜鲜明地反右,是正确的。
周老师根据宪法和中央文件,结合现实,对新自由主义的错误观点和思潮针锋相对地批判,却被贴上“左”的标签。这种做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偏离了正常的学术交流。比如,周老师发表一篇纪念《共产党宣言》170周年的文章,其中引用消灭私有制的原话,却遭到理论界一些学者和企业家借题发挥,进行大批判甚至“围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共产党宣言》观点显得不合时宜,强调发展公有制被当作走“极左”的路线和错误的主张,岂非咄咄怪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所有制上采取公有制为主体、私营经济共同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把公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理论上错解为相互排斥关系,舆论上制造二者对立,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同宪法和中央文件相对立。宪法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中央文件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绝不动摇,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市场经济中,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代表着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经济学家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发声呼吁,符合社会经济的客观规律。但学术的争鸣,一方面是应该积极、健康的,有利于国家决策不偏不倚,出台的政策不“左”不右。另一方面,争鸣要在基本的学术范围内,要求具备起码的理论素养。有些人在攻击周老师“极左”的时候,提出既然周老师要求消灭私有制,那就没收周老师财产。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消灭剥削的经济基础,不是消灭个人生活资料。《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显然,这里讲的是资本不是资产,是生产工具不是生活资料。因而提出没收周老师财产的主张既是违法的,也是荒唐可笑的,暴露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缺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
